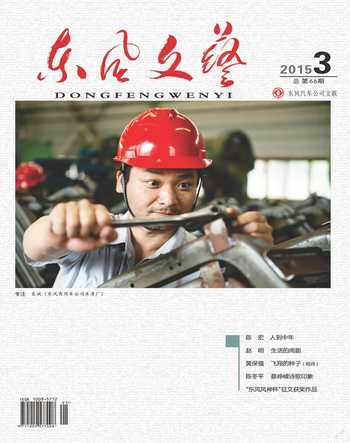抗日三题
谢大立
鬼子来了
断水已是第三天了,还是在沙漠的深处。
小战士不停地对老班长说,我感觉身上的东西越来越重了,实在是一步也走不动了!
老班长说,走不动也得走!
小战士说,那我们把身上的东西扔掉些再走吧?
老班长说,你要扔掉什么,你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扔掉的?
小战士说,用不上的东西,重的东西……
老班长瞪一眼小战士,看看四周,大喊一声说,鬼子来了!拔腿就跑。
小战士惊慌地跟着老班长拼命地跑。
他们一口气翻过了横在面前的沙丘,顺着坡往下滚,躺到了一个水洼里。
水!小战士惊喜地叫。
老班长的脸上也开着花般地笑。两人趴在水窝里一阵牛饮后,老班长说,你不是一步也走不动了吗,跑起来怎么比我还快。
小战士说,打不过就跑,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又说,鬼子呢?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老班长说,不骗你,你怎么会跑,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水……
小战士打断老班长的话说,原来你真是骗我的……
老班长说,那不是骗,那是在告诉你,鬼子时刻都有可能出现,我们的心里必须时刻都有鬼子,才能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也是毛主席说的。
水喝饱,水壶装满水后,小战士再次对老班长说,我们虽然是不渴了,但饿,要不把身上的东西扔掉些走快点,抢在鬼子的前头从沙漠里走出去,我们即使不死在这沙漠里,也会死在鬼子手里……
说着,小战士坐到地上,把枪往沙里塞,把腰里的子弹袋卸下来也往沙里塞……老班长说,你要干啥?
小战士说,你不是说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吗?这些东西日后还可以找回去,人不在了,这些东西即使是带到了阴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老班长又一声吼叫说,鬼子来了!
小战士没像刚才那样,爬起来就跑,反而十分不屑地一歪嘴说,你干脆说狼来了吧,狼来了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老班长说,起立,跑!鬼子比狼还残忍,我们的心里必须时刻装有鬼子的残忍……
话没说完,叭的一声枪响从远处传来,老班长一声卧倒,扑向小战士,把小战士压在了自己的身下。
小戰士懂得,这是老班长为了保护他。
他们趴在沙地上看枪响的地方,看到了五个鬼子。
他们在沙漠里和这五个鬼子纠缠得很苦。为了保护大部队的转移,他们连奉命把一个团的日本兵往沙漠的深处引。在沙漠的深处,鬼子一个团的兵力一天天减少,最后剩下来五个,他们一个连也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他们就在沙漠里玩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老班长说,他们五个我们两个,现在他们是猫,我们是老鼠,直到有一天我们战胜了他们,把他们变成老鼠。小战士就在老班长的带领下,和这五个鬼子兵在沙漠里兜起了圈子。
五个鬼子兵从老远的沙丘上居高临下地朝他们扑来。老班长和小战士爬上沙丘,对敌人形成居高临下。五个鬼子兵似乎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虽然处在地理的劣势,还是一边扫射,一边直奔他们下方的水洼地。老班长一边指挥小战士射击,一边说,他们是冲水来的,想占领水源,如若让他们喝上水,于我们就大大地不利了。
五个鬼子兵,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下,才开始重视他们,卧倒,匍伏前行,两个人前行,两个人掩护。只要他和老班长一露头,就有子弹射过来。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他们虽然靠着有利地势消灭了两个敌人,老班长却受了重伤。最后,老班长在撂倒又一个敌人后,不行了,把枪和腰里的一颗手榴弹交到小战士的手里说:
记住孩子,一个战士,心里必须时刻装着自己的敌人,任何时候,战士是不能放下自己手中的枪的,战士要保存自己,只有靠手中的枪,国家要存在于世,必须靠自己的部队,部队是国家手里的枪。我们先前所做的事,就是为了保存我们的大部队……枪里的子弹是跟鬼子周旋的,手榴弹是供你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老班长说完,闭上了眼睛。
小战士以一对三,和敌人一阵周旋后,见敌人喝水心切,佯装死去。敌人把喝水当成重中之重,连检验他是否真的死了也顾不上,就趴在水坑里牛一样地饮起来。小战士就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扔下了那颗手榴弹。
战斗结束,他解下敌人身上的弹药,背到自己的身上继续往前行,饥渴几度让他昏倒,他几次想卸下身上的负担轻装前行,几次都听到老班长在他的耳边喊鬼子来了,他硬是在多少天后的某一天,全副武装地从沙漠里走了出来。
这个故事,是我们进沙漠执行任务时,我们的连长给我们讲的。连长讲完后对我们说,这个故事里的小战士就是我,我今天能站在这里给你们讲这些,得益于什么你们明白了吗?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鬼子来了!说完后是笑,笑后是久久的沉思。
阿六报仇
“阿六,你可别就这么走了,就是走,也要把眼睛睁开一下,看我最后一眼。兄弟十个,就剩下我们两个了。二十年前,我虽然一怒之下把你赶出了师门,我的心里却是舍不得你的。我能活到现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你要走了,往后我还怎么个往下活法……”
声音虽然很陌生,阿六一认真听,还是听出了是阿大。阿大来了!阿六有些感动,一使劲,眼皮真的被拉开了,嘴唇还跟着蠕动了一下。
“阿六,你睁开眼了!听他们说你有十天没睁开过眼睛了,我来看你,你能把眼睛睁开,真的是叫我很感动……”
睁开眼睛的一瞬,阿六看到了阿大,也看到了他的那些丐帮兄弟。心里的感动打起折扣来,他这时候来看我,在我昏迷的时候当着我的兄弟们说这些话,是不是又有图谋?想把我的这一帮叫花子兄弟玩弄于他的股掌?
习惯性的,阿六的眼睛瞄向阿大脸上的疤痕。疤痕正一跳一跳呢!阿大要害人杀人,疤痕就一跳一跳。师父死时,师叔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盯了眼阿大脸上的疤痕,背后告诉阿六,阿大是日本武士,入耀武门是图谋,说不定你师父就是他害的……不久,他就看到了阿大杀师叔,他的刀从背后捅向师叔时,脸上的疤痕就是这样一跳一跳的。
杀阿蕊时也是一样。
阿蕊是师父的独生女,一个花朵儿般的女孩子。阿大脸上的疤痕一跳动,持刀的手犹都没有犹豫一下,把刀捅进了阿蕊的胸腔,抽出来时,还刀尖往上一挑,又往左右一拉,让阿蕊那耀眼的胸乳呈现于众目睽睽下。他还要把刀尖伸向她的下身时,是他阿六挡开了他的刀,他也就受到了阿大挑断右脚筋,赶出耀武门的惩罚。阿大还对他说,知道我为什么留你一只脚吗?是留给你日后报仇用的,有本事你就来找我阿大报仇好了!你护这贱人,不就是赞成她杀我吗?有本事你也杀我试试。
从此,阿六成了流浪汉,乞丐帮的头,也成了个复仇使者。为自己复仇,更为阿蕊复仇,为耀武门的兄弟们复仇。他曾多次暗暗发誓,这辈子要杀不了阿大,也要找个机会与他同归于尽。
“我还能与他同归于尽吗?”
阿六想,自己连把眼睛往下睁的力气都快没了,又有什么办法与人同归于尽。阿六一泄气,眼皮就重新合上了。合上了的眼皮,还挤出来泪。有人帮他擦泪,他重新睁开眼,看到的又是阿大,还有他的丐帮兄弟们对阿大感激的眼神。
“不能让他再演下去!不能让他再祸害我的这些丐帮兄弟……”
阿大边帮他擦泪,边重复上面的那些话:
“阿六,我的好兄弟,你别闭上眼睛,你快把眼睛睁开,你要就这么走了,我也活不了多久了,让你陪着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说是我的精神支柱……”
阿六虽然不懂什么精神支柱,但他知道支柱这两个字的意思。入耀武门前他是个木匠,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想让砍木头的斧子变成杀日本人利器,投身了耀武门。一个房子抽去支柱,房子会轰然倒塌.一个人的支柱被砍断了,是不是会像房子一样崩溃……
要砍他的支柱,必须把他的话反过来说。
“阿大,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我们是兄弟,我也从来没把你当过兄弟。”
阿大的眼神警觉地一愣,仿佛在说,这家伙怎么又说起了话。
“阿大你就别猫哭老鼠了,你知道的,我们不是兄弟,也不是你所说的朋友,我们是敌人,你死我活的敌人……”
阿大又一阵警觉,阿六的心里一喜。
阿大说:“阿六,我知道你神志不清了,我们是朋友,兄弟。”
阿六说:“不!我的神志一點不糊涂!”
阿大打断阿六的话说:“阿六,你蓄点精力,别再说胡话了。”
阿六冷笑说:“你怕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说的猫哭老鼠点到了你的筋上?”
阿大大惊失色。
阿六不紧不慢地说:“是朋友、兄弟,你就不会弄残我,我也不会杀你。杀你的事过去我一直没承认,今天我宣布承认。你想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不承认吗?为了杀你……”
阿大的眼睛睁圆了,眼珠子快要弹出来了。阿六惊吓,但只一会儿,阿六的心里蹦出来一个字——好!
“那次杀你,是我和阿蕊阿七一起谋划的,阿蕊失手了,阿七急中生智对我的大腿上打了那一枪,叫我把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之后饮弹身亡的。”
阿六哭起来:“可怜我的阿七兄弟呀……”
阿大快要弹出的眼球,变成了两颗红灯泡。
“阿二找你决斗也是我的一句话,你想知道什么话吗?师叔把你是日本鬼子的事告诉了我,我又告诉了阿二,阿二和我一样,都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他死在你的手里,是他技不如你,但他相信有人会帮他杀掉你的。”
阿大死死地盯住阿六,脸上的疤痕又跳起了嘣嘣嚓。
只差最后一击了,阿六想到阿大的两面性。
阿大虽然杀死了阿蕊,但他背着人的耳目又多次去阿蕊的墓前祭祀,并一直没再娶,这说明阿蕊在他的心里是很重要的,他杀阿蕊是迫于什么,如果拿阿蕊说事,也许是致命一击,于是,阿六说:
“我还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阿蕊的会阴部有一块记,阿蕊为报父仇,表面上是你的女人,暗地里却和我好,在成为你的女人前,早就跟我有那回事了,你花了那么多心机把阿蕊弄到手,也不过是吃了块我嚼过的馍……”
阿大的脸成了猪肝色,骂:“你这个畜牲!”
阿六说:“你阿大才是畜牲,你们日本鬼子才是畜牲,比畜牲还没有人性!”说着,目光如注,与阿大对峙。阿六的乞丐兄弟们为他喝采,打狗棍把地杵得山响。
阿大话不成句,说:“你,敢骂,老子……”说着,两手向阿六掐来,中途被乞丐们的打狗棍架住了,一阵颤颤巍巍后,一口血,从阿大的嘴里喷薄而出,眼球翻白,头一歪,身子歪倒到地上。
“阿大死了,被我的话弄死了……”阿六欢呼。
“我报仇了!阿蕊,阿二,阿三,阿四……我为你们报仇了!”
阿六奇怪自己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力气?就这么一奇怪,他听到了嗤的一声响,是那种车胎穿孔的声音,他的力气也跟着没了。
他想说,阿蕊,对不起,为了置这个不共戴天的日本鬼子于死地,我说了瞎话……话没说完,他听到一个来自天国的声音:
“阿六,你干得好,我在这边等你呢!”
梦里的喊声
团元老哥从来没有梦到过父亲。近些时来,不但梦到了,还真真切切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在他的梦里不停地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直把团元老哥从梦中喊醒。
团元老哥恨父亲胜过恨祖父。祖父只是好心办坏事地让他继承了个地主成分,父亲却完完全全是有意让他背上土匪儿子的包袱的。这个包袱压在团元老哥背脊上整整三十五年,压得他差点连个媳妇都找不到、断了这个书香门弟的烟火。
父亲像个孩子似的每夜都在他的梦里喊,没法,他只好按父亲说的溯江而上,找到父亲在梦里所说的地方。这是个平原与山的交接处,无数的推土机正忙着把土从高处推到低处,土里,有一半是白花花的骨头。
父亲在这些骨头里?其中的某几根是父亲?团元老哥顿时毛骨悚然。
尽管团元老哥面对这些骨头棒子茫然不知所措,还是往蛇皮袋子里装进了许多,离开时无可奈何地留下了一句话: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然后背起来往回走,回到他的白水湖老家,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把骨头棒子埋下。
果然的,他的梦里再没有出现父亲的喊声。一天没有,两天没有,一个月都没有。蹊跷,他禁不住与木匠作坊铺的祥伯说。祥伯是与父亲拜过把子的兄弟,也是父亲他们拜把兄弟中唯一仅存的。祥伯能活到今天,据说是父亲他们的有意安排——他们如有个三长两短,有个人照顾他们的家小。祥伯照顾他,他也就把祥伯当父亲样依靠。
祥伯听了,说,这么说,你找到你的父亲了!我的那些兄弟们终于有了音信了……说着,老泪纵横,仰起那颗全是白发的头颅望着蓝天白云直喊,苍天有眼!包括祥伯在内,谁都不知道当初的那帮年轻人后来去了哪里。有的说,他们去当了土匪,后来都被打死了;有的说他们不像是当土匪的样,兴许还在,说不定到了国外……
人们这么说,都是一种推断。依据他们当时在小镇的街心烧香磕头拜把子的的一种推断。拜把子的场景带些血腥——杀了一只鸡,血滴在酒碗里,喝血酒。喝完碗里的酒后,像一群梁山好汉一样,把碗摔在街心的青石板上。梁山好汉,你能说他是土匪吗?
要怪,他们不该神秘失踪。解放后,只能按他们喝血酒定性——不三不四的会道门。就这个性质,祥伯就被折腾得脱掉了几层皮。先是三反五反,祥伯这个余孽上台挨了斗;文化革命,又被当成地富反坏右没完没了地游街。他的后人也被殃及,尽管他们像团元老哥一样很优秀,但社会都不容纳他们。
祥伯到了他兄弟的墓地,往上堆了些土找块有草的地方坐下来抽烟、自言自语地说话——你们干嘛去了那个地方也不捎个信回来,死了也不知道弄点动静回来,你们走了一走百了,可是害苦了我们……你们要泉下有知,就在梦里告诉我们一声是怎么客死他乡的……
说着说着祥伯又老泪纵横,弄得团元老哥也跟着泪流满面。
随后,他们就等那个梦中的声音再次响起,又是一天,两天,一个月,那个声音仍然没有响起。祥伯就踢踢腿扩扩胸对团元老哥说,你再陪我去一趟那个地方吧,看能不能在那里找到你爹他们是怎样到的那里,又是怎样死在那里的?你一定要陪我走一趟,对我对你对你们的后人们都是一个交代。
真是神速,才两个月不见,那些推土机不见了,一道高高的围墙把整块的地方都圈住了,人进不去了。他们只好望着墙,望着墙上的两块牌子发愣。两块牌子一块是当地公安机关宣布为重点保护区域的牌子,一块是单位名——中日合资绿色食品加工厂。
他们不想就此打道回府,就于墙的外围转圈。转着转着,终于找到了与他们此行有关的内容。山坡坡上,一群老人正在把成堆的朽骨往一個个白色的匣子里装,并告诉他们,装的是整个一个师包括师长在内的全体将士们的侠骨。当初在这里发生过一场十分惨烈的战斗,正是这些将士们,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挡住了日本皇军的西进……
老人们说,战争的惨烈震惊中外,也是有史可查的,日本鬼子是想从这里进川占领全中国的……不待老人们再说,祥伯又老泪纵横起来,突然拉过团元老哥一起跪下,像对那堆白骨又像是对那些老人一连三拜说,我明白了,怪不得你爹不再闹着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