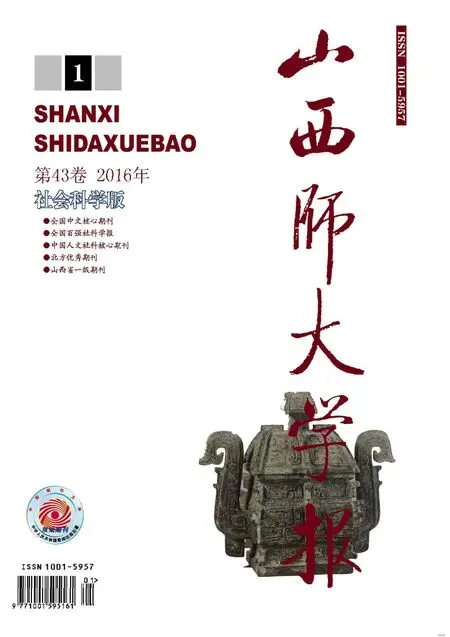麦考莱辉格主义政治思想述评
裴 亚 琴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辉格主义政治传统是英国从传统至现代的过渡阶段,是英国政治制度个性所系。英国议会政治家和史学家麦考莱(T. B. Macaulay, 1800—1860)在表达19世纪辉格党的政治立场和塑造辉格史观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亲身政治活动和系列政论文,他系统地阐述了反对抽象理论的思想方法和支持议会改革的政治立场;通过对光荣革命时期英国史的书写,展示了不能被冠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标签的辉格主义政治态度。辉格主义史学旨在通过书写历史表达特定的政治态度,这一点在麦考莱这里得到最辉煌的呈现。理解麦考莱,就是理解辉格主义和英国政治传统。
一
与超脱于政坛的思想家不同,麦考莱是议会中辉格党的代言人,其著作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他明确区分政治活动和抽象推理,认为演绎法不适用于分析政治问题,在早年与詹姆斯·密尔的辩论中,着力于批判将抽象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做法。
在《论政府》一文中,密尔以人性自私的假设为前提,认为政府是必需的,政治提供法律和秩序防止民众出于自利而彼此掠夺,从而确保自己的劳动果实。但政府由具体的个人组成,这些人难逃自私本性,势必运用手中权力掠夺臣民。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能有效约束统治者。从这一逻辑出发,密尔分析了三种传统政府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认为它们均无法保护共同体利益。民主制不可行,因为将共同体全体成员集合起来处理政府事务是不现实的;在贵族制下,拥有统治权的贵族会任意从共同体其他成员那里掠夺自己所需,从而违背政府之所以建立的目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类似,根据人性法则,一个人若能够,就会从他人那里夺取任何他们拥有而他想要的东西。只要政府权力没有掌握在共同体手中,无论掌握在一个人、几个人还是少数人手中,抑或实行将三种简单政府形式予以结合的混合政体,掌权者都会利用手中权力摧毁政府存在之目的。[1]59—61在密尔看来,代议制是获得善政的唯一路径。但若要议员对行政权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他们必须有广泛的选民基础——密尔建议实施成年男性普选权,并大大降低议员任期。唯其如此,才能使议员真正代表民众,从而保护共同体利益,实现政府之所以成立的目的。
麦考莱的反驳论文《密尔论政府》发表于《爱丁堡评论》(1829)。在麦考莱看来,密尔的首要错误在于,试图以几何学方法处理人类事务。密尔从一种假设出发,用演绎法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普适而貌似科学的结论。然而,政府的科学是一种实验科学,在这里,人们只能用归纳法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具体的经验教训。政治与人相关,是与几何、数学和逻辑完全不同性质的领域,用几何般的精确来界定人类行为是不可能的。当人们像谈论线段和数字一样开始谈论权力、幸福、不幸、痛苦、快乐、动机等时,就堕入了无穷的矛盾和荒唐。密尔将抽象逻辑运用于政治的做法是虚妄而傲慢的。逻辑不承认妥协,而政治的本质是妥协。真正的政治家不在意逻辑,“如果他们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他们就是理性的,尽管他们有可能是矛盾的。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就是荒谬的,尽管随时在逻辑地论证”[2]53。相应地,麦考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康德等人的哲学体系敬而远之。[3]17
其次,密尔推论的整个前提是错误的:其人性假定完全不切实际。密尔根据人们压迫和掠夺他人的欲望和倾向进行推理,好像人们除了通过掠夺和压迫来满足的欲望之外没有别的欲望。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某些只有通过伤害邻人才能满足的欲望,也有一些只有通过取悦邻人才能满足的欲望。爱名(获得他人好感)的欲望是否总比爱财的欲望更强烈,或者相反,对于一个人而言尚不明确,更不用说普遍描述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人和人不同,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不同,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不同。教育、地位、性别、年龄、偶然机遇等,都产生无穷多样性。”[4]127不可能发现任何能绝对说明一切人类行为的一般性概括。密尔将人们追求快乐最大化片面化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没有承认对他人好感的欲求,而后者在麦考莱看来恰恰是十分重要的。
麦考莱断定,大多数社会中有两种人,穷人是政府应予以限制的阶层;拥有某些财产的人则是政府权力可以托付的阶层。穷人更在意物质,富人更在意名声;为了满足物质欲望去掠夺他人是穷人的倾向。[4]107—108统治者对臣民好感的欲求,或者从消极意义上说,对臣民反抗的恐惧和羞耻感促使他们不可能以掠夺为目的[4]115—116。在积极意义上,贵族更具有为善或服务于“公共善”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对于密尔倡导的使政治更加民主、更能代表共同体利益的男性普选权,麦考莱予以断然否定。
在麦考莱看来,密尔的政府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荒唐的,在实践中也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密尔的激进主义与17世纪的清教徒不差上下。清教徒仅仅考虑人与神的关系,轻视世俗差别,消弥人类中最伟大者和最卑下者之间的区分。在政治领域,清教徒“在主面前低微到尘埃,却把脚踩在国王的脖子上”[2]12。哲学激进主义与清教徒类似,他们的哲学傲慢正如前一时代清教徒的精神傲慢一样,蔑视既定秩序,引发民众不满情绪,造成反抗。
二
麦考莱批判密尔,是要揭露一种完全不适于道德和政治讨论之推理的恶果,其直接目标是为声援议会改革添砖加瓦。19世纪初的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的宪政体制运行一个多世纪之后,环境以缓慢、渐进而不断积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麦考莱称之为“无声的革命”。[5]它不是历史学家乐于称道的重大事件,也不由军队或议会立法达成,它包括经济条件从贫穷到富裕、道德风尚从残暴到人道的变化,宗教派别的兴起,以及在文学品味、服饰、公共娱乐、家庭生活和人际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有的变化是“进步”,有的变化则造成秩序混乱和民众怨恨,即便变化本身是受欢迎的。例如,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宗教热情增强,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人口的变化等。最终,政治制度始终如一,其他领域却发生了无声的转变,导致它们之间日益明显的不均衡,从而使社会出现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在1831年的英国,由于未能细察社会变化,统治者已经与民众完全疏离,议会不再表达公众的声音和意志。面对这场与17世纪的英国相类似的危机,统治者应该做的,是及早发现无声的革命并做出制度调整。
议会改革前夕,无声的革命导致的冲突集中体现在选区划分不合理、天主教解放问题以及谷物法引起的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麦考莱看来,面对政治体制与环境的不相适应,两种极端政治态度是有害的。一种是密尔代表的激进分子,另一种是以温灵顿托利政府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后者以强硬态度对民众的不满情绪予以压制,执意不进行改革,认为改革就是在英国引入民主政治,永远脱离英国旧有宪政。
与前文所述贫富“两种人”相应,麦考莱认为存在两种出于性情、理解和利益的不同而分化的人。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异不仅存在于每个社会,而且涉及各个领域:
无论何处,总有一群人对过去异常留恋,即使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改革会带来更多益处,但在接受新事物时,他们还是充满了疑虑。同样也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敢于怀疑,一直奋力向前,总能看到现存事物的不足,他们轻视改革过程中的危险和不便,相信每一个变化都能给人类带来进步。……前者中的极端分子变成了顽固的老朽,后者中的极端分子成为肤浅草率的经验主义者。[6]68—69
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矛盾,是托利政府对阵无处不在的激进运动导致的破坏性冲突:一边是傲慢的寡头,一边是愤怒的民众。支持独裁权力的朝臣和支持革命的民主派是两个有害的派别。托利党过分喜好和平而不顾民众的正当要求,对公民和宗教自由事业毫不关心,从而有可能从上层威胁宪政均衡;民主派则狂暴激进,对那些与他们自己的逻辑推理和抽象学说不相契合的宪政部分毫不在意,完全不顾和平,从而有可能从下层造成威胁。这两种极端尽管针锋相对,却同属于“教条主义”。密尔的演绎法是一种追求逻辑完美而不顾现实的教条;顽固的托利党人也因恪守教条而不愿改变现状。教条主义者关心的不是现实政治,而是逻辑或某种意象。由于他们没有妥协精神,势必造成分裂和冲突。
近年来,国家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各级各部门对采空区治理工作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在治理过程中,一般习惯于把采空区作为灾害体,采取注浆充填以确保治理效果。这一思路虽然消除了安全隐患,但与将采空区作为空间资源进行改造和利用等先进理念相比,则存在较大差距。胶东地区水资源贫乏,废弃金矿采空区是非常好的地下水蓄水空间,且矿脉与断裂关系密切,在水文地质上具有很好的导水或蓄水意义。如何在保证地面稳定性的前提下进行采空区改造,变废为宝,实现采空区蓄水功能是深入思考的治理方向[3-7]。现以文登市大时家废弃银金矿采空塌陷隐患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为例,探讨采空区改造含水层方法的可行性。
所以,唯一的出路是拒绝教条,反对专制和激进两种极端,既不固守现状,也谨防革命,力求没有专制的秩序和没有无序的自由。“温带就是在将人烤焦和把人冻僵的气候间调整。英国的宪法在土耳其的专制统治和波兰的无政府状态间调整。”[6]164害怕专制的人必须承认秩序的价值,而担心无政府的人必须承认自由的价值。在当前情势下,当务之急是进行议会改革,使政治制度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使统治者回应民众要求,担负起服务于公共善的政治责任。除了对选区划分进行改革之外,确立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以保障一方面扩大选举权,另一方面防止全民参政的极端民主。有资格并有能力担负改革重任的只有辉格党,它“代表的贵族,介于国王和民众之间,他们有责任施加等级和财富的影响,这种影响力若明智、诚实并合乎时宜地行使的话,会为社会提供稳定与和谐”[7]3;托利党人虽然也代表贵族利益,但在麦考莱笔下,托利党人被描绘成乡巴佬,通常是只在乎自己狭隘的眼前利益的小地主,只顾塞满自己钱袋的地方暴君;辉格党人则眼界开阔、教养良好,具有公共善的热情,富有贵族的公共责任感。[6]217—218
对于辉格党本身,麦考莱也有一种独特的非教条的理解:“我理解的辉格党人,不是盲从任何书本内容的人,即便那本书的作者可能是洛克;不是对某政客任何行为都表示支持的人,即便那个政客可能是福克斯;不是接受任何圈子流行观点的人,即便那个圈子可能由该时代最优秀最高贵者组成。对我而言,回顾历史,我能够辨认一个伟大的政党:这个党时常受挫,却从未灭绝;尽管带有时代的缺陷,却总是处于时代领先地位;尽管犯有很多错误甚至罪行,却在坚实的基础上确立了我们的公民和宗教自由。对于这个党,我很自豪是它的一员。”[8]21—22
相应地,麦考莱极力支持的是具有保守目的的议会改革,防范激进民主是改革的重要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如果统治阶层强硬拒绝任何改变,就会迫使公众观念转向激进和反动的极端,民众会以激进方式表达不满,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内战。为了不给教条主义者利用和动员社会不满的机会,有必要及时进行让步。通过改革对制度进行适度改变,旧制度就能够重获民众支持和忠诚,而不是遭受敌意和抵抗。通常麦考莱对“进步”大加赞赏,但它一般而言限于科学、实用艺术、经济和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等领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避免堕入无政府或独裁的危险,在政治层面并没有通向某种理想的发展目标。由于英国政治并不需要激进革命,相应地,也不需要思辨哲学或教条主义。对哲学的反感与珍视宪政连续性、同时反对固守现状相呼应。他将这一倾向归于英国政治和法律的固有性格:
在英国法律中,相对于思辨,实践因素一直具有极大优势。不考虑对称,更多地考虑便利;从不因为某种东西异常而移除异常;从不革新,除非已经觉察到某种不满;从不革新,除非只有革新才能消除不满;从不制定比特殊事件所要求的更宽范围的规定;这些就是从约翰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一般性地引导我们250届议会之审慎的规则。[5]
以“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提倡议会改革,麦考莱代表的辉格贵族立场既得到较为激进的中下阶层的支持,也得到保守人士的信任。保守主义者在他所支持的改革立场中发现了古老的强调中庸和均衡的基本宪政原则。麦考莱诉诸历史并以独特的风格书写历史,以光辉的叙事表达政治要求,这一做法使贵族成为他的同道,从而使他能够有效而真诚地阐述民主观念,而不用像激进主义者一样做得过火,也不用与有保守倾向的政治家斗争。因此,历史书写构成麦考莱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
三
出于对政治是实验科学的理解,麦考莱认为,要积累政治智慧,应该学习的是历史,而不是哲学和宗教。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1828)的论文里,麦考莱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其一,完美的历史应当结合理性与想象;其二,历史是文学的一种,与其他艺术有共同特点;其三,历史不仅记载公共事件和重大事迹,也应含括普通人的生活。
历史的功用在于为政治家提供先例和警示,历史知识只有在引导人们形成有关未来的正确看法时,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在进行历史写作时,史学家要做的不是搜集奇闻轶事,或进行大事编年,而是要书写有助于政治态度表达的历史。对于后来备受批评的以当下眼光歪曲历史的辉格史观,麦考莱认为这是英国史学家的共性: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像英国政治家这样,受过去的影响如此之深,因此,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像英国的历史学家这样,受现在的影响如此之大。……在我们国家,政党最热衷于在古籍研究的结果上下赌注。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古籍研究者会把党派精神倾注到他们的研究中去。……当涉及英国原有政体中自由和特权的界限问题时,那些著者通常会显示出某种倾向,他们的语气并不像公正的法官,而是像义愤填膺、居心叵测的鼓动者。因为他们正在讨论的并不是纯理论问题,而是时下最重要、最振奋人心的事情,这些事情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6]18—19
在麦考莱看来,史家秉持主观态度是相当自然的,因为历史研究应该是对政治才能的一种帮助。他本人也不是专门为了理解过去的专业史学家,追求的不是与其他考虑截然分离的客观历史。
为了可信地传达一种对政治的独特理解,对史实进行取舍十分重要。通过选择,通过仔细编排前景和背景,通过生动地呈现特定人物和事件,让人们铭记一般真理。同时,史学家要做的不仅仅是说出事实,还应该具有说服力地呈现事实:应当借助于文学技巧,生动地刻画历史景象。理性分析和文学技巧同为好的历史不可或缺的要素。麦考莱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波利比阿、塔西佗、休谟、吉本等古今历史学家,尽管他十分欣赏他们的某些方面,但认为这些人的著作,不是缺少分析,就是疏于文学,远远称不上是完美的历史。[5]麦考莱的历史著作风格明快,语言生动辛辣,引人入胜。一次民众集会曾通过一项对麦考莱表示感谢的决议,因为他“写了一部工人都能读懂的历史”。[9]494在他去世时,The Times评价他“是我们时代最有力量、最受欢迎、最有才华的作家”。[10]13可以说,麦考莱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兴趣的英国作家。
最后,历史的内容应该着重于表达有利于提高民众福祉的观点。麦考莱直白地蔑视政治哲学,认为它如果不是有害的,例如詹姆斯·密尔鼓励教条的过分简化,就是乌托邦和不现实的,例如柏拉图,或者不相关的,例如孟德斯鸠或自然状态理论家。高冷的政治哲学与普通人的生活毫无关联,与民众福祉相关的政治智慧最好在历史中寻找。相应地,史学家的注意力不应仅限于战争和朝廷以及内阁会议,他们更应该做的是研究民众生活的潜流,普通大众的幸福所系是独立于胜利或失败、革命或复辟的事业。它们不用法律规制,也没有记录于档案,这些才是史学家要努力理解的事物。大多数史学家聚焦于重大事件,是奇怪的狭隘。他们必须像聪明的旅行者,观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混迹于群众,造访咖啡馆,获准坐在普通人家的炉火旁。切不可把宫廷辉煌与民众幸福相混淆。[2]29
在《英国史》中,孕育着进步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麦考莱不惜笔墨描写过去民众在住房、食物上的贫瘠,赞叹现今拥有的工业技术及其带来的物质繁荣。“进步”对他而言意味着与民众福祉密切相关的物质福利和个人自由。政治的运行应该为了民众的好处,为了确保民众生活水平、个人自由以及和平与秩序。因此,《英国史》最重要的主题,是确认面对重大困难,达到安全、繁荣及国内和平的政治路径。这一切都与保障个人自由密切相关。
麦考莱对公共善的热情毋庸置疑,无时不在关注“普通大众的幸福所系”。但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幸福的首要条件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个人自由的享有,而不是亲自参与政治。在民众被允许参与政府之前,必须受到良好教育。因此,麦考莱反对极端托利固守原则和反对激进分子的民主要求同样不遗余力。政治应着眼于民众福利,政治重任则应由贵族来担当。
四
上述思想方法、政治立场和历史书写三个层面互为表里,彼此印证:诉诸历史与实验科学的方法一以贯之,由此也决定了麦考莱妥协和中庸的政治态度。这样的方法和态度是不能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标签来界定的,因为它不具备逻辑上的首尾连贯,不是脱离于实际的某种抽象。在历史书写上,并不严格追求史实的客观与著者的中立精神,从而势必受到几方面批评。
首先面对的是出于历史客观性的批评。最为人熟知的是巴特菲尔德对历史之辉格解释的攻击,[11]他认为辉格派史学家站在当前的制高点上,用今日观点编织历史,失去了历史叙述的客观性。麦考莱的传记作家布莱恩特也指出:“麦考莱身上带有的自然活力和气质促使他过度以黑白分明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及其动机,作为具有党派身份的演讲家的习惯又加强了这种趋势。因此,在他笔下,詹姆斯是十足的坏蛋,威廉则是大好人。”[12]108的确,麦考莱在谈到詹姆斯时自始至终是一派轻蔑嫌憎口吻,这种描写无法让人接受。至于威廉的形象,则又因“聚光过强而弄得面目失真”。[9]497他也未能鉴别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例如,他低估了詹姆斯二世,把他仅仅当作暴君的样板;忽视劳德主教的其他个性,把他当作反对所有变革的死硬分子。对于那些具有强烈宗教感的人,麦考莱无法神会,而将他们描绘为狂热分子。
如果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获得对政治局势和个人性格的全方位理解,那么麦考莱的很多判断都过分简单,也不太公正。但是,从麦考莱的立场看,历史的目的不是欣赏顽固分子和狂热分子的意图或理解他们的复杂性。相反,历史的目的在于展示这些人的危险,教育政治家,提醒他们保护国家免受此种极端之害的责任感——即便这意味着忽视了复杂性、做出了不公正的评判。因此,麦考莱的历史书写与兰克学派的客观史学完全不同。兰克学派认为,每当历史学家利用过去来呈现他关于人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应当如何行动的主张时,过去的画面便开始变得歪曲和虚假。历史学家应恪守其任务界限,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13]40—41兰克史学与辉格史学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前者认为历史的任务是提供客观史实,价值判断要留给读者自己来完成。后者则是为了通过叙述历史来引导读者相信某些价值,利用历史塑造特定的政治态度。对麦考莱而言,历史书写当然是有目的的,历史应当传达对现实政治的认知。
另一种批评认为,麦考莱够不上纯粹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麦考莱处于庸俗的思想境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下文称小密尔)即持此种立场。根据小密尔的观点,麦考莱尽管很有能力,却是“一个除了在文学方面之外,丝毫不拥有这个时代观念的人”。换句话说,他不属于思想上的先驱——在小密尔看来,这些人置身于德国和法国知识分子中。麦考莱“跟所有伦敦人一样,是思想的侏儒,圆滚滚,矮墩墩,在其体内没有任何进一步生长的细胞”[14]223。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小密尔批评英国生活中的因循守旧,恪守习俗,少有个人闪光,少见恢弘伟大,没有灵魂。[15]179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批评是对的。的确,麦考莱不是思想上的冒险者。对他而言,理论探险只有在与普世相关时才是可接受的,而他恰恰不关心如此宏大的主题,因而对德国的思辨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家拥有的世界主义态度避而远之。他关注的仅仅是现实政治,诉诸理性和常识,因此很少系统探讨政治哲学。
“庸俗”和狭隘造就了麦考莱的岛国心态。他的视野仅限于英国:英国民众的福祉和英国政府的作为。民众的福祉在于物质生活,自由在于具体权利的享有。同样出于实用的考虑,政府应该由受过良好教育、对公共善富有纯真热情的贵族来掌控,不应为了抽象的民主理念而由民众直接参与。他以实用态度书写历史,回归古老的中庸理念,立足于英国本土宪政的连续性特点,力图调和对手,避免极端,在极力维护自由的层面上,流露出与欧洲大陆不同的自觉和自豪。同时,他无法一以贯之地认同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因为他并不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进行思考的,一切取决于理论对现实诉求的效用。他曾自认为是进步主义者,但1839年,“如果谷物法被废除,爱尔兰教会被改革,将开始考虑成为保守主义者”。1852年,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更为保守”。1853年,自认“同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家”。[2]125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称其为机会主义者。然而,与通常仅以自身利益为鹄的的机会主义不同,麦考莱体现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诉求的是民众的自由和权利。
作为积极投身于议会政治的政论家和史学家,麦考莱诉诸常识和理性,以保障民众物质福利和自由权利为目标,以高超的文学技巧讲述一种正确的政治路径的历史。这一路径就是中庸,以变化寻求秩序和宪政连续。在此过程中,他传达了历史自信、未来自信和贯穿始终的进步与自由精神,开创了一个解释历史的传统。缺乏抽象思维和世界视野的确是一种缺陷,但是,至少在麦考莱看来,它是一种幸运的缺陷,因为如果政治家的目标是民众的物质福利和自由,那么着眼于本国的现实政治就是正确的。麦考莱奠定的辉格主义史学反映了一种历史书写的普遍倾向,它可能是意识形态,却绝不限于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狭隘意识形态:在确保民众权利和自由方面,它甚至堪称为统治者提出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1] James Mill. Essay on Government. Jack Lively and John Rees. Utilitarian Logic and Politics: James Mill's “Essay on Government”, Macaulay's critique and the ensuing deb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2] Joseph Hamburger. Macaulay and the Whig Tra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3] Gerhard Walcha. Macaulay als Geschichtschreiber. Groβenhain: Verlagsdruckerei Georg Weigel, 1931.
[4] Macaulay. Mill's Essay on Government: Utilitarian Logic and Politics. Jack Lively and John Rees. Utilitarian Logic and Politics: James Mill's “Essay on Government”, Macaulay's critique and the ensuing deb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5] Macaulay. History (1828). T. B. Macaulay,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Lord Macaulay, vol. 1,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and Roberts, 1860.
[6] (英)麦考莱.英国史:第一卷[M].周旭,刘学谦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
[7] Ian Newbould. Whiggery and Reform, 1830- 4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Catherine Hall. Macaulay: A Liberal Historian Simon Gunn and James Vernon. The Peculiarities of Liberal Modernity in Imperial Brita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 (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 Margaret Cruikshank.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G. K. Hall & Co., 1978.
[11] H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31.
[12] Arthur Bryant. Macaulay. Edinburgh: Peter Davies Limited, 1932.
[13] (美)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M].刘耀春,刘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 FA Hayek. 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 London: Routledge, 1951.
[15] (荷)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M].刘雪岚,萧萍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