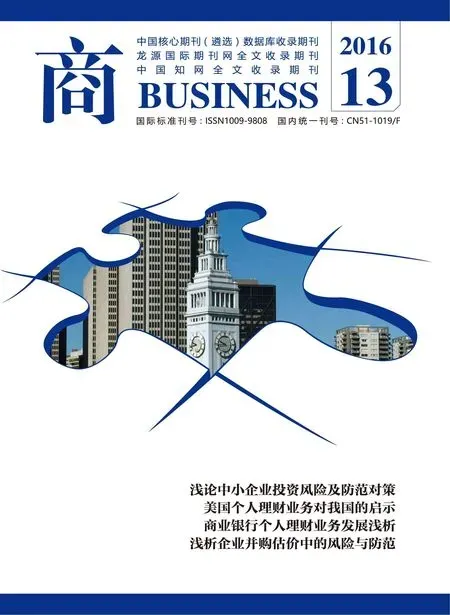浅析“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
郭文辉
摘 要:“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一种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原则为目的的纯粹假设,有别于古典契约论的“自然状态”亦异于文明之初的原始状态。在这个订立契约的理想性背景中,最为特色鲜明的是其“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的主观环境预设。虽然《正义论》(On Justice)从发表之初就备受内部的自由主义以及外部的社群主义的无情批判,但本文认为“无知之幕”与“原初状态”对我国当下法治建设与改革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无知之幕;原初状态;正义与平等
一、“无知之幕”与“原初状态”
在某种程度来说,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对古典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运用了类似“自然状态”的论证方法——“原初状态”。在《正义论》的开篇,罗尔斯运用大量的篇幅对“原初状态”的假设进行诠释,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把握:首先,“原初状态”是一种虚构的原始环境,不同于古典契约论中人人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亦异于真正的文明之初的原始环境,而是一种理性的订立契约的背景状态,具有非历史性和非现实性的特点;其次,“原初状态”是一种代表机制,其参与者是具有一般理性、享有基本自由,并且地位平等的“道德人”,作为正义原则的选择者是这些“道德人”的代表;最后,“原初状态”是一种订立契约的环境,具体而言包括作为客观物质的中等匮乏以及作为主观状态的“无知之幕”,前者使得社会合作或者说选择共同的正义原则不致没必要,后者在于消除偶然因素对主体选择的干扰,从而创设平等的契约地位。
二、“原初状态”与“自然状态”的比较
霍布斯《利维坦》(Levithan)中的“自然状态”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虽然都具有浓重的社会契约的色彩,但却是两种迥异的理论预设:两者在人性定位以及公共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体归宿。首先,前者在人性的定位上选择“人性恶”,一方面承认平等的天赋人权,另一方面主张人类的极度野蛮自私;后者以“人性善”为出发点,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都是具有善的观念的“道德人”。其次,前者以前政治社会为背景,理智使人民通过订立契约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形成“公共权力”来保障“自然法”的施行,从而理论的要旨在于国家具体的政府组织形式;后者预设了客观物质的中等匮乏以及主观状态的“无知之幕”的理论环境,使得“道德人”基于善的观念选择正义原则,产生一般适用的正义观,以此来解决社会基本价值的平等分配的问题。最后,前者在社会政治形态上是一种与“人人相互斗争”的“自然状态”最为接近的君主专制政体,后者在实践中实际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所推崇的是一种兼顾公平与正义的民主宪政政体。
三、关于“原初状态”的争端
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使得当代政治哲学论坛一片哗然,不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对此颇有成见,外部的社群主义也咄咄逼人,更是受到了包括社会学、法学等学术界的关注与争论。
(一)自由主义对“原初状态”的批判
尽管都坚持个人利益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但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内部对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原初状态”为中心展开激烈的抨击。首先,诺齐克将矛头直指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中的纯粹正义程序的纰漏,主张“差别原则”作为外在的模式化标准才能用以检测程序与结果的正义与否;其次,诺齐克对“原初状态”中的社会合作产生质疑,一方面承认社会中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民之间的合作具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充分运用资格理论来诘难“原初状态”中社会合作的不确定性;再次,作为极端个人主义者,诺齐克对罗尔斯“无知之幕”的理论预设表现出极具攻击性,“无知之幕”的理论要旨在于消除人民的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从而实现起点的公平,而诺齐克把这种消除差异的行为视为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最后,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展开批判,尤其认为差别原则的单方实质性,指出处于劣势地位的有利以及处于优势地位的不利实则对个人权利掠夺。
(二)社群主义对“原初状态”的反驳
社群主义以“社群”为出发点,以社群利益为衡量和观察问题的标准,推崇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这也必然引起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学者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之间的分歧。首先,桑德尔指出“原初状态”作为罗尔斯理论的“阿基米德点”自身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罗尔斯借用休谟的环境概念,并且对道德的选择主体进行了基本善以及欲望满足的预设,以此来处理“目的王国”的现实问题,但这样也就导致了形而上与经验主义的内在冲突;其次,桑德尔对“无知之幕”后的选择主体进行辩驳,一方面,“纯粹无知”的“道德人”没有真正的选择能力,另一方面,主张个人的价值和目的是“社群”赋予的,并且个人的选择也由他所处的“社群”所决定;最后,坚决否认“原初状态”所选择的正义原则的契约本质,由于“无知之幕”消除了选择主体的多样性,从而导致契约主体的单一性,并将此定性为斯宾诺莎的“个人形式主义”。
四、“无知之幕”与“原初状态”的法治意义
尽管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受到了内部自由主义与外部社群主义的激烈抨击,同时也引发了法学界对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审视与反思。本文认为,“无知之幕”与“原初状态”的理论预设对我国当下法治建设以及法律实务大有参考借鉴之处。
一方面,作为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无知之幕”通过消除那些会影响平等自由的偶然因素,这无疑体现了法之平等的基础价值。我国司法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法治建设本应处处、时时贯彻平等的法治理念,坚持公正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在实践中严格落实三大诉讼法,推进权威发布、司法公开,增强司法透明度。另一方面,“原初状态”通过“无知之幕”的预设,有选择地排除相关因素,从而确定初始的平等地位,以此实现了平等、自由和理性的选择主体的特征设计,暂且搁置对“原初状态”的各种非议,罗尔斯的公平理论的开端就凸显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在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大可适用“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的理念来反向检查各种具体制度、程序设计的合理性与公正性。这对当下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善提供借鉴,对现存欠合理的具体程序也是一种倒逼。(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 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 诺齐克,何怀宏译,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