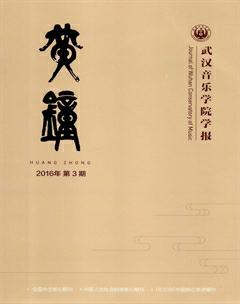满怀赤诚 执着追寻
丁卫萍

摘要:陆华柏先生命运多舛,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位先驱。本文从陆华柏手稿、信件、思想汇报等第一手资料探寻他1949年后的心路历程,以陆华柏先生建国后的辉煌、蛰伏期的执着、晚年彷徨矛盾的心理,分段梳理了他1949年后的艺术人生追求,洞察陆华柏隐秘的内心世界,发现他既具有那一代知识份子心路旅程的共性特征,又具感人的个人情怀,为推进、丰富近现代音乐教育界代表性人物的学术研究充实有价值的文献。
关键词:陆华柏;近现代音乐史;音乐创作;音乐教育;新音乐
目前,学界关于音乐家陆华柏(1914-1994)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音乐文论《所谓新音乐》研究、音乐教育研究及部分音乐作品研究,且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深入并受到学界重视。本文从陆华柏的心灵深处进行考察、探寻,通过从陆华柏故居收集到的思想汇报、信件等史料及采访人手,对陆华柏的心路历程进行梳理,以期增进学界对陆华柏艺术人生的认识。
1914年11月16日,陆华柏出生于湖北荆门一个普通家庭。陆华柏一生历经中国极为动荡的社会变化,他的音乐生涯时而冲向耀眼的辉煌,时而又陷入泥泞的深渊。陆华柏曾自称是“动荡的大时代中一位搞音乐的知识分子小人物”,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几分辛酸。1994年3月18日,走过八十个春秋风雨人生的陆华柏先生,长眠于广西南宁这片他深爱的热土。
从1949年起,他的心路历程具有那一代知识份子的共性:既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欢欣鼓舞,也品尝了1957年“反右”之后被无端迫害带来的压抑。虽然1977年陆华柏迎来春归大地的精神世界,但他的内心又由于一些特殊历史事件而一度陷入彷徨苦闷,从而使陆华柏的心灵具有鲜明的个性遭遇。在洞察1949年后陆华柏心路之前,此将1949年前他的音乐人生作简要回顾。
陆华柏1934年毕业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科,留校任教。1937年暑假在南京访友时与友人组成“雅乐五人团”,由画家徐悲鸿推荐,于抗日前夕去广西。1937-1942年间,陆华柏在广西从事推广音乐工作并在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广西艺术学院前身)任教,积极参加抗战活动,创作了包括《故乡》、《勇士骨》在内的艺术歌曲及《保卫大西南》、《磨刀歌》等抗日群众歌曲,在桂林抗战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篇章。1943-1945年间,陆华柏任教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音乐创作与教学工作进行顺利。1946年至解放前,陆华柏在江西体育专科学校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香港等处任教。
笔者将1949年作为探索陆华柏心路历程的重要年份,主要是根据陆华柏写于1993年11月16日的手稿。在这份标题为《陆华柏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手稿中,他将自己的人生阶段作如下分期:第一阶段“解放前”;第二阶段“解放-划右派”;第三阶段“再度回到广西(1963年一现在)”。鉴于此,笔者在尊重陆华柏人生分期的基础上,根据陆华柏实际音乐生涯和社会时事变化,将1949年后的陆华柏心路历程再细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7年;1957-1977年;1977-1994年。
一、1949-1957年:满怀赤诚 谱写新篇
1949年上半年,陆华柏在湖南音乐专科学校任教。长沙解放前夕,陆华柏因收到有人冒充贺绿汀、李凌从香港发来的一份假电报而来到香港@。在香港,他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在永华影片公司任作曲专员,并担任香港音乐院院长一职。1949年10月,香港六国饭店举行港九音乐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由陆华柏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的文章《港九音乐工作者,在五星红旗下团结起来吧!》表达爱国热忱。
停留于香港的短暂时期,陆华柏满怀赤诚投入工作并取得了可观成果。1949年10月1日,香港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陆华柏作曲的曲集《闹花灯组曲》,扉页题记为:“谨以此曲庆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此曲集包括《解放军,向南开》(大众康塔塔),《打到台湾去》(男女二部合唱)、《解放歌》(男女三部合唱)、《闹花灯组曲》等。1949年10月15日。香港音乐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陆华柏编曲的《红河波浪》(民歌独唱集),收集有带钢琴伴奏的云南民歌《红河波浪》、新疆民歌《洪里洪巴》、青海民歌《送大哥》、甘肃民歌《小放牛》等12首民歌改编曲。香港音乐教育出版社于1949年10月,出版了聂耳原作,陆华柏配四部和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合唱谱》。同月,陆华柏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刚决定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编写了管弦乐队谱,应征寄于国务院。
可见,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不到一年,陆华柏在香港满怀赤诚,声名显赫,为新中国及祖国音乐事业饱蘸激情,奋谱新篇。
1950年春,应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之邀,陆华柏毅然回到大陆。他先在湖南衡阳第四十九军文工团、中央戏剧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后于1952年11月来到江城武汉,任武汉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这是一个百废待兴而又欣欣向荣的年代。陆华柏写道:“1949年全国(除台湾外)解放后,一直到1957年,我感到确实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事业……一切都处在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进程中。”陆华柏厚积薄发,伴随新中国建立后一切都呈现一片生机盎然,1952年到1957年上半年,是陆华柏人生中最闪耀最丰收的年代:为了配合教学工作,陆华柏在武汉工作的几年中连续出版了多本曲集和钢琴独奏曲,还出版了一部管弦乐作品《康藏组曲》。
二、1957-1977年:身处逆境 依然执着
好景不长,正当陆华柏的艺术追求和音乐事业如日中天时,1957年11月,陆华柏被错划为“右派”,进行劳动改造。陆华柏和夫人甘宗容双双被下放在江汉平原西端荆州与宜昌交界的草埠湖农场劳动。对于这段经历,陆华柏在1980年向党组织提交的思想汇报时这样写道: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我是个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生活作风带有许多旧包袱,这是我自己也觉察到了的。因此,改造,我并不抵触。但是我怎么会同党、同无产阶级、同人民闹成敌我矛盾呢?这点我百思不得其解。
尽管内心有冤屈,陆华柏还是努力接受劳动改造。据甘宗容回忆,在草埠湖农场,因陆华柏体力太弱,不善干农活,农场长让陆华柏负责照看小毛驴。农场里上海知青多,陆华柏还负责为知青收发信件,他每天骑着毛驴为知青们收发信件,养猪、养驴。甘宗容说:
当时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一定带了很多不好的思想,所以每次思想汇报都写得很好,虚心接受改造。当地农民对我们很好,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摘帽了,成了摘帽右派。
摘帽后的陆华柏被遣往湖北艺术学院工作了近三年。1963年12月,陆华柏与妻子一起调往广西。1964年起在广西艺术学院工作。刚开始的几年,陆华柏随学生去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采风,深入考察当地民间的多声部现象@。陆华柏匿名发表的作品《彝族女民兵》经过层层筛选,该作参加了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业余艺术观摩会演”进京演出。
1966年文革爆发,这场风波我们还是幸运的,没有挨打。但毕竟是做了头号右派,我们与外界断了联系。陆华柏当时就像一个机器人,广西所有的歌舞团演出,都让陆华柏配器,他们每天晚上送来,第二天就要来取走。陆华柏最了不起的就是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坚持翻译,他的英文全靠自学,他的口袋里都是装满英文单词的小字条。他总是对我说,外语别丢。当时我们都被斗得要死,谁还有精力学习。要是谁知道陆华柏学外语就会背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所以他晚上翻译完将译稿偷偷放在床底下。陆华柏对我说,“你信不信,以后我还有用。”
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柱使得陆华柏即使身处“牛棚”依然悄悄翻译外国音乐理论著作?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得陆华柏坚信他“以后还有用”?下面这段“思想汇报”可以清晰地看到,陆华柏在面临委屈,深陷逆境中他所作的深层思考,他对党未来的坚信和对人民的艺术执著的追求。
我想: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任何变革不能不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时是作出必要的牺牲,有时是也可能某种错误造成的牺牲;我自认为我和许多人就属于后者……我本来是革命部队在前沿阵地里的自己人,我们的炮兵从后方向敌人吊炮,出于测量的俯仰角低了一点,炮弹落在我们头上,造成牺牲。只有这样想吧!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能进入社会主义,能过幸福日子,我就在做不得不支付代价的一部分吧。
显然,陆华柏是把个人所受曲折作为将来社会能够过上好日子的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这等信念、这等忠诚犹如虔诚的信徒,彻底解开自己的胸怀,为成全祖国和人民,牺牲自己也值得。
“从牛棚里出来,陆华柏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家,而是先去琴房过“琴瘾”。文革中,陆华柏是一个“逍遥派”。虽然如此,漫长的岁月仍削减着陆华柏的创作热情,20年间,陆华柏很难发挥各方面才能,音乐创作接近停滞。
支持陆华柏走过艰难岁月一是因为对音乐艺术的发自内心的爱,这份爱非常执着;二是因为他坚信正义之光必将出现,坚信党和社会是有希望的,这份信任也非常执着。因此,他努力地“顺应”时代,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他在维持个人与时代之间艰难平衡的同时,又在内心时刻进行着“反省”和自我激励。怀着对未来纯洁的信仰,跌人人生最低谷的陆华柏依然勤奋工作,热爱音乐,坚信光明的未来。
三、1977-1994年:老骥伏枥 苦乐彷徨
1977年,陆华柏到广西东兰一带采风,被当地铜鼓舞深深感染,一气呵成完成了钢琴曲《东兰铜鼓舞》。这首用西方奏鸣曲式写成的作品犹如陆华柏生命中的春天奏鸣曲,预示着艰难生活的终结,标志着陆华柏又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命与心灵旅程。那年,陆华柏63岁。陆华柏对国家和个人焕发出新生的活力:
接受了二十二年的严峻考验,虽然自己做得还是很不够,但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终于有了这样一天!这不是一个人的恩怨问题,我看见的是党中央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逐步展开的宏伟政治图景……我重又感到党和国家前途确实是光芒万丈。”
1979年9月,陆华柏被任命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从此,陆华柏更常常工作到深夜。1980、1981年,他向党组织提交了两份思想汇报,剖析自己经历,表达对党的忠诚,并第四次向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1980年的思想汇报中写道:
我申请入党,既不是出于虚荣心光荣感,也不是为谋求个人的好处,我觉得我在旧社会、新社会生活了几十年,从最初政治上的无知盲目到应有觉悟到多懂得了一点马列主义道理,这无不与党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帮助或影响分不开。在总的趋势上我是一步一步更靠近党的,所以我把入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看成我的最后的归宿。
1984年,在第四次提交入党申请书后,70周岁的陆华柏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陆华柏常说:“共产党要我,我跟共产党走,共产党不要我,我也跟共产党走!”
很多人不理解陆华柏的做法,当时工作单位有的人散布此传言:“你陆华柏拼死拼活,不就为捞得一顶红帽子吗?红帽子,入党也……过去你是右派,后来成了‘脱帽右派,现在算是‘改正右派——你总还是个右派吧”@。1979-1984年陆华柏担任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期间,尽管精神焕发,但常感工作阻力很大。陆华柏也曾反思过自己的一些弱点,如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同志一起工作、工作中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等等。甘宗容回忆陆华柏时,曾称他为“书呆子”,说他一天到晚只会看书做学问,不会与别人打交道,说话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这些“不圆滑”的性格特点也曾令陆华柏彷徨和苦恼。尽管面临困境,陆华柏还是希望在音乐系组建“实验民歌合唱团”、“实验民族乐团”、“实验交响乐团,希望广西民族民间音乐艺术逐渐发扬光大于世界音乐之林。在陆华柏和同仁共同努力下,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形成了定期举办音乐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学与业务实践关系更加密切,为该校音乐系之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当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在陆华柏及同事们的辛勤努力下渐有起色时,1984年,对于陆华柏来说又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他情绪起伏的一年。那年,陆华柏检讨了40多年曾的《所谓新音乐》原文被发现,一时激起千层浪,打破了陆华柏的平静生活。对照原文,陆华柏发现1940年李凌批评他时的“引用部分”却均未出自原文,陆华柏认为李凌“把我那篇文章中某些失之偏颇的提法极度夸大,特别是把音乐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他开始为自己申辩,连续发表了2篇质疑文章,与李凌展开笔战。看来,虽距《所谓新音乐》发表时间已过去40多年,但此文给陆华柏带来的心灵伤害和精神包袱深重如山,故而一触即发,“新音乐事件”无疑是陆华柏晚年生活中一道求证愈伤的重题。陆华柏于1987年亲自到江西南昌、广西桂林收集民国时期发表的音乐文论。当他发现20世纪40年代在江西南昌《中国新报》上刊载的不少文论表明了他相对完整的音乐观,他开始写作长文《四十年代我的音乐观》,旨在证明当时的音乐观是积极全面的。他认为一个人的音乐观不会改变得如此之快,1940年的《所谓新音乐》确实不合时宜,但他总体上来说是爱国爱党一心为中国音乐事业努力工作的。此文为陆华柏手稿,未公开发表。
1985年,陆华柏教授从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系主任职位退休,他对自己的处境颇感满意,因为退休意味着他将过上“专业作曲者”的生活:
我对我的退休,可从事专业写作,是很满意的……为什么向往过“专业”作者的生活呢?因为我觉得,只有“专业”作者的心情才适合于一个搞音乐创作的人的心情。
1985年10月我被“获准”退休,但没有放下笔,而是重新开始,当个过去向往已久的“专业”作者,争取再多做点贡献。
退休后的陆华柏主要以写作音乐文论为主。这些音乐文论有关于广西多声部音乐研究,一生创作经验总结,更多的则是回忆抗战音乐活动及对创作历程的回顾。《晚年逢盛世,笔下又生辉》也正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1987年,陆华柏亲自赴广西桂林、江西南昌查找自己民国时期报刊上发表的音乐文论。当他查到1946至1947年间在《中国新报》发表的多篇音乐文论,体现了他较为全面的音乐观,而这些音乐文论与《所谓新音乐》的发表时间仅相距短短几年,更觉乐界长期以来仅关注《所谓新音乐》而一概忽略了其他音乐文论,内心波澜又一次激起。他遏制不住内心不平,立即从报刊上将文论复印下来,并很快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写成长文《四十年代我对“新音乐”的态度以及当时我的音乐观——为中国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一点有关参考资料》,该文陆华柏以史料文献为证,将报刊复印的音乐文论剪贴件原封原样贴在文中。只是此文未能发表成为陆华柏晚年的一件憾事。
然而,陆华柏的艺术创造和价值被世人尊重。198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风和月亮——陆华柏歌曲选》。1988年12月25日,广西艺术学院为陆华柏隆重举办了“陆华柏从教55周年纪念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对陆华柏一生音乐创作成就的概览回顾。他为此忘情投入,从向广西自治区申请经费,到确定演出节目、撰写台词、组织音乐会排练及彩排等相关事项都付出了艰辛努力。音乐会上,特邀高伟任指挥,陆华柏的老朋友温可铮先生从上海赶到南宁,王逑、俞子正等都在音乐会上一展演技。音乐会非常成功,演出结束时,上台合影的陆华柏露出了发自心灵的幸福笑容。
陆华柏的晚年生活就在这样的心潮起伏、矛盾彷徨中度过。从他与台湾、香港及内地音乐学者的信件联系来看,陆华柏仍有未了的心愿:
譬如心愿之一,希望三首钢琴曲能在台湾出版。1993年6月23日陆华柏曾写信给台湾学者欧阳如萍表达希望将他心爱的钢琴曲在台湾出版的心愿:“……寄三首钢琴曲存你处,我是想作为‘中国感情的作品(教材)能够在台湾出版,并向海外华人学校及爱好音乐者推广,起些影响。你遇有机会,请你试向乐韵出版社或其他出版社介绍一下。”
心愿之二,希望《中国民歌钢琴小曲集》能重版。陆华柏曾收到了一封来自人民音乐出版社第二编辑室1985年12月11日的回信。他一直期待着后续回应。
心愿之三,希望音乐界不要片面认识陆华柏四十年代的音乐观(前文已述)。
心愿之四: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对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配伴奏的事情有全面认识与回复。陆华柏遗稿文件袋中,有一个名为“国歌提案”文件袋,袋里包括《义勇军进行曲》齐唱、合唱、钢琴伴奏、管弦乐伴奏规范的配套通用谱。晚年陆华柏写的不少文童未见发表,这些遗稿资料坦露了陆华柏的真实心迹但是均未能被发表,这给他增添了一层不被人理解的孤独与苦闷。
1990年起,陆华柏患鼻咽癌,听力和与人交流日渐困难。生命最后几年中的陆华柏,最令他欣慰的是有戴鹏海先生为其编写《陆华柏音乐年谱》。对陆华柏来说,年谱是对他一生努力的如实记录。因此,陆华柏将多年来收集到的所有资料都提供给戴鹏海,并和戴鹏海通信多封,沟通探讨年谱编写。所幸《陆华柏音乐年谱》于1994年初(陆华柏逝世前三个月)由广西艺术学院内部印刷,陆华柏得以在临终前看到年谱。
关于“新音乐”事件使陆华柏的晚年情绪产生波动。尽管心情有起有落,晚年陆华柏对自己要求愈发严格。据陆华柏夫人甘老师回忆,晚年陆华柏对“公家”有更多的顾忌,他们的外孙在小时候常问外婆:“公家是什么?公家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陆华柏坚决不让外孙翻动在他看来是“公家”的东西。陆华柏的女儿回忆说,陆华柏夫妇的公费医疗卡从来不用,俩人看病都是自己掏钱,连做系主任时办公室里的钟也是自己掏钱买的。陆华柏坎坷的人生经历,对他造成一次次的心灵冲击与伤害,难免有忧虑与苦闷,譬如,这些影响使得他并不支持家人后代学习音乐艺术的态度。1983年起,陆华柏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陆华柏看不惯广西艺术学院招生中的不正之风,与其夫人甘宗容教授联合广西艺术学院另外四名教授,联名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投诉,揭发广西艺术学院招生中存在的不当现象。当时的陆华柏和甘宗容,甚至还为民请命,被民众称为“青天”。
结语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旧知识分子要想被新政权接纳,忏悔和表态是一道必须过的关口”。从陆华柏的思想汇报可以看出他的自我反省和表态。事实上,解放后陆华柏的心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心路的一个缩影,但由于诸如数十年间的《所谓新音乐》等事件影响。陆华柏又有其不同之处。1949年后的陆华柏是不断接受“改造”,不断将自己和时代艰难融合、再生创造的心路历程。陆华柏曾称自己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斗争、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等系列重大社会变动与变革。
1949年,当解放的消息传到香港,陆华柏毅然决定回国。一心想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忽然被打成右派,更没有想到1957-1976年的20年间会跌至人生泥泞深渊。然而即使生处逆境,他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1984年,《所谓新音乐》一文的原稿被重新发现,瞬间打破了陆华柏原本平静的生活,他开始为自己辩护。1987年,当他在江西南昌发现早年发表在《中国新报》上诸多音乐文论后,更加一发不可收,觉得自己蒙受了冤屈。所幸陆华柏生命的最后时光,有戴鹏海研究员为他编写《陆华柏音乐年谱》。陆华柏临终前的几个月年谱得已印出,“陆华柏日夜捧读,爱不释手”。晚年陆华柏内心矛盾彷徨,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在第四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后,终于在70周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员。陆华柏晚年彷徨却坚持笔耕,撰写了总结创作经验的文章、广西多声部音乐研究论文多篇和大量回忆录。陆华柏之所以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取得成果,和他对音乐事业的热爱分不开,更和他坚定的个人信念分不开。了解陆华柏的心路历程,就能够理解陆华柏为何在逆境中仍能坚持学习音乐,也更能够理解晚年陆华柏依然老骥伏枥坚持笔耕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探究1949年后陆华柏心路。对于学界了解真实的陆华柏具有一定意义。
(责任编辑 刘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