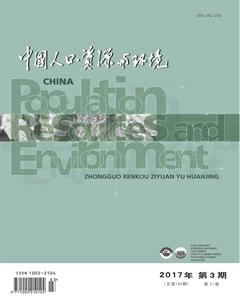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及争论
范明明++李文军

摘要生态补偿的概念自提出便受到学界和政府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近20年来生态保护的主要政策手段。虽然基于生态补偿的政策手段被大范围使用,但是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却处于发展与争论的阶段,该理论的适用性及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在实践过程中备受质疑。本文梳理了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过程,将其总结为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机制的构建三个主要阶段。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层面,如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效果评估等方面,但是对基础理论探讨不足。本文从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三个过程,综述了目前对生态补偿理论的讨论及争议,认为在处理“社会—生态”关系的核心问题上,尤其在一些长期依赖并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地区或者民族地区,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均对此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解,这也是实践中生态补偿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本文提出用“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一词代替目前所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理论上避免忽视社会系统及社会与生态系统二者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当外部政策干预。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补偿;社会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205;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13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6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类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草地、森林、农田、河流和湖泊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均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温室气体也在全球尺度上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国际社会对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视日益增强,经济手段成为解决生态与社会两个系统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生态补偿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在近十几年的时间内被迅速用于全球范围内。中国也正在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生态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生态补偿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远落后于实践,这也是生态补偿效果未达到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1生态补偿的发展与构建过程
国外相关研究中,生态补偿通常用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简称PES)一词,或者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简称为PES),即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其中前者的运用更为广泛。本文为与中国政策语境一致,均采用“生态补偿”一词。总体来看,生态补偿理论的发展与构建过程是基于以下三个阶段:即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机制的构建。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s)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其最初的目的是将生态系统功能构建为人类可获益的服务,从而引起公众对于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1]。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将不同尺度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连接起来,并且强调了社会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在这一阶段,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仅是用于更加形象地表征生态系统功能,而并没有在生态保护的实践领域内起到重要的影响[2]。
从20世纪末期开始,尤其是Costanza等人[3]在Nature杂志上的文章首次评估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推向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起到了里程碑的意义。随后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4]、基于各国和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经济价值评估[5-6],使生态系统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在公众面前。生态系统功能非市场价值的货币化表示,引起了政策制订者对生态保护的极大关注,也为生态补偿在实际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2000年之后,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基础上,生态补偿迅速成为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手段[7]。生态补偿的逻辑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将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体现出来,可以促使资源使用者形成保护生态的激励和行为[8-9]。从理论上讲,生态补偿被当做是一种保护生态系统的正面激励机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向提供者支付费用,既能够鼓励资源使用者主动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社会整体所获得的生态服务价值高于支付费用,因此政策实施具有成本效益[9-10]。
范明明等: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及争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鉴于在理论分析上的诸多优势,生态补偿已经成为保护或者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政策手段,被应用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等众多领域[11]。如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服务补偿体系、美洲国家的森林碳汇补偿体系、美国的流域生态补偿等[12-18]。综上所述,可以将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总结为: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重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货币化的衡量方式在社会活动中体现生态系统的价值,并最终将其纳入到社会经济系统之中作为生态或者经济政策决策的依据。
2生态补偿的概念及理论研究点
2.1生态补偿的概念
Wunder提出了生态补偿的经典概念,即“生态补偿是建立在某一清晰界定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上,提供者和購买者之间的自由交易,它包括五个方面:①自愿交易;②对生态系统服务有清晰的定义;③存在至少一个买家;④存在至少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⑤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提供”[8]。这一定义基于科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解决外部性问题,强调了生态补偿的市场激励,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之间进行自愿交易[9]。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之中,学者们发现Wunder所定义的纯粹市场机制过于理想,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生态过程及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对于大多数的生态服务来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纯粹的市场[19-20]。从生态系统服务生产的角度,由于气候、环境、人为干扰等多方面的作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具有很强的时空异质性和动态变化性,很难像其他商品一样保证稳定的供应[21];从生态系统服务购买的角度,只有少数类似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交易受益者是直接的购买者,而如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等服务,受益者往往数量众多,因此只能是政府或者一些机构组织成为唯一的购买者[9,19,22];从价格形成的角度,生态系统服务的价格并不能由经典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而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财政、政治等方面的影响[23]。Muradian[24]从激励机制、交易方式和生态服务的类型等三个方面对概念提出质疑,并重新定义:“在自然资源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使个人/集体的土地利用决策与社会利益达到一致,而在社会成员之间所进行的资源分配”。这一定义更加强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以及资源的正义分配,而不是将经济激励放在首位[10]。Vatn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生态补偿虽然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市场机制,但是事实表明在此过程中,具体实施更加依赖社区或者国家的参与[25]。而在我国,一般将生态补偿定义为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26]。
虽然各方学者对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对于生态补偿的设计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①目标确定: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即对于购买者/提供者来说,购买/提供的对象是清晰的;②利益相关者的确定: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的影响范围,确定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③实现途径:在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与购买者之间进行利益分配。
2.2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点
现有生态补偿的主要研究热点包括生态补偿的标准、补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成本有效性与公平、可持续性等方面。
生态补偿的标准是生态补偿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根据Wunder等人对于生态补偿的分析,当补偿的金额大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机会成本,小于生态系统服务本身的价值时,则可以同时对于购买者和提供者形成有效的激励[8-9]。目前有关生态补偿标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机会成本的确定,另一个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关于机会成本,补偿对象异质性及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两个问题,使得生态补偿的标准往往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27-28]。但由于机会成本的核算更为简便,目前绝大多数的生态补偿标准都属于基于机会成本的补偿,如尼加拉瓜草牧生态系统补偿依据最佳土地利用价值作为标准[29],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项目用造林的机会成本作为标准[30],我国的草场生态补偿政策则利用牧户的放牧损失作为标准。而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目前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供求关系的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等[31-32]。
交易成本是生态补偿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设计能否有效进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完整制度框架、明晰产权安排和利益分配机制是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33]。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需要重点考虑,研究表明在这些地区更多地依赖于社区参与和集体行动才能降低交易成本[24-25]。因此,当社区层面被包含在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中时,生态补偿建立时的交易成本以及监督执行成本都能够得到有效的降低[34]。
成本有效性是政策开发和运用的重要标准,生态补偿政策作为全球性的环境政策工具,目的在于在资金约束条件下获取最大的環境收益/效益。成本有效性的研究需要明确两个方面,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清晰定义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标准[35]。首先,生态系统服务在很多项目中难以明确定义,很多实践过程中采用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等同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导致理论的计算结果往往与实际保护效果相去甚远[35-36]。与此同时,目前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合理的核算与评估标准,因此导致补偿资金使用效率难以衡量,进而影响通过市场手段首先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供给[28]。公平往往与上述的成本有效性同时成为研究学者的关注目标,尤其是生态补偿项目通常发生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相关的研究中更加强调在公平前提下的成本有效性[37-38]。
能否通过生态补偿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有效供给是很多实践项目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生态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主要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①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与生态效果之间的关系,如果在项目期内没有实现生态系统的改善或者效果不佳,那么从购买者角度则不愿意进行继续支付[39];②生态补偿的实施方式,基于个体的补偿方式往往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项目初期较高的接受程度,但是基于当地社区组织能力建设的生态补偿,更容易得到本地居民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形成保护生态的长效机制,提升补偿计划的可持续性[9-10];③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或者资源,以保障当补偿项目停止的时候,资源使用者会不会回归到原有的资源使用方式上[40-41]。
3对生态补偿的理论争议
虽然生态补偿的逻辑简单清晰,并且相比以往的生态保护手段,生态补偿有诸多优点: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简单;对于购买者经济上更加有效;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来说,增加现金流,生计方式多样化;可以为生态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42]。但是,不少研究学者指出,正是因为这种处理社会和生态之间矛盾的简单化逻辑,生态补偿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激励或者产生保护生态的行为,反而会对生态系统以及资源使用者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从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来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化价值评估以及生态补偿的具体实践中,都反映出如何理解社会和生态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对于社会和生态系统关系的假设前提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本文总结了对生态补偿质疑的相关观点,并将其总结为如下几点。
3.1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区别
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忽略了其他非人类所需的生态系统功能,在生态补偿项目中往往要求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会使生态系统面临潜在的风险[43]。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最初是为了强调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生态系统服务往往是利于人类、积极的、正面的,但是实际上,洪水、疾病、火烧等对于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而往往不纳入“生态系统服务”的范畴内。因此,在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之中,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大多数情况还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一方面可以被人类利用的被称之为“服务”,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会因为人类的利用而受到损害。
正如Boyd所说,生态系统服务是受益依赖的(benefit dependent),人们对受益的偏好决定生系统态服务的范围[43]。比如,一条河流即可以提供清洁的水源,也可以作为游憩的场所,还可以作为水电能源的来源,这些都是对人类有益的服务功能,而最终如何管理这条河流取决于人们更偏好哪一种服务。而不同的管理方式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生态系统服务并不是生态系统状态的客观体现,二者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在生态补偿理论和应用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逐渐成为整个生态系统评价的指标,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越多代表生态系统状态越理想。因此,当用经济手段激励仅人类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时,实际是在试图对有限的变量的控制来为人类提供稳定的服务[23]。
然而,成功控制单一变量极有可能导致系统在其它时空尺度变量的变化,从而对生态系统其它非人类需要的生态系统功能造成破坏[44],以下一些案例也说明了追求单一或者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对生态系统的影响。Peterson 等人通过模型模拟湖泊管理的时候发现,以淡水输出、灌溉、娱乐等生态服务为目标的管理模式,最终会导致该湖泊生态系统的崩溃[45]。再比如,在强调某些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时,人们将固碳能力强的单一物种取代了原有的生物多样性,虽然提高了碳汇的服务功能,但却不利于整体系统的持续[46]。
3.2生态系统服务商品化对生态系统功能存在损害风险
在如何体现生态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贡献方面,将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货币化的衡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社会决策。但与此同时,生态补偿将生态系统服务简化为单一的货币化价值,进行物质化、商品化的交易,忽略了生产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生态系统功能,有可能造成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害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19,47-50]。
以生态服务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模式,是一种“通过买卖进行保护”的逻辑,这并不能触碰到生态问题产生的本质。目前,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对于货币资本积累的崇拜,以至于忽略了生态系统中其他非货币化的价值所导致的[50-51]。因此,将生态服务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时候,难免又陷入到资本积累的怪圈中,用货币去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大化生产,会造成新一轮的生态系统功能失衡[48]。
Peterson等人[48]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有可能造成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市场价格掩盖了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对于商品的贡献。与此类似,当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商品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就成为了劳动力。正如市场中的其他商品,生产的逻辑会掩盖“生态系统工人和原材料的痕迹,对“生态系统工人”的忽视,以及用货币对其进行替代,与生态系统服务重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初衷背道而驰。
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过程简化了生态系统的内部组分和生态过程的复杂性,这种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上的保护方式并不能达到目的[19]。在生态补偿的实施过程中,一般以对自然资源(或者土地)的产权明晰为前提[25],以便生态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的交易。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这種产权上的明晰将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过程分割成了不同的交易单元,忽略了某一单元内的生态功能或者过程是依赖于其他单元实现的,人为的物理意义上的分割有可能增强某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但是却损害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47]。如在欧盟的农业环境计划中,将农场主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进行补偿,以此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但是基于农场尺度的个体补偿,并没有实现在将景观作为整体进行管理, 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聚集奖励(Agglomeration bonus)”的方式寻求重新整合个体牧场主的途径[52-53]。
3.3经济激励对个体内在保护机制的“挤出/挤入效应”
生态补偿试图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使社会群体产生保护生态或者停止生态破坏的行为,但是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激励所造成的社会结果是复杂的,尤其对于一些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社区,外部经济激励可能对原有内在的保护和利用机制造成“挤出效应”,影响生态保护的效果[20,23,49,54-57]。在长期依赖自然资源为生的社区,其内部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宗教文化、制度安排等均与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密切相关,一些案例研究也证实这些内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使得这些地区避免了公地悲剧,保持了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58]。
根据保护动机内在性的强弱和收益特点,Reeson等人将公共物品或者服务的提供动机分为纯粹的利他主义、一般的利他主义、公平和信任、他人的认可、互惠、正式激励,并通过实验模拟的方式验证了在已存在内在保护动机的人群中增加外部经济激励,存在挤出内部机制的效应,对生态保护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见图1)[54]。Bowles 等人通过经济学实验的方式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市场机制鼓励竞争与个人主义,这种基于市场逻辑的制度能够塑造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而可能会破坏先前基于道德、文化、合作、互惠、社会关系的保护意愿等[55]。内在机制嵌套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持久性和自我约束能力,而现行的生态补偿激励往往来自于社区外部,如政府、组织或者私人企业等,“挤出效应”会使得外部经济激励停止时,生态保护的行动无以为继,形成“no pay, no care”的现象[57]。有的学者也将其称为“补偿逻辑的困境”,即只有当补偿金额越来越多的时候,保护生态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才会持续[20]。
此外,将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并进行交易的过程,会形成复杂的社会响应,利益群体对于收益、公平、权力的感知变化会对生态保护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47]。在生态服务的价格制定、交易等过程中,一般生态服务的购买者(企业、组织或者政府)具有绝对优势的信息和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补偿机制,会使生态服务的提供者产生抵抗、消极、愤怒、质疑等不确定的反应,导致不理想的生态保护效果。
4研究评述
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热点主要侧重在生态补偿的实
施层面,如补偿标准如何确定、政策成本效益等。对于理论层面的争议,本文认为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生态系统,生态补偿在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了解目标系统的复杂性,并且意识到生态补偿机制其简单逻辑背后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关系。
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有赖于两个层面问题的解决,首先是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问题,其次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源于资源利用社区(通常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对象)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这里我们称之为生态补偿需要解决的“一阶问题”。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处理资源利用社区和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即通过怎样的外部干预可以促使社区保持某种理想的利用资源的状态,这里称之为“二阶问题”。因此,生态补偿政策应该首先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内部作用机制,即目标社会生态系统如何产生所需的服务,然后通过外部经济激励的政策设计保持这种理想的状态,即解决二阶问题。但是,从目前生态补偿的研究热点来看,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二阶问题的解决方案,如补偿标准的确定,生态补偿成本效益等问题,而很少讨论其一阶问题。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解决外部性的手段,经常会将外部性的解决转化为一种简单化的外部干预,尤其是当政府作为补偿方和资本相结合时,这种外部干预的弊端就会更加显著,其结果就是忽视目标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差异性[59]。这种不当外部干预通常的表现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和生态问题,而缺乏对内部资源使用者、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剖析。因此,生态补偿的目标虽然是通过经济手段激励资源使用者的保护行为,但是实际上却往往因为这种外部不当干预的视角,导致目标系统不能够被完全理解,如上文提及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时限和范围等等一般均由政府决定,补偿对象的参与程度很低[19,22,24]。其结果通常是将目标系统内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简单化,并可能导致与预期相反的效果[60]。
此外,现有关于生态补偿的争议一般局限在单纯的社会系统或者单纯的生态系统的讨论中,而缺乏将二者作为整体进行考虑。一直以来生态系统服务一般被理解为人类从生态系统所获得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收益[4],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同时人类活动也一直被视为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政策往往过度关注人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61]。但实际上,纯自然的、无人类干扰的生态系统很少存在,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态,关注以往长期的人类活动影响对生态系统的塑造过程,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同样重要[61]。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一些新的表述,如“文化景观生态系统服务”(cultural landscapes ecosystem services)、“社会生态服务”(Socialecological services),以表征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作用[61-62]。
基于以上认识和分析,本文认为采用“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一词代替目前中所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够在理论上避免由于仅强调生态系统而忽视社会系统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导致的不当政策干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SocialEcological Systen Service)是指人类能够从某些特定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收益,如在草原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人—草—畜”放牧业生产系统,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系统、哈尼族的梯田体系等,这些传统的社会生态系统都为所在地区提供了长期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收益。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不是为了否定传统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或者创造一个新的概念,而是为了通过此概念在生态补偿设计及实施的过程中对于认识和处理生态和社会之间关系,强调两个方面:第一,区别以往单纯强调人类对生态系统负面干扰的生态治理思路,突出人类的文化、经济活动、观念等在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重要作用。第二,突出社会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及对政策响应的复杂性,了解生态系统服务的内部机制,特别是社会及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
如果以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补偿的目标,必须要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反馈关系、相互作用机制。与单纯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不同,以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补偿的对象不是排除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而是考虑如何维持人利用资源的活动,保持一种理想的人与自然的反馈状态,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对这一問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走出现有的政策误区,对接下来更大范围内的生态补偿政策提供新的视角。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ESTMAN W. How much are natures services worth? [J].Science, 1977, 197(4307):960-964.
[2]NORGAARD R B.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eyeopening metaphor to complexity blinder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69(6): 1219-1227.
[3]COSTANZA R.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Nature, 1997, 387 (6630): 253-260.
[4]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the assessment ser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2005.
[5]谢高地,鲁春霞,成升魁.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J].资源科学, 2001, 23(6):5-9. [XIE Gaodi, LU Chunxia,CHENG Shengkui.Progress in evaluating the global ecosystem services[J].Resources science, 2001, 23(6):5-9.]
[6]欧阳志云,郑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机制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 2009, 29(11):6183-6188. [OUYANG Zhiyun,ZHENG Hua.Ecological mechanisms of ecosystem services[J]. Acta ecologica sinica,2009, 29(11):6183-6188.]
[7]GóMEZBAGGETHUN E, DE GROOT R, LOMAS P L, et al. The history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early notions to markets and payment schem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6): 1209-1218.
[8]WUNDER S.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ome nuts and bolts[R]. Indonesia: CIFO,2005:6.
[9]ENGEL S, PAGIOLA S, WUNDER S. Design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663-674.
[10]FARLEY J, COSTANZA R.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local to global [J].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11):2060-2068.
[11]LANDELLMILLS N, PORRAS I T. Silver bullet or fools gold[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2002:11.
[12]PAGIOLA S, BISHOP J, LANDELLMILLS N. Selling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marketbased mechanisms for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M]. Earthscan, 2002.
[13]ASQUITH N M, VARGAS M T, WUNDER S. Selling tw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kind payments for bird habitat and watershed protection in Los Negros, Bolivi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675-684.
[14]PAGIOLA 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Costa Ric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 (4): 712-724.
[15]WUNDER S, ALB A N. Decentralized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the cases of Pimampiro and PROFAFOR in Ecuador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 (4): 685-698.
[16]CORBERA E, SOBERANIS C G, BROWN K.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n analysis of Mexicos carbon forestry programm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3):743-761.
[17]FROST P G H, BOND I. The CAMPFIRE programme in Zimbabwe: payments for wildlife servic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776-787.
[18]靳樂山, 李小云, 左停. 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生态经济, 2007(12):156-158.[JIN Leshan, LI Xiaoyun, ZUO Ting.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lessons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y, 2007(12):156-158.]
[19]MURADIAN R, RIVAL L.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the challenge of governing ecosystem services [J]. Ecosystem services, 2012, 1 (1): 93-100.
[20]MURADIAN R, FROGER G, GARCIAFRAPOLLI E, et al.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fatal attraction of winwin solutions[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3, 6(4): 274-279.
[21]FISHER B, TURNER R K, MORLING P. Defining and classifying ecosystem services for decision making[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3):643-653.
[22]KEMKES R J, FARLEY J, KOLIBA C J. Determining when payments are an effective policy approach to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2069-2074.
[23]REDFORD K H.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challenge of saving nature [J].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9, 23 (4): 785-787.
[24]MURADIAN R, CORBERA E, PASCUAL U, et al. Reconcil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6), 1202-1208.
[25]VATN A.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6): 1245-1252.
[26]中國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Research Group of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in China.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in China[M].Beijing:Science Press,2007.]
[27]KOSOY N,MARTINEZTUNA M,MURADIAN R, et al.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watersheds: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cases in central Americ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1( 3) : 446-455.
[28]FERRARO P J.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contract design fo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 810-821.
[29]PAGIOLA S, RAMíREZ E, GOBBI J, et al. Paying for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f silvopastoral practices in Nicaragu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4(2):374-385.
[30]SNCHEZAZOFEIFA G A, Pfaff A, Robalino J A, et al. Costa Ricas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 intention,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J].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7, 21(5):1165-1173.
[31]王燕, 高吉喜, 王金生,等.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述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11): 337-339.[WANG Yan, GAO Jixi, WANG Jinsheng, et al.Review of evaluation method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3, 23(11): 337-339.]
[32]李晓光,苗鸿,郑华,等.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主要方法及其应用[J].生态学报, 2009, 29(8):4431-4440.[ LI Xiaoguang, MIAO Hong, ZHENG Hua, et al.Main methods for set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their application[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9, 29(8):4431-4440.]
[33]WUNDER S, ENGEL S, PAGIOLA S. Taking stoc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834-852.
[34]CORBERA E,BROWN K, ADGER W N. The equity and legitimacy of marke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J]. Development & change, 2007, 38(4):587-613
[35]KROEGER T.The quest for the ‘optimal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 ambition meets reality, with useful lessons[J]. Forest policy & economics, 2013, 37(C):65-74.
[36]李文華,张彪,谢高地.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 (1): 3037-3046.[LI Wenhua, ZHANG Biao, XIE Gaodi.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9,24 (1): 3037-3046.]
[37]GAUVIN C, UCHIDA E, ROZELLE S,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with dual goals of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J]. Environmental mannagement, 2010, 45(3): 488-501.
[38]GROSSCAMP N D, MARTIN A, MCGUIRES, et al.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an African protected area: exploring issues of legitimacy, fairness, equity and effectiveness[J]. Oryx, 2012, 46(1): 24-33.
[39]FERRARO P J, KISS A. Ecologydirect payments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J].Science, 2002, 298 (5599): 1718-1719.
[40]PAGIOLA S, RAMíREZ E, GOBBI J, et al. Paying for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f silvopastoral practices in Nicaragu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4(2):374-385.
[41]徐晋涛,陶然,徐志刚. 退耕还林:成本有效性、结构调整效应与经济可持续性——基于西部三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 2004(4):139-162.[XU Jintao, TAO Ran, XU Zhigang.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costeffectiveness, structural effec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4(4):139-162.]
[42]PATTANAYAK S K. Show me the money: do payments supply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0, 4 (2): 254-274.
[43]BOYD J, SPENCER B. What are ecosystem services? the need for standardize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unit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2): 616-626.
[44]HOLLING C S, MEFFE G K.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J].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6, 10 (2): 328-337.
[45]PETERSON B G D, CARPENTER S R, BROCK W A. Uncertain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multistate ecosystems: an apparently rational route to collapse [J]. Ecology, 2003, 84 (6): 1403-1411.
[46]CHAN K M A, PRINGLE R M, RANGANATHAN J, et al. When agendas collide: human welfare and biological conservation[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7, 21(1):59-68.
[47]KOSOY N A S, CORBERA E.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s commodity fetishism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6): 1228-1236.
[48]PETERSON M J, HALL D M, FELDPAUSCHPARKERA M, et al. Obscuring ecosystem function with application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concept[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1): 113-119.
[49]GOMEZBAGGETHUN E, RUIZPEREZ M. Economic valu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J].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2011, 35 (5): 613-628.
[50]POKORNY B, JOHNSON J, MEDINA G, et al. Marketbased conservation of the Amazonian forests: revisiting winwin expectations [J]. Geoforum, 2012, 43(3): 387-401.
[51]陈学明,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中国社会科学, 2012(11):4-23.[CHEN Xuem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ecological crisi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11):4-23.]
[52]PARKHURST G M, SHOGREN J F, BASTIAN C, et al. Agglomeration bonu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to reunite fragmented habitat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2, 41(2):305-328.
[53]ADMIRAAL J F, WOSSINK A, GROOT W T D, et al. More than total economic value: how to combine economic valuation of biodiversity with ecological resilienc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3, 89(4):115-122.
[54]REESON A, TISDELL J. When good incentives go bad: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stitutions, motivations and crowding out[R]. Sydney: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Society (AARES) 50th Annual Conference,2006.
[55]BOWLES S. 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 [J]. Science, 2008, 320 (5883): 1605-1609.
[56]KINZIG A P, PERRINGS C, CHAPIN F S, et al. Paying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romise and peril [J]. Science, 2011, 334(6056): 603-604.
[57]FISHER J. No pay, no care? a case study exploring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Uganda [J].Oryx, 2012, 46 (1): 45-54.
[58]埃莉諾·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0.[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M].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2000.]
[59]韩念勇.草原的逻辑[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HAN Nianyong. The logic of grassland [M]. Beijing: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1.]
[60]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SCOTT J C. Seeing like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4.]
[61]REDMAN C L, GROVER J M, KUBY L H. Integrating social science into the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 Network: social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hange[J]. Ecosystems, 2004, 7(2):161-171.
[62]HUNTSINGER L, OVIEDO J L. Ecosystem services are socialecological services in a traditional pastoral system: the case of Californias Mediterranean Rangelands[J]. Ecology & society, 2014, 19(1):8.
收稿日期:2016-11-10
作者简介:范明明,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管理。Email:fanmm@cass.org.cn。
通讯作者:李文军,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管理与政策。Email:wjlee@pk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草畜平衡的弹性管理:系统外因素的影响机制”(批准号:4117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