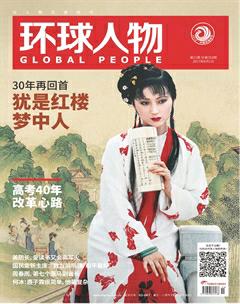姜德明,天生痴情唯有书

每次见到姜德明先生,我总会想到那句“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有一年,我陪《钱江晚报》记者张瑾华、马黎去采访黄永玉先生。在画室的墙上,正好挂着黄先生书写的这副对联,后来黄先生还在对联旁拍了照。
姜德明曾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退休前几年还出任了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其间推出了以“百家丛书”为标志的一批好书,是一位具有文人情怀的出版家。他与书有缘,可以说,书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
在1987年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之前,我就与姜德明认识了,一直喊他“老姜”。我与老姜缘起于约稿,相识时他还不到60岁。当时,我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开设了“居京琐记”栏目,因为很喜欢老姜的书话与随笔,便写了约稿信。1985年10月,老姜寄来文章《戏单》,写他留存的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戏单。他在1950年看了此剧,三十几年后重看戏单,感慨颇多:
翻看这戏单,我的眼睛有些潮湿了。
我舍不得丢弃它,尽管戏单的纸发脆发黄了,却分明又染着我青春时代血红的颜色。就像恋人们保存着永不褪色的红叶一样,它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
今后,我仍将珍惜地保存着它。三十五年来,我很少再在剧场里那样激动地看过戏了。一翻这戏单,我就想起当年的那些青春伙伴。如今我们山南海北,都已年近六旬,成了老头和老太婆了。我们当中有的历经坎坷,包括已经不在人世的,都保持着青春时代的真诚。我愿借着这份戏单,留下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留下那些使人难以忘怀的历史风雨。
通过戏单,老姜感悟生命,重温他们那代人从风雨坎坷中走过的青春历程。我当即去信,请他寄来照片,以便请丁聪插图。丁聪很快为《戏单》配了一幅精彩的插图。
从最初相识到同在一个报社工作,三十几年来,我们每次交谈,主要话题总是书:书的版本变迁,作者的命运遭际,逛旧书摊淘书的乐趣……“有意思!真有意思!”他连声感慨,脸上是掩不住的兴奋和陶醉。我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决定着他的文化情怀与走向。藏书和藏戏单都是老姜的兴趣所在。正是这种留存老物件的兴趣,使他在前辈唐弢之后,成为当代藏书丰富、藏名家书信丰富的藏书家。
如今,收藏已成为一种时髦,或者说一种投资方式。可对老姜而言,藏书是他偏爱历史、景仰前辈文人的方式。没有这样一种与书的天生痴情,他就不会在贬低文化的年代,还把业余时间和有限的财力,几乎都用在逛旧书摊和古旧书店上。对文化的特殊情感使老姜具有独特眼光,他喜欢收藏“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签名本,搜寻到了一些曾受到冷落的孤本、珍本。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真正文人与书之间纯粹、真诚的情感。如老姜在《戏单》中所说,是恋人之间的永不褪色的红叶。
老姜还珍藏了大量前辈文人写给他的信。有一次在他家,我们聊到兴起,他拿出这些信让我欣赏。叶圣陶、茅盾、俞平伯、巴金、孙犁……他们在信中谈书、谈掌故、谈那些不大时髦却仍令他们迷恋的话题,可见都把姜德明视为知己。两代文人的情怀因而连结在一起。
1989年秋天,我常到老姜的办公室里聊天。一次,他对我说:“你何不去图书馆,找找《国闻周报》,当年丁玲失踪、被捕后,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就在上面连载。这个连载后来结集成《记丁玲》,有过不少删节,你可以去校勘一下。”
多好的建议!我历来喜欢翻阅史料,从不觉得枯燥。于是一连几个月,我坐在图书馆里翻看《国闻周报》。读后,我再将它们复印,细细校勘,在沈、丁半个世纪的交往故事里,追寻文人间的恩恩怨怨。我还分别从唐弢、范用两位先生那里借来了《記丁玲》上、下两册,将之与连载进行校勘。最后发现删减部分,多达数百处、数千字。
校勘之际,我忽然想到,何不请熟悉的前辈,讲讲他们眼中的沈从文与丁玲。于是,我在1990年走访了巴金、张兆和、施蛰存、赵家璧、萧乾、冰心、凌叔华、陈明、刘祖春、汪曾祺、林斤澜、徐迟、周明……在他们的回忆中,历史的恩恩怨怨,渐次分明。看似个人间的交好、决裂,恰是那一代文人身处历史漩涡之中不同选择的呈现。
1992年11月,我终于完成了这段难得的历史追寻,出版《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由老姜写序。他详述了与沈从文、丁玲各自的交往,并提出了对我的建议:
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彼此又成为同事。我们年龄有别,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和书刊。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弄这又弄那。……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告诉他,希望他来完成。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国闻周报》,据以校勘辑录出使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人来做。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从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所发展,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不仅仅是研究著作,已经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
我感谢老姜。因为有了这本书,我的写作风格也有所改变,两年后,在《收获》杂志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由此而延伸。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思和兄策划出版“火凤凰文库”系列,请老姜编选《流水集》列入其中,并于1997年出版。2000年,我策划了一套袖珍版“大象漫步书系”,再次约请老姜编选《猎书偶记》列入其中。老姜还为这本《猎书偶记》写了一篇颇为有趣的前记,记录了他与人民日报图书馆老馆长谢兴尧先生的交往故事:
集近两三年写的随笔,编完这本记书人书事的《猎书偶记》,拍拍手松了一口气。完成一件工作总是愉快的。因想张守常教授托我转交谢兴尧先生的《太平军北伐丛稿》留在舍间几天了,这是一本新著,理应让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先睹为快。说走便走,拿起书就上路了。
谢老今年九十五高龄,这天睡到上午十时才起身。我问他天天如此吗?他说不是,昨夜失眠,今天起迟了。我说何不吃点安眠药。谢老说,他什么药也不吃,现在的药吃了也不管事。这是老人的幽默吧,意指市面上假药的泛滥。
顺问老人对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的看法,回答说看过了,那是玩艺儿,娱乐么,怎么拍都可以,不必反对。这同历史是两码事,若讲历史可就没那么好玩了。又讲到他有时还写点毛笔字,不过几句题跋之类。别的不敢动了。
老人问我还常写东西吗,我说偶一为之。他忽然冒出一段北大往事。那年,他用三十元买了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是线装本,装满了一辆人力车。见到胡适时他讲到此事,随口说了句,好像《饮冰室文集》里也没有太多的东西。胡氏大不以为然,很严肃地跟他讲起梁氏的学问,认为那也代表了一种新思潮,不应对故人这么漫不经心。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小。
莫非谢老有意在写作上想指点于我?因为我写书话亦时涉前人。
老姜的文字就是如此,少雕琢,平淡朴实,却借一段故事,谈学问与写作的关系,耐人寻味。
我与老姜同住在一个大院,他的藏书就成了“强大后盾”,让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写文章,我缺少老书或者旧杂志,便打电话去询问。不出几天,他就会找出来让我去取。
在“沧桑看云”专栏中,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田汉的《落叶》。多年后,老姜还记得此事。一次去看他,他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里面是他整理出来的与田汉相关的资料。多好的前辈,时时想着我写过的人物,清理资料时总会给我留下一些什么。这些文人情怀,时时温暖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