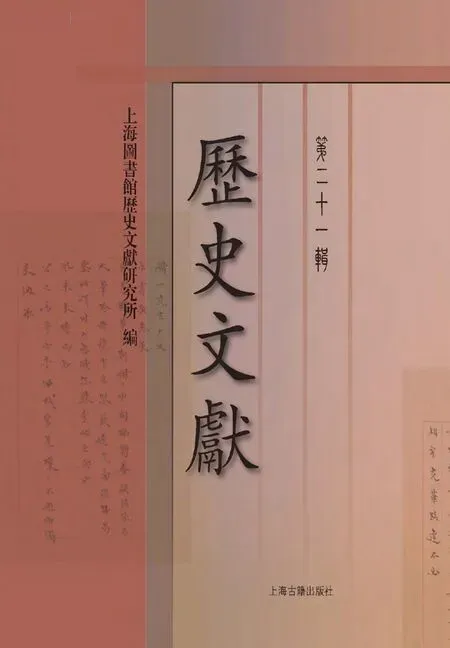《遠東時報》興衰小考
□ 徐錦華
1898年,通過“美西戰爭”,新興的美利堅合衆國從歐洲老牌列强西班牙手中獲得了加勒比海的完全控制權,還以2 000萬美元的“代價”拿到了西太平洋上的菲律賓地區的統治權。這場戰爭似乎印證了美國人的“昭昭天命”將通過太平洋繼續擴張到整個亞太地區。菲律賓和關島作爲美國在西太平洋重要基地的歷史,也由此展開。經過三年時間的鎮壓,美國清除之前在菲律賓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起義軍勢力,正式建立了對菲律賓長達40多年的統治。1904年,一位35歲正值壯年的前美國隨軍記者,在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的戈伊蒂廣場(Plaza de Goiti)的麥卡洛大樓(McCullough Building)租借了辦公室,①創辦了《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雜誌。
這位後來被稱爲李亞(George Bronson Rea)的美國記者,②在發刊詞中宣稱:“欲知一人,先觀其友;欲知一報,觀其訂户及廣告品味……《遠東時報》將是遠東地區毫無爭議的最佳報刊,無論是内容、紙張還是發行管道……我們發行量衹有3 000份,③但這3 000位訂户都將是最佳人選。”④這段文字多少有自我吹噓的成分在内。但當時這位發行人兼主編對於菲律賓和東亞的良好發展前景的預期也在發刊詞中展露無遺:“接下來將是菲律賓和東亞大發展的時代了。遠東已經從數個世紀的睡夢中驚醒,火車機車的汽笛撕鳴、有軌電車的鈴鐺振動、工業機械嗡嗡作響,這些將快速驅趕走長久以來對西方觀念的偏見。”在描繪了遠東從城市到港口、鄉村一派忙碌的建設與發展景象後,李亞號召道:“對菲律賓和遠東的鐵路、工程、金融和貿易感興趣麼?快訂閲《遠東時報》!尋找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擴展自己業務的機會麼?想要尋找遠東的買家麼?想要爲自己的機器和産品尋找潛在的客户麼?快在《遠東時報》上刊登廣告!”這樣的發刊詞,不難讓人聯想到19世紀美國西部“邊疆地區”充滿活力、機遇和挑戰並存的環境。也許在成長於美國南北戰爭後的李亞眼中,遠東正是下一個“邊疆”所在。
這是一個美國人眼中20世紀初的東亞,此時終結“不列顛和平”的“一戰”“二戰”尚未發生,美國也還没有從英國手中接過“海神三叉戟”。這是殖民帝國主義的頂峰,也幾乎没有人想到終點將至。此時的李亞猶如那些“西進運動”的前輩,將自己看作是“文明”與“進步”的代表,前往“蠻荒的邊疆”,試圖把“現代化”的福音傳遍世界各個角落。
“美、加、墨三國全年定價2.5美元,其他郵政聯盟加盟國全年定價3美元,每期零售價0.25美元。廣告費率歡迎來函接洽”。⑤1904年6月,《遠東時報》的創刊號發行,發行人兼主編的李亞在“《遠東時報》的方針”中强調:“這是一份商貿與工程雜誌,不偏向某一政治立場或者利益集團……我們不刊登冗長的政論、流言蜚語、幽默故事或者是私人軼事。我們的版面不受收買,我們將免費刊登遠東相關的信譽良好的商業新聞。我們的目標是整合諸多的工商業資訊,展示各類業務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希望不僅是遠東,也能爲歐美的資本和製造業提供機遇。”⑥
雜誌創刊號的内容,在發刊詞之後,是“《遠東時報》的方針”和一些菲律賓當地新聞,之後是配有多幅地圖和照片的主題文章,包括《馬尼拉的島嶼制冰工廠招標出售》、工程師主管(Engineer in Charge)凱斯(J.F. Case)撰寫的《新近核准的馬尼拉供水系統擴建計畫》、菲律賓農業局水稻專家(Rice Culturist Bureau of Agriculture, P.I.)布德羅(Wilfred J. Boudreau)撰寫的《現代水稻文化》、礦業局主管(Chief of Mining Bureau)麥卡斯基(H. D. McCaskey)撰寫的《布拉幹省的昂阿特鐵礦區》。還有按照不同行業門類劃分的短訊與新聞,共100多條:“遠東建築新聞”(包括新的馬尼拉政府大樓的資訊)、“遠東鐵路資訊”(包括泰國、日本、菲律賓、中國、澳大利亞、馬來半島、朝鮮等地鐵路相關簡訊)、“遠東礦業評論”(菲律賓、馬來亞半島、斯里蘭卡、日本等地的礦業簡訊)、“遠東建設與工程新聞”(包括上海工程師與建築師協會年會資訊在内,涉及港口與海運、橋樑、有軌電車、個人資訊、電話與電報、道路、建築等諸多方面的新聞簡報與招標資訊)、“遠東金融評論”(銀行相關新聞、各類投融資專案資訊、公司財務狀況等)、“遠東及新加坡證券市場行情”、“工業速記”(製造業、工業相關新聞)、“遠東市場行情”(菲律賓、香港、上海、三藩市等地的現貨、期貨行情),以及各類“公告及聲明”和“航班資訊”、補白。
這些新聞報導與資訊,有的出自當時菲律賓官方機構人士的手筆,相信和李亞在菲律賓的人脈及活動有關;少量是從其他報刊轉載的消息,更多的則是没有署名的新聞消息以及一些類似廣告的招投標資訊與業務需求。在48頁的篇幅中濃縮了大量的工商業、金融、礦産資訊,而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社論、政論,恰如“《遠東時報》的方針”所强調的,和雜誌的副標題一致,其是一本“商貿、工程與財經”(commerce, engineering, finance)雜誌。
然而,當日的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激流迭起,歐美新老列强之間、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還有獨立或半獨立的亞太國家嘗試或被迫進入全球化/現代化的大潮中帶來的各種衝突。這些孕育着各類機遇,但不僅僅是屬於商人、企業家、投資者的,更是屬於政客、投機者、冒險家的。
就在《遠東時報》創刊的同時,日俄戰爭正在中國東北地區酣戰不已。雖然在前幾期中都没有直接的相關報導,但《遠東時報》的編輯部顯然是一直在關注戰爭的動向。在1904年12月號,題爲《20世紀的亞洲》的編者按,⑦認爲日本由於“過去三十年中明顯的進步”,已經“可以與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媲美”,是“現代亞洲的代表”,這一切“可以用最近日俄戰爭中,日本取得的勝利作爲證據”。《遠東時報》和它的主編李亞明確提出,亞洲今後將是一個“迅速發展的、西方化的現代亞洲”。這段篇幅不小的編者按語,顯然已經跨越了創刊號上“衹談經濟,不談政治”的界線。這究竟是曾經以隨軍記者身份見證美國軍隊履行自己的“昭昭天命”的李亞的一貫想法,還是在現代化大潮的裹挾中身不由己地改變初心,現在已經很難斷定了。但無論如何,《遠東時報》的基調和它原本宣稱的“純粹”雜誌已經開始漸行漸遠了。
在接下來的雜誌上,李亞不斷在編者按語裏鼓吹自己的政治觀點: 建立一個“現代化的西式的亞洲”。同時也開始了《遠東時報》的業務擴張之旅。在1905年,雜誌社建立了中國辦事處,辦公室位於當時上海外灘5號大樓内。並且和别發洋行(Kelly & Walsh, Ltd.)等建立了代理關係,通過這些出版社的發行管道在上海、香港、天津、長崎、横濱、新加坡等地流通雜誌。同年内,中國辦事處又多次遷移地址: 九江路9號、北京路4號A座……到1906年,位於横濱的日本辦事處以及位於倫敦、三藩市的英、美辦事處先後設立。整個雜誌的業務擴張態勢不可謂不良好。就連廣告業務也是明顯增加,雜誌前後的廣告頁從第一卷的寥寥數版增加到30多版。1906年的《北華案頭行名録》(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已經刊登有《遠東時報》上海辦事處的資訊,中國業務負責人爲米德(C. W. Mead)。⑧
隨着業務的擴張,《遠東時報》上的專欄文章、通信簡訊越來越多地出現中國、日本、朝鮮等東北亞地區相關的内容,尤其是在晚清最後幾年的動盪中。因此在1911年11月號上,辛亥革命成爲頭條報導,袁世凱成爲題圖人物可謂是毫不令人意外。這一期雜誌用16版的篇幅配以大量清晰的人物照片,詳細報導了中國發生的事件。編輯部認爲“多年以來歐美一直期待的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覺醒”,而現在正是轉變發生的時刻。此後連續數期,對中國的政治局勢,雜誌都以“The Chinese Situation”爲題做了專門報導。1912年4月號上,李亞署名發表了《革命的金融史——通貨的威力》一文,⑨以40多版的篇幅,撰寫了他個人對辛亥革命從爆發到結束的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考察。
就在同一年,《遠東時報》雜誌社的總部從菲律賓遷往了中國上海。不管是對中國持續關注的熱情導致了這次遷移,還是從辛亥革命的劇烈震動中感受到了“昭昭天命”使然,李亞本人也隨同雜誌社一起在上海紮根。
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的中文報刊上也不時出現明確是從《遠東時報》轉譯的文章: 《協和報》《中華實業界》《鐵路協會會報》《直隸實業雜誌》《國貨月報》《時兆月報》……在1915—1930年間,有200多篇此類的文章,大多是和中國的工商業情況相關的報導。可以看出,此時《遠東時報》在中國的影響力正在逐步擴大。雜誌的發行地從最初的“Manila”到“Manila-Shanghai”再變爲“Shanghai”,這也説明,整個雜誌社的重心已經從南向北遷移,正緊追着20世紀東亞全球化的步伐,尋找“現代化的亞洲”建立的時代脈搏。
在1919年3月號和6月號的《遠東時報》上,刊登了有孫中山英文簽名署名的文章《中國的國際化發展計畫》(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這似乎説明《遠東時報》與孫中山之間有着某種程度的聯繫。事實上,早在1912年,李亞就曾寫信給孫中山,希望能將《遠東時報》變爲由孫出資支持的刊物。而就在同年,一位原澳大利亞記者——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加入了《遠東時報》的團隊。這位原澳大利亞記者1902年以悉尼《每日電訊報》通訊員身份來遠東,後歷任《德臣報》《先驅報》駐滬記者,還曾擔任過孫中山的私人顧問。他的加入對於《遠東時報》的發展,顯然是頗有助力的,1912年4月號上刊登的《中國的革命》一文的作者就很有可能是端納,也因此,他很快就成爲雜誌的主編,在雜誌社内的地位僅次於李亞。李亞也最終獲得了孫中山的認可,在孫中山建立的鐵路總公司中擔任了顧問。1919年前後,喬治·索克思(George Sokolsky),一位美籍俄裔猶太記者,在這一時期和孫中山交往甚多,也逐步加入《遠東時報》的工作團隊中。看起來,李亞要把《遠東時報》變成孫中山支持的刊物的想法正在逐步實現。
可是,20世紀東亞的歷史進程是如此的詭譎,一方面,《遠東時報》上不斷刊登關於孫中山和他的政治、經濟思想的報導: 1923年5月號的封二,配以孫中山肖像畫的短文《孫博士向世界的宣告》;1924年1月號第9頁,《孫和關税》闡述孫中山對於關税和建立中國統一政府的關係的看法;1926年4月號第145、146頁,索克思的署名文章《孫逸仙主義》;1929年3月號刊發了署名“吕彦直”(Lu Y. C.)的《紀念孫逸仙》……在孫中山去世時,《遠東時報》上《孫逸仙: 中華民國首任總統,革命家與愛國者,古老民族現代化運動的領袖》一文,給予了孫中山高度評價,認爲他是“過去三十年裏中國事務中表現卓越的人”,並且“有一套清楚的關於讓政府組織、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現代化的建設性計畫”,“任何一個想要修正中國的外交關係、繁榮商貿和交通,讓中國擺脱混亂的領導,都必須遵循孫所指定的原則”。另一方面,在1920年前後,端納和李亞發生了不合,而不合的原因在於,端納認爲《遠東時報》對於日本的態度過於親密。考慮到從《遠東時報》創刊起,包括三井物産公司這樣的大財閥在内的日本公司是雜誌重要的廣告收入來源,以及在日俄戰爭期間,李亞流露出的對“可以代表現代化亞洲的日本”的好感。可以説李亞及《遠東時報》的親日立場是有其現實原因的,同時也反映了李亞一貫的思想: 20世紀的亞洲應當是一個現代化的亞洲,如果哪股勢力能夠展現出符合他心目中的“現代化”標準,他就願意支持誰,孫中山也好,日本也好,也許在李亞看來,都是能夠代表這種趨勢的。然而,端納對日本卻有着更爲複雜的認識,也許他已經從“一戰”的陰影中感受到了“現代化”對人類社會帶來的暴戾一面,也許是他在“二十一條”泄漏給媒體的事件中的經歷,讓他對日本的擴張野心與迷夢有所警惕,他最終選擇了離開《遠東時報》雜誌。
之後更换的新主編没能長期任職,最終李亞自己又一肩挑起主編與發行人的雙重職責。1912年遷移到上海後,《遠東時報》上政論性的專題文章數量就明顯上升,以1925年上半年爲例,1月號目録有27篇文章,前9篇都是政論性的文章;2月號目録有21篇文章,有6篇屬於政論性文章;3月號目録19篇文章,4篇政論性文章;4月號22篇文章,6篇政論性文章;5月號28篇文章,6篇政論性文章;6—7月合號爲一期,目録47篇文章,政論性的文章4篇,但超過2/3的文章是關於日本的,介紹日本在市政建設、工程技術、鐵路發展、工業領域取得的各類成就,猶如一期“日本專號”。同時,以往那類豐富的市場訊息、專案短訊則開始從《遠東時報》上逐漸消失。
當然,與此同時,《遠東時報》依舊保留了不少高品質的經貿、工程、金融類的專題報導,尤其是鐵路、礦産、建築等領域的報導,專題文章圖文並茂,内容翔實。李亞、端納、索克思等人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對於提供此類資訊無疑是非常有説明力的。在建築方面,無論是上海、香港,還是東京、横濱、馬尼拉等,舉凡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重大建築工程完工,都會有相關的資訊乃至專題報導,配以精美的外立面圖、内景圖,甚至是建築設計圖。比如1924年9月號上,介紹翻修後的外灘24號横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的大樓,雜誌稱其爲“外灘建築皇冠上的明珠”。而對於1930年代,國民政府在江灣實行的大上海計畫中的幾幢標志性建築,以及新住宅區的規劃,雜誌都有相應的文章。
然而,隨着世界經濟形勢的日益惡化,《遠東時報》上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市場不景氣的糟糕資訊。另一方面,它的政論性文章的立場也越發親日。在1926年11月號上,李亞發表署名文章,批駁抵制日貨運動;1929年,又發文指責英國破壞英日同盟;李亞一直鼓吹美日合作,攜手建設“現代化的亞洲”……1930年,《遠東時報》雜誌社的編輯部搬入了横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大樓内。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發生,《遠東時報》的相關報導或明或暗地都在爲日本開脱責任,如此明顯的傾向性,當時的中國輿論也不會看漏。1935年的《報學季刊》上,一篇補白性質的短文《偏袒日本的〈遠東時報〉》,直接抨擊《遠東時報》,認爲“該報的編輯政策是反對早日取消在華之領事裁判權,並主張美日兩國在遠東方面之合作。美人在華所辦的報紙,要算該報是很明顯的偏袒日本了”。一些後來的研究著作,比如《近代在華文化機構綜録》,認爲《遠東時報》此時已經被日本收買,淪爲日本在華的“宣傳工具”。
僞滿洲國成立後,李亞走得更遠,出任了僞滿洲國外交部的顧問。1933年7月號上,李亞撰寫了“滿洲國真相”一文,爲僞滿洲國辯護。到了1935年,他又出版《滿洲國真相》一書,在書的前言中,“作爲一個在東亞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人;作爲因爲同情那些古巴革命中遭受痛苦的人們而從工程師變爲記者的人”,李亞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認爲他關於東亞的經驗總結,乃是“美國爲首的西方對東亞毫無章法的態度是導致東亞問題的原因”,他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的政治立場——“滿洲國的支持者”。他認爲“滿洲國的獨立”,使其擺脱了當時中國其他部分的混亂與内戰;“滿洲國被指控是日本的傀儡”,但在李亞看來,日本是“滿洲這塊土地獲得幸福的唯一機會”。隨後,在書中,李亞將“滿洲國”描述爲日本在遠東抵抗蘇聯和“共産主義”的橋頭堡,還繼續提出,希望美國能夠和日本合作,維護這一橋頭堡的存在。這位曾經義氣奮發,和美國軍隊一起前往亞洲實現“昭昭天命”的隨軍記者,此時已經是一位垂暮老者。他曾爲日俄戰爭中日本/亞洲擊敗沙俄/歐洲而震動,也曾爲中國的辛亥革命鼓吹,還堅信“現代化的亞洲”,游走於各色勢力之間,但最後選擇了日本。1936年去世的李亞大概未曾料想到,五年之後,他眼中的“現代化亞洲”的代表日本,將會和他負有“昭昭天命”的母國——美國之間爆發爭奪太平洋霸權的戰爭。如同40多年前美國從西班牙手中以戰爭的方式獲得殖民地菲律賓,隨後又殘酷鎮壓菲律賓的人民起義。“旭日帝國”的日本打着“東亞共榮”的旗號,宣稱要從“英美鬼畜”手中“解放”倍受壓迫的亞洲人民,實則給亞洲帶來了衆多的暴行與蹂躪。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還是禁不住想要知道,如果李亞活到1941年以後,他又將如何解釋這場戰爭,將如何理解自己信念裏的“20世紀的現代化亞洲”不單有轟鳴的機器、延伸的鐵路與繁榮的市場,更有南京大屠殺、巴丹死亡行軍、“饑餓地獄”的瓜島、殘酷血腥的硫磺島……
李亞去世了,《遠東時報》還在出版,接任負責人的是之前長期擔任副主編的拉瓦爾(C.J. Laval),此後,《遠東時報》徹底成爲日本宣傳機構的一環,在掌控現代化的輿論導向上,日本學習西方的速度也同樣迅速。早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就注重營造自身在外國媒體的形象,同時嚴格掌控國内媒體的報導口徑與尺度。在“二戰”中,活躍的“筆部隊”更是炮製了一篇篇鼓吹“皇皇戰績”的報導,營造出全民狂熱的氛圍。從1942年起,雖然《遠東時報》的雜誌開本縮小了一號,但在文章中對於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辯解、對於美化日軍占領區下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文章卻增加了許多。館藏的1943年1月號也許也是最後一期,封面照是整齊行軍的日本97式中型坦克的編隊,刊物裏充斥着《過去一年日本帝國海軍的輝煌戰績》《重慶政府的財政瀕臨崩潰》這樣的文章。然而這種粉飾太平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此時太平洋上的戰爭局勢正向着日本失敗的局面演進: 中途島戰役的失敗、瓜島的丢失……“定價上海地區中儲券20元,其他地區日本軍用票20元”。没有向其他日本控制的媒體那樣,在戰爭的末期聲嘶力竭的叫囂“一億玉碎”,而是戛然而止,對《遠東時報》而言也許不是最壞的結局。
另外兩位在《遠東時報》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人物: 澳大利亞人端納,在離開《遠東時報》雜誌社後,在北洋政府、張學良、蔣介石等處擔任顧問類職務,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協調,1938年因和宋美齡的衝突而離開中國。在東南亞被日軍俘虜,被解救後,於1946年在上海去世,享年61歲。索克思則在1935離開中國回到美國,經營報紙和電臺,以社會活動家、評論家的身份活躍到他69歲的人生盡頭,在1962年因心臟病去世。他生前是麥卡錫的堅定支持者,終身反對共産主義和蘇聯。
李亞、端納、索克思,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與故事,《遠東時報》成爲他們一個集合點。在將近40年的時間裏,這份雜誌的興衰與相關人物的經歷,也許不如其他同時期發生在西太平洋的故事那樣傳奇,但也足以成爲洶湧、詭譎的歷史浪潮中值得留意的一滴。誕生於交接西太平洋霸權的美西戰爭之後的菲律賓;終結於“二戰”,一次同樣血腥的轉移霸權嘗試中途的日本;與孫中山、蔣介石、張學良、宋子文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遠東時報》的命運,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講述。
即使拋開這本雜誌紛繁複雜的幕後故事,單純作爲一個經濟史、物流史、金融史、新聞史的原始史料文獻,《遠東時報》也有着相當重要的價值。比如廣告,不同於其他面向社會大衆的雜誌的廣告往往側重日常生活用品,《遠東時報》上每期少則數條,多則上百條的廣告,很大一部分是生産資料、生産機械、金融銀行方面的。造船業、機械製造業、火車製造業、建築業乃至軍火,從中可以發現,在20世紀早期有哪些相關領域的廠商試圖進入或者開始重視亞洲市場。而每月連續的期貨、股票行情資訊,可以和其他來源的相關資料進行互補、對比,從而更深入地瞭解當時西太平地區的經濟、金融的整體發展趨勢。鐵路、航運方面的文章、報導,則是反映相關領域在相應歷史時期進展的一手文獻。建築方面的圖片、圖紙,對於研究相關的老建築有所裨益。事實上,我們很欣喜地看到,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注意到這份雜誌。希望這次的影印出版,能夠讓更多有需要的人更方便地使用《遠東時報》,我們也期待大家能從中發掘中更多的歷史資訊,還原更多的歷史現場。
(作者單位: 上海圖書館)
① 創刊時的雜誌地址,參見Far Eastern Review (Vol.1, No.1, p.4)的出版資訊。
② 此人生平,還可參見《上海名人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在1935年的《報學季刊》第1卷第2期第55頁上的《偏袒日本的〈遠東時報〉》一文中稱,當時該刊物每月銷售數約6 000份。
④ 發刊詞,FarEasternReview, Vol.1, No.1, p.1。
⑤ 同注①。
⑥ The “Far Eastern Review” its policy,FarEasternReview, Vol.1, No.1, p.4.
⑦ Twentieth Century Asia,FarEasternReview, Vol.1, No.7, pp.10-11.
⑧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1906, p.54.
⑨ The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The Power of Money,FarEasternReview, Vol.8, No.11, pp.33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