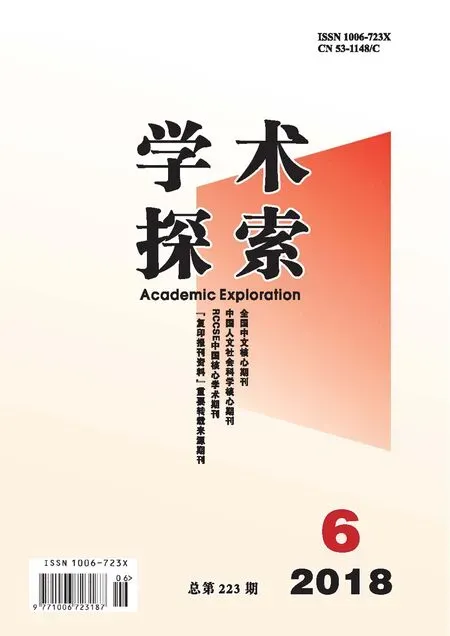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
吴 凯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美与道德是天然的盟友,而非你死我活的劲敌。无论是康德先验体系中的“美是道德的象征”,[1](P201)还是黑格尔所强调的脱离一切社会关系而超然存在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P142)我们均能在先贤大师那里寻得美与道德的相融之处。美与道德面向的是不同的世界,“一个领域只是把我们与各种意象,即各种纯粹的心灵创造联系起来,另一个领域则使我们与生活世界产生联系”。[3](P261)若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美与道德的相融之处大抵给我们展现的是:面向自我的道德养成和面向社会的审美化改造。面向自我的道德养成既有对个体在道德养成中的自我反思与精神重塑,也有对当前道德教育负效、无效、低效的解构与重构。面向社会的审美化改造则是对“解析道德教育的时代困境”[4]的回应,是对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尝试性探索,以期通过审美化改造来重现道德教育的审美特性、审美意味和审美价值。正所谓,以美载道,以德彰美。
道德教育是真、善、美的统一。真启迪我们的心智,善导引我们走向美好生活,美则教会我们以何种态度去观察、体验和评判这一过程。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并非简单地将道德教育置于审美原则之中,而是试图通过个体在意象世界的审美体验,将严肃、刻板、生硬的道德教育融于欢快、生动、活泼的审美化改造之中,激活个体自我创生道德教育的审美活力,打通道德教育通往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审美之路,以此摆脱外界“对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怀疑”。[5]
一、道德教育的审美遮蔽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境,讲求的是和谐有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境界,是天与人、象与意、形与神、用与美的统一。道德教育的审美遮蔽,主要是由道德教育中美与善的相对化倾向所造成的,这其中既有人们急于摆脱道德教育负效、无效、低效困境的功利之心,也有来自人们对道德教育工具之美的精神饥渴和审美狂热。不管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道德教育都应是美的,而且也只有通过美的体验和彰显,道德教育方能蕴情契形。以美载道,道德教育可以有力促进主体道德人格的精神觉解。“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6](P158)王国维一句简单的“入”与“出”,就真切地道出了道德教育走向审美之境的玄妙与诀窍。“入乎其内”,就是说对道德教育要深入观察、体会、领悟和了解,要对道德教育的本质内涵进行深刻理解和运思。“入”是对道德教育的理性审视和思考,是人观物的过程,也是“立象”的过程。“出乎其外”,则是说对道德教育要“超乎象外”,在静观的基础上实现远观,要以超越常人之视界来达成对主体道德人格的精神超越和审美境界。“出”是对道德教育的感性把握,是人观情的体现,也是“尽意”的表达。“入”和“出”的关系,生动地说明了道德教育审美化改造的基本路由,也间接地指出了道德教育审美遮蔽的缘由所在。
道德教育的审美遮蔽,表达的是对当前道德教育美与善相对化倾向的担忧。面对道德教育时代困境的“阵痛”,人们企图通过美感形式来实现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意图顺利解决道德教育的有效性问题。然而,“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检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被抓到手的艺术形式”,[7](P59)这种企图通过艺术“包装”来实现道德教育审美化改造的努力,究竟是道德教育对审美文化的理性渴求还是感性狂热?当大家无处不谈美,无美而不谈时,我们在美中还能看到什么,美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当审美沦为拯救感性沉沦大众的“治病良方”之时,审美还有多少形上意义可言?这种审美倾向,所要不断表现的并非是主体道德人格的精神觉解和自由人格的塑造,而是以功利化和工具化的心态,企图实现自我需要的满足,以此达到娱乐人生的目的。在这种审美冲动的促使下,审美只会给道德教育带来片刻的欢娱,而不能彻底解析道德教育持续“阵痛”的病症所在,也无法将审美真正融于道德教育全过程,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也只能最终沦为无意义的行动。本是“借船出海”,不料却因“娱乐至死”的审美狂热,道德教育也终将伴随着漫无目的审美“扩张”,再次隔断自己走向美善共生、相融的审美之境。这实则是将审美彻底矮化和工具化的表现,“审美向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实现的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审美精神,而是生发出一种感性崇拜和娱乐至上的追求”。[8]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道德教育要时刻警惕一切美感形式的审美化改造,对审美抱着拒斥的态度呢?当然不是!
审美可以赋予道德教育以情感温度,将理性的道德教育目的感性化,严肃的道德教育过程愉悦化,抽象的道德教育内容形象化,僵硬的道德教育方法生动化,并把理性融于其中,理性之中有感性,感性之中有理性,理性和感性始终处于和谐有序状态。在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中,美善分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化区分标准和导入机制。在导入美的过程中,过于看重美的形式化内容,盲目的追求感官刺激和视觉享受,以至于一些带有低级趣味的审美冲动涌入其中,这虽然满足了个人的审美欲求,但却与道德教育的公共理性和审美理想背道而驰。道德教育审美化改造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理性之“思”与感性之“畅”统一起来,在导向道德教育本真存在的同时,以有限的个人存在走向无限的自我超越和实现,“这样的自我实现,既是最高的美也是最高的善,既是审美意识,也是道德意识,既有审美愉悦感也有道德责任感。人生的意义也就在此”。[9](P103)近年来,网上频频曝光的教师带学生在KTV上课,穿龙袍讲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因为对部分道德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如何促进主体道德人格觉解和审美境界的提高,而是更看重暂时的课堂抬头率,片面追求以直观的表达、欢娱的气氛、娱乐的形象来掌控课堂,并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这种泛化形式的审美化改造,对合理解决道德教育有效性问题于事无补。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对道德教育本真存在的意义追问和审美期待,如果失去了对主体道德人格觉解和审美境界提高的关注,道德教育也就失去了审美的意味和空间,留下的只是片刻的欢娱和仅仅止于形式的美的表达。
审美虽然是人的感性把握,但正是这种感性把握却能给我们带来别样的趣味,拉近我们同客观世界的距离,导引我们以自然平和的心态去观察、发现、体验客观世界之美。此时,美就不再作为抽象意义上的概念而存在,它成了客观世界映射在我们理念中的美的想象、体验和表达,它可作为我们悦享生命活动的具体化的理念,可以同我们对话、交流和互动,并以较为直观的方式把握我们、激励我们、启迪我们、感动我们、愉悦我们。
道德教育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演绎和坐而论道,它是理性化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道德教育既有理论的训导,又有实践调适,它具体指向主体道德人格的升华,是一种持续性的道德养成和精神解放。审美则较为感性,它强调人的心灵解放和精神愉悦,渴望的是对客观世界困扰精神生活的超越,即摆脱外在客观世界的束缚而走向内在的精神超越,然而“审美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存现实,并不能使生活的渴望真正实现。所以审美的‘畅适’只是心理的,而不是实际的;只是虚幻的,而不是现实的;因此它也只能是瞬间的”。[10](P19)以此观之,道德教育与审美似乎并无存在通约的可能。一个是理性的道德养成,一个是感性的精神超越;一个是持续性的精神解放,一个是瞬间的心理畅适。正是这种偏执化的思路困扰着我们,给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设置了诸多蔽障,令道德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常常陷入二元对立的两难境地,以致有学者倡导建立一种“审美人格的实现”[11](P34)的德育美学观,试图探寻道德教育的审美空间,实现道德教育的美善共生与“情”“理”合一。
二、道德教育的审美期待
清初诗论家叶燮在美学领域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即“理”“事”“情”学说,“‘理’,就是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事’,就是客观事物运动的过程;‘情’,就是客观事物运动的感性情状和‘自得之趣’”。[12](P497)“情”“理”合一是道德教育的审美期待。具体而言,“情”是道德教育自由人格的象征,是道德教育审美体现的形上追求;“理”是道德教育普遍之善的意义追问,是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情”“理”合一表征着主体道德人格的审美追求,衍射着道德教育美善共生的灿烂之光。“情”“理”合一意味着道德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要把正确反映道德教育之“理”的“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能把道德教育之“理”简单地视为概念归纳、演绎的注脚,而应在“理”的基础上对“情”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展开审美追问,并灌注以美的情感、意味和想象。整体而言,道德教育的审美期待分别赋予“情”“理”以一定的道德想象和审美体验。“情”的道德想象不仅要全面彰显自我境界超越的愉悦体验,还要积极促成主体道德人格的实践养成。“理”的审美体验不仅要正确揭示道德教育的运动规律,还要赋予道德教育以审美的意味、精神和价值。
道德教育之“情”并不是对“理”的基础性地位的排斥和否定,而是在正确反映“理”之感性情状的前提下,以一种特定方式对之进行的审美表达与建构。“情”具有建构性的审美意味,它使我们注意一些往往在道德教育中容易引起人们道德想象的情感性力量。“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二者密切相关。人的情绪状态影响着他的全部活动。”[13](P434)道德教育之“情”的情感性力量使我们的审美体验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并统一和服务于主体道德人格觉解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由“情”所建构和传达的具有审美意味的道德想象,在特定情况下服务于建立和支撑道德王国的永久性构筑。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之“情”除了要充分阐释“理”的规律性问题之外,还要通过深层次的情感投入和表达,为道德教育的诗性之思和诗意表达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感价值,并最终获得具有审美价值的道德认同,达到“情”“理”合一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德教育之“情”就赋予了道德教育以审美意味,并最终在道德王国的永久性构筑中,以深度的情绪感染、情感认同影响着主体道德人格觉解和自我境界超越。“情”是由“理”出发而进行的审美思考。它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道德教育之“理”如何彰显其“情”的审美意味,它面对的一个难题则是道德教育如何处理“情”“理”之间的内在张力。由“情”所引发的问题和难题,则需要我们在道德教育“情”“理”之辨中深刻把握道德教育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旨归。“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它是活的善,这活的善在自我意识中具有它的知识和意志,通过自我意识的行动而达到它的现实性。”[14](P187)黑格尔所强调的伦理是从社会、关系、秩序的维度上进行理解的,是一种实体的而非抽象的社会伦理。而道德教育之“情”就是要在对“理”进行审美建构的同时,通过建立一种具有普遍规定性的导入机制和转换机制,将停留在自我审美体验层面的善,化约为能够统摄道德共同体的社会伦理。可以说,道德教育之“情”是在审美体验和自我超越层面对“理”的意义再阐释,它具体指向了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体验。
道德教育之“理”除了要正确揭示道德教育的运动规律之外,还要对道德教育展开本体反思和意义追问。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主体道德人格的觉解,它着眼于人的生活实践和道德养成,是一个不断完成的过程。道德教育之“理”包含着对普遍性善的审美观照和诗性运思,旨在通过道德教育的情感表达、深化、认同来增进人们的审美体验,使人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获得真实、生动、优美、独到的审美享受,从而达到主体人格的道德养成和自我超越的目的。同时,“情”“理”合一也规定了“理”应致力于对道德教育的诗性追求,在对道德王国的诗意阐释和理性构筑中,实现人们对道德王国的整体把握、意义分析和审美享受,并将其作为自我审美沉思的对象,逐步增强人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正如尼布尔所言,“我们理性的发展程度越高,我们就越能够正确地评价其他生命的需要,就越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动机与冲动的真正性质,就越能够协调产生于我们自己生命的冲动与产生于社会的冲动之间的相互冲突,就越能够选择有效的方法去实现我们所赞许的目的”。[15](P17)可以说,道德教育之“理”所倡导和构筑的并非是单个人的道德王国,而是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社会共同体的道德王国。对道德教育之“理”的探求,意味着道德教育的终极意义并不能满足于对道德教育规律的解释,以及对普遍性善的建立,而是旨在通过情感关联、意义发生和审美超越,来实现具有审美期待性质的道德王国的永久性构筑。这不是本能的、低级的、简单的探求,而是具有审美意味、审美精神、审美价值的艺术化探求。因为“情”“理”合一的道德教育,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对道德王国诗性之思中实现道德教育象与意、思与诗的同频共振。
道德教育的“情”“理”合一,是道德教育本真之善走向审美之境的唤醒与融合。道德教育虽是对主体道德人格的觉解,但从更为重要的价值层面而言,“情”是对“理”的诗性思考,“思考的真实在于,它是美好人性和理想社会的‘前显现’,借‘思’来展现将成为现实的东西,而这东西又要超过思考本身”。[16](P10)因此可以说,道德教育之“情”既内含着对“理”的审美之思和诗意阐释,也在“情”的陶冶和传递过程中不断升华着“理”,使“理”超越其本然的存在,并最终上升到自我超越的审美之境。
三、 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
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是一种具有情感意味、超越性质和审美活力的改造活动,它并非是道德教育的审美“变形”,而是对道德教育如何才能获得美感形式、体现审美特性、彰显审美价值的回答。道德教育审美化改造的途径有多种,本文不拟对构建何种可供操作的途径进行深入讨论,而是对途径的选择条件做出相应的思考与规范。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有限的道德教育实践要走向无限的崇高追求;其二,道德教育的“自身目的”要转向道德教育的“全面目的”;其三,道德教育要以有限的在场显现无限的不在场。
人是有限的生命存在,生命的有限直接决定了实践的有限,但这种有限并不是人止步于实践的借口,人应该在有限的实践中去追求无限,这种无限即是对有限自我的自由超越和境界提升。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首要任务就是由有限的道德教育实践走向无限的崇高追求。有限的道德教育实践受到人的德性、原则、规范、理性的牵制和引导,无限的崇高追求则是人在可见、可听、可感、可触的道德教育实践中的感性体验。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并不能只靠有限的实践来完成,它还需要无限的崇高追求来赋予道德教育以审美意味、审美精神和审美价值。无限的崇高追求既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审美体验,它可以突破年龄、性别、肤色、地域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赋予人以内在生命的显现、自由意志的勃发和人生境界的超越。无限的崇高追求规定了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应是突破自我、走向社会和面向生活的,要求它是对人的生命直观和自我超越,而不是仅仅在学校、课堂、书斋里进行抽象的理论讲授和概念演绎。只有赋予道德教育以最直观的形式,让其在鲜活、生动、形象的实践中获取厚重、优美、神圣的审美体验,人们才能深刻洞见道德教育的本真性与道德自我的自由性。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不是由被动的知觉构成,而是一种知觉化的方式和过程”,[17](P192)这种“知觉化的方式和过程”不能根据感性的审美体验来获得,它必须依靠客观的、现实的、理性的实践活动来进行,并且还要赋予这种实践活动以充分的能动性、创造性、自由性。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是建构着的创造性的活动,并且只有依靠这种创造性活动,道德教育才能突破有限而达到无限,我们才能发现道德教育的优美与崇高。在道德教育从有限走向无限的过程中,道德教育的本真存在和自由境界也就自然地获得了美感形式,它的审美特性、审美精神、审美价值也就得到了彰显,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也就成为现实。
道德教育总是与一定的目的相伴随,“但是应当看到,目的之中也有区别。它有时是实现活动本身,有时是活动以外的产品。当目的是活动以外的产品时,产品就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18](P2)道德教育应着眼于它本身以外的目的,道德教育本身以外的目的更能赋予其价值,更有利于道德教育获得美感形式,彰显其审美价值。一般而言,道德教育包含着对其“自身目的”的理解,但道德教育“自身目的”并非是其最终目标,它理应将实现“全面目的”作为其最终目的,并在“全面目的”的实现中完成自身的审美化改造。“自身目的”是道德教育以“属人”方式去建构“成人”生活的前提,是人德性养成和道德实践的手段,具有主体道德人格的特征。“自身目的”是道德教育的具体目的,但不是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道德教育最高目的的实现,必须依靠“全面目的”的实现来完成。“全面目的”既可以理解为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也可以理解为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全面目的”并不是将道德教育的“成人”问题作为目的,而是在对“成人”问题的理解中,将主体道德人格的觉解全面融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之中,在道德共同体中实现对道德自我的实践养成,从而为建构一种可能的良善生活提供发展思路,并将其视为道德教育的“全面目的”。“全面目的”是对道德教育发展现状的检视和反思,是道德教育生动实践的形象表现,它寻求的是对道德教育“自身目的”的发展完善,它彰显的是道德自我的自由超越,它表达的是良善生活的确定性寻求,它建构的是道德教育审美价值的实现。显然,“全面目的”高于“自身目的”,且超越了道德教育实践本身,正如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19](P45~46)因此,由“自身目的”走向“全面目的”,就使道德教育把注意力由“成人”问题提升到建构一种良善生活的意义上来,促使道德教育始终处于“完形”状态,而这也正赋予了道德教育以超越性的审美特性和价值,从而走向本真的存在。
纵然无限的崇高追求和“全面目的”的实现可以使道德教育趋向于审美的境界,但若缺乏相应的规范指导,不能摆脱低级审美趣味和审美功利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就会丧失对意义的直观能力。道德教育需要以有限的在场而走向无限的不在场,要超越道德教育语言、内容、方式、意义本身的可能限度,以“留白”的方式给道德教育留下塑“象”造“境”的可能空间,以此达到畅适和敞亮的审美境界。“留白”是中国书画创作中最高的审美境界。道德教育亦需要通过“留白”的方式来完成其审美化改造。道德教育的“留白”,不是道德教育价值目标的空场,而是在道德教育内容建构、语言表达、情感传递的过程中留下可供人想象的空间。这种想象不是无的放矢的空想、幻想和假想,而是包含着“普遍性概念于其自身”[20](P158)的对意蕴无穷的道德教育的创造性想象。同时,道德教育要想显现无限不在场的审美境界,还需要通过“召唤结构或召唤性”[21](P178~179)为人们参与道德教育的创造与再创造提供机会。从道德教育本身而言,这种创造与再创造其实就是以有限在场显现无限不在场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对道德教育内在结构、参与对象、表达方式等有限在场的超越;另一方面,它又指向了道德教育不可穷尽的意义想象与意境创造。道德教育的语言、内容、方式是有限的在场,但道德教育所蕴含和表达的意义、意象、境界却是无限的不在场。无限的不在场虽“不可描述”,但正是这种广阔的想象空间给道德教育带来了愉悦的审美体验。人们在其中可以超越有限的生命存在而走向无限的自我超越,道德教育也借助超越在场而走向具体的生活世界和生动的道德实践。无限的不在场,赋予了道德教育以新的视界和期待,使人们在超越有限中去探寻新的审美关系、审美体验、审美价值,并以此为道德教育创造一个可能的美好世界。这个美好世界,既是对道德教育情感的真挚流露,也是对道德教育意象的空间建构,更是对道德教育审美价值的实现。
审美化改造作为一种生动、直观、形象的创造性活动,其主要特征在于:审美化改造使道德教育的理性引导与人的感性体验统一起来,在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中激发人对自我有限存在的超越潜能,从根本上实现对意蕴无穷的道德教育的审美体验,抵达人生命存在的本源,通达人性能达的境界。审美化改造唤醒了人“改变世界”的精神力量,这其实也是对人在道德教育审美化改造中“自由意志”的彰显。“自由意志”本身就具有超越性的审美价值,它可为人解决道德教育面临的时代“阵痛”问题提供省察和反思的能力,燃起人对建构良善生活的自由渴望。审美化改造对道德教育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但是,审美化改造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准入、引导、转换和调节机制,最大限度地阻断功利的、娱乐的、低级的、盲目的、随性的、任意的行为对道德教育审美化改造的影响,为道德教育审美化改造营造纯净、清新、自由的审美环境,使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自信的态度、创造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道德教育的审美化改造之中,从而迈向自由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爱弥儿·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余玉花.解析道德教育的时代困境[J].伦理学研究,2008,(4).
[5]张康之.对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怀疑[J].学术界,2003,(4).
[6]王国维.人间词话[M].周公度,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8]王行,刘雨.当代审美精神的失落及其复归策略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9]张世英.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1]檀传宝.德育美学观[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1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3]孟昭兰.人类情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5]R.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16]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7]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伽达默尔.赞美理论[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0]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1]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