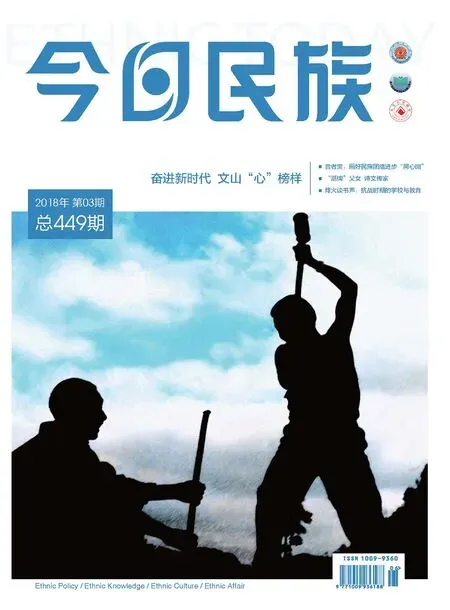盈江麻竹岭杆的董萨
□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熊思云

① 念鬼前的准备

② 分祭肉

③ 公房火塘

④ 农尚
清晨8点,景颇山上的草叶还带着露水,空气凉而刺骨。然而这个时候,麻竹岭杆举办“农尚”仪式的公房里已经升起了火烟。
一群老人围坐在活动室的火塘边,烧着昨晚没有吃完的稀饭和肉包,喝着用竹筒煮的茶水提神。此时,早相还未醒来,他是这次祭祀的董萨。火塘边的被窝,传出他沉重的呼吸声。昨晚,一场念鬼的仪式结束时已是半夜,于是他和其他参与的几个就在活动室睡了一晚。今天是祭祀“农尚”的第二天,也是最忙碌的一天,还有很多的鬼要念,很多仪式要完成。
这是2018年1月,笔者在盈江县卡场镇卡场村委会麻竹岭杆村见到的场景。这个靠近缅甸的景颇族山寨,近年来随着多种外来文化的涌入,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祭祀农尚
祭祀“农尚”是景颇村寨里的公共仪式,全村人都参与,地位十分重要。农尚,类似汉族的“官庙”,由一栋公房和周边的空场地组成,但狭义上,农尚也指承载了大部分祭祀活动的这栋房子。
农尚中平时供奉着天神、地神、水神、以及家堂神(山官祖先)的祭架。但在举办祭祀活动时,农尚(公房)前的空地,也搭建需要加祭的鬼神的祭架。祭架由竹子和茅草搭建,上面摆有若干小竹筒,不同竹筒代表不同的鬼神。
祭祀农尚,一般持续三天。第一天,是各项准备工作,第二天,正式祭祀。因为祭祀鬼神很多,每个鬼神都要祭祀,所以,第三天还要继续。
今天需要祭祀的鬼神就有水神、天神、口舌鬼“木让”、家堂神“载本瓦”、土地神“吉同”、风神“崩培”、破坏鬼“宁苏”和牲畜鬼“阿乌朗”。这些祭祀,由早相来主持。所需时间,短则10多分钟,长则两个小时。
传统上,祭祀农尚,每年两次。一次是播种前,向各种鬼神祈求关照,并许诺若得丰收,年底还有更丰厚的祭品;另一次就是春节前的笔者所见的这次,这是兑现之前的承诺,所以仪式似乎也更为热闹。
当然,村子里若有重大事情发生,也会增加祭祀。这样下来,祭祀农尚的次数,可能会超过一年两次。
不过,在麻竹岭杆,祭祀农尚活动,已经中断了3年。今年之所以祭祀,也是因为他们觉得中断太久,所以才有了笔者所见的场景。
尽管中断过,但一旦开启,这场活动,还是十分有人气。村子里多了很多人,一些外出的村民也赶回来参加。
早上9点,祭祀农尚的公房逐渐热闹起来。有的男人开始搭木桩,为杀牛做准备。还有的男人则用竹子制作祭祀用的器具……
董萨
董萨是整个仪式中的灵魂人物,是各种看似散乱的活动的中枢。
几天前,为了这次的祭祀活动,早相跟过去一样,在农尚附近进行过一次占卜。他把一根翠绿的竹子放在火上烤,烤到一定时间,竹子就会炸裂。然后,他观察炸开处纤维的形状,并由此推断,今年是否适合举办农尚的祭祀,以及祭祀中需要什么样的祭品。

① 丰收神祭架
早相是麻竹岭杆唯一的斋瓦(景颇族级别最高的大董萨),也是整个盈江县为数不多的斋瓦之一,因此,也是这一带的忙人,尤其在年底这段时间。
在景颇山上,从收完谷子到春节的这段时间,是各家各户念家堂鬼的高峰期。每到这个时候,景颇山上的董萨们,就过上了天天走村串寨的日子。早相从上个星期开始,已经连续祭祀了5场家堂鬼,他忙得只有在两场祭祀之间的空余时间才能回家一趟。前几天,早相家三女儿出嫁,在女儿嫁人的前一天,他还在卡场街做祭祀。
作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宗教职能者,董萨们的生活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有时候,哪怕家里有事,他们也要先帮别人完成。一年里头,他们在家的时间,比在外面的时间都要少。
今年58岁的早相,22岁时开始学习做董萨,那时正好是上世纪80年代初,民族民间文化、民间信仰,遭遇了外部带来的挫折后,又重新被接纳,活力复苏。
早相算是天赋比较好的那一类人,只学习了两年的时间,就出师了。此后,开始承担本村,以及附近村寨家庭或者公共的祭祀活动。并且,随着近些年来,老一辈董萨的相继去世,早相已经成了这一带仅存几个大董萨(斋瓦)之一,邀请他做仪式的,除了本地还有瑞丽市、陇川县。
在景颇山上,董萨是一份很特殊的职业。董萨帮别人家念经,通常有报酬,但这个报酬并不固定。通常,念一次家堂鬼,要花1到2天,而董萨会得到一些仪式中祭献过的肉,以及额度不等的现金。普通景颇家庭,有时只是象征性给几十块,但也偶尔有富裕人家,能给到几千甚至上万块。
不过,董萨作为沟通人与鬼神的中间者,他的劳动具有特殊性。帮景颇族的家庭去做各种仪式,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传统赋予的义务,很难拒绝,而那些景颇家庭付出的报酬,也通常被视为表达尊敬和感谢,而不是“劳动薪酬”。
在卡场镇这个片区,有很多资历深浅不一的董萨。董萨讲传承,早相有老师,而他在40岁后也开始带徒弟。如果有董萨忙不过来时,会请其他董萨,或者他的徒弟来帮忙。大型的仪式,从头到尾,那更少不了各董萨之间的分工协作。比如说,这次农尚的祭祀,需要祭祀的鬼神多达20多个,早相就从外面的村寨请了两个徒弟过来帮忙。早相20年前收徒至今,带出来的徒弟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楚。但目前,跟着他学的,还有40多个。

② 分祭肉

③ 祭肉

④ 颇具规模的纺织合作社 龙成鹏 摄
董萨的传承,现在依然是口耳相传的模式,没有专门的课堂或者课程,都是在共同参与某个仪式中传授。在这种传统模式下,一个董萨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的历练。先是在仪式上处理祭品,熟悉了各种流程之后,便从最简单的祭词开始念起,先是念诵鸡蛋干鱼之类的最基本的祭品,再到复杂一点的鸡、猪,直到难度最大的水牛。
成为董萨是一个漫长的学习和实践过程,随着资历的增长,到可以念太阳神木代时,就晋阶为大董萨(斋瓦)。这个过程,从学做董萨算起,需要几十年。早相,22岁学习念鬼到2014年,54岁时才成为斋瓦。以前斋瓦民间有认证体系,现在由政府颁发证书。
在景颇山上,要成为一个董萨有太多的门槛,用他们的话来讲,首先要“带点仙”,这样才能获得和神圣世界交流的资格。另外就是要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人,理解不了深奥的祭词。再一点就是要记性好,这样才能记住复杂和冗长的祭词。
一面是门槛很高,另一面是待遇很差——至少不能靠做董萨奔小康——因此,今天的年轻人,几乎都不太愿意去做董萨。早相的学生,最年轻的是三十多岁这一代,更年轻的90后就没有,传承环境跟早相二十多岁时显然大为不同。(在卡链村的葬礼上,笔者遇到一个17岁的少年董萨,他说在景颇山上,他这个年纪的人,学习做董萨的,几乎没有。)
更严峻的问题是,无论是早相家里的孩子,还是村子里的其他年轻人,对于董萨从事的各种传统祭祀,跟上一代比,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笔者观察,祭祀农尚时,年轻人尽管也依旧有敬畏,但这种敬畏,多是对传统和规则的敬畏,而不再是对仪式背后的鬼神的敬畏。
改变
董萨传承的困难,不止这些。
实际上,董萨的仪式,从语言上就已经很难被理解了。这种神圣语言,不同于日常口语,所以,即使是当地人,也很难听懂。所以,某种程度上,学习董萨,就是要再掌握一门语言。

在农尚广场搭建祭架
新的变化是,从语言到仪式,年轻一代都越来越陌生、疏离。笔者参加了多次祭祀家堂鬼的活动。活动中,年轻人对这些仪式并不完全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按照长辈的指示,完成仪式中的工作,避免触犯禁忌。
在邻村卡链,一个景颇少年跟笔者说:“这种迷信么,是他们大人要搞的,我们么,就跟着他们说的做了嘛。这些东西我也不懂。”
年轻的一代,无论是读书的,还是打工的,都已经走得更远,所以,世界观已经跟父辈有很大不同。即使他们最后又回到村子,成家立业,但外出的经历影响依旧在。不过,传统对于年轻一辈而言,并非“不再相信”这么简单。事实上,传统仪式,还发生了一种变迁,那就是它的意义在改变。
如果说,仪式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神圣世界,那么,年轻一辈在对这个传统信仰淡化后,反而注重仪式的另一功能,那就是它的社交功能。所以,年轻人在传统仪式中,依旧在场,意义已经不同,祭祀之后的聚会,对他们更具吸引力。
卡场镇在盈江西北,距离县城40公里。盈江现在是坝区,在坝区周边的山地,分布有不同支系的景颇族。卡场的景颇族文化,董萨的传承可能最具特色。据早相介绍,盈江有3个斋瓦,这3个斋瓦,都在卡场镇。因此,由卡场的麻竹岭杆,也大致可以看出整个盈江传统信仰的情况。
麻竹岭杆,正在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传统信仰,自然是这个村寨尚存的底蕴之一。近年来,这个村子开始酝酿很多变革,包括发展村寨旅游,村子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渴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