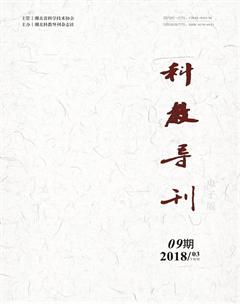中外关系转换对内蒙古城市发展的影响
摘 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而内、外蒙则是列强觊觎之主要目标,其中以俄国和日本为首。经过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清廷先后与俄国、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若干条款涉及内、外蒙古的权益问题,如在内外蒙筑路、开矿、贸易等。俄国、日本藉此先后打开了内外蒙古的大门,随即在该地区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培育政治势力甚至谋求侵占内外蒙。这一切,加速了蒙古地区半殖民地化进程,对整个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 内蒙古城市 中外关系 战争与城市 区域发展
1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对城市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影响内外蒙古地区对外关系的主要有《恰克图条约》、《尼布楚条约》两个条约。1689年,清军在雅克萨彻底击败入侵的沙俄侵略者,迫使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1728年,中俄两国又签订《恰克图条约》。以上两份条约成为鸦片战争前界定中俄两国关系的法律依据。这两份相对平等的条约,其内容事实上多关联内外蒙古地区。大体包括确定了中俄两国沿蒙古东段的中俄边境线,允许中俄两国人民过界往来,允许在尼布楚、恰克图等地进行通商互市等。这两份经过较为平等的谈判且在清王朝作出了一定让步的条件下而达成的条约,对内蒙古地区影响甚远。
首先,两份条约的签订使得中俄两国商人在中俄边境有了合法的贸易中心—恰克图和买卖城,中俄商人逐渐云集于此两地进行“典型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进而带动了内外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据统计,在1755-1760年这5年间,在恰克图市场用以交换的俄国和中国的商品总价值从837000卢布,增加到1358000卢布,增幅高达62%。这样的贸易量还意味着恰克图的城市经济和城市规模得以迅速膨胀,如学者何秋涛便感叹道:“菊海以南,燕然以北,广裹数千里,商贾皆萃于库伦所属之恰克图,为朔漠之间一都会也。”
其次,这一时期的中俄边贸以农牧产品为大宗,且交易方式主要为以货易货,故贸易的繁荣刺激了本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
再次,中俄边贸的开展,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商人深入到内外蒙古地区赚取利润,并逐渐寄居于恰克图等地,从而撕开了清廷在内外蒙古实行的民族隔离政策,开启了汉族民众移民内外蒙古的大门据学者何秋涛分析,当时长期活动于恰克图的山西商人有很多,其中旅蒙商人数量占多数, “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得有八十余家。”
最后,两份条约的签订使蒙古地区在此后的一百多年内没有再出现较大的边患,中俄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双边关系。
2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变化对城市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通过战舰和火炮陆续强加给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清王朝闭关锁国被终结的同时,中国与列强之间间亦形成了侵略与被侵略、殖民与被殖民的双边关系。
上述关系在内外蒙古地区具体反映在如下条约内: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根据这几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俄国在割占大批中国领土的同时还获得以下特权:俄国商人可以在恰克图—张家口—北京、科布多—归化城—天津两条商路上自由往来,同时可利用沿途的驿站和邮传设施;允许俄国在库伦等地设立领事馆,俄商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贸易免税;俄商可以自由出入蒙古各旗,销售和收购蒙古地区的商品等。同时,依照所谓“一体均沽”原则,沙俄可以享有在内外蒙古地区所攫取的这些特权,其他列强也有权享有。故上述条约事实上使沙俄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获得了进入内外蒙古进行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机会。于是,从漠北的库伦、科布多到漠南的归化城、张家口,直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伊犁以及东北的齐齐哈尔、长春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国商人的踪迹。尤其是有近水楼台之便和有着传统贸易往来的俄国商人,迅速涌入到内外蒙古地区的主要城镇,大建商店、大开货栈,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甚至强买强卖,“俄国商人应纳各税,概拒不纳,强行在蒙古各地征发驮马等车,运输貨物,且擅在彼建造囤茶之场,种种强暴,不胜枚举。”整个蒙古地区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随意驰骋的猎场。
同时,在中国内外蒙古作为猎物的过程中,列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如1907年英俄两国订立《英俄条约》,“划分亚洲势力圈界限,以蒙古划归俄国。”而经过明治维新并取得中日甲午战争胜利的日本则直接对中国东三省、内外蒙古虎视眈眈,“自满洲以至中国一带为日本工商业上必争之地,故日本欲于近邻得一好市场,非藉满洲中国之开发,其势不可若”。沙俄则急切于在远东建立所谓“黄俄罗斯”,两害由是相争,日俄战争爆发。时人曾对这场战争作有如下悲愤的预判:“交战者,日俄,而立于必败之地者,乃吾中国耳。”实情亦的确如此。战胜的日本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继承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划定蒙古境内的海拉尔、察哈尔、满洲里等地区为商埠,并取得15年的安东至奉天铁路经营权等。日本势力自此大规模的侵入内蒙古地区。
不过,沙俄并不甘心就此退出远东,与日本争夺朝鲜、中国东北控制权失败之后,沙俄转而把注意力聚焦到外蒙古地区。时人指出,“日俄战后,俄国于南满洲既挫其锐锋,一意经营蒙古,扩张其南下之势力”,为此,俄国人一面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立中俄道胜银行分行进行资本侵略,“一面散布金钱买足喇嘛收揽民心,并笼络蒙古王公等”,这不能不令人焦虑:“恐外蒙古一带中国之地,不久将成为第二满洲。”不幸的是,此种焦虑最终变成事实。
在沙俄长期收买挑唆下,外蒙古的分裂势力逐渐滋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认为时机已到,12月1日,怂恿煽动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结库伦,正式通知清廷驻库伦大臣,“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并勒令清廷派驻库伦文武官员及兵丁三日内离境。同月28日,哲布尊丹巴沐猴而冠,登基称帝,宣称“独立”,“大蒙古国”终于粉墨登场。 然而,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现一个所谓“大蒙古国”,故对双方施压,迫使外蒙古上层集团接受。袁世凯当权的北洋政府允许外蒙古自治。1915年,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而行“自治”。但所谓“自治”,“其实是外蒙古想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不过,无论“自治”还是“独立”,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分裂行动从未得到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之承认。即便如此,作为内外蒙地区中外关系上的一件大事,“外蒙古的脱离中国使中国和外蒙古人民深受其害,使俄国获得重大的侵略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外蒙古宣布“独立”,使得中国北部边疆隐患重重:“外蒙古独处高原,西控新疆,东通关东,南出中原,北避强敌,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得之则边患甚少,失之则边患众多,故外蒙古之失,关系到中国边防甚大。”
(2)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对中国政府及中国商人采取排挤政策,库伦等地的中国商人被迫撤离甚至回到内地,这严重削弱了内外蒙古的商品贸易,阻碍了该地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俄国自煽动库伦独立以来,为独占外蒙贸易之计,将库伦、漠北各地所有汉商之营业者,悉行驱逐,而代之以俄商……迩来外蒙与中原内地之贸易殆归断绝。”
(3)外蒙古的所谓“独立”,给内蒙古形成示范效应,一些分裂势力借机生乱,严重损害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如呼伦贝尔盟的巴尔喀部17旗佐领,拥戴地方豪强胜福为盟主,在海拉尔“宣言独立,逐道台董任福而施行自治”,其后更宣称:“如库伦政府不足以保护统一巴尔喀,则彼等将相率而归化于俄人,何苦更受民国之统治”。
(4)外蒙古日益殖民地化。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俄国借机强化了对外蒙古政治和经济的控制。1912年11月,沙俄和外蒙古签订《俄蒙协约》。这份条约使俄国完全掌控了外蒙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乃至文化教育,以至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断言:“无论其表面之口实与对外的辩解何如,不能不断谓蒙古已纯成为俄国之保护国也。”《俄蒙协约》规定:“俄国属下人等及俄国商务照旧在外蒙古享有此约所附专条内开各权利、特权,其它外国人自不能在外蒙古得享权利多于俄国人在彼得享之权利。在《商务专条》内,俄国人为自己规定了特种权利:俄国人在外蒙古各地可以自由移动,经营事业;俄国人进出口货物一概免税;俄国银行有权在外蒙古开设分行;俄国人有权在外蒙古租赁或购买土地,建造工厂、店铺、码头和经营牧场、开垦耕地等;俄国人与外蒙古协商关于享用矿产、森林、渔业及其它;有俄国领事之处及有关俄国商务之地,均可由俄国领事与外蒙古协商设立贸易圈;俄国人有权乘坐自有商船往来航行外流至俄国境内河流,与沿岸居民贸易;俄国人运送货物,驱赶牲畜,有权由水陆各路行走;俄人可割草渔猎;俄人可以设立邮政、建造桥梁等。”由此可见,外蒙古完全成为了俄国的殖民地。外蒙古商人运入到内蒙古各种土货商品进行商品贸易,俄国的洋货也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这些显然直接干涉了内蒙古地区的经济贸易秩序,侵占了内地贸易市场。虽然扩大了内蒙古地区的贸易市场。但是从客观上来讲,俄国可以更加有力地与中国内地商人在外蒙古地区竞争。除此之外,俄国掌握着外蒙古的铁路权,独占对蒙古的经济利益,并将蒙古纳入了俄国经济圈,严重影响了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
俄国不仅挑唆外蒙古独立以使其成为殖民地,且与日本共谋瓜分内蒙古。1912年7月8日,俄国与日本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在内蒙古划分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即以东经116度27分为分界线,日本在此线以东的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俄国在此线以西的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综上可见,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大背景下,内外蒙地区的中外关系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只有被侵略、被殖民的厄运。这样的国际关系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内外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走向,从而影响着该地区城市经济、城市体系、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乃至城市兴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外蒙地区日趋半殖民地化,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外蒙古 “独立”,表明内外蒙地区各种权益在鸦片战争之后到民国期间被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践踏侵吞,中国日益丧失内外蒙地区的国家主权,而国防安全也遭遇严重威胁。
其次,内外蒙地区日益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原料掠夺地、资本输出地,畸形经济活动较前繁荣,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内外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传统游牧经济的解体。如俄国商人在内外蒙地区倾销毛织物、棉织物、金制品、火柴、颜料等工业品,而购入“马匹、有角畜类、家畜原料品、茶绢、布”,且“俄商挟其雄心,欲征服蒙古西部之市场,且将以蒙古原料,多运入西伯利亚之市”。又如归化、海拉尔等内蒙古地区重要城镇,随处可见英美倾销的纺织品、日用品和奢侈品的同时,亦遍布以掠夺各种原材料为主要目的之洋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列强在内外蒙地区经济掠夺活动的频繁,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该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如包头的皮毛行业,自清末出现第一家经营该行业的洋行后,到1926年增加至14家,且每年收购销往英、美、日、俄的绒毛达600万斤,从而推动了包头城市经济的繁荣。
最后,屈辱的对外关系甚至影响到了蒙古地区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的兴衰。如外蒙古所谓“独立”后,留住库伦的16000多“华商”,被强制禁止不准出入喇嘛圈内、不准集会、不准同“内地交通”,甚而“勒令华商改易蒙古装”。又如以商贸闻名的塞外名镇张家口,“迄民九外蒙独立,张垣商务否运开始,洎民十三蒙政赤化,汉商更无发展之望,自十八年抗俄之役后,中国商业完全为外蒙古政府没收,总计商务损失在一万万两以上,自是张库隔绝,此张垣商务一落千丈,现状萧条之大原因。”
3战争、匪患与城市发展
战争和外部掠夺对于城市的兴衰起落有着重要影响,因为战争可以用最残暴的方式将昔日名城变为废墟。“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人口、资源和社会财富,一旦发生战争,城市就自然成为作战双方首先攻打的主要目标”。民初以来,内蒙古地区长期被战火硝烟包裹,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发动之侵略战争,加之众多盗匪肆虐城乡,故对整个区域及区域内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3.1军阀混战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民国期间,内蒙古地区遭遇的军阀混战不计其数,其中破坏最大的则是两次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于1922年1-5月之间。其时,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随后,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开战,最终奉系败走关外,直系控制北京。不过,奉系并不甘心困守关外。1924年9月,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动15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近二十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随后,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迅速战败,11月,吴佩孚率残部自塘沽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冯玉祥、段祺瑞三方的最终胜利而结束。
两次直奉战争,战火过处,均烧及内蒙古地区。尤其第二次直奉战争,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混战,对北方地区造成的破坏更为巨大。冯玉祥等于10月30日通电便曾概括地指出:“此项战祸渐兴,糜烂至十余省,骈殉军士以累万计,耗费军需以累百万计,各被难人民以累千万计。至其间直接间接,政府、国民因战争影响而受之损失,更不可以数字计。”而热河作为主要战场,所受兵灾甚为惨重。时人致段祺瑞呈文便指出,这场战争使热河“十五县之间,甚至数十里无人烟,多少村无釜甑”。
除以上两次军阀混战外,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之战和1927年阎锡山晋系与奉系之战,均波及内蒙古地区。这些军阀混战,对内蒙古地区城镇的破坏可谓惊人。
首先,各军阀部队所过之处,巧取豪夺,搜刮地方民脂民膏,严重摧残了城市经济。如绥远省所辖丰镇县,“最发达时,为民国十三四年间。商号数目七百余家。凡邻近陶林集宁凉城等县,皆以此为贸易中心。民国十五年,国民军西退,大兵云集,供给浩繁,而溃兵散匪,劫掠财物,地方元气大伤”,具体如“花布业,发达时,至五十余家。现仅二十余家。”又如1927年,晋奉战争爆发,奉系郑泽生奉命攻打清水河县城,入城之后,“民间所藏,罗掘殆尽”。再如1926年,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因奉军攻击而被迫撤出有“西北门户”之称的包头时,“向各商户派捐摊饷,搜刮至二千万元之巨。于是包头各业,元气凋伤。”
其次,各军阀部队混战之处,物态的城市本体、城市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破坏。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锡元部在张家口发动兵变,“此届兵变,张垣几被一空,损失之巨,达数百万,被火者数十里,实为西北空前之浩劫。”1927年晋奉战争期间,奉军为阻止晋军进入丰镇,拆毁了京绥铁路丰镇区段线路,而晋军商震部同样乘奉军不备拆除京绥铁路,阻断交通。
再次,军阀混战时期,城市社会严重失序,城市管理混乱,民众饱受煎熬。1928年3月,奉军进驻绥远期间,其官兵甚为蛮横,在土默特一带任意敲诈商人,鞭打百姓。驻扎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的奉军,聚赌包娼,征收苛捐杂税,十室九空。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赤峰的游民奸商“乘此机会,或则造谣惑众,或则破坏金融,或则高抬物价,人心惶恐,商业混乱。”
最后,军阀混战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大量流失,中断了城市发展的正常脉络。如赤峰因受两次直奉战争影响,“秋收无望,又值盗匪迭出,富者转为贫,贫者流为乞讨。凡本县住民,壮者均各携眷逃往他乡,别谋生活。其老弱不能动移,不外牛衣对泣坐以待毙而已”。
3.2匪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社会失序,经济凋零,加之蒙地民风彪悍,故盜匪出没于内蒙古地区的山间街市,或数人一伙,或数百上千一群,严重阻碍着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变迁。其表现则如下几方面。
(1)匪患肆虐,无日不休,民众安居乐业可谓泡影。如绥远地区,“出城市三五里内即有遭劫之祸,倘在农村居住,三日遇匪,五日被劫,终日不得安宁”。又如固阳匪患,“无时无之,只以去冬间,杨白皮、刘迷糊股匪,鼠扰境内大半年之久,人民逃避,几至一冬无家可归”,至于财产如“钱银财物、粮食牲畜,抢掠殆尽”。
(2)盗匪攻城略地,肆行抢劫,城市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如1905年冬,悍匪卢占魁率匪伙攻陷萨拉齐县城,“盘踞数日,全城商号,抢掠殆尽,钱当两行,均归倒闭”, 萨拉齐县城市面自此萧条,一蹶不振。再如武川县,1930年冬被杨姓匪徒聚众攻陷县城,匪众“沿户搜枪,市民无幸免者,商悉闭者,无资营业,气象萧条,城市顿成荒村”。
(3)盗匪过处,烧杀掳掠,许多城镇毁于一旦。如1912年,五原县遭盗匪攻陷,“镇地适当其冲,横罹劫杀焚烧之祸,商号倒闭者大半,繁盛之市,几成废墟” 。1916年,卢占魁匪帮几近万人,横行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所过之处,“劫杀商民,焚毁城池”,饱受痛苦的内蒙古人民不能不有“水深火热之叹”。
(4)兵匪一家,兵纵匪,匪靠兵,整个内蒙古地区如同“恐怖世界”。如热河匪患严重,地方凑集粮饷请驻军剿匪,但,凡“官军路过县城、集镇,莫不强住商家。人非大米、白面、酒肉不食,马非鼓子、料豆缺一不可,应酬稍缓,打骂随之。……间或出队剿匪,彼此多系素识,虚开枪弹听贼饱扬,贼则抛弃枪马,稗兵卸责。实则贼之枪弹半买之于兵,抱薪救火何时可灭!”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匪患十分严重,对民众生活、城市公共治安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城市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阻碍了城市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加深了区域社会经济的贫困。
3.3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近代蒙古战争连续不断,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对城市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和影响,导致蒙古地区城市本身的发展系统无法正常运转,特别是在日俄战争时期,由于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领土内。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使北部地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在蒙古地区的日俄战争,更是如此。帝国主义的战争创伤要依靠中国人自己解决。因此,日俄战争后,蒙古地区开始处理日俄战争带来的恶果。
“日、俄双方在军事上的设施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已经使蒙古问题显得十分紧迫,不论最后的胜利属于何方,蒙古都要解决这些问题,第一要有积极的军事准备,其次是喇嘛教的觉醒,提高蒙古文化教育,使其有中心思想。第三要以科学的方法指导蒙古的牲畜,第四是卫生设备,第五科学教育的设施。以上这些措施才可以解决蒙古的问题”。同时,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特别是在“在蒙古地区的主要商埠,如张家口、归化城、海拉尔、满洲里、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城市均有外国银行或办事处,在俄、日、英、美诸国的银行之中,以沙俄银行影响最大,危害也最深。”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导致内蒙古地区城市各项功能发展停滞,部分城市因为战争而走向了衰落。
3.3.1日俄战争与内蒙古城市的发展
日俄战争本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但由于发生在中国境内,对蒙古地区的影响颇大。“日俄两国,因为立国制度不同,所以日俄假使发生第二次战争,战争的胜利属于何方,这实在影响着蒙古同胞的命运。”日俄战争对蒙古民族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很深的影响,蒙古东隣日本,北接赤俄,属两大帝国主义侵略之要地,环境险恶,匪言可喻。往昔因循苟且之心理,实不足以图存于今日,惟有同心努力。日俄战争的起因本是为了争夺在华利益,战争的结局是日本战胜俄罗斯,日本强迫晚清政府将俄罗斯在华利益转让给日本。
“中国政府承认俄国所转让给日本满洲国的一切权利,帝国主义打开了通往盛京的大门,划定蒙古境内的海拉尔、察哈尔、满洲里等地区为商埠。安东至奉天的铁路,由日本政府经营,期限是十五年。中日进行合作,砍伐鸭绿江石岸的森林,砍伐经营年限等一切事宜再商议。允许南满铁路所经营的各项材料,免纳税捐”。内蒙古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内蒙古东部的城市受到控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影响,铁路沿线的东北三省和东部内蒙古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受损严重,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扎兰屯和富拉尔基一线实行了殖民统治。
日俄战争虽然属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但并未影响到帝国主义对自己国家的破坏,战争使内蒙古失去铁路自主权后,中东铁路沿线的城市也失去了各项功能,导致内蒙古东部城市迅速衰落。帝国主义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给蒙古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社会经济更是难以发展。即使后来进入蒙古地区的苏联,也同蒙古地方政府发生了不少冲突,蒙古地区仍然是多方争夺的焦点,蒙古地区不断同多方发生冲突。据库伦通讯云,“蒙军在库伦与俄军冲突中,各方死伤五百余,形势极为严重,居民到处避难,发生的原因,系俄军在蒙横暴,又因内蒙政府已经下了动员令,集中军队到边境防俄及抵抗外蒙古自卫联合军。在海拉尔地区,苏俄联军在外蒙古各处征兵,准备进攻海拉尔,其侵略之心引起了蒙民的不满,蒙民将有反动”。
无论是何种原因,帝国主义视蒙古地区为战略要地和兵家必争之地,严重影响了蒙古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3.3.2抗日战争对内蒙古城市发展的影响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兵力开始积极的向着北满及内蒙古推进,军用铁路、公路开始积极建设。内蒙古东部沦陷为日本殖民地,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以及呼伦贝尔、西布特哈地区均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33年,日本占领了热河省全境,日本在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以及呼伦贝尔、西布特哈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日本马上开始侵略蒙古地区,“1937年l0月14日,日伪军侵占了塞北重镇—归绥。日寇一进城就把太阳旗插在新旧城的鼓楼上,大街小巷到处是端着枪的日本兵和伪蒙古军”。
日本对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控制长达14年之久,西部地区的殖民统治也长达8年之久。日本对蒙政策及内蒙古东部采取了独立、自治的运动,在东西部地区实施其殖民范围。东部的殖民范围包括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呼伦贝尔北部和西布特哈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但西部地区仍属于蒙疆。日伪时期的殖民统治对蒙古东部城市的政治制度、经济措施、教育文化政策进行了殖民统治,城市政治方面实施地方行政建制调整,废除“旗县并存”制,盟旗制度发生了改变,调整了地方行政建制,改变了城市原有的城市政治制度政策。城市经济政策及措施也发生了改变,推行鸦片政策、处置蒙旗土地问题,对畜产资源统制与掠夺,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经济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也造成了障碍。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编号:2016M592977)。
作者简介:赵晓培,(1985— )女,河南郑州人,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6:186-187.
[2]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5:131-132.
[3] 李自学.中俄恰克图贸易述评[J].暨南学报,1992(02):119.
[4] 何秋涛.朔方备乘[M].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759+761.
[5] 阿岩,乌恩.蒙古族经济发展史[M].远方出版社,1999:268.
[6] 佚名.俄人近在蒙古之舉动[J].广益丛报,1907(143):14.
[7] 葛布斯基.逐鹿蒙古[M].李汉如译.兴华周刊,1936,33(15):4.
[8] 日俄战纪[J].新民丛报(44、45号合刊),1903:20.
[9] 守肃.日俄战争及于中国之影响[J].政法学报,1904,3(06):3.
[10] 徐春霞.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述论[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0.
[11] 佚名.俄人经略蒙古之可危[J].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31):32.
[12] 陈崇武.外蒙古近世史[M].商务印书馆,1926:156.
[13] 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J].历史研究,2004(04):106-115.
[14] 孙福坤.蒙古简史新篇[M].文海出版社,197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