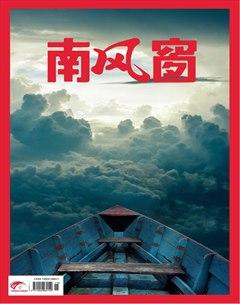人生是一场想做猪而不得的旅程
董可馨

4月12日,《南风窗》记者在北京的理想国出版社见到周濂,他要出版一本新书,被安排了密集的采访。
刚结束一场,他迫切地想出门抽支烟。采访者担心自己的提问不够深入,站着没有离开,他温和地笑着否认:“没有没有,我们聊得很好。”
在生活之中,周濂有意收敛自己的哲学老师身份。他觉得只有和真正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对话,才能进入哲学意义上的交流,“我跟陈嘉映老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入到真正的语境当中去。哲学,还是有点专业的门槛。”
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周濂无疑在从事着将哲学日常化的努力,“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人生是一场想做猪而不得的旅程”,说起来,多么“周濂”啊。
他用轻松又严肃的,通俗的、机灵的、富有美感的话语,向公众展示出一扇充满魅惑力的哲学大门。
但他坦言,“进去之后90%都是苦,我展现出来的只是那10%”。那90%到底是什么,周濂和《南风窗》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谈。
哲学思考要和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发生关联
南风窗:如今哲学需要证明自己,说服公众接纳自己,比如你经常要回答“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但在哲学诞生之初,它还没有那么高冷。借用威廉·巴特雷的话,在古希腊,哲学不是一门特殊的理论学科,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是对人和宇宙的总体看法,个体的人据此度过他的一生。但现在的哲学却越来越边缘化,让公众敬而远之。这是哲学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
周濂:这个问题挺有意思。作为曾经的哲学学生和现在的哲学老师,这一点我的感触特别深。学生时代过年返乡,在火车上大家被问起各自的专业,别人说法律、商业、经济的时候,不会有人惊讶,但到我说读哲学,基本上大家都会停顿一下。我当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时候,我妈在当地毛纺厂工作,她的一个同事跟她说:“恭喜你,你儿子以后就是坐在领导人边上的人。”这是普通人对哲学的理解。

南风窗:这一点一直如此,从未改变,我身边的经验也不少,哲学在中国要么被视为很神秘、很高深的东西,要么就被认为全然无用。
周濂:哲学本来是一个外来物,这个概念来自日本学者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到中国。中国原来其实没有哲学,只有一些思想,或者关于人生伦理的反思。哲学,尤其古希腊以降以逻辑思维和论证为主要特征的思考方式,对中国人来说都很陌生。
而说服公众接纳哲学,我好像从来不做这个工作。因为很难用三言两语去说清楚哲学是什么,它其实还是一门相对专业的课程,需要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慢慢把握。所以我通常不会在生活中去强调自己的哲学老师的身份,但是我会通过写作,通过课堂教学,通过一种比较长线的方式,向公众展示。
哲学这门学问,它能提供的最有效的参与公共讨论的方式是对事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对具体事物的内在逻辑的探讨。
南风窗:越来越多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哲学书籍和哲学概念,但是其实哲学变得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在学院内才有“资格”去谈论的事物。但你的新书《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写得严肃又不失通俗。
周濂:其实我不管是写书、录喜马拉雅的音频,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西方哲学智慧的课程,我都希望把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状态拉回到人间。西塞罗评价苏格拉底时说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说的是他不去研究自然哲学而转向伦理学,但我愿意借用。我希望用直接生活经验去软化那些超级概念的坚硬外壳。
我所理解的哲学不是晚间萤火虫那般闪烁的,我希望它是有内在勾连的。比如我在讲西方哲学智慧,以及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在意的是讲不同哲学家之间、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不同的哲学时代之间的关联。讲西方哲学史是纵向的一个串,但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时候,我希望是在横向上也把不同的事件串起来。
南风窗:在我对哲学发生兴趣的时候,我会觉得宁可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也不想去做一头快乐的猪,但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你也一定遇到过和我同样的问题。
周濂:的确是,今天是高度娱乐化的一个时代。我自己有时候也蛮喜欢看娱乐节目,以前经常看《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最近这两年少了。我不是一个拒绝娱乐化生活的人,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人不能永远做快乐的猪。事实上我认为,人生是一场想做猪而不得的旅程。你不可能永远做猪,总会在人生的某一刻你开始反思,开始思考一些相对宏大的问题,在对人生的某些遭遇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一刹那,你可能就遭遇苏格拉底了,就遭遇哲学了。
更温和,也更有力
南风窗:我们知道古今的生活不同了,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古代的哲学家力求建立一套整全的知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建立政治。但现在解构变得非常时髦,世界似乎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没有任何哪怕是暂时的道德共识。你觉得如今要如何去建立一个道德共识,并且为社会提供一个统一性的基础?
周濂:道德共识不是一个已经在那的东西,它是有待形成,需要我們去努力争取的“目标状态”。今天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发声,当然上面还是有权力的统摄,但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跟以往相比,空间要大一些。
当然也导致一个后果,专家学者越来越边缘化了。但我觉得也是件好事情,因为它让我们更好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参与到道德共识的建设中。大家会意识到,我的观点只是诸多观点之一种。虽然我对自己的观点有自信,它经过了充分的推敲和理性的思索,但是它的正确性以及它的可接受性并不是想当然的。如果这么想,人就会比较平和一些。
南风窗:现实好像并不平和。前两年开始流行后真相时代的说法,是说现在的公众舆论是被情绪所主导的,公共讨论往往因为情感先于真相、事实让位于态度而动辄变成争吵。我们从事媒体工作对此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对于某些事情,明明是想理性探讨,却发现被很多极端的情绪笼罩,理性探讨的空间似乎越来越狭小。
周濂:我太理解这种沮丧的心情。公共文化心理的培育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可能要几代人的观念转变。而且仅仅通过说理去改变一个人,尤其改变他的根本价值观或信念,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也越发要求我们要放平心态,不要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前两天还有人说你们70年代就是过渡的一代,我说我同意,但我觉得在过渡的过程中,我能够发挥一点点微薄的力量,也挺好。
另外,虽然哲学主要是说理的活动,但我们还要记住休谟的那句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我当然不会百分百认同这个说法,但我会时时刻刻把这句话当成警示格言,就是你要意识到人们的确经常会被情绪和偏好左右,不去顾及道理本身。这时候我们怎么回应?一方面是坚持说理,但另一方面跟听众的情绪要产生呼应。你不能简单地说那些极端情绪彻底错了。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合理性可能来自历史,来自灌输和教育,来自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总之,你要部分承认它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之上再去讲道理。
如果一上来就说你们都是傻子,都是无知的人,那你跟他就没有任何同步的起点。我是希望能够首先站到对方的立场上,试想他的合理性,然后通过漫长的、曲折的说理把他从原来的轨道上面稍微移开一点,试着往我的轨道上拽。当然这个过程会非常的艰难,可能经常会失败,但是更温和,同时也更有力。
南风窗: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有没有天然的义务参与到公共讨论当中?
周濂:我在参与,但是我个人对自己的期许是不参与到特别具体的案例中去。我不擅长写快速的评论,另外我觉得哲学这门学问,它能提供的最有效的参与公共讨论的方式是对事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对具体事物的内在逻辑的探讨。经验性的东西,可能别的方面的专家比我做得好,那我就可以往后退一步,作一些更根本性的讨论。
苏格拉底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哲人应有的面貌。那就是,你所说的应该是你所信的,然后在生活中去反复实践所信。
比如说在某个事件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本身是不是有误用?为什么?这个事件背后所展现的事物的逻辑,它有什么更普遍的道理和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趋势?
想放弃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纠结
南风窗:时代让人奋起,也会让个体幻灭。20多岁正是非常危险的年纪,一如你所说,这个年纪很容易由理想主义走向破灭,是停留在破灭后永远颓废的状态,还是第二次走向更成熟的理想主义,人在此时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不禁让我联想起你常常提到的维特根斯坦,他对自己的考问也永远都不会过时:“如果说谎对我是有利的,为什么我还要说真话?”
周濂:这种困惑和焦虑是时时存在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维特根斯坦所思考的问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新来考问我们。“如果说谎对我是有利的,为什么我还要说真话?”面对小利,这句话会出现,面对大的威胁,这句话也会出现。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智力游戏,不是一个需要去做的思想实验。它是非常真实的,最终涉及你的人格完整性。
我觉得这就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吸引我地方,它把你放置到现实世界的鲜活和拧巴的矛盾中去,然后逼着你作选择。
我想到苏格拉底。绝大多人在法庭上作自我辩护的时候,都是要尽可能让自己开脱,但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的抗辩,是他决定去死的抗辩。他没有为自己开脱罪名而寻找各种托词,而是要为自己的一生作辩护,为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作辩护。为此他不惜主动去赢得死刑。
苏格拉底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哲人应有的面貌。那就是,你所说的应该是你所信的,然后在生活中去反复实践所信。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反复做的事情,成就了他本身。当然这会伴随所谓的“痛苦的苏格拉底”的问题。
南风窗:但是现在第一个环节就出问题了,在“所信”这里,价值观的丧失带来困惑,所以年轻人中丧文化、佛系才会这么流行。
周濂:对的。但我不愿意苛求每一个具体的年轻人,因为个体在这个时代面前永远是很无力的。如果我们这些过来人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的支持和资源,不能够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典范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底气去批评和苛求他们。
南风窗:我前两天和朋友谈到这个话题,我们觉得年轻人最应当保持的品质还是真诚,但要做到这点很难。
周濂:我想起以前在课堂上讲到卢梭时,有一个问题是卢梭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我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文学评论家叫特里林,他写了一本书叫《诚与真》。
书里谈到从17-18世纪开始,当时的欧洲开始思考一个主题,一个人的真实所是和他所表现的样子,这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分离。特里林问了一句话:为什么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真实的,而到死亡的时候就成了赝品?赝品的意思是你成了你所不是的,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需要自问的是,为什么到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成了赝品。
南风窗:我想到了木心的那句話,一个人能做的就是长途跋涉地归真返璞。
周濂:是,但我不愿意用初心这个词,初心不是天然正当的,我们需要反复地去锤炼它,擦拭它。
南风窗:刚说到卢梭,他非常的复杂而丰富,在《忏悔录》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他所呈现出的是纯粹、敏感又有些无赖的形象,很多行为都不符合日常的生活伦理。但卢梭有很动人的一面,他很真诚,那种真诚其实是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那么多人喜欢他,也许因为他代表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某些高光时刻和理想时刻的那种状态。
周濂:对于卢梭或者尼采这样的人,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人们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他们。消费他们的意思是說你谈论他,你假想自己成为他,然后你觉得自我得到了安慰,你能够以此给自己庸常的人生提供某些借口,说我其实是一个不甘堕落的人,一个站在泥坑里面依然仰望蓝天和星空的人。我挺警惕这种心理的,这种心理非常廉价,它让我们不堪忍受的人生显得好像还可以忍受,但其实只是一种自欺欺人。
南风窗:读卢梭和尼采是有危险的,它会炸毁原来的一些东西,但不负责重建。
虽然某种意义上矛盾是生活的本质,但是人在矛盾中如此悠游自在,我觉得就有问题了。还是不要太容易妥协,在放弃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纠结。
周濂:对,他们属于闯入瓷器店的犀牛,四处破坏。而破坏,是所有年轻人或者说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人都有的内在冲动,正因为我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面去破坏,所以我们在文学或者哲学作品当中去想象破坏,由此得到快感和满足,以及自我安慰。
我一直在反复说,我们不能因为想象自己是卢梭,就真认为自己成了卢梭。我们不能想象自己是梅西,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梅西。这不真诚,也不正常。我们这个时代让大多数人丧失了真实生活,而习惯在各种场合有一张假面。你自觉到自己的假面,但却丝毫不觉得这其中存在矛盾性。可以说中国人的这种“辩证法”玩得特别好,虽然某种意义上矛盾是生活的本质,但是人在矛盾中如此悠游自在,我觉得就有问题了。还是不要太容易妥协,在放弃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纠结。
南风窗:习惯于假面,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内心不再有破坏的冲动了,而如果有一天一个人的内心不再有破坏的冲动,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不再年轻了?
周濂:是的。我现在慢慢地就越来越守成。我愿意更多地看到我不同意的那些人的好的地方,当然这也是成熟的表现,但另一方面,破坏的冲动确实比以前弱了,我会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这个世界的合理性,而不是它的不合理性。
我觉得这跟我的生活支点越来越多有关系。年轻人的生活支点很少,他有的只是他自己,那无怨无悔的青春和没有任何轮廓的未来。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也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在逐渐丧失,那种破坏的冲动就会减少。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遭遇和心境,说得大一点,在古希腊悲剧的意义上,你要接受它,命运推你走到了这个阶段。
南风窗:锐意虽然少了,但力量更深厚了。
周濂:我想到塞尔维亚的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他当年在战火纷飞的地下室里一拍一拍地练习击打,他真正的力量来自全神贯注,每一拍的练习都是实打实的。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更持久的力量来自写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