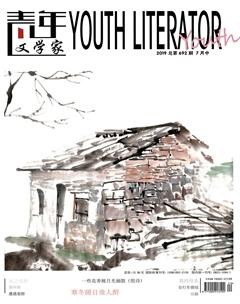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凶残的乌鸦》中的灭绝话语分析
摘 要:灭绝话语是一种主要基于“野蛮”种族将被欧洲文明的到来所取代的假设共识,它为塔斯马尼亚土著人被剥夺、拘禁和死亡的政策奠定了基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塔斯马尼亚土著人已被歼灭,然而,这种说法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谬论。土著人不再被定义为一个种族类别,而是一种在社区中具有的基础身份。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灭绝话语的内涵;其次分析了灭绝话语在《凶残的乌鸦》中的运用,并试图在后殖民语境中建立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土著身份观,小说中的灭绝话语元素主要包括对“消亡的种族”进行调查书写的倾向,对最后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比喻象征的依赖,以及介入混杂性概念来描述现代土著人;最后,塔斯马尼亚州的个案研究可对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的文化遗产斗争提供比较深刻的见解。本文作者希望就塔斯马尼亚文学中的灭绝话语提供一种新的观点,同时进一步探究土著人的文化身份建构和文化遗产继承。
关键词:灭绝话语;身份;土著;混杂性
作者简介:白玉婵(1994-),女,汉族,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3
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e, 1943-)生于墨尔本,幼年时迁往西澳大利亚,在那里接受教育。德鲁1961年任《西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后迁居悉尼,任《澳大利亚人报》文学记者(1971- 1974年),同时也为《时代报》和《公报》杂志撰稿。他是一名出色的记者,曾分别在1976 年、1981年和1990年获有关奖励。
罗伯特·德鲁是澳大利亚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极具独创性的声音。像他之前的其他作家一样,德鲁关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困境,仔细审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并对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和土著问题表现出深刻关切,这在其长篇小说《凶残的乌鸦》(The Savage Crows, 1976)中有很明显的表达,尤其是对消亡种族文化传承的关切。
一、灭绝话语的内涵
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中的“种族灭绝”一节中这样写道:“从17世纪末开始,大量文献致力于西方白人文明的致命冲击所造成的原始种族的毁灭”。灭绝话语是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分支,用福柯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话语形成”。就像东方主义和其他版本的种族主义一样,它不尊重学科的界限或高低的文化等级;相反,在这一话语中随时随都能发现欧洲白人与土著人的会面。灭绝话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无论他们的分歧如何,人道主义者,传教士,科学家,政府官员,探险家,殖民者,士兵,记者,小说家和诗人都基本同意原始种族会不可避免地消失。这种大规模且极少受到质疑的共识使灭绝话语极为有力且无情地朝着它经常反对的结果努力,即相信原始种族的灭绝。在许多作品中,对原始种族的消亡庆祝和哀悼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理解并有时庆祝这种消亡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同时,其中又融合表达了一种多愁善感的种族主义。
欧洲人的出现意味着土著人口急剧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暴力和战争;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疾病;许多人认为,第三个原因优先于暴力和疾病,通常被视为主要或甚至唯一的原因,即野蛮的习俗:游牧、战斗、迷信、杀婴、同类相食。简言之,土著人经常被视为是自我消亡的。自杀式种族灭绝或种族自杀的幻想是指责受害者的一种极端形式,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这有助于合理化不是欧洲征服和殖民化使得种族灭绝的论述。认为野蛮正在自动地从进步和光明的世界消失的信念减轻了殖民者的罪恶感,有时还免除甚至鼓励了那些被认为是对野蛮人的暴力行为。即使野蛮没有被认为是导致自己灭绝的原因,人们经常认为,有些种族不可能被文明化,因此无论他们有什么风俗习惯,都注定会被抛弃。
在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地方,许多十九世纪的作家采用了临终哀伤的形式描写最后一位土著人。塔斯马尼亚土著人是欧洲定居者大规模屠杀的受害者,他们之前经常遭受残忍的杀害和掠夺,最终搬迁到巴斯海峡的弗林德斯岛——这一系列事件经常被称为种族灭绝。到1855年,塔斯马尼亚土著人只有16名幸存者,包括特鲁加尼尼和威廉·兰尼。很明显,威廉·兰尼的去世在科学界和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尽管欧洲种族科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和测量已灭绝的、原始的文明人类的骨骼,显然没有人有远见去收集最后一个原始种族男性的标本信息。因此,随着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人的死亡,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的成员和其他种族的科学家们都醒悟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对兰尼尸骨的盗墓和残害。
灭绝话语在其他现代帝国和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具有重要影响。澳大利亚的灭绝话语受到多种相互矛盾的动机和证据形式的推动,其中包括缓解“负罪感”的愿望。
二、文本中灭绝话语元素的突显
十九世纪的灭绝话语——一种主要基于“野蛮”种族将被欧洲文明的到来所取代的假设共识——为塔斯马尼亚土著人被剥夺、拘禁和死亡的政策奠定了基础。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e)1976年的小说《凶残的乌鸦》或许比其他任何一部小说都更能体现出灭绝概念在文本中的运用。这本书有两条故事主线,分别是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的日记和主人公斯蒂芬·克里斯普(Stephen Crisp)调查塔斯马尼亚种族灭绝事件的故事。克里斯普被描绘成一个颠覆性的局外人,一个调查澳大利亚殖民核心黑暗秘密的边缘居民。一些评论家认为它是一部对塔斯马尼亚历史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的作品。
乔迪·布朗(Jodie Brown)在她的文章“忘却主导的表现方式”(“Unlearning Dominant Modes of Representation”)中提到,这部小说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标准惯例提出了挑战,同时揭示了“社会不公正和种族偏见”的各个方面”(1993:77)。同样,大卫·克尔(David Kerr)认为这本书“声称是对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灭绝的愤怒呼声”(1988: 63)。相比之下,评论家苏珊·马丁(Susan Martin)批评德鲁参与澳大利亚殖民计划。她指出了反复出现的肢解隐喻及其在文本中创造的结构,她认为这些结构使当前土著社区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2003:65)。
1. 对“消亡种族”的书写
由于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部分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的澳大利亚,斯蒂芬·克里斯普能够用相对较新的术语“种族灭绝”来描述欧洲人来此定居带来的灾难结果。小说一开始有提到,克里斯普正在尝试写一篇“狩猎、屠杀、强奸、杀婴、背叛、驱逐、和灭绝四五千人的独特种族”的调查。
对种族灭绝的了解破坏了克里斯普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他对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灭绝这一事件感到深深的内疚。克里斯普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因为他的朋友和家人希望他能遗忘那段历史历史以对抗他自己对塔斯马尼亚种族灭绝的罪恶感,而他却拒不接受。他的兄弟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对土著人的死亡和社会问题如此痴迷,而他的同事们同样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激进派”(Drewe,1976:123)。可以看出,塔斯马尼亚种族灭绝是对其身份建立的道德基础的挑战。在很多方面,这部小说关注的是重新审视塔斯马尼亚的历史,以减轻非土著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负罪感。
克里斯普试图与继续压迫塔斯马尼亚土著居民的人做斗争,从而产生一场更加痛苦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最后一章中,克里斯普与生活在巴斯海峡岛屿(the Bass Strait islands)上的土著社区的会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具体表现为作者一方面希望能从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灭绝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接受原住民身份的真实性,从而形成了双重的语言意识。普拉姆(The Blue Plum)是岛民社区的代表,他告诉克里斯普,他的社区代表着“通过杂交而形成的一个全新的人类群体”(Drewe,1976:252)。从其性质上看,这一想法似乎排除了土著社区获取其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可能性,实际上否定了当代土著人身份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克里斯普似乎接受了这个有问题的表述作为事实,他随后放下了他对种族灭绝的负罪感,认为塔斯马尼亚土著人通过变成一个新的混杂种群而幸免于难。然而,对土著人的狭隘的种族定义似乎排除了他们的存在。正如普拉姆说的那样,现在的岛屿居民是“新的人口”(Drewe,1976:252),似乎并不像克里斯普所希望的那样代表土著身份的延续。
2. 对最后一位土著人的隐喻象征
《凶残的乌鸦》最后一页的比喻体现了小说中的现代土著人其实并不被认为是真实的,这进一步说明了灭绝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当克里斯普离开岛屿时,他发现了“两个棕色的小生物”—蜱虫—钻进了他的皮肤,于是他用香烟把它们烧掉了(Drewe,1976:263)。这一意象既表明了他的罪恶感(挖掘)的焦虑,也表明了他想摆脱罪恶感的欲望(燃烧)。棕色的概念至关重要,因为它象征着混合社区的棕色皮肤。很明显,尽管克里斯普对岛民的语言和文化很感兴趣,但克里斯普并没有发现除了他们有着褐色的皮肤以外,还有任何关于岛屿社区的土著特征。然而,他所要寻找的正是这种特质,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曾经的土著人”,或者说岛屿社区。虽然不是真正的土著人本身,至少是真正的土著人的后裔。在了解这一点之后,克里斯普就可以摆脱他的罪恶感,而这种情况在他烧掉蜱虫时已经有所隐喻。这本书中的最后一个意象完美地概括了灭绝话语如何支撑小说中土著性的建构。克里斯普离开了岛屿社区,因为据他所知,虽然岛屿上的居民不是真正的土著人,但至少有一小部分土著人的痕迹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然而,他的结论完全基于狭隘的种族定义,因此也是有缺陷的。
斯蒂芬·克里斯普对土著人的身体特征的迷恋与他们在死前和死后所遭受的暴力相对应。他详尽地描述了对“没有头颅、没有四肢的最后一个人”威廉·兰尼的挖掘和解剖(Drewe,1976:24),兰尼据说是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男性。在被埋葬之前,兰尼的头和手被科学家拿去做骨骼检查;埋葬后,他的棺材被挖出来,他的身体其余部分被独轮车运走了(Drewe,1976:18-9)。同样地,特鲁卡尼尼(Trukanini)在去世后,被“挖出,整理,涂漆,钉在博物馆的墙上”(Drewe,1976:238)。这些亵渎行为是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种族灭绝历史中最后一个象征性的句號,当克里斯普重新发现这段历史时,他感到非常生气。但是,与威廉·兰尼(William Lanney)被挖掘、解剖类似的是,克里斯普自己也在挖掘和审视历史。他对土著人的尸体和他们遭受的暴力行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所遭受的暴力是一段需要保存的历史。克里斯普认为兰尼和特鲁卡尼尼是他们种族的最后一个男人和女人。他的动机完全投射在那些寻求保留兰尼头骨的人身上,仅仅是因为它是土著人的最后一个头骨。
德鲁很可能打算将克里斯普用作是一种工具,从而探讨这些复杂的关于作家是否参与了殖民地和后殖民的呈现问题,或白人作家在面对土著人民的苦难时的复杂心情。棕色蜱虫的隐喻可能是对此的一种表述,这是克里斯普对他所遇到的岛上土著人的真实本性的肤浅参与的一种证明。
3. 生物混杂性概念的介入
毫无疑问,有一些例子支持这部小说具有讽刺意味。普拉姆宣称他的种族是“通过杂交形成的全新人口”(Drewe,1976:252)。这表示岛屿社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真实的,正如普拉姆描述自己种族的繁殖性质不是土著人,而是“非洲-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人”,(Drewe,1976:252)。很难想象德鲁会将此作为对土著塔斯马尼亚人目前状况的讽刺性评论。相反,似乎德鲁更多地将灭绝话语作为他对土著居民观点的权威来源。同时,德鲁陷入灭绝主义的影响也是对围绕着小说中的殖民和种族概念的持续讽刺的可能解释。
这种殖民地思维方式的延续只会将土著居民置于种族概念之中。当然,以这种方式构思土著必然导致其真实的身份在1876年与特鲁卡尼尼一起消失,而今天的土著塔斯马尼亚人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都不是土著人。最初这个结论的得出就给社会带来了痛苦,当时人们通过血液将所谓的纯净者和被玷污者分离开来。在允许灭绝主义限制土著人的代表性时,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特权学术和制度化话语其实强化了它打算推翻的霸权。文化间对话的概念虽然本身不足以克服土著人学术陈述的霸权主义分量,但却创造了一种空间,可以对这些表征进行批评,回应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