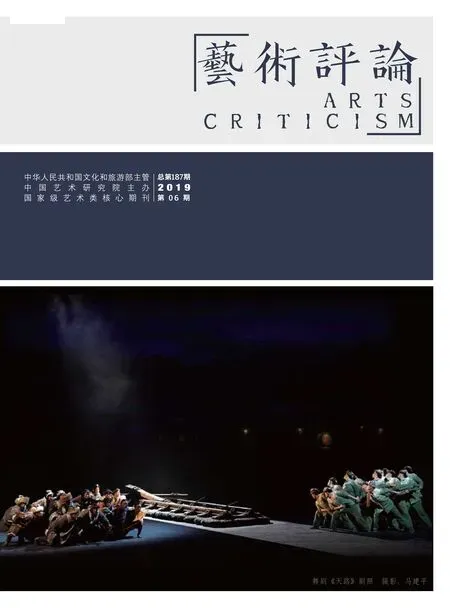沉重·童真·轻逸
——论“曹文轩新小说”《穿堂风》《蝙蝠香》《萤王》
[内容提要]在“新小说”系列《穿堂风》《蝙蝠香》《萤王》中,曹文轩延续了既往的风景描写和优美情调,同时含有“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新的气象”。他书写了一系列处于孤独和压抑中的少年。他们或备受猜疑与歧视,或直接被视为怪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紧张。但曹文轩并未将人物置于绝境,而是留下了和解的可能。他以童真援解困境,将沉重的现实轻逸化处理,借以实现治愈或救赎。
曹文轩的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自我印记,《草房子》《红瓦》《细米》《我的儿子皮卡》都使用了个人经验,即便他在作品中隐藏自我,采用人物的视角,那些视角也总是多多少少带有曹文轩的个人经验。在“新小说”系列中,曹文轩尝试放弃了带有自我色彩的视角,写相对“边缘”的儿童的生活。小说中少年主人公身世异常坎坷,《穿堂风》(2017)中橡树父亲做贼入狱,母亲离世,奶奶失明;《蝙蝠香》(2017)中村哥儿妈妈远走,爸爸又瞎又聋;《萤王》(2018)中的爷爷屈宝根因为一段奇遇,痴迷萤火虫,被众人视为怪异。“曹文轩新小说”中的“新”字,不只是指它们是他的新作,还有“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新的气象”等其他含义。当然,这些故事中荡漾的依然是曹文轩的情趣。文化人的情趣与别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别人很不以为然的东西,在他这里,却进入意识,并对此产生了一种很雅致、很有意境的审美。
一、孤独与压抑
在“曹文轩新小说”中,虽境遇不同,但主人公都处于孤独与压抑之中。《穿堂风》(2017)一开头,炎热扑面而来,乌童家的“风洞”出场,孩子们在这里躲避炎热,一起玩耍、学习,其乐融融,但是这一切背后,藏着一双眼睛。直到一个男孩叫起来,另一番图景展开:“一个光着脊梁的男孩,头戴一顶草帽,正在没有遮挡的田野上穿行。仿佛要躲避阳光,他一直在跑动。那时的太阳光十分强烈,他跑动时,样子很虚幻,像是在田野上游荡的魂灵。”这是一个不被欢迎的孩子,寂寞地在田野间穿行,“像是在田野上游荡的魂灵”。这一比喻阴气森森,被隔绝在热闹之外,人世之外,友情之外。橡树,一个在异样目光中成长的少年,父亲做贼入狱,母亲早逝,奶奶失明。纵然在母亲去世后,他没有偷过一根草,却屡屡被怀疑、被陷害。与曹文轩以往小说中的人物如桑桑、细马、根鸟等相比,橡树是一个孤独到了极致的孩子,他几乎没有一个朋友。虽然乌童对他有几分善意,但这善意深藏且犹疑。
怀疑和猜忌直接而猛烈。油麻地丢了很多东西,矛头纷纷指向橡树。备受冷落的橡树异常孤独,只能跟羊说话,跟鱼聊天,却被主人们一再误会,只能躺在田埂上。恍惚间,天地之大,无处可以容身:“瓜田进不得,河堤下走不得,鱼塘边站不得,那,橡树还能坐在哪儿?蹲在哪儿?站在哪儿?走在哪儿?要么,上天?在天空中飘着倒好,可橡树是人,不是鸟。他上不了天。”一连串的反问,其实道出了橡树的无奈与作者的悲悯,橡树只是一个小孩子,但被周围人贴上了“贼”的标签,在有色眼光的笼罩下,他处处是错,步步是错。关于人被标签化,再难得到公正对待这样的故事,橡树并非曹文轩笔下的个例。如被冤枉的何九,明明没有偷船,却活在村民鄙视的眼光里,如坐针毡,直到他用几年辛辛苦苦拾田螺的所有积蓄,买了一条大船,自此之后,愤而出走,背井离乡(曹文轩《田螺》);明明是牛偷吃了卖粮款,但麦子爸爸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因为村民的标签既然已经贴上,就不想再费力撕下来,且咬定是麦子爸爸搞鬼,或许还有收回粮款的可能(曹文轩《麦子的嚎叫》)。将人标签化,既能站在道德高点,又简单便捷,它满足了群体施虐的渴望,又不用花费时间、精力去探究真相。至于那个贴满标签的人,他的委屈、他的愤懑、他的痛苦,是群体并不关心的。
因瓜丘的偷盗与“栽赃”,橡树与村民的隔膜进一步加深。橡树不愿再忍受冤屈,跟踪瓜丘。瓜丘察觉后,威胁他要让整个油麻地人相信,是橡树一直在偷,要偷光整个油麻地。橡树很无助,一步步走进陷阱。瓜丘偷了羊,将它拴在橡树屋后的林子里。橡树来到林子深处选“棍子”,看到山羊被拴在树上,正要解开,却被乌童和秀秀撞见,元福二爷因此认定是橡树偷了他的羊,就连奶奶也用拐棍打翻橡树,让他跪倒在地。在瓜丘的精心设计下,橡树百口莫辩,奶奶也不再相信他,为自己的儿孙一再做贼,老泪纵横,痛不欲生。橡树的痛苦在于,他既无法辩解,又很难自证清白,只能孤注一掷。
《蝙蝠香》(2017) 中村哥儿的妈妈是全村最漂亮的女人,她一直向往一个更大的世界,离开村庄后,再也没有回来。她的出走带给母亲和丈夫巨大的打击,丈夫重病后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村哥儿外婆一下子变老。村哥儿因为妈妈远走高飞,爸爸又瞎又聋,孤独到了极致。他对母亲的思念如此强烈,又难以表达,只能在梦游中寻寻觅觅。梦游时,村哥儿唱着妈妈曾唱过的歌谣,忧伤、凄凉。“此刻的夜晚,除了林子里不时响起一两声夜鸟的啼叫,几乎没有别的声音——这世界清静到仿佛萤火虫的闪光、蝙蝠的飞翔,甚至是月光,倒有了声音。在这样的夜晚,村哥儿的歌声尽管低低的,却依然十分清晰。只是这样的时刻,可惜没有人听着,只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听着,只有飞来飞去的蝙蝠听着。”这一幅图景带有优美的诗意,天地安静,只有一个男孩低低地唱着忧伤的歌,将思念融进曲调,但他如此孤独,令人心生恻隐。
《萤王》(2018)讲述了一个颇为奇幻的故事。爷爷8岁时被美丽的豆娘吸引,误进芦苇丛深处并迷路。在又累又饿的困境中,萤火虫带领爷爷走出芦苇丛,还帮他找到解饥解渴的鸟蛋,拯救了爷爷。自此爷爷与萤火虫结下不解之缘:为了萤火虫,爷爷与秋虎斗了大半辈子,又与侵占芦苇丛的“城里人”抗争,被捕入狱,直到58岁得知大限将近,萤火虫落满全身,死后骨灰引来大片萤火虫,成为真正的“萤王”。小说对萤火虫的描写与主人公心境密切贴合,萤火虫缓缓飞行,身子前行了,但身后留下的金色曲线,却留在空气里如游丝一般飘动着。五只萤火虫交叉飞行,于是空气里就留下了互相缠绕的发光游丝,如梦如幻。五盏小灯笼,就在这荒无人烟的世界里,温柔而执着地用它们神秘而悠远的光牵引着爷爷。失踪的爷爷重新回到他的村庄时,人们发现,他彷佛中了魔法,变得有点古怪了。他很少与人说话,只跟萤火虫说话,并且没完没了,彷佛那些满天飞舞的萤火虫都能听懂他的话似的。爷爷与萤火虫成为知己,萤火虫围绕着他飞,在他的头顶上空织成一个旋转的金环,他冒险跳进大河,救助落水的萤火虫,为了萤火虫,与孩子们一再打架,被视为怪物。其实曹文轩写过很多人与动物的故事:青铜与牛的故事中,牛是知音,是伙伴,更是得力的助手(《青铜葵花》);小姑娘蓝蓝与小猫“短尾巴”的故事中,小猫是伙伴,更凝聚了乡间的美好与情谊,不容背叛(《云雀谣》);少年与海牛的故事中,牛是需要征服的对象,是成长的表征(《海牛》);桑桑与鸽子的故事中,鸽子是情绪的载体与外化(《草房子》)。但爷爷与萤火虫的故事,颇具奇幻色彩,更多是人与自然的神秘相通,传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内蕴。
在爷爷看来,萤火虫是小精灵、小生命,在秋虎看来,自己作为人尊贵无比,而萤火虫只不过是一些闪闪发亮的小虫子,只要能够取乐,可以随意处置他们。他们捕萤火虫、取萤火、做“鬼脸”,并非藏着多恶毒的心思,但就是这样的不经意,使得萤火虫丧生。下面这段对话,将冲突暴露无遗:
秋虎从水中冒出脑袋后,指着在空中飞舞的萤火虫,大声地问爷爷:它们是你老子吗?
爷爷指着水中的秋虎:“我不准你再杀害它们!”
爷爷在说“杀害”这个词时,目光冷冷的,完全不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这个词让水中的秋虎哆嗦了一下,但很快笑了起来:“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飞虫,我才不在乎这些飞虫呢!”
爷爷站在船边,警告秋虎:“你要是跟它们过不去,我就跟你过不去;你要是一辈子跟它们过不去,我就一辈子跟你过不去!”
两个叔叔在黑暗中笑了起来。
可以看出,萤火虫对爷爷而言,意义非凡,它们是自己的救命朋友和小伙伴,需要用生命捍卫,不可以让任何人伤害。但对秋虎而言,萤火虫不过就是小小的飞虫,无所谓生命,可以用来取乐,也可以用来赚钱。成人只觉得这是孩子之间闹气,幼稚可笑。但二者的冲突反映的是如何看待生灵,如何看待自然的分歧:是将人视为世间主宰,天下万物,任我取用,还是尊重自然,尊重生灵平等的生存权利的分歧。这考量的不单单是孩子心性,更是关于大地伦理的探索。
二、和解的可能
在新小说系列中,这些被“抛弃”或者“隔离”的孩子往往钟爱高处:村哥儿爬上高高的风车顶上,等待妈妈回来;橡树站在祠堂的屋顶上,眺望整个村庄。眺望是源于内心的期待,也是源于对现实的无奈。等待,是他们共同的姿态。巧的是,孩子们登上高处,总会有一群大人替他担心,哄他下来,这一情节设置透露出作者内心对人性温暖底色的期许,在一个相对“极致”的情境下,人的恻隐之心会被唤起,这些孤独的孩子会得到一些关注。
橡树在自家低矮的茅屋中,总是感到沉重,他来到乌童家的草棚下,享受穿堂风,却被乌童爸爸撞见,引起怀疑,也打开了乌童的回忆。原来橡树曾经在乌童与众人走散的深夜,将乌童渡过河,并且陪伴乌童走过漫长的夜路。橡树帮助乌童,并非无心之举,而是注意到乌童没有回家,特意到渡口来接她。这个被众人冤屈、误解的小男孩对世界依然保有善意。但他被众人冤屈,却只能仰赖瓜丘的良心未泯。瓜丘表面上作恶多端,但其实也是一个大孩子。在被橡树拷住之后,大概是为了回家求救,瓜丘不顾一切将橡树拖向自己的方向,无意间却把橡树拖到了坟场,许是橡树讲起妈妈临终的嘱咐,唤醒了瓜丘的恻隐之心。天亮之后,瓜丘将自己偷的东西一一报出,洗清了橡树的冤屈。《穿堂风》故事情节非常单纯,孤独的男孩游离在人群之外,因为过往,因为父亲,因为陷害,被村民误会,他用勇敢和坚忍为自己洗清冤屈。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一个太单纯的故事。但故事中的意义与深度,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蝙蝠香》中,同伴发现了村哥儿的梦游,纷纷嘲笑他。村哥儿回家向爸爸求助,爸爸善意的谎言,本想要安慰村哥儿,却唤醒了村哥儿对田小童的怒火。村哥儿和田小童恶战,都觉得对方才是蝙蝠。二人越战越勇,田小童以“你妈妈不会回来”刺激村哥儿,村哥儿一震,不住摇晃:
村哥儿哭了起来,哭着哭着,泪眼模糊地望着田小童:“你妈妈也不会回来了!”
“我妈妈会回来的!”田小童说。
“我妈妈也会回来的!”村哥儿大声地说——不是说,而是喊叫。
不知为什么,两岸一片寂静。
樱桃低下头,无声地哭泣起来——樱桃的妈妈也已经有三年没回家了。
这一幕令人伤感。一群同样思念妈妈,渴望母爱的孩子彼此攻击,“你妈妈不会回来了”成为武器,他们本能地觉得这句话能最大程度击痛对方,却忘了它同样能够刺痛自己。他们打架,伤害彼此,但共同的伤痛为理解对方处境提供了可能,也为后文的和解埋下伏笔。
《萤王》中饭豆在漆黑的夜里意外落水,爷爷呼唤出草丛里成千上万的萤火虫结成亮光,帮忙搜寻饭豆:“萤火虫的亮光不一会儿就旋转到了搜救者们的上方,黑暗的大河被照得一片明亮……那片萤火虫的亮光在扩散着……爷爷的目光似乎看到了什么,拼命将船撑了过去!喝饱了水的饭豆已漂浮到水面上。”拯救饭豆,是萤火虫大放异彩的时刻。萤火虫拯救爷爷,许是出于偶然,但拯救“虫头”秋虎的儿子,萤火虫善到了极致,也美到了极致。爷爷与秋虎半辈子作对,但当饭豆危急时刻,爷爷却召唤出萤火虫救助饭豆,也给了秋虎一个转圜的机会。秋虎用萤火虫钓鱼是为了赚钱,收购萤火虫是为了赚钱,直到萤火虫救助了他的儿子,良知被唤醒,他也成为萤火虫的守护者。这个情节甚为巧妙,秋虎是虫头,萤火虫却以德报怨,救了他的儿子,故事发生翻转。
三、救赎或治愈
被众人冤屈,橡树起意报复,但对妈妈临终前的承诺再次提醒了他,他在妈妈的坟前倾诉委屈,同时完成了一个重要计划。他出其不意用手铐铐住瓜丘;瓜丘被铐住后,毒打橡树,想要逼出钥匙,但橡树咬着牙,绝不发出一声叫唤和呻吟,“在瓜丘的巴掌和拳头轮番向他打来时,他居然想起了奶奶,想起了妈妈,甚至还想起了爸爸。瓜丘有一拳打得特别狠,橡树觉得有点晕。模糊之中,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乌童家的草棚,心里莫名地升起一股渴望——渴望凉爽的穿堂风”。手铐将瓜丘和橡树牢牢拷在一起,瓜丘难以摆脱,最终招认。真相大白之后,橡树拒绝了乌童的邀请,选择去大河那边的寺庙,或许他需要更多时间去消化自己的委屈。乌童和其他孩子也一天到晚在田野上玩耍,“草棚下,穿堂风每天空空地、寂寞地吹过那条长长的过道……”空荡的草棚,寂寞的穿堂风,与开端草棚的热闹形成对照,余味无穷。这是一个以智慧与勇敢自我救赎的故事,也是一个通过抗争赢得认同和尊严的故事。
《蝙蝠香》中失明失聪的爸爸跟踪梦游的村哥儿出门,全靠迷迭香识别儿子的气息:“迷迭香的气味放佛一条光滑闪亮的绸带,一头抓在村哥儿的手上,一头抓在爸爸的手上。无数的蝙蝠陶醉在迷迭香精油的气味中,精灵一般地飞翔着……”此处的比喻将气味具象化,将情感具象化,跟着儿子的爸爸虽多次摔伤,却感到很神圣,很庄严,不时地有一种幸福感如暖流般涌满心田。这样的书写或许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亦实践了以艺术引领生活的主张。“爸爸总是赞美着妈妈——妈妈的一切。只要村哥儿和他坐一块儿,他就会面孔朝着天空,赞美妈妈,是由衷的,毫无条件的。爸爸没有怨恨,爸爸也不想村哥儿有怨恨。村哥儿不怨恨妈妈。”到创作中后期,曹文轩笔下的人物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极致,或许曹文轩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极致。通过曹文轩对废名《桥》的解读,可以尝试探索作者的意图:
读《桥》,没有浮躁感,没有灼热与冲动,而只觉得存在于一种恬静安宁的氛围里……即使是感情上有所失落,抑或是有什么灾难降临,人们也都没有跌落于疯狂的绝大的伤悲,而是以无声的眼泪或目光或以无语的姿态,让人觉察出一种空虚……人有一颗平常心,才能活得自如。有了平常心,就不会那么感情浓得化不开地待人接物,就不会把事情的实质夸张了看,就不会把天灾人祸看得多么了不得。
审美的态度使得笔下人物的哀痛和煎熬变得从容,不再那么强烈灼人。曹文轩的笔下并非没有激情和愤怒,只是激情和愤怒的表达克制含蓄,源自于对秀美感和静美感的追求。对待梦游这件事情,曹文轩也没有将它奇观化,而是让孩子们真正学会了平常心。“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鸭鸣村的孩子们渐渐地觉得,这样的日子再正常不过了,村哥儿夜游几乎是一件很好——甚至很美好的事情。”孩子们有了值班表,不分寒冬暑夏,保护村哥儿和他的爸爸,直到第二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之后,村哥儿不再梦游,不治而愈。
《萤王》爷爷8岁与萤火虫结缘,58岁离世,整整50年都在捍卫萤火虫,为此,他与小伙伴打架,为此,不惜与全村人作对,为此,他被关进铁窗。他对萤光心醉神迷,乃至最后成为传奇。他的一生是与自然亲密接触、神秘相和,与美同行,超然也寂寞的一生。他无意伤害任何人,但为了萤火虫,却多次陷入愤恨不平。他也曾经怯懦退缩,但那五只萤火虫,是他最初的梦,也是最终的执。直至他逝世的前几年,那些曾经一度被填平的湖泊又重新掘开,人类为自己的欲壑难填付出了代价,终于反省,努力进行补救。纵然一生坎坷,但爷爷坚信,只要有水、有草、有芦苇,就会有“小东西”。“小东西”这一昵称,就像叫自己的宠物、自己的孩子,一般亲切,透露了爷爷一生的执着。
四、 美的脆弱与坚韧
曹文轩很注重故事,但他的小说最有吸引力的往往不单是故事,故事的百转千回是初读时最大的动力,但情趣的清波荡漾才是一再重读的魅力所在。他笔下的风景不单单是目之所至,更从内心流淌而出。风景来自于有情趣、有雅趣的作者意味深长的凝视。
《蝙蝠香》中村哥儿的梦游不治而愈,难耐失眠的爸爸开始深夜走出门外,去寻找曾经的路线,曾经的幸福。村哥儿发现了爸爸的秘密,悄悄跟出门,陪伴爸爸。父子俩坐在大河边,一起唱:
“秋风起,草木黄/弯弯月下雁一行/夜半一声好凄惶/春去春又来/秋来秋又去/那人儿不知在何方/风一天,雨一天/鼓一遍,锣一遍/泪眼望,一条大河依旧空荡荡/云散去,念不断/坐村头,倚桥旁/却听得天边有人唱/草也唱,花也唱/音还在,人无影/愁煞了一个望断肠/问月吧,月不知/问鸟吧,鸟不晓/不知不晓那人却来入梦乡……”
这首歌颇有古典情韵,曾被妈妈、村哥儿、爸爸在不同情境下多次吟唱。妈妈唱它许是单纯的抒情,寄托忧思;爸爸、村哥儿的吟唱却有了具体的对象,承载着父子俩最深切的思念。他们来到妈妈坐船走的大河边,在深深的夜里,静静守望,陪伴他们的是蝙蝠香。深夜,父子俩唱着同一首歌,思念着那个美丽的女人,她是妻子,也是妈妈,但是作者并不愿对她进行任何的道德审判。“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则可获得一种道德效果:宽容……小说家应当看到世界的无限多重与道德观的时空性,从而至少保持住一种沉稳的、温和的叙述。”这就使得人物的思念不仅获得道德同情,也获得审美同情。
“美”有时候也会招惹无妄之灾,城里人的婚礼要用萤光制造浪漫,捕捉萤火虫借此赚钱的是一群孩子。在孩子眼中飞舞的萤火虫不再是美丽的生灵,点点萤光是硬币的闪光,在金钱面前,孩子们丧失了审美的乐趣与心情。爷爷为此心痛,与孩子们周旋、斗争,之后为了守护萤火虫,爷爷破坏了城里人的推土机,被关进铁窗,几只萤火虫赶来“探望”,倔强的爷爷愤恨不平,为萤火虫喊冤。爷爷真诚地认为众生平等,在乎与萤火虫的情意,萤火虫的美感,他无法理解人为什么要抢占萤火虫的生存空间,剥夺萤火虫的生命。他是耽溺于美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现实逻辑和丛林法则,或许也知道一些,但始终无法理解,更不能认同。
曹文轩写《海牛》,要以征服剽悍的海牛,来完成少年的成长,《萤王》中的爷爷显然与此不同;同时,与桑桑的调皮机灵,杜小康的优秀坚韧,细马的倔强凶悍相比,爷爷柔软了许多,他会因为在冬日里思念萤火虫而哭,用冰碴儿模仿萤火虫的亮光:
那轮白色的“玉盘”才升起一半,天地间就充满光华。草丛中、芦苇中,彷佛布置了成千上万盏小灯,月光只轻轻一照,一瞬间就将它们统统点亮了,星星点点,闪闪烁烁。别说是爷爷,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一情景,都会立即想到被萤火虫照亮草丛、芦苇丛的夏日傍晚。
爷爷的浪漫情怀再次呈现,用冰碴儿的亮光模拟荧光,亦属巧思。曹文轩似乎对冰颇为偏爱,青铜就曾经用冰为葵花制作了一串冰项链:“灯光下,那串冰项链所散射出来的变幻不定的亮光,比在阳光下还要迷人。谁也不清楚葵花脖子上戴着的究竟是一串什么样的项链。但它美丽的、纯净的、神秘而华贵的亮光,震住了所有在场的人。”冰带来惊喜,这是美的光芒与力量。因为萤火虫的美,爷爷感到来到这个世间是值得的,美成为爷爷最重要的生存意义:“想想你能一辈子,每年到了夏天,都能看到这些小东西,你一定会在心里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很值得的……”这其实亦是曹文轩一贯的艺术主张,“在我看来,美的力量常常要比政治的、伦理的力量深刻和长久……”正是琳琅美景、种种美好的事物让人觉得人世间值得一活。
萤火虫在小说中是美与善的化身,萤王成为美与善的守护者。沈从文曾经讲过,“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留在一种婴儿状态中”。其实爷爷为萤火虫着迷的时刻,他的情绪也停在了“婴儿状态”。婴儿状态是人的原生状态。它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与那烂熟的成年状态相比,它更多一些朴质无华的天性,更多一些可爱的稚拙和迷人的纯情。“美”难免被现实逻辑蚕食,这番稚拙与纯情却使其坚韧存在,且生生不息。
曹文轩认为:与前人相比,现代化的环境使人们少了许多人情味,也少了许多由村社生活、田园生活养成的情趣。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文学)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儿童小说应当往培养儿童的优雅情趣和宁静性格方面多做一点文章,使他们获得一片明净的世界,使他们不至于全部丢失从前的淳朴的伦理观念。《萤王》美的力量颇为奇幻,小说中彰显的依然是田园生活的伦理价值,及其所面临的冲击和遭遇的困境。如果说《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描绘的都是相对封闭的自足的田园,那么在“新小说”中,田园被打开,面临资本的冲击。田园日益破碎,但美依然有种恒定的力量。
在作品中,曹文轩很少直面当下现实进行发言,或者是对当下过于拘谨地进行描摹。他的目光穿过历史,去描摹昔日的爱与痛,悲与歌,但并非为了缅怀往事,而着力于追随永恒。现实主义更多是种精神,而不拘泥于故事的讲述。故事的背后是经验,是体悟。温情与苦难并行不悖,正是在苦难、在沉重中,人性绽放出最璀璨的花朵。
注释:
[1][3][4][11]曹文轩.穿堂风[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7:133,10,57,121.
[2][14][21][22]曹文轩经典作家十五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3,39—40,43,44.
[5][9][12][13][15][16]曹文轩.蝙蝠香[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7:9,98—99,42,120,122,130-131.
[6][7][8][10][18][20]曹文轩.萤王[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8:19,37,74,146,84,87.
[17]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31—232.
[19]曹文轩.青铜葵花[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1:156.
[23]曹文轩.曹文轩论儿童文学[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