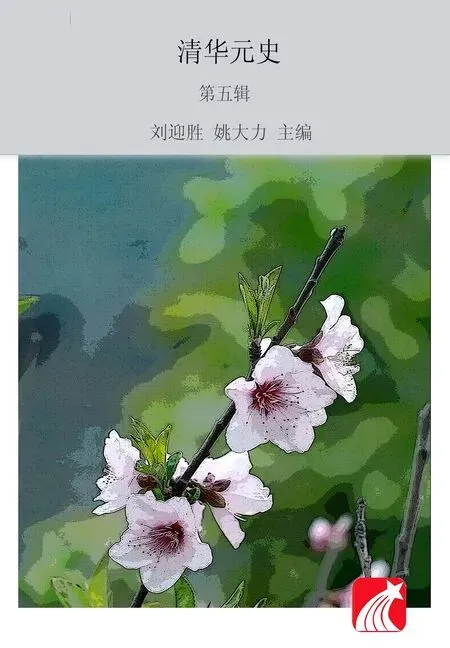元朝的宣赦仪式
——兼与唐、宋、金诸朝比较*
王敬松
中国古代的赦免有多种类型,然其规模最大、对象与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者乃属大赦。元朝同样。在元朝资料中,大赦有三种提法,一种称“大赦天下”,有时也简称为“大赦”。这也是社会上最常见的称呼。一种提法称“赦天下”。需要说一点的是,清朝法学家沈家本先生在《历代刑法考》中将“赦天下”一概简称为“赦”,而且单立,不统计立“大赦”数目内[1]参见《沈家本全集》第三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444 页。,意为其与大赦不同。这是沈氏的误解。“赦天下”同于大赦,只是名称稍异。不仅元朝如此,唐朝即有制名为赦天下而内容是大赦的诏令。[2]如唐玄宗开元五年五月《巡幸东都赐赉扈从赦天下制》,制名为“赦天下”,文内则为“大赦天下”。参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79,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54 页。还有一种是“肆赦”。肆赦皆用于代称大赦或赦天下,不过,元朝诏赦等正式文件中,一般不使用“肆赦”一词。为一致起见,本文均以“大赦”概言之。
一次大赦一般有以下几个程序,如提出(建议)与决定大赦,撰写大赦诏书,讨论研究(集议)赦免之外的其他条文,颁布大赦诏书,大赦的执行,以及对执行中出现问题的追究与解决等。宣赦,即大赦诏书的颁布。大赦不仅覆盖全国,涉及罪囚及其亲属、社会关系等众多人员,而且不同背景的大赦,与国家的政治(如皇位更替)、社会、经济、司法、军事形势等各方面都有一定或者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宣赦,则是大赦从酝酿到实施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也是由高层密室操作到向社会公开的最后环节,自然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
汉朝是中国古代大赦开始盛行的王朝,宣赦随之产生。史载:汉朝“践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谋反、大逆不道诸不当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复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传驾行郡国,解囚徒,布诏书。郡国各分遣吏传厩车马,行属县,解囚徒”[1]李昉:《太平御览》卷652《刑法部十八·汉旧仪》,上海涵芬楼本。。帝国疆域广大,受当时交通、信息传递条件所限制,这条材料概括提示了汉帝国政府赴郡国宣赦的官员官职,地方政府逐级宣赦的体制;但是,材料中没有提及在首都宣赦的情况。当知,汉朝似没有这一仪式。此后,首都的宣赦仪式出现并且渐次趋繁。从北朝时期,尤其是从唐朝开始,首都的宣赦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而赴地方传达赦令的程序则相对比较简略,宋朝的情况亦大体相同。到元朝则反之,在大都宣赦极为简单,而有关赴地方宣赦的程序则较为繁复。可以说,唐、宋二朝的宣赦仪式,是隆于中(首都)而简于外(地方),而元朝则是隆于外(地方)而简于中(首都)。金朝则是对中外宣赦皆重视。
还要说明一点。大赦,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赦包含在皇帝诏书之中,它只是皇帝诏书的内容之一;另一种情况是为某一重大事项,皇帝专门实施大赦。前者中,最突出的如皇帝即位。元朝皇帝即位诏书中多提出实施大赦。由于元朝制定有专门的“皇帝即位受朝仪”,规定“侍仪使以诏授左司郎中,郎中跪受,通译史稍西,升木榻,东向宣读。通赞赞曰:‘在位官皆跪。’读诏,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 。皇帝即位的“次日,以诏颁行” 。[1]《元史》卷67《礼乐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就是说,此类大赦条文是与该诏书一同颁布,而非单独进行。后者中,如战争获得胜利(如忽必烈灭宋朝、征乃颜之战等),灾异频仍(元代灾异频发,因灾异而实施大赦屡见不鲜。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此不赘)等。这种大赦自然是单独发布大赦诏书。本文所谈的宣赦,多指此。因为前者,诏书中有多方面的内容,且有规定的仪式,虽然隆重,然重点在庆贺皇帝登极等,而非单纯的大赦。当然,在行文中,前者的某些内容也会被涉及。
关于元朝的宣赦仪式,至今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在与唐、宋、金诸王朝的宣赦仪式相比较之同时,着重叙述元朝在大都和派员赴地方宣赦的仪式以及有关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与读者指正。
一、在首都的宣赦仪式
(一)唐、宋、金诸朝宣赦“中繁”
唐。《唐六典》云:“凡国有赦宥之事,先集囚徒于阙下,命卫尉树金鸡,待宣制讫,乃释之。”[2]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尚书刑部》卷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2页;又《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旧唐书》、《通典》又记载道:“其有赦之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宫城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讫,宣诏而释之。”[1]《旧唐书》卷50《刑法志》;杜佑:《通典》卷169《刑七·赦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7 页。仪式是:
其日质明,本司承诏宣告内外,随职供办守宫设文武群官次于朝堂如常仪,群官依时刻皆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礼设文武群官次版位于顺天门东西,当朝堂之南,文东武西,重行北面相对为首,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南向。……[2]省略号部分见本节后文。宋、金部分同。通事舍人引群官各就位,中书令受诏讫,遂以诏书置于案,令史二人对举案,通事舍人引中书令持幡节者前导,持案者次之,诣门外位立,持节者立于中书令之南少西,令史举案者于中书令西北,俱东面立定,持节者取节衣,持案者进诣中书令前,中书令取诏书,持案者以案退,复位,中书令称宣诏,群官皆再拜。宣诏讫,群官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刑部尚书七受诏书,退复位。持节者加节衣,通事舍人引中书令幡节前导而入。通事舍人引群官还次。[3]《通典》卷130《礼·宣赦书》,第681 页。
宋。宋朝因为皇帝亲自出席宣赦,故其仪式比唐朝为繁复、庄严。《宋史》载:
御楼肆赦。每郊祀前一日,有司设百官、亲王、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位宣德门外,太常设宫县、钲鼓。其日,刑部录诸囚以俟。驾还至宣德门内幄次,改常服,群臣就位,帝登楼御坐,枢密使、宣徽使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楼上以朱丝绳贯木鹤,仙人乘之,奉制书循绳而下,至地,以画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案上。阁门使承旨引案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百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付刑部侍郎承旨放囚,百官称贺。阁门使进诣前,承旨宣答讫,百官又再拜、舞蹈,退。若德音、赦书自内出者,并如文德殿宣制之仪。其降御札,亦阁门使跪授殿门外置箱中,百官班定,阁门授宰臣读讫,传告,百僚皆拜舞称万岁。真宗宣制,有司请用仪仗四千人,自承天殿设细仗导卫,近臣起居讫,则分左右前导之。
至徽宗,“初建明堂,礼制局列上七议”[1]《宋史》卷117《礼志二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
金。据《金史·礼志九》,金国制定有专门的《肆赦仪》与《臣下拜赦诏仪》,详细规定了肆赦及拜赦的种种程序。在宣赦的当天,分别举行肆赦与臣下拜赦两种仪式,皇帝、皇太子均出席肆赦仪,其后,皇太子还出席臣下拜赦诏仪。故,金国的宣赦仪式比唐、宋更为隆重繁冗。
《金史》记载大定七年(1167)、十一年(1171),两次在应天门颁赦。其仪式为:
前期,宣徽院使率其属,陈设应天门之内外,设御座于应天门上,又设更衣御幄于大安殿门外稍东,南向。阁门使设捧制书箱案于御座之左。……又设捧制书木鹤仙人一,以红绳贯之,引以辘轳,置于御前栏干上。又设承鹤画台于楼下正中,台以弩手四人对举。大乐署设宫县于楼下,又设鼓一于宫县之左稍北,东向。兵部立黄麾仗于门外。刑部、御史台、大兴府以囚徒集于左仗外。御史台、阁门司设文武百官位于楼下,东西相向。又设典仪位于门下稍东,西向。宣徽院设承受制书案于画台之前。又设皇太子侍立褥位于门下稍东,西向。又设皇太子致贺褥位于百官班前。又设协律郎位于楼上前楹稍东,西向。尚书省委所司设宣制书位于百官班之北稍东,西向。司天台设鸡唱生于东阙楼之上。尚衣局备皇帝常服,如常日视朝之服。尚辇设辇于更衣御幄之前。
躬谢礼毕,皇帝乘金辂入应天门,至幄次前,侍中俯伏,跪奏:“请降辂入幄。”俯伏,兴。皇帝降辂入幄,帘降。少顷,侍中奏:“中严。”又少顷,俟典赞仪引皇太子就门下侍立位,通事人引群官就门下分班相向立,侍中奏:“外办。”皇帝服常朝服,尚辇进辇,侍中奏:“请升辇。”伞扇侍卫如常仪,由左翔龙门踏道升应天门,至御座东,侍中奏:“请降辇升座。”宫县乐作。所司索扇(五十柄),扇合,皇帝临轩即御座,楼下鸣鞭,帘卷扇开,执御伞者张于轩前以障日,乐止。东上阁门使捧制书置于箱,阁门舍人二员从,以俟引绳降木鹤仙人。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宫县乐作。凡分班、合班则乐作,立定即止。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分班相向立。
……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楼上乘鹤仙人捧制书,循绳而下至画台,阁使奉承置于案。阁门舍人四员举案,又二员对捧制书,阁使引至班前,西向称:“有制。”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讫,以制书授尚书省长官,稍前搢笏,跪受,讫,以付右司官,右司官搢笏,跪受,讫,长官出笏,俯伏,兴,退复位。右司官捧制书诣宣制位,都事对捧,宣右司官读,至“咸赦除之”。所司帅狱吏引罪人诣班南,北向,躬称:“脱枷。”讫,三呼“万岁”,以罪人过。右司官宣制讫,西向,以制书授刑部官。跪受讫,以制书加于笏上,退以付其属,归本班。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又再拜。
典赞仪引皇太子至班前褥位立定,典仪曰:“拜。”皇太子以下群官皆再拜。典赞仪引皇太子稍前,俯伏,跪致词,俯伏,兴。典仪曰:“再拜。”皇太子以下群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侍中于御座前承旨,退临轩宣曰:“有制。”典仪曰:“再拜。”皇太子以下群官皆再拜。侍中宣答,宣讫归侍位,典仪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典赞仪引皇太子至门下褥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分班相向立。侍中诣御座前,俯伏,跪奏:“礼毕。”俯伏,兴,退复位。所司索扇,宫县乐作,扇合,帘降,皇帝降座,乐止。楼下鸣鞭,皇帝乘辇还内,伞扇侍卫如常仪。侍中奏:“解严。”通事舍人承敕,群臣各还次,将士各还本所。
皇太子出席的“臣下拜赦诏仪”为:
宣赦日,于应天门外设香案,及设香舆于案前,又于东侧设卓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定。阁门官于箱内捧赦书出门置于案。阁门官案东立,南向称:“有敕。”赞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讫,复位,皆再拜。阁门官取赦书授尚书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书省令史二人齐捧,同升于卓子读,在位官皆跪听,读讫,赦书置于案,都事复位。皇太子宰臣百僚以下再拜,搢笏,舞蹈,执笏,俯伏,兴,再拜。拱卫直以下三称“万岁”,讫,退。其降诸书,礼亦准此,惟不称“万岁”。[1]《金史》卷36《礼志九》 ,中华书局1975年版。
这两条材料说明,金国的肆赦仪,主要是皇帝颁布大赦诏书,释放罪囚,显示皇帝的威严与恩德。臣下拜赦诏仪,则是由皇太子代表皇帝向尚书省宣读、交付赦书,由尚书省予以实施。
归纳以上,唐、宋、金诸朝在首都宣赦有以下特点。
首先,宣赦是一个隆重而严肃的大场面,还是一个准开放性的集会。帝制时代,由于政治等因素制约,有民众参加的规模聚会是极为罕见的,而唐、宋、金在首都的宣赦仪式,恐怕是少有的例外。
其次,既然是仪式,对颁赦的地点、程序、参加的文武官吏、宣读赦书的官员、相关官吏在颁赦仪式中的职责与站立的位置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形式庄严且固定。如仪式举行地点,宋朝宣赦始初多是在文德殿,徽宗后改在御楼,而在明堂宣读赦书。“徽宗初建明堂,礼制局列上七议……七曰:赦书、德音,旧制宣于文德殿,自今非御楼肆赦,并于明堂宣读。”[2]《宋史》卷117《礼志二十》。金国宣赦一般在应天门举行。[3]金末哀宗也在端门举行。如“开兴元年五月庚子,御端门肆赦,改元开兴” 。参见《金史》卷17《哀宗纪上》。宋、金时,肆赦与宣读赦书,乃分开地点,或者分开场合举行。皇帝、皇太子均亲自参加宣赦仪式,这是金国宣赦仪式的一大特点。另外,宋朝除颁布大赦令外,发布德音等视同大赦,也举行同样的仪式,这是与唐、金不同之处。
再次,集中待赦囚犯于宣赦现场的特定区域。唐初,将“大理及府县徒囚”均集中于宣赦现场;后,据《通典》记载,宣赦现场集中的只是在京师关押的待赦囚徒,“遂击鼓,每击投一过,刑部侍郎录京师见囚集于群官之南北面,西上,囚集讫,鼓止”。宋、金始初即集中关押京师的待赦罪囚。宣赦仪式结束时,囚徒脱去刑械,当场释放。
最后,要提到的是树金鸡。这是宣赦现场的一个标志性程序。
唐朝在宣赦现场,由“刑部侍郎帅其属官陈金鸡于西。朝堂之东南向置鼓杖于金鸡之南”。《封氏闻见记》记载:“国有大赦,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武库令掌其事。鸡以黄金为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毕则除之。凡建金鸡,则先置鼓于宫城门之左,视大理及府县徒囚至,则捶其鼓。”[1]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4《金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 页。
宋时,“舍人诣楼前,侍臣宣敕立金鸡。舍人退诣班南,宣付所司讫,太常击鼓集囚。少府监立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末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幡,获者即与之”[2]《宋史》卷117《礼志二十》。。
金时,“少府监设鸡竿于楼下之左,竿上置大盘,盘中置金鸡,鸡口衔绛幡,幡上金书‘大赦天下’四字,卷而衔之。盘四面近边安四大铁环,盘底四面近边悬四大朱索,以备四伎人攀缘”。在宣赦仪式进行中,“侍中诣御座前承旨,退,稍前南向,宣曰:‘奉敕树金鸡。’通事舍人于门下稍前东向,宣曰:‘奉敕树金鸡’。退复位”。“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树讫鼓止。竿木伎人四人,缘绳争上竿,取鸡所衔绛幡,展示讫,三呼‘万岁’。”[1]《金史》卷36《礼志九》。
宣赦时树竿立鸡之制,由来已久,说法不一。唐人封演说:“金鸡,魏晋以前无闻焉。或云‘始自后魏’,亦云‘起自吕光’。盖自隋唐废此官而卫尉掌之。”[2]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4《金鸡》,第29 页。一种观点认为始于北齐。《隋书·百官志》云:“北齐尚书省有三公曹,赦则掌建金鸡。”《通典·刑法典》:“北齐,赦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脱枷锁,遣之。” “北齐每有赦宥,则于阊门前树金鸡,三日而止。万人竞就金鸡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越数日间,遂成坑,所司亦不能禁。”也有观点认为始于西凉国。《宋史》载:“金鸡事,六朝已有之,或谓起于西凉。”宋人曾慥《类说》也记载大赦建金鸡可能始于西凉吕光。[3]参见于赓哲、吕博:《浅谈中古放赦文化的象征—金鸡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 期。吕光先为前秦苻坚将领;公元396年,吕光建国大凉,即后凉。
至于树金鸡的含义,也有不同看法。多认为源于卦易五行学说或星象学关于鸡的寓意。如北齐武帝高湛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设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光禄大夫司马膺之,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鸡星动,必当其赦’。由是赦以鸡为候。其后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先是有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祖孝徽与和士开谮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言孝琬为天子,建金鸡也。’齐王信之,而杀孝琬。则天封嵩岳,大赦,改元万岁登封。坛南有大檞树,树杪置金鸡,因名树为金鸡树。”[1]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4《金鸡》,第30 页。这是将金鸡与帝王联系在一起。《杨文公谈苑》曰:“究其旨盖西方主兑,兑为泽,鸡者巽神。巽主号令,故合二物置其形于长竿,使众者睹之。”《宋史·仪卫志》载:“其义则鸡为巽神,巽主号令,故宣号令则象之。阳用事则鸡鸣,故布宣阳泽则象之。”吕光据有西部,依据阴阳五行学说,“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因此将二者合一,树金鸡于长竿,观者即皆知此乃君主发号施令的象征。从基本意义上说,树金鸡是权力的体现,并非单为大赦而立。然新皇帝即位时多实施大赦,故大赦用金鸡乃成为皇位及政权更替的象征。[2]于赓哲、吕博前揭文。金鸡之金,似非单指金饰,乃有五行之金的含义。[3]参见葛承雍:《唐代金鸡风俗考》,台北《历史月刊》1993年第11 期。
此后,金鸡逐渐成为大赦的代称。在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中,金鸡还被作为大赦的形象比喻而出现。如李白在其《秦女休行》一诗中写道:“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安史之乱后,李白因追随永王李璘而卷入唐王室的权力争斗。乾元元年(758) 春天,李璘被肃宗李亨所败,李白因站错队获罪,在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巫山),曾作诗《流夜郎赠辛判官》曰:“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4]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李白集校注》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75、854 页。李白以盼金鸡比喻希望早日获得赦免的心情。宋陆游在《迎赦呈王志夫李德孺师伯浑》诗中也写道:“平明置骑传诏函,帝意欲与东皇参。青城回仗国人喜,金鸡衔赦天恩覃。”[1]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一)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 页。
(二)元朝宣赦“中简”
到了元朝,在首都的宣赦仪式发生变化。
涉及元朝在大都宣赦的官方规定,现在只看到两点:一是关于公服,一是关于官员站位。
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太保刘秉忠及王磐、徒单公履等提议并得忽必烈同意,令:
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各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2]《元史》卷8《世祖纪五》。
这是史料中与大都宣赦有关的第一条规定,它是与元正、朝会、圣节、宣敕官员诸场合并列,一起要求的。内容只有一项:着公服,即在迎拜官员的服装上提出规范。显然,此前在举行上述活动时,官员们的着装不统一。
公服规制一般包括服装的材质、式样、颜色、纹饰,还包括头饰、腰带、笏、靴等。官员依照不同品级、官职,着官方规定的不同公服。公服是官员职务、品级的体现,元朝的公服,与其他此前的朝代一样,按官员品级予以区分:
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
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
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见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
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
笏,制以牙,上圆下方。或以银杏木为之。
偏带,正从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黄金为荔枝。五品以下以乌犀。并八胯,鞓用朱革。
靴,以皂皮为之。[1]《元史》卷78《舆服志一》。
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确定了军官系统的公服系列。是年闰二月,枢密院提出“军官服色,未见定到体例”。中书省交礼部与太常寺、翰林国史院的官员共同商议,其意见是,“故太保相公、老的每商量来,奏准文资官定例三等服色,军官再行定夺。今收附诸国数年,所据军官,拟合依随朝官员体制造”。中书省批准了这几个部门的协商意见,并下文依此施行。具体为:
公服:俱右纴。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一品:紫罗服。大独科花,直径五寸。二品:紫罗服。小独科花,直径三寸。三品:紫罗服。散答花—谓无枝叶,直径二寸。四品、五品: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服。无纹罗。
偏带:俱系红鞓。一品:玉带。二品:花犀带。三品、四品:荔枝金带。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俱乌犀角带。[1]《元典章》卷29《礼部二》“文武品从服带”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关于公服的性质,下面一件事可以表明:
皇庆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中书省、御史台呈:皇庆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本台官朵儿赤中丞等奏,“殿中司文字里说有,昨前拜年时分,徽政院里佥院忽都小名的人,皇帝根底拜了之后,大殿里穿着公服,月鲁帖木儿知院根底跪着与手帕来。俺商量来,穿公服与人厮跪呵,无体例一般。俺省家与文字教立个体例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礼部议得:公服乃臣子朝君之礼。今后百官凡遇正旦朝贺,候行大礼毕,脱去公服,方许与人相贺。都省准拟。[2]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8“公服私贺”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 页。
即公服不同于一般的官服,“乃臣子朝君之礼”,故参加朝仪和其他仪式之后,必须脱去,方可进行其他活动。金国似没有公服与官服之别。[3]《金史》卷43《舆服志》。
公服的制作费用,分为自费、公费两种。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十五日,斡耳朵里奏准:“每遇圣节、元日、诏赦并各官受宣敕,除沿边把军官再行定夺外,诸路官员合无令各官照依品从,自造公服,迎拜行礼。”大德四年(1300)十二月二十四日,御史台奏:“四怯薛行礼,怯薛歹每合穿的公服、窄紫关了,行罢礼合,都不来纳有。”奏呵,奉圣旨:“今后行罢礼呵,限三个日头不纳呵,柒棒子家打者。百官每借的公服,都教纳者。”[1]《至正条格》卷3《断例·回纳公服稽缓》,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07年版。从上述材料可知,公服自费制作,主要是地方官员。而参加相关仪式的四怯薛,其公服须在活动结束后三日内缴公,否则要挨棒子。既然要求缴公,当是由公款制作。官员借穿的公服,用后也要缴还,这应该是指中央机关的官员。
对违犯规定的官员,还要予以惩处。如至元四年(1267)三月,御史台呈:“侍仪司典簿章国仁,听读诏书,不入班次行礼,僭用紫服金带。量笞肆拾柒下,解任标附。”都省准拟。[2]《至正条格》卷3《断例·僭用朝服》。侍仪司为礼部下属机构,正四品,职掌“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 ,典簿为其首领官,从七品。[3]《元史》卷85《百官志一》。而章国仁以侍仪司七品首领官之职,却执法犯法,“紫服金带”。紫服为一品官员公服的颜色,金带是三四品官员佩戴的标志。章国仁僭用,自然要受到惩罚。又如英宗即位初,铁木迭儿嫉恨上都留守贺伯颜“素不附己”,乃奏英宗“下五府杂治,竟杀之”,罪名就是“以便服迎诏”。[4]《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位,五月贺伯颜被杀)虽然一般认为,权臣铁木迭儿杀贺伯颜,是公报私仇,可毕竟找到了“以便服迎诏”的借口。
上面说的主要是汉人官员的公服。在朝见皇帝时,蒙古官员(如四怯薛等),如前所述,亦当着公服。他们着的是不是只孙服?史料多处表明,只孙服是蒙古王公大臣出席皇帝举行的重大宴会的服装。故这个问题尚须另外讨论。
这是第一个问题。到元中期文宗朝,官方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官员的站位。
元统二年(1334)二月,礼部呈:“监察御史言:‘今后凡遇朝贺行礼、听读诏赦礼,先省部、院、台,次及百司,依职事等第、官品正从,以就序列。敢有不遵,比同失仪论坐,标附。’”都省准拟。[1]《至正条格》卷3《断例·失仪》。礼部提出并得到中书省批准的这个规定,也只有一项,即提到在朝贺行礼、听读诏赦时,官员的站立、排列顺序问题。其原则是按照官府的职事等第、与官员品级的正从,即从官府、官员两个方面确定官员在听宣赦时的站位。有违反,同失仪论。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忽必烈即位初期的情况。至元八年(1271)四月二十四日,监察御史魏初在奏议中写道:“自祖宗开国以来,其创法立制,至陛下为最备,故外域远方,企仰朝廷,以为中朝礼义之国。昨闻御前食肉,负者裸形舞唱,恐非所以正朝廷、待臣下、尊天子之礼也。自今御前不可作此戏举,务存大体,天下幸甚。”[2]魏初:《青崖集》卷4《奏议》,《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本。与此前后,翰林学士承旨兼太常卿王磐也不客气地指出朝仪场合秩序混乱的情况:“时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虑为外国耻笑,王磐上奏忽必烈曰:“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谓之阑入,由外及内,罪轻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得进。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纠察罚俸;不应入而入者,宜准阑入治罪,庶几朝廷礼肃。”“后遂定朝仪如公言。”[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忠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3 页。魏初、王磐可以说描绘了中统与至元年间早期,忽必烈帐殿内外的“无序”景象。
自至元六年(1269)始,各种朝仪制度开始相继建立。至元八年(1271)八月,以忽必烈生日天寿节为发端,开始实施朝仪制度。各项朝仪中毫无疑问都包括官员站位问题。皇庆二年(1313)十二月,御史台在奏文中就写道:“皇帝根底行礼间,但有失仪的,依例罚中统钞捌两。上殿去时,各依资次,不教紊乱。扎撒孙、监察御史好生整治行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2]《至正条格》卷3《断例·失仪》。“上殿去时,各依资次,不教紊乱。”仁宗重申了官员站位的要求,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官员失仪受罚的钞锭数额。
所以笔者认为,前面所提到的文宗时期的规定,恐怕不是最初的规定。另外,宣赦在此前已非一次两次,宣赦时官员的站位问题,不可能到此时才提出,规定至此时才建立。
不过,直至元末,元初的“无序”状况虽然大有改观,但官员公服、站位的失仪情况仍时有出现。元统二年(1334)十月,顺帝仍在要求“内外官朝会仪班次,一依品位” 。至正年间任监察御史的苏天爵谈到举行朝仪时的问题时,仍指出官员不按规定着装、不分级别站位等问题:“迩年以来,朝仪虽设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为衣紫;从五与正五杂居,共曰服绯,七品与六品齐列。下至八品、九品,盖亦莫不皆然。夫既逾越班制,遂致行列不端,因忘肃敬之心,殊失朝仪之礼。”并提出建议:“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先尽省、部、台正从二品衙门,次即诸司、局、院,各验执事散官序列,正从班次。如有逾越品秩,差乱位序者,同失仪论,以惩不恪。”[1]苏天爵撰,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26《请详定朝仪班序》,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0 页。顺帝从之,“至是复正朝会班次焉”[2]《元史》卷83《顺帝纪一》。。朝会班次问题,是不是顺帝这一次就彻底纠正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率越班行,均为衣紫。”可以说,元朝在朝堂称贺、听宣赦时的官员着服、站位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
除了前述的官方记载外,下面的两条材料提示出了宣赦的地点等。
一条材料是张昱《辇下曲》中的一首,它也涉及宣赦的地点等。该诗文是:
崇天门下听宣赦,万姓欢呼万岁声。
岂独罪人蒙大宥,普天率土尽关情。[3]《张光弼诗集》卷3《辇下曲》,《四部丛刊续编》本。
张昱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光弼。他先任职于元朝中央政府机关,曾为宣政院判官。后任地方官员。元末至正中期,参加与红巾军战事,领军者败亡后,张即退隐西湖。明初卒。张昱自述这些诗作,乃“据事直书,辞包鄙近。虽不足以上继风雅,然一代之典礼存焉”[4]《张光弼诗集》卷3《辇下曲》。。另一条材料涉及忽必烈时期的一场地震。至元二十七年(1290)癸巳八月(10月4日),武平发生大地震。《元史》载:“地大震,武平尤甚。压死按察司官及总管府官王连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坏仓库局四百八十间,民居不可胜计。”[5]《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九月地震再次发生,“武平地震,盗贼乘隙剽窃,民愈忧恐。平章政事铁木儿以便宜蠲租赋,罢商税,弛酒禁,斩为盗者,发钞八百四十锭,转海运米万石以赈之”。随即,忽必烈宣布赦天下。[1]《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佛祖历代通载》仅记为“庚寅九月日大赦”。《佛祖历代通载》卷2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77),第449 页。庚寅年即至元二十七年。武平路原名北京路,后改为大宁路,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武平路,后复为大宁路(今为内蒙古赤峰宁城县)。
关于地震的起因,众多材料皆归罪于权臣桑葛的财政政策。“是年尚书省以民间逋负系官钱粮,速哥(即桑葛)奏立征理司,设官置吏,使轺将命者旁午于道,所在贪墨吏并缘为奸,欺民赀产破荡不足偿,至榜系犹累累相属,民间骚然,几无以存活。时彗星见方扫,扫宿指处,山崩地震。上春秋高,权奸方务蔽塞聪明,而其威焰轧天下,人怀私愤无敢为言者。”时忽必烈在柳林,任嘉议大夫、知秘书监的岳铉即上奏言:“今天垂象,星耀光芒,地震动,坤道失其常,况皇上圣躬违和,皆大臣欺圣明,虐黎庶所致,非除旧布新洗濯苛秽,则何以回天心释民怨?”于是,忽必烈“即柳林命词臣草诏,大赦天下。北使臣驰至阙,命百官具朝服诣崇文门听德音”[2]郑元祐:《侨吴集》卷12《岳铉第二行状》,北京图书馆藏明弘治九年刻本。。
关于这次大赦赦书起草的过程等,有的材料记述与此不同。由于与本文无涉,故不赘述。[3]不同的记载内容为:大赦是时在大都的赵孟頫最初提出,经由阿剌浑撒里密报忽必烈,获得同意后,由赵孟頫在都省向两院诸公宣读赦书草稿。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赦免条款遭桑葛反对,经激辩后桑葛改变立场,后即颁布。杨载:《赵孟頫行状》,见赵孟頫:《松雪斋文集》;欧阳玄:《赵孟頫神道碑》,见欧阳玄:《圭斋集》卷9,及《元史》卷172《赵孟頫传》。而上引材料则说,仅由“词臣”在忽必烈驻地柳林草诏赦书,等等。但这条材料提到了大都宣赦的地点:崇文门,同时提及宣赦时“百官参加”,这两点很重要。
比较二者,张诗为“崇天门”,《岳铉第二行状》则说颁布大赦令在“崇文门”,二者明显不一致。崇天门“正南出周桥。灵星三门外分三道,中千步廊街。出丽正门,门有三。正中惟车驾行幸郊坛则开。西一门,亦不开。止东一门,以通车马往来”[1]《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 页。。“崇天门”居元大都宫城南墙三门的中央,也叫午门。[2]参见陈高华、史为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6 页。“崇文门”则在大都城南三门之一的文明门之南。[3]陈高华、史为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第41 页。既然由百官听宣赦,不可能在外城,故应该是“崇天门”。著名学者陈学霖先生对此诗的解释是:“描述在宫城中央之崇天门(一称午门)下听闻皇帝颁发诏旨的情况。”[4]陈学霖:《张昱〈辇下曲〉与元大都史料》,《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94 页。张昱的诗为概述,而《岳铉第二行状》所指的就是该次大赦。说明崇天门是元朝政府向众大臣与社会宣读诏赦的地点。
综上,元朝在首都举行的宣赦,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宣赦时,使用两种语言宣布,先“国语”后汉语。国语,即以忽必烈前期开始推行的八思巴文为文本的蒙古语。前引“皇帝即位受朝仪”言,宣读即位诏书时“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单独举行的宣赦会议是否也如此呢?史无明载,不过可举一例作为旁证。泰定三年(1326)十二月二十日,泰定帝大赦。前一天即十九日夜,中书省平章政事乌伯都剌召开紧急会议,说,帝将大赦,宣赦诏书“盖两相亲草,已经御览”,今晚的会议只是要求将赦书 “译为华言而已”,于是“一夜译成”,“明日,竟降诏赦”。[1]宋褧:《燕石集》卷15《宋本行状》,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可知,宣赦依然需要两种语言,其顺序也是先国语后汉语。如果不是语言问题,或许这场深夜会议就不需要召开。
第二,宣赦不在朝仪之列。《元史》载:
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2]《元史》卷67《礼乐志一》。
朝仪包括于国家有重大意义与影响的皇帝及皇室活动。皇帝、皇太子(元朝立皇太子的次数不多)不参加宣赦仪式,故在首都的宣赦并没有被包含在这些众多的“朝会之仪”之中。
第三,宣赦仪式简单。唐、宋宣赦现场安排的金鸡、金鸡杆等道具皆有一定的规矩:(唐时)“金鸡位于仪仗南方,竿长七丈,鸡高四尺,鸡头用黄金装饰,嘴衔七尺红色长布,承以彩盘,维以绛绳”[3]《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周密对南宋宣赦时金鸡规制描述为:“金鸡竿,长五丈五尺,四面各百戏。一人缘索而上,谓之‘抢金鸡’。先到者得利物,呼万岁。(缬罗袄子一领,绢十匹,银碗一只重三两)。”[4]周密撰,钱之江校注:《武林旧事》卷1《登门肆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 页。据看到的材料,元朝的汉人士大夫几乎没有谈论过树金鸡事。只有元末明初的沈梦麟写过一篇《金鸡竿赋》。沈梦麟(1308—1400),湖州归安人,传元儒金履祥、许谦之学。至正十三年(1353)中乡试,授婺州路学正,迁武康县尹,元末避乱归居归安花溪。与赵孟頫为姻亲,刘基有赠诗,二人并有交往。《金鸡竿赋》中云:“(金鸡)一鸣而天门开,三唱而离户明。”“乃竖鸡竿,绛幡翩翩。爰有鹤仙,羽衣跹跹。循朱绳以来下,捧紫泥以敷宣。于以端天下之本,于以开人心之天。”“乾为金,巽为鸡,斯刚断之有取,亦申命之莫违。故金鸡之有赦,所以轶李唐而有光,式帝命于九围也。”沈梦麟基本上也是承袭前说从乾卦五行角度叙述金鸡和金鸡杆的,但他侧重的主要是金鸡、金鸡杆代表赦免的方面,而且以此表达了希望大赦的意境:“遐邦小臣敢再拜而献颂曰:‘维鸡有星,煌煌厥灵。于以肆赦,乃平其刑。维鸡有竿,绛幡翩翩;维刑之恤,王道平平。’”[1]沈梦麟:《花溪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八),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2—153 页。
有学者在总结金鸡放赦仪式消失时认为:“‘金鸡’出身扑朔迷离,隋唐时期的人们已经说不清其来源典故了,继续沿用此礼只是因循惯例而已。……‘金鸡放赦’的模糊出身,为其最后的消亡也埋下了种子。”[2]于赓哲、吕博前揭文。这是从金鸡起源角度解释金鸡放赦仪式消失的说法。无论从鸡的卦象抑或从鸡的德性分析,这些对于蒙古统治者而言应该都是没有意义的。故从金鸡缘起的不确定性来说明金、宋以后金鸡放赦仪式的消失,至少对于元朝而言是不成立的,而元代恰恰是弃用金鸡放赦的开始,尽管元朝实行大赦的次数与频率并不低。自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在首都举行隆重的宣赦、宣赦时树竿置金鸡的场面与景象,就从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综上所述知,元朝一共大赦三十余次,没有看到有关大赦仪式的记载。显而易见,元朝在大都宣赦时,没有举行如同唐宋金那般的繁缛与隆重的宣赦仪式,没有集待赦囚徒于宣赦现场,也没有树金鸡杆等程序,它只是在崇天门举行的一次宣读赦免诏书的中央机关官员会议。故《元史》等史料中没有大都宣赦仪式的记载。
二、赴地方宣赦的仪式
(一)唐宋宣赦“外简”
唐时,“其赦书颁诸州,用绢写行下”[1]《旧唐书》卷50《刑法志》;《通典》卷169《刑七·赦宥》,第897 页。。宣赦官员抵达地方后,地方官府迎接诏书的仪式非常简单:“应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进使者前,使者取赦书,持案者退复位。使者称有制,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讫,又再拜,舞蹈,又再拜,释囚。”[2]萧嵩:《大唐开元礼》卷130《嘉礼·皇帝遣使诣诸州宣赦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南宋时,各地在京城临安(今杭州)设有进奏院,宣赦仪式之后,诸州进奏院“各有递铺腰铃黄旗者数人”,迅速前往各地宣读赦令。为取“太平万寿”之意,速递手最先到达太平州、万州、寿春府。有关材料还描述说,当时竟出现“以次俱发,铃声满道,都人竞观”的景象。[3]周密:《武林旧事》卷1《登门肆赦》,第15 页。就是说,宋朝不是由中央政府派员赴地方,而是由地方官府设在首都的机构和官员,犹如今日的驻京办官员各返各地宣读赦书。驻京办为地方政府派遣机关,其官员乃地方官的下属,他们各赴本地宣赦,既可以看作是受中央的委派,更是完成地方官府委付的职责或任务,而非专任的朝廷“钦差”。从这一点言之,宣赦仪式简单似可以理解。
(二)元代宣赦的“外繁”
元朝政府就赴地方宣赦,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在宣赦实施的过程中,遇到或者地方上也反映了一些具体操作问题,如迎接赦书的官府与官员问题、迎赦书时官员服装问题、“班首”问题、宣赦官员抵达时间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元中央政府部门,或请示皇帝,或商相关部门,多予以回复,以便于地方迎送诏赦活动的执行。下面就一些问题分别予以说明。
1.赴地方宣赦的体制
如前述,宣赦体制自汉朝以来,即是逐级进行的。汉朝廷只派员宣赦至郡国,唐朝廷只派员宣赦至各州,其下的县,分别由郡国或州派官吏宣赦。元朝在宣赦体制上亦是如此。即元中央政府只派员至宣抚司、行省、宣慰司这些地方官方宣赦,后者以下原则上是逐级派员宣读,即由宣抚司或者行省及宣慰司再差人员宣赦。
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即位以后,于翌年四月在其统治的北方地区,颁布十路宣抚司圣旨条画,设立了十路宣抚司以管理地方事务,宣抚司是当时地方最高管理机构。这十路(又称十道)宣抚司分别是燕京路、益都济南等路、河南路、北京等路、平阳太原路(河东南北路)、真定路、东平路、大名彰德等路、西京路、京兆等路(陕西四川等路)。同年十一月,十路宣抚司罢。后主要改设行中书省,最后确定为十个行省,分别为:陕西、四川、甘肃、辽阳、河南、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岭北。中统三年(1262)十二月,又立十路(道)宣慰司,亦为中书省派出机构,分领未置行省的诸路。[1]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期》(上册)乙编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58 页。
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江南行御史台:据淮西江北道按察司申:庐州路牒:“两淮运司差使臣赍擎圣旨前来开读,准备迎接。”检会到按察司承奉御史台至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札付该:“中统二年四月内设立十路宣抚司圣旨条画内一款节该:‘宣抚司官除诏赦迎送外,其余并不须迎送祗待,以妨公务。’……呈奉中书省札付该:‘都省相度:仰照依元立宣抚司钦奉圣旨条画事意施行。’”[2]《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卷28《礼部一》“察司不须迎送接待”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提到,早在中统二年(1261)四月,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即规定宣抚司官迎送诏赦,而不参加其他的迎送活动。这个规定在至元十六年(1279)仍被引以为据。中统五年(1264)八月,忽必烈下达圣旨:“行中书省除迎送赦诏及诸王外,其余并不须迎送。”[3]《通制条格》卷8“贺谢迎送”条,第126 页。
仁宗时期的一份材料说得十分清楚。皇庆元年(1312)正月,淮东廉访司通过南台报中台,并经中台报中书省一事,即“扬州正当南北繁剧去处,朝廷遣使分道宣布诏赦圣旨,该系江浙行省一道,必须此处开读”。而“河南行省又复差人来,遍历州郡,不惟致使各衙门官吏迎接,妨废公务,虚负铺马、首思” 。中台意见是:“今后遇有诏赦、圣旨,宜从都省札付,差去江浙使臣经过河南拘该驿路,就便开读,似为便益。”即中书省派赴江浙行省的宣赦人员,在路过河南行省时,宣赦人员可以在相关路分“就便开读”。礼部呈报中书省的报告否定了这一意见:“照得凡遇颁降诏书圣旨,所差官照依元坐,前去各处行省、宣慰司衙门开读。既已开讫,理合回还。其差去官多因己私,辄往属郡僭越开读,不惟虚负首思、铺马,中间实有未便,似亦合行禁约。”中书省同意礼部意见,即中书省赴地方宣赦,只到“各处行省、宣慰司衙门开读。既已开讫,理合回还”。不得“随路开读”。[1]《元典章》卷28《礼部一》“使臣就路开读不许辄往属郡”条。至英宗时,在处理某一报告时,仍然维持“照依先行来的圣旨:诏赦,行省、廉访司各衙门都教迎接”[2]《典章新集·礼部·迎接》,见《元典章》。。
但是,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十五日,元政府颁布了关于元日外路拜表仪,外路迎拜诏赦,送宣、受敕的有关规制,其中的“外路迎拜诏赦”,其仪式如下:
外路迎拜诏赦。送诏赦官到随路,先遣人报。班首即率僚属、吏从人等,备仪从、音乐、彩舆、香舆,诣郭外迎接。见送诏赦官,即于道侧下马。所差官亦下马,取诏赦恭置彩舆中。班首诣香舆前上香,讫,所差官上马,在彩舆后,班首以下皆上马后从,鸣钲鼓作乐前导。至公所,从正门入。所差官下马,执事者先于庭中望阙设诏赦案及香案并褥位,又设所差官褥位在案之西,及又设床于案之西南。所差官取诏赦置于案,彩舆与香舆皆退。所差官称“有制”,赞,班首以下皆再拜,班首稍前跪,上香,讫,复位,又再拜。所差官取诏赦授知事,知事跪受,上名司吏二员齐捧诏赦,同升宣读,在位官皆跪听读,讫,诏赦恭置于案上,知事等复位,班首以下皆再拜,舞蹈叩头,三称“万岁”。[1]官属叩头中间,公吏人等相应高声三呼“万岁”。就拜,兴,又再拜讫。班首以下与所差官相见于庭前。礼毕,所差官行,班首率僚属、公吏、音乐,送至城外而退。[2]《元典章》卷28《礼部一》“迎送合行礼数”条;又《通制条格》卷8“贺谢迎送”条,第127 页。
这个仪式详细地列举、规定了从使者抵达宣赦城郭外,地方官出郭迎接,然后同至官府衙门授受诏赦的整个议程。在衙门中举行的迎拜诏赦程序,尤为其重点。
问题在于,前面已经谈到,元朝中央政府直接赴地方宣赦,只是到宣抚司与后来的行省一级,而这个圣旨的标题为“外路迎拜诏赦”,如何理解这里的“外路”?此处的 “路”,并非指作为固定的元朝一级地方行政机关的“路”(总管府),而是一种习惯称法。譬如前面提到的“诸路宣抚司”,还有“十路宣慰司”等,都有“路”字。所以,这一“外路迎拜诏赦”,实即对前宣抚司、后行省及宣慰司关于迎送诏赦的规定。不过,宣抚司存在的时间很短(仅七个月),故这一种情况主要体现在行省以及宣慰司方面,下文中除必要处外,不再言及宣抚司。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元朝宣赦的“外繁”,乃指此而言。
行省、宣慰司以下官府,则由行省、宣慰司派员宣赦。如英宗至治三年(1323),冯翼翁奉命“布赦恩于澧、鼎、辰、沅、靖、思、播,所至无留滞,悉却馈赆,未一月而返”[1]王礼:《麟原前集》卷12《冯翼翁哀辞》,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60 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76 页。。 “鄂省”即湖广行省。据《元史·地理志》,湖广行省下辖路三十,其中就包括冯翼翁受命宣赦的澧州路、鼎州路、辰州路、沅州路、靖州路、思明路、播州路。元朝路分设置数目多,故行省分别派员赴所辖路分宣赦。冯翼翁宣赦的七个路,乃是湖广行省派出的宣赦路线之一。
下面的一个事例,从侧面也说明地方逐级宣赦的体制。至顺三年(1332)六月,根据发生在乾宁的一事件,刑部提出:“乾宁安抚司知事李元鼎、司吏莫让,于至顺二年二月初一日,钦承诏赦,不即差人宣布,经隔肆日,通同指以措置支持为名,于元差人林德宽等处,科要中统钞贰拾贰定,才令前去开读。又将本司钦录全文行下各翼文字,私家藏收壹伯零陆日,使涣汗之恩,不能周偏。合准所拟,将各人杖断壹伯柒下,除名不叙,罪幸遇免,标附。”都省准拟。[2]《至正条格》卷2《断例·稽缓开读》。乾宁军民安抚司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相当于路一级。[3]《元史》卷63《地理志六》。此处提及的“元差人林德宽等”,当是宣慰使派出的宣赦人员。
分析前面两则材料可以得知,行省派员赴其下官府宣读赦书,一般不举行繁冗的仪式,其再下的机构宣赦,当亦没有。另外,乾宁安抚司事件还显示二点。其一,中有“本司钦录全文行下各翼文字”一句,当知,安抚司是将赦书全文抄录,而不是留下差人宣读的原件,否则也不会有“私家藏收壹伯零陆日”的情节。差人还要持原件赴其他路分宣读。而中央派员赴行省、宣慰司宣赦的赦文,即诏赦原件,是否留在行省、宣慰司,史料中没有明说。可从前引的“外路迎拜诏赦”看,似乎是留下来了。“本司钦录全文”说明,安抚司抄录的是诏赦原件。其二,“科要中统钞贰拾贰定,才令前去开读”一句,说明在乾宁,是由差人宣读赦书的。而看“外路迎拜诏赦”的规定“所差官取诏赦授知事,知事跪受,上名司吏二员齐捧诏赦,同升宣读” ,表明中央派员赴行省、宣慰司宣赦,是由迎拜诏赦官府的吏员宣读的。
2.关于参加迎送诏赦的机构与官员
宣抚司、行省、宣慰司迎送中央宣赦官员,并且举行宣赦仪式,自然这些官府的官吏参加迎送宣赦。其他的地方官府与官员是否参加呢?
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庐州路报淮西江北道按察司,曰:“两淮运司差使臣赍擎圣旨前来开读,准备迎接。”但根据中书省“仰照依元立宣抚司钦奉圣旨条画事意施行”[1]《元典章》卷28《礼部一》“察司不须迎送接待”条。的意见,即早在中统二年(1261)四月,规定宣抚司官迎送诏赦之同时,由于提刑按察司“与宣抚司俱系一体监司衙门”,故明确提出提刑按察司不须迎送接待。至武宗至大二年(1309)三月,中书省官员又提出:“行省官、廉访司官,诏赦、圣旨依体例迎接者。”[2]《通制条格》卷8“贺谢迎送”条。这与上述至元十六年规定的“提刑按察司不迎送诏赦”不一致。显然,此时或之前,与提刑按察司不同,肃政廉访司已被要求参加行省的迎送宣赦仪式。英宗至治年间,中书省批示江西行省上报的文件,又重申了这一规定:“照依先行来的圣旨:诏赦,行省、廉访司各衙门都教迎接。”[1]《典章新集·礼部·迎接》。就是说,只可行省与廉访司官员参加迎送宣赦仪式,其他衙门均不参与。
元朝政府之所以一再关注这个问题,不仅在于参加迎送诏赦的官员多寡,而还在于诸王、公主、驸马、省部官吏、寺观护持等,纷至沓来,使得地方官府“每日迎送使臣”,严重影响衙门事务的办理,已成地方官府的沉重包袱。
至元二十九年(1292)九月,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提出:“不时诸王、公主、驸马并出使官员经过,今后迎接,合无止摘府官一员出郭,不致耽误府事。”就是说,这些人出行路过宣慰司时,如有必须,宣慰司只派一名官员迎接。前引至大二年(1309)三月大宁的例云:“收拾户计的,打捕豹子的,圣旨也教迎接有,城子里勾当哏迟误有,么道,那里的廉访司官人每根底与文书来。”江浙行省也有相同的反映,并提出建议:“俺商量来,行省官、廉访司官诏赦圣旨依例迎接者,经过去处休开者。若行省与廉访司有合一同干碍的圣旨有呵,各一员官迎接,其余的听者。除这的外,寺观多人根底与来的执把的圣旨,呈献的鹰鹞豹子稀罕物资等有呵,休教迎接呵,怎生?”武宗同意这个意见。[2]《通制条格》卷8“贺谢迎送”条。自武宗的这个圣旨开始,元朝迎拜诏赦的官府即定为行省、宣慰司与廉访司。而与行省、宣慰司、廉访司有政务关系的圣旨,这三个衙门只是各派一名官员参加迎接。英宗至治年间,中书省对江西行省的批示:“若干碍行省、廉访司事务的圣旨呵,各一员官迎接者;除这的外,寺观护持诸人执把的圣旨,休迎接呵。”延祐七年二月,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延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奏过事内一件:“如今御史台官人每备着江南行台文书,俺每根底与将文书来:‘近年开读圣旨,多不是中书省奏来的,也不是干碍御史台、廉访司事理。若依在前圣旨不迎接呵,上头却写着御史台、廉访司衙门有。依在前圣旨体例里。’么道,说有。照依先行来的圣旨:诏赦,行省、廉访司各衙门都教迎接;若干碍行省、廉访司事务的圣旨呵,各一员官迎接者;除这的外,寺观护持诸人执把的圣旨,休迎接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都省咨请钦依施行。[1]《典章新集·礼部·迎接》。
此与武宗的规定一致。
3.赴地方宣赦的官吏
虽然《金史》明确指出,“其外郡,尚书省差官(宣赦)”,但也没有说明赴地方宣赦的是何等官员。元朝派遣何官员赴地方宣赦?前引《元典章》至元八年(1271)的材料中没有说明,只是写道“送诏赦官”。《元史》载:“客省使,秩正五品,使四员,正五品;副使二员,正六品;令史一人。掌直省舍人、宣使等员选举差遣之事。至元九年置,使二员,一员兼通事,一员不兼。大德元年,增置四员,副二员。直省舍人二员,至元七年始置,后增至三十三员,掌奏事给使差遣之役。”[2]《元史》卷85《百官志一》。
客省使是中书省下属的直属机构。从上引其职责看,当是负责中书省选派人员赴地方的差遣事宜,宣赦应是其中的任务之一,而客省使中的宣使是宣赦的主要承担者。宣使是元朝官府中的主要吏职之一,一般设在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及行省、行台、行院等一、二品衙门中,承担上传下达的职责。另外,行省的宣使多达40名,“宣劳力于列省而为之使,日惟更直” 。是元政府各部门中编制最多的吏职。宣使负任外出,“缓则往返留滞,或阅岁时;急则日驰数百里,连暮夜弗止,不兼旬为去来”[1]杨翮:《佩玉斋类稿》卷1《宣使房壁记》,《四库全书》珍本。。元曲中有反映在地方宣赦的场面,剧中也是由宣使宣赦的。如郑廷玉《宋上帝御断金凤钗》第四折中有这样的描述:(七兄弟)讲到传达赦免诏书的事:“自从巳时,到午时,多不到半炊时。不想这报我恩的大人为宣使,追我魂的太尉立在阶址,救我命的赦书从天至。”[2]参见王季思主编:《金元戏曲》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 页。至元末,也出现首领官赴地方宣赦的情况。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顺帝宣布大赦后,“选文学之臣识通便者分道往谕。于是擢君(即王唯善。此前为国史院典籍)崇福司经历,使广东”[3]李继本:《一山集》卷4《送王唯善序》,《湖北先正遗书》本。。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4]《元史》卷89《百官志五》。。即“主要负责管理基督教各派神职人员和信徒”[5]高铁泰:《元崇福司考》,《西域研究》2014年第2 期。。崇福司的经历,属首领官,从六品。选派王唯善赴广东宣赦,如前所述,乃是出于“选文学之臣识通便者”,与崇福司的职责,以及与基督教没有关系。除崇福司的王唯善外,当然还有其他部门的“文学之臣识通便者”参加宣赦,因材料所限,无法举出更多的事例。
关于行省派员宣赦,并没有具体规定。如前引“布赦恩于澧、鼎、辰、沅、靖、思、播”的冯翼翁,为永新人,科举及第,授官为汉阳丞,后迁为鄂省照磨。中书省“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1]《元史》卷85《百官志一》。。照磨属于首领官,在首领官中,照磨的职责带有审计性质。行省照磨的职责大体相同。不过,冯翼翁赴路府宣赦,与其照磨职责当没有关系,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派遣,属“省差使臣人员”。林德宽等人赴乾宁安抚司,是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派遣的宣赦者。
4.宣赦者抵地方的时间问题
宣赦者抵达迎送宣赦的官府的时间,牵扯到宣赦场面的预先安排、听读赦书人员的等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故并非细小之事。在实际中,等候迎接诏赦与上一节叙述的送往迎来一样,成为地方官员时常处于的一种困境。
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河南道按察司提出,并由尚书省、御史台呈报忽必烈的材料说:“使臣人员赍擎圣旨各路开读,常是预先行移前路官员率领司县官吏出城迎接,或十余日才方到来,以致妨夺公务。”并建议:“今后合无斟酌驿程,约定必到日期,行移前路官司迎接。”中书省的意见是:“除诏赦并来擎御宝圣旨使臣,预期一日行移前路官司依例迎接外,其余宣使、省差使臣人员,不须迎接。”[2]《至正条格·断例》卷2《稽缓开读》。这是忽必烈前期的材料,即从使臣确定即将抵达时间的前一日,通知地方官府,以便安排迎接。不过,这一办法并未改变宣赦者延迟的情况。
至武宗时,这样的问题仍然存在。至大二年(1309)三月初二日,赤因帖木儿丞相向武宗转奏御史台来自廉访司的文书:“大宁等处开赦书圣旨去的使臣,教迎接者,么道说将去了,二三日之后才来到的也有。来呵,遇着雨雪也要穿公服有。收拾户计的,打捕豹子的,圣旨也教迎接有,城子里勾当哏迟误有。”[1]《元典章》卷28《礼部一》“迎接”条;又见《通制条格》卷8“贺谢迎送”条,第126 页。
从看到的材料,这个问题直到文宗时才解决,办法是限定宣赦人员日行里数。天历三年(1330)九月,文宗敕:“使者颁诏赦,率日行三百余里。既受命,逗留三日及所至饮宴稽期者治罪,取赂者以枉法论。”[2]《元史》卷33《文宗纪二》。就是说,宣布诏赦的官员按每天须走三百里路程,没有特殊情况,地方官府据此可以知道宣赦使者到达的大体时间。其实,唐、宋时即有此规定:《兴元赦书》言:“赦书日行五百里。”宋,“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又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由内侍省发遣焉”[3]《宋史》卷154《舆服志六》。。相比,元比唐、宋日行分别缩短了二百里、一百里。
这一制度,只是规定了中央赴行省一级宣赦的日程,行省派员赴下一级宣赦,是否也按日行三百里计算,尚不明确。现以前引乾宁安抚司事例,略做分析。乾宁安抚司在至顺二年(1331)二月初一日收到赦书,距离这个时间最近的大赦,当是前一年十二月初四文宗颁布的,那么算起来,由首都宣赦到乾宁安抚司接到赦令,已有两个月的时间。而乾宁安抚司的承办官吏知事、司吏,在故意耽搁四日后,编造虚假原因,索要了“好处费中统钞贰拾贰定”,宣赦者才得以开读。之后,又将抄录的需要下传至各翼的赦书,“私家藏收壹伯零陆日”。至此,时间又过去一百二十天,即四个月。就是说,历经半年之久,大赦令还停留在安抚司衙门,没有抵达基层,安抚司所辖区域的军民还不知道,赦令自然无从落实。虽然贪赃渎职的知事、司吏后来受到杖断、除名的惩罚,可是,本应获赦的囚徒,却枉多坐了半年的牢狱。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情况而延迟宣赦,在元朝恐非个别。
还有一个近乎无法理解的事例。大德十年(1306)七月,成宗宣布“释诸路罪囚,常赦所不原者不与”[1]《元史》卷21《成宗纪四》。。然而,成宗的这次赦免令,仅在大都、上都等处得到落实, 其他地方没有实施。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书省上奏成宗曰:“前者夏间,大都、上都等侧近城子里有底见禁罪囚每,教放了来。外据行省里不曾行来,不均的一般有。如今,外辖路分里,应有底罪囚依先体例,尽行疏放者。”成宗同意。“圣旨了也。钦此。”[2]《元典章》卷3《圣政二》“霈恩宥”条。覆盖全国的赦令,颁布五个月后,才发现没有在绝大部分地区实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事后也没有问责。当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宣赦时间的问题了。
5.关于“班首”
所谓“班首”,元朝指举行重大活动时,众官员中的领头人、代表者与组织者。中央举行重大仪式,也有班首。如“皇帝即位受朝仪”、“元正受朝仪”等都规定了班首的职责。“祖宗以来,皇帝登基,中书率百官称贺,班首惟上所命。”就是说,在中央举办新皇帝即位、百官朝贺时,班首的人选是由皇帝临时指定的。如英宗将举行即位大典时,中书省官员提出这个问题,英宗答复:“以铁木迭儿为之。”当时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相,“恒病足”[1]《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故有此问。
在迎送诏赦时,由于有众多官府与官吏参加,故地方上也要有一个班首,也就是当地官府迎送诏赦的主要官员。
上述所引的规定中提出以官员的品级为依据,参加宣赦,故地方官府的主要官员即为迎送诏赦的“班首”。可有的地方上有驻军,关于驻军军官参加迎接诏赦仪式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如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十五日在发给大司农、御史中丞兼领侍仪司的文件中说:“斡耳朵里奏准:‘每遇圣节、元日、诏赦并各官受宣敕,除沿边把军官再行定夺外,诸路官员合无令各官照依品从,自造公服,迎拜行礼。’奉圣旨:‘除沿边把军官外,那般行者。’钦此。已经呈覆。今据侍仪司申:‘检照到旧例,外路官员如遇圣节、元日、诏赦并各官受宣敕礼数,开申前去。外有合行礼数,逐旋讲究申覆。乞照验施行。’备呈中书省照验施行。”[2]《元典章》卷28《礼部一》“迎接合行礼数”条。至元初年的这个规定只简单地写道 “沿边把军官再行定夺”,但如何“定夺”,未明。
成宗即位之初,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一月,河南行省就有关迎宣接诏、国家祭祀并朔望行香时的班首一事请示中书省:“止是守土有司为班首。自立行枢密院以来,镇守军官亦要与民官俱作班首。礼部议得:上项事理合准守土官员为班首。都省准拟。”[3]《至正条格·断例》卷2《稽缓开读》。就是说,不能完全以级别论定,而是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为班首。这里所谓的守土官即地方行政长官达鲁花赤。班首问题至成宗初得以最后确定。
但翌年即大德元年(1295),松江地区又出现了管民官与驻军军官因级别而争夺班首的问题,且在行文中明确提到开读诏赦问题。松江府奉江浙行省札付:来申:“本府达鲁花赤、松江万户府达鲁花赤,凡遇开读圣旨诏赦、天寿圣节并贺正之时,祭祀行礼班首。”移准中书省咨:“送礼部议得:‘松江万户府虽系三品,镇守、征行、屯戍去处无常,终非守土之职。凡遇进贺行礼,若令守土官为班首,于礼相应。’”“‘松江万户府虽系三品,终非守土之职,难以品级定论班序。如依本部已拟,似为长便。’咨请依上施行。”中书省最后同意礼部意见:因万户府官“终非守土之职”,从长远考虑,仍然以都省“咨请依上施行” 。[1]《元典章》卷28《礼部一》“守土官行礼班首”条。
金国似没有班首一称。《金史·礼志》所载的“臣下拜赦诏仪”中,仅言“长官”率其僚属吏从,迎送诏赦。
6.流外官的“公服”问题
前面已谈到,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已规定,逢重大节日举行仪式或者宣读诏赦、宣敕等活动时,官员必须服公服,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均同。公服系列是按照官员品级确定的。那么,没有品级即流外官参与这类活动,其公服如何处理呢?
从上节知道,班首只是率领官吏迎拜诏赦,而从使者手中受接诏赦的是该官府首领官。这就出现了需要解决问题,即散府、州衙门不设首领官知事(流官)一职,其首领官分别是提领案牍、都目、吏目,这些首领官不入流品,没有公服。可参加迎接诏赦仪式,没有公服显然与场面不协调,有失庄重。于是,至元九年(1272)三月,根据濮州提出“本州不设知事,如遇捧接诏赦,其提领按牍合无制造公服”的问题,中书省吏礼部经过研究,“议得,诸路总管府并散府、上中下州所设提领案牍、都吏目,俱系未入流品人员,难拟制造公服。遇行礼,权拟衣檀合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呈奉中书省札付准呈,仍遍行合属,依上施行”。[1]《元典章》卷29《礼部二》“提控都吏目公服”条;又见《通制条格》卷8“贺谢迎送”条。制作、穿着公服是流品官员参加重大活动的政治待遇。而提领案牍、都吏目均未入流品,鉴于参加迎接诏赦事体重大,故散府的提领案牍,州一级都目、吏目在遇到宣赦时,只是“权拟”,也就是制作临时公服参加迎接。其式样为“衣檀合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中书省同意了吏礼部的意见。
最后说一下县典史的公服问题。成宗大德七年(1303)九月,根据都省“未入流品人员,权拟檀褐罗窄衫、乌角束带、舒脚幞头”的规定,江西行省提出“即目各处典史,拟于应得都吏目人员内选差,未审合无制造”的问题。礼部的意见是:“在前司县典史,路府自行迁调,目今腹里省部里注,其江南者行省定夺。所据公服,虽无通例,却缘臣下致敬之仪,理合严谨,合准制造。”[2]《元典章》卷29《礼部二》“典史公服”条。都省同意礼部的意见。从上诸材料可知,行省、宣慰司派员赴下级官府宣赦,散府、州都可能有迎拜诏赦的机会,故其首领官提领案牍、都吏目就存在是否穿着公服的问题。还有的路分,“路官员率领司县官吏出城迎接”诏赦,随之出现了(录事)司、县典史的公服问题。加之对典史管理权限的提升,且典史又是都吏目的重要来源,故中书省同意典史也可以制造公服,其式样等与散府、州的提领案牍、都吏目的公服一样。
元政府一直按着最初制定的公服制度实施,后未见有新的规定,说明始终维持公服自费原则。散府、州、县的首领官制造公服,其费用自然由这些官员个人承担。虽然自费,但这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依然搜寻理由,积极地逐级请示,盼望中央能够答应其制作公服的请求,可谓趋之若鹜。原因很简单,在帝制时代官本位体制下,公服是官员身份地位的另一种体现。
三、结语及其他
以上对元朝的宣赦仪式、宣赦传达体制、宣赦的相关制度等,作了叙述与分析。那么,元朝政府为什么突改胜国宋、金的制度,在大赦诏书首次公之于众之际,其程序会如此简单,与宋、金产生如此大的差别呢?
或许可以用蒙古人性格质朴,不惯于繁文缛节来解释。可是,自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开始,至至元八年(1271)前后,元朝相继制定了皇帝即位、元正日,天寿节等受朝仪,册立皇后、皇太子仪,甚至官员送宣、受敕仪式,等等。从记载诸多仪式的《元史·礼乐志》、《元典章》中可以看出,这些仪式虽繁简不一,但都固定有序,即使最简单的官员受敕,也有明确的程序和相关要求,更不要说连续举行数日的皇帝即位等朝仪了。因此,这种解释应该不成立。
或者,元朝之所以大大简化在大都的宣赦仪式,是对于金国之制度的否定与拒绝。比如,忽必烈以其严苛,坚决地废除了金泰和律。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下引金国的“臣下拜赦诏仪”,做一比较:
其外郡,尚书省差官送赦书到京府节镇,先遣人报,长官即率僚属吏从,备旗帜音乐彩舆香舆,诣五里外迎。见送赦书官,即于道侧下马,所差官亦下马,取赦书置彩舆中,长官诣香舆前上香,讫,所差官上马,在香舆后,长官以下皆上马后从,鸣钲鼓作乐导至公厅,从正门入,所差官下马。执事者先设案并望阙褥位于庭中,香舆置于案之前,又设所差官褥位在案之侧,又设卓子于案之东南。所差官取赦书置于案,彩舆退。所差官称:“有敕。”长官以下皆再拜。长官少前上香,讫,退复位,又再拜。所差官取赦书授都目,都目跪受,及孔目官二员,三人齐捧赦书,同高几上宣读,在位官皆跪听。读讫,都目等复位。长官以下再拜,舞蹈,俯伏,兴,再拜。公吏以下三称“万岁”。礼毕。明日,长官率僚属,音乐送至郭外。[1]《金史》卷36《礼志九·臣下拜赦诏仪》。
与前引忽必烈时期颁布的“外路迎拜诏赦”相比,除了前文已提到过的“班首”,还有元无而金有的“五里地”(即地方官府须到五里地外迎接诏赦)等细节外,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大的区别,可以说,元朝的“外路迎拜诏赦”基本上是金国“臣下拜赦诏仪”的翻版,承继性十分明显。而元朝对金在制度方面的继承远非这一点。之所以有这些制度的继承性,其中一条原因是,像元初的刘秉忠等汉人官员,原大多是金国的臣民,他们亲身经历的金国制度,往往成为他们为忽必烈提供制度建议的基础。故这样解释也说不通。
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考虑:皇帝颁布的诏书很多,诏赦只是皇帝诏书之一种,不可能发布任何诏书都实行大赦。再,元代灾异频发,因为灾异而大赦,不在少数。像泰定帝时期,于泰定二年(1325)、三年、四年连续三年实施三次大赦。[1]参见《元史·泰定纪》。蒙古统治者认为,灾异源于阴阳失调,狱囚太多,实施大赦是对于各种灾难的补救措施之一。还有,大赦命令更多是需要地方各级官府执行,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或者仅由大都来实施。当然,这些多偏重于推测。对此,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最后提出一点的是,朱元璋赶走蒙古统治者建立大明以后,在洪武年间制定了“迎接诏赦仪”,引如下:
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使者下马,奉诏书置龙亭中,南向,本处官朝服行五拜礼。众官及鼓乐前导,使者上马随龙亭后,至公廨门。众官先入,文武东西序立,候龙亭至,排班四拜。使者捧诏授展读官,展读官跪受,诣开读案。宣读讫,捧诏授朝使,仍置龙亭中。众官四拜,舞蹈山呼,复四拜毕。班首诣龙亭前,跪问皇躬万福,使者鞠躬答曰:“圣躬万福。”众官退,易服见使者,并行两拜礼。复具鼓乐送诏于龙亭。如有出使者在,则先守臣行礼。[1]《明史》卷56《礼志十》。此为删节。原文可见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74《开读仪》,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193 页。
这个仪式,无疑是对元朝同一制度的继承,包括“班首”这一称呼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