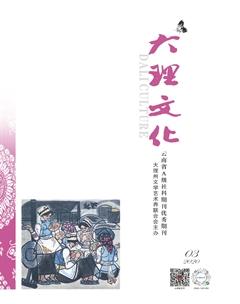苍洱英烈施介
杨鲲峰
20世纪20年代,在凤凰的故乡凤羽,一只美丽的凤凰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从罗山凤水起飞,飞越茈碧湖,歇息在秀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然后飞越碧鸡关,落在滇池畔。又不远千山万水振羽飞到太阳升起的延河边上。最后化作一只美丽的丹顶鹤,永远栖息在内蒙古西辽河畔的白城。他就是凤羽骄子——施介。
苦难童年
施介乳名施仲山,学名施汝显,1909年农历十一月出生在洱源凤羽凤翔镇元士充。
享有“文墨之乡”的中国历史名镇凤羽历来注重耕读传家,施介祖上同样是一个书香农家。施介的祖父施士铭,是清朝贡生,被乡里尊称为“贡爷”,父亲施照富同样也是饱学之士的文生。加之家中有四五亩田产、六七匹骡马,在乡里还算是殷实富足之家。
可是,到了他的父亲施照富当家立业时,家道中落,父亲只得放下书生架子,以苦力维持全家温饱。不早不迟,施介恰好在这时来到了世上。为了让儿子长大后重振家业,光宗耀祖,父母给他取乳名施仲山,学名施汝显,对儿子寄予厚望。
不料,到施介五六岁时,而立之年的父母相继去世,弟弟夭折,伯父和叔叔也先后离世,施介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饱尝了人世的艰辛和炎凉。所幸的是,好心的三婶不顾丈夫离世、家中困难收养了他,并把施介和自己的儿子施汝成同样对待。
1916年,施介七岁,三婶把他送到元士充端严寺读私塾,熟读成诵的“三字经”“千家诗”开启了他学习文化知识的门扉。三年后,施介又转入凤翔文庙中的凤翔两级小学中读书。年幼的施介很懂事,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在学校勤奋学习,成绩优异。1925年,16岁的施介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
当时,正值云南军阀争斗,滇西匪患不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三婶一人操持全家,实在无力继续供给施介读书。无奈之下,施介只有顺从三婶的劝诫,暂且辍学在家务农。为了减轻三婶的负担,他利用农闲去做工挣钱,或赶牲口翻越罗坪山随马帮到乔后井驮盐巴到右所街卖。
不过,胸怀大志的施介没有放弃学习,两年中,他一边帮三婶种地放牧和打工挣钱,一边抽空刻苦学习。
1927年秋天,18岁的施介突然得知远在百里之外的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招生,便私下和同乡的马锦、老友李绍善、茈碧大果的马曜一起去报考,等到出榜被录取之后才告知三婶。心地善良的三婶喜忧交加,最终被施介读书的志向所打动,再三思索后,毅然节衣缩食供给他到大理读书,而让小学毕业的亲生儿子施汝成放弃学业,在家务农。
大理求学
进入大理省立二师,施介被分在师范初师二班。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各种进步的思潮也在云南迅速传播。1926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成立,中共云南特委领导下的迤西區区委也在大理秘密开展活动。在悠久的白族历史文化以及各种民主、科学进步思潮的影响下,施介视野大开,心境豁然,于1928年(19岁)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迈开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进步思潮的影响、革命理论的熏陶使施介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理论,社会的黑暗、政府的反动又加深了他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坚定了他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在大理读书期间,施介与洱源学子成立声援正义斗争的学会,与志同道合、思想激进的马曜等同学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向旧世界宣战。
有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晚会,其中有一幕话剧描写几个军人上饭店白吃不给钱,在场观看的有几个大理国民党驻军官兵对号入座,认为节目有意直指他们,便回部队夸大事实加以虚报后,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到校对手无寸铁的师生大打出手。学校因此被迫停课,最后以校方出面向部队赔礼道歉才平息。这件事对施介刺激很大,心中暗自下定了寻求光明、反对黑暗、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
通过进步思潮的影响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施介慢慢懂得了一些革命理论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加深了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与同学行走在大理街上,看到兵丁押着几个蓬头垢面、带着镣铐的百姓在干劳动,大家对此事各抒己见,施介认为这些人因生活无着落而被迫犯罪,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不好造成的,见解切中时弊,让其他同学折服。
由于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影响,施介也不信鬼神迷信。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施介和其他同学上街看到大理城中的许多百姓在烧纸钱冥衣,树上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冥衣随风飘舞,有几个胆小的同学吓得胆战心惊,施介却不相信,也不害怕,一边在树下取下冥衣,一边大声说:“孤魂野鬼,如果你们真的有灵,就到大理师范第二寝室头排床位领吧,我叫施介,一定加倍赔偿。”
施介还把自己的原名施汝显改为施介,自号介庵,借谐音寓刚直不阿,表明立志做一个光明磊落耿介正直的人。他还与马曜结为诗友,经常在一起唱和吟咏,借以抒发胸中的愤懑和志向,兴奋时热烈激动,悲恸时声泪俱下。他俩还共同作了“举目皆大敌,甘心做小人”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联意直指当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在大革命遭受重创时期,正值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成立以后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全部转入秘密地下工作,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立场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党,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同志,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云南的革命斗争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与各地的地下党组织相继中断联系,施介也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30年,施介于省立大理师范即将毕业的春节期间,在三婶的敦促和操持下,按照当地风俗,与自幼订有婚约的同乡姑娘杜小年成婚。虽然施介心中也爱怜与他结发的这位贤惠善良的农家女子,但他更加惦念求知的学堂,向往伟大的事业。婚后蜜月未满,就与新婚妻子依依惜别返校读书。别后,杜小年曾拿出私房积蓄,并东借西挪,凑足100元大洋,托亲戚捎给他。施介收到钱后,百感交集,更加刻苦学习,以不负三婶和妻子的情意。
1930年7月5日,施介在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与同学毕业合影的照片背面,他奋笔留言:
要从这黑暗里寻找光明,是彻底扫除一切障碍!我们的工具,唯有牺牲和奋斗。
誓言铿锵,施介这位风华正茂的凤羽白族小伙子说到做到,以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完全践行了自己立下的誓言!毕业后,施介回了家乡凤羽一趟,与家人短暂的相聚后,他又告别亲人,离开了哺育他成长的故土,与挚友马曜、马锦等几个同学结伴上昆明。从此,施介为了黨和人民的事业辗转南疆北国,再也没有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凤羽。
就读省立一师
施介在大理省立二师毕业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护独裁统治加紧“清共”“反共”活动,云南地方当局也追随南京政府的反共政策,一次次在云南掀起反共高潮,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云南地下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1931年元旦,施介与马曜等几个同学在血雨腥风中历经艰辛,徒步来到省城昆明。此后,同学们各奔前程。施介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高级部,马曜补习后考上上海光华大学,马锦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在对日抗战中随滇军血战台儿庄。
昆明省立第一师范高级部属于培养全省优等师资的高等学府,由政府给予公费待遇,自然减轻了施介的学习费用,但由于家境贫寒,三年中,施介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依然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吟诵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胸中充满了以身许国、驰骋沙场的豪情;阅读《大公报》《生活周刊》,心里树立起寻求光明、献身革命的理想。
在新思想的引导下,施介关心时事政治,观测斗争动向,并与东陆大学的李崧荫等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结为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
施介有厚实的古文学功底,诗文立意新颖,豪放激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马曜在回忆施介时说:“先父非常重视施介的品学,欣赏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特别钦佩他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人。”在此期间,施介以“剑尘”为笔名,寓“时政混浊、宝剑蒙尘”之意,借以发泄对黑暗专制社会的憎恶,用诗歌抒写热血青年的志向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养垢不磨剑上尘,屈指何须计芳春。
挑灯看剑魂驽起,怕见深闺梦里人。
30年代初期的省城昆明乌云翻滚,万马齐喑。在昆明就读期间,施介组织在昆老乡创办《洱源》杂志和校刊《心声》,写文章诗联抨击时弊。两个青年因不堪现实所迫而短见,他作挽联痛悼:
世混污而不清兮,或饮弹,或卧波,先觉者,人生了了耳;
国家亡而颠覆矣,为鞭尸,为击贼,后死辈,责任诚诚然。
联语犀利,对“混浊不清”的乱世加以有力探诉,唤醒民众起来与黑暗社会作斗争。
当时,昆明市内有个洱源会馆,坐落在黄公祠东街荩忠寺坡上,可隔窗远眺翠湖,风景优美。施介有时也到馆中与乡亲小聚,看到坡下敛财万贯、富及一时的省财政厅长陆崇仁公馆中,军政要员趋之若鹜,终日宾客如流、灯红酒绿,洱源会馆却经营惨淡,门庭冷落。两相对比,有感而发,给公馆写了一副对联:
与厅长比邻而居,身价十倍;
傍翠湖春色在望,美景四时。
用“身价十倍”含蓄讽刺和针砭陆公馆中的趋炎附势之徒,同时充分表达了对官僚腐败深恶痛绝的心情。
1932年冬天,云南省立昆明第一师范学生因反对校长杨天理庇护克扣学生伙食费的教师掀起罢课学潮,施介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并以一个热血青年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起草上书省政府和教育厅呈文,强烈要求校方严惩贪污分子,撤换校长。檄文义正辞严,强烈控诉封建买办的法西斯旧式教育制度的弊端,极力维护和保障学生正当权益及合理要求。为了伸张正义,施介放弃再读一学期就可以拿到的文凭,坚定不移站在全校师生的最前列,向反动当局进行不屈的斗争。
罢课学潮长达数月之久,政府当局被迫撤换校长,答应兑现学生克扣的伙食费,并惩处贪污职员。但风波一平,政府当局撕去伪装,露出反动嘴脸,无理开除了施介等10名带头组织学潮的学生,被撤职的校长也官复原职。
学潮虽以失败告终,但年轻的施介却从中得到了锻炼,同时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训,并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堕落和反动本质,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斗争的信念。
学潮失败,施介被迫离校。除夕之夜,孤灯难眠,听到远处传来的鞭炮声,施介百感交集,忧国忧民,写下《除夕感怀》:
满怀往事等烟消,举杯难将明月邀。
莫怪前朝鞭炮少,留得一半在今宵。
由于学潮之故,施介被学校开除,失去了衣食之源和遮风避雨之所,与组织也失去联系。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消息后,便与志同道合的同学李崧荫商量,决定前往苏区找党组织。
千里南寻党组织
1933年春天,施介和李崧荫秘密离开省城昆明经贵州抵达湘黔边境,时值国民党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调集六十多万兵力,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第四次“围剿”。一路上,敌占区封锁严密,碉堡林立,无法通过,只好折返。
尽管沿途艰难险阻,但施介和李崧荫意志坚定,相互激励,百折不挠,一心想找到党组织,几经周折后辗转到了四川成都,与朱显达、何象尧等云南籍的革命党人见面,更加坚定了信心。在成都作短暂的停留后,两人又决定继续东行,前往南京、上海寻找党组织。但两人从云南到四川,步行数月,跋涉千里,路费已用完。为了节省开支,他俩只好步行到了四川永川,找到在该地驻军郭勋祺“模范师”任职的云南缅宁(今临沧)人廖鼎高。出于同省之谊,廖鼎高热情招待了他们,并予以关照。告别了廖鼎高后,两人徒步到达重庆。在重庆,施介在马曜的哥哥马昶那里得知同学马锦的哥哥马鏻在驻防南京的滇军范石生部队任职,便决定取水路前往南京。但两人身上只有买一张船票的钱,最终在船上一位好心工友的帮助和掩护下,两人交替用船票蒙混过了查票关,得以顺利乘船南下。
到了南京,两人不仅没钱买前往上海的船票,连吃住也无着落。为了生计和躲过敌特,经人介绍,李崧荫到行政公署当职员,施介在马鏻的推荐下在国民党中央炮兵第五团当文书。
1933年下半年,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蒋介石经过半年的准备,调集百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并自任总司令。为集结兵源,担任南京防务的部队也抽调前线,施介所在炮兵团也奉命南下参战。行进在蒋介石反共部队南下的行列里,身不由己的施介心急如焚,心想自己千里迢迢是去找黨组织干革命的,而目下却是南辕北辙无法脱身,心中万分难受。好不容易熬到1935年的春天,上峰有令去留自便,施介迫不及待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去寻找失去联系的李崧荫。
由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在六安行政公署任职的李崧荫被捕入狱惨遭迫害,得了精神分裂症。施介得知后马上前往六安探望,并想法将李崧荫营救出来,送往苏州福音医院住院治疗。
一年后,李崧荫的病情仍未见好转,施介与他的弟弟李崧棻商量后,决定将他送回云南老家治疗。当时,南京到云南的路还没通,李崧荫病情较重,行动不便,一行人只得取道海路经上海南下、绕道香港、广州进入越南海防,再乘滇越铁路坐火车北上回到云南。护送李崧荫回到他的老家后,施介还陪他住了一个多月,给他安慰和鼓励,才返回昆明。
两年的宁沪之行,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却增强了施介的革命意志和信念,特别是了解到苏区的情况,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加深了对敌人的憎恨。在给老友李绍善的信中,他写道:“此次出省,并非为了逃命,而是为了寻求人类普遍光明。苟利以国,生死以之。大江南北,遍地烽烟。今后我的行踪靡定,望勿为我系念。”
其中可见施介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浪迹千里寻求光明,以身许国的赤子之心。
开远任教播火种
1935年秋天,南行无望,施介只好返回昆明。在马曜父亲马东初先生的举荐下,他乘滇越铁路窄轨小火车南下开远,到开远县立中学师范班任教。任教期间,施介在学生当中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指引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施介还借路边行乞的人启发学生,要解救饥寒交迫的人们,只有彻底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向进步倾向鲜明的王锡令、何继民、陈开明等人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告诉他们中国有了共产党,讲苏区红军的斗争,并让他们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使进步学生从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一个学生在回忆录中也写到:
施介老师经常对我们讲:“人生最高理想,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理想是指路灯,一个人缺乏很好的理想,就不会有正确的方向;没有方向,就像没有灵魂,生活就毫无意义,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一个人当追求的目标越高时,他的才力发展也越快,对社会的贡献才会显著。”
1937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消息传到开远,施介借机先向具有先进思想的个别学生讲解,然后通过这些学生带动全校学生讲解,再通过这些学生带动全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满怀爱国激情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同时还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广泛宣传,使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在开远边城广为传播。
“七·七事变”,北京卢沟桥的枪声点燃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烽火。外族入侵,民族危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中华大地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发展成为公开的群众运动。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开远县立中学进步师生率先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施介的倡导下,学校成立了“开远中学学生抗敌后援会”,施介的好朋友陈开明为会长,王锡令等思想进步的同学为宣传委员。在施介的领导下,“学抗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募集钱物支援前方抗战将士。施介还亲自起草《告开远父老书》,由师生抄写后四处散发,阐述民族团结、抗日救国大义,呼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学抗会”还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歌唱《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流亡三部曲》等激励群众抗日斗志。
开远县立中学进步师生轰轰烈烈救亡活动深深感染了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捐钱捐物。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影响到了邻近各县,蒙自、建水、弥勒等县也相继成立“学生抗敌后援会”,并派人到开远县立中学索要施介起草的《告开远父老书》,并与开远中学结成盟友,相互声援,共同行动。
但是,由于受国民党负面抗战思想的限制,施介领导的开远县立中学进步师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及其影响使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镇压,使用各种阴谋诡计,妄图解散“学抗会”。一个冬天的下午,国民党开远县党部书记胡瑧在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簇拥下,气势汹汹闯进学校,宣称“学校抗敌后援会”未经县党部和县政府批准,属于非法组织,要加以取缔,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胸中充满着爱国热情的施介再也听不下去了,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撩开长衫健步登上台阶,昂首怒目直视盛气凌人的胡某等人愤然反驳道:
日寇凶残,要亡我中国,灭我民族,几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大片国土已落入敌手,关东父老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危在旦夕,共赴国难何罪之有?难道说学生爱国有罪?凡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是决不当亡国奴的!
施介还不等对方反应过来,紧接着声色俱厉,大声说道:“我是方老师请来的教师,外地人只有我一个,就住在三层楼下,我日不关门,夜不闭户,若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
施介临危不惧的气慨和爱国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话音刚落,在场的师生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充满正义感的反驳理直气壮,压倒了县党部胡某一伙的嚣张气焰,他们无言对答,面对群情激愤的师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6月,施介调到“抗大”直属部队,在延河水畔与朱家璧结识,两人一见如故。朱家璧也是云南人,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后回云南在滇军警卫团任连长等职,抗战后奔赴延安,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学习工作。
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布置,为在云南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远在延安的施介、朱家璧、刘林元三人一起对云南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状况作了细致的分析,最后决定由施介执笔,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写了一份《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工作意见的报告》(现存中央档案馆)。
当时,党中央原计划派施介回云南开展革命工作,但得知他在云南已被反动当局及敌特所关注,便改变方案,派朱家璧回云南。
1939年初,施介结束了抗大的学习生活,被调中央组织部总务处当处长。后于1940年调陕北公学(今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务处副处长,1941年调延安大学任党总支书记。1942年,施介作为延安大学的负责人,带领全校师生开展整风运动,彻底改造了世界观,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延大师生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施介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了抗日战争极为严峻的烽火岁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为一名出色的党务工作者。
转战北疆献青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抗击蒋介石因独裁统治而向关外发动的大举进攻,10月初,施介随中央派出的两万名干部和十万大军千里行军挺进东北,开辟和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施介和战友们一道挥别哺育自己的红色摇篮延安,踏上新的征程。
10月底到达了阜新,施介被任命为阜新地委(热辽边地委)组织部长。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和土匪的骚扰,有“黑金”美称的阜新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施介和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发动群众,恢复生产,组建农民武装,消灭土匪,清除汉奸,使矿区和农村出现转机。
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相继占领锦州、义县、阜新等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以施介为代表的阜新地委深入对敌斗争第一线,撤出阜新城后转移到阜北彰武一带进行游击战。带领群众拆铁路、炸桥梁,骚扰敌人据点,伏击小股敌军。
1946年初,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率部出关,像一把尖刀直插东北敌人心脏,于1月16日攻克东蒙战略要地通辽,并成立了通辽中心县委,施介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任通辽县委书记。
通辽位于哲里木盟中心,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成为东蒙地区的南大门和前哨阵地,控制边沿地区的咽喉,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4月29日,根据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的指示,建立哲理木盟地委,辖通辽等五旗。5月24日,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到通辽,宣布哲里木盟地委由11人组成,施介为四个常委之一。同时成立通辽县委,施介任哲里木盟地委组织部长兼任通辽县委书记。
通辽地域辽阔,环境特殊,社会复杂,加上日军占领东北时的蓄意纵容和国民党反对派的豢养扶持,境内地主土匪、王爷反动武装及各种“门会”五花八门。这些团体拥兵自立与人民政府作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施介不畏艰险,认真执行地委“创立政权机构、发展党组织、建立武装”的决定,在武工队配合下,率领干部深入边远地区,发动贫苦农牧民,组织群众武装,清匪反霸、打击敌人,恢复生产,建立党组织和农牧民基层政权,使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在草原上扎根。
10月,国民党71军81师侵占通辽,为避开国民党的疯狂进攻,保存实力,哲盟地委政府机关及蒙汉联军和科左中旗政府暂时撤退到辽北打游击,并组成“长江骑兵团”,施介兼任政治部主任。
那是一段极为艰险的岁月。原辽宁省人大副主任赵石在其《情操友谊话施介》一文中曾这样写到:“1946年10月,敌人进攻通辽,我们一块撤到辽北,因地区缩小了,地委改为工委,我率领蒙汉联军、蒙古武装转战,施介和吕仁明率领政府机关到高力坂成立了一个长江骑兵团,施介兼任团政治部主任。12月,蒙汉联军挥戈南下,回到科左中施地区打游击,那是蒙古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反动王爷的压榨和国民党匪军的疯狂掠夺,条件艰苦,施介带领部队在那一带打游击,困难可想而知。”
1947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东北战势犹为紧张,哲盟地委區域日益缩小。为适应敌后游击斗争,哲盟地委改为工委,中共辽吉省委任命施介等8人为工委委员,施介还任常委及组织部长。
在组织工作中,施介知人善用,积极发挥党的政工作用,深受干部信赖,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施介为人忠厚老实,工作任劳任怨,由于长期在艰苦的环境忘我地工作,不幸染上了肺病。尽管如此,施介处处以身作责,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作战时,他总是不顾安危冲在前;撤退时,他总是在后掩护;宿营时,他总是把热炕让给战士;行军时,他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不论什么场合,都可以看到他精干灵巧的身影,听到他鼓动人心的声音。即便是病痛加剧的时候,他仍然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坚持工作与战斗。
初春的塞外,到处冰天雪地,朔风怒号,黄沙扑面。由于风寒的侵袭,施介肺病加剧,咳嗽不止,但为了不影响战士们的情绪,他咬紧牙关,竭力克制,时常憋得脸色苍白,眼角流泪。实在忍不住时,他把马缰绳咬在嘴里,或把前胸顶在马鞍上,有时干脆下马急步行军,以减轻病痛的折磨,以坚韧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
施介身为工委组织部长和骑兵团政治部主任,肃匪反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生产、发动支前等所有工作交织在一起,工作十分繁重,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毅力同病魔作斗争,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工作。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工作,施介向来任劳任怨、身先士卒,平易近人、关心下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由于长时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忘我工作,施介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及并发性脑膜炎,8月,被送往吉林省白城医院抢救。
得知施介将要离开通辽的消息,当地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学校师生、城里百姓纷纷赶来,不约而同前来送行。虽说没料到这是最后的诀别,但看到施介面颊消瘦、颧骨突出,不少人泪满衣襟。而倦意十足的施介虽然心中也有万千话语,却已没有说话的力气,只有默默地望着送行的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留下血汗和足迹的西辽大地。
虽然中苏名医进行联合会诊和精心治疗,但由于没有及时医治,施介病情恶化,不见好转,生命垂危。临终前,施介在医院的病床上从昏迷中苏醒时,吃力地睁开眼睛,对守候在身旁的省委领导及医护人员断断续续地说:“可惜我不能回去为党工作了!”
1947年9月18日11时30分,施介怀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对战友的依念,对远方故土和亲人的眷念闭上了眼睛,年仅三十八岁。
施介同志逝世后,他的骨灰安葬在白城。当地政府和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而非常痛惜。时任中共辽吉省委书记的陶铸与省委组织部长曾固为他题写了碑文:
我们最好的同志为工作而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为了纪念施介烈士,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这位“通辽的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哲里木盟通辽市所在地以施介命名的机关、街道、学校、道路、医院、工厂有十九个之多,还于1958年为施介等三十三名革命烈士修建了纪念碑,在烈士陈列室中陈放着施介等五十位革命烈士的骨灰。于2011年投资120多万元,历近半年时间修建了120平方米的施介烈士纪念馆,并于2014年把纪念馆当作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在吉林省白城市烈士陵园里,施介的墓碑位居182位烈士墓碑正中,上下两层,高大壮观,格外引人注目。
鉴于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施介被列为中央指定立传的云南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7名烈士之一,名列第三。洱源县政府为之立传为《苍洱英烈——施介》,并为其在凤羽古镇修缮故居,竖立大理石碑。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
且欣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这是施介留下的一首遗诗,表达了他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之心及以身许国的崇高思想。施介说到做到,用坚贞的革命信念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用壮丽的青春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生命之歌,他永远活在蒙汉白各族人民的心中!
编辑手记:
施介,生于大理洱源县的凤羽,其一生辗转大理、昆明、滇东、宁沪、延安、内蒙等地,在经历过南疆北地的艰苦后,他的红色革命思想也经历了从萌芽、成熟到实践。最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于我國北疆。通过此文,我们不仅能看到施介作为后辈对婶母的感恩、作为丈夫对妻子的忠贞、作为战士对革命的坚决、作为成员对组织的忠诚,透过他,我们还看到了劳苦大众对摆脱压迫的渴望和战友同志之间相互帮扶的情谊。修身立德、共赴时艰正是当时千千万万革命前辈的真实写照,也应为后辈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