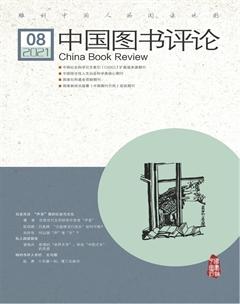执守大地的温情与温暾
晏杰雄 陈璐瑶
【导 读】《十月的土地》一改“野蛮东北”旧有刻板书写,似能读出南方小说的绵细深长,体现一种淳厚温和美感。“十月”“土地”意象所指丰富,喻义大地上的收获及人与土地的深层联系;主人公章文德的传统美德不随时代动荡而移易,彰显人性的光辉;特别是他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情谊,在艰难情境下坚持种地,体现农民对土地的忠诚信仰。叙事上采取内视角透显人物心理,语言具有民间风味。
【关键词】土地 传统美德 温暾
自“寻根文学”兴起后,新时期乡土作家致力于深入原始文化岩层,发掘儒家文明之前那自然、血性的一面,为民族勇武性格寻求地域文化的本源性依据。关于东北的记忆书写大多与20世纪的抗日历史共存——肥沃的黑土地与鲜血融合,东北汉子同仇敌忾,穿梭拉网,与血红的高粱地布景形成浑融的映衬,生机、野性、粗粝相应成为东北文学创作的主流风格。而读津子围的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却读出不一样的感觉,在葆有厚实的东北气质外,似读出南方小说的绵细深长。这在一片“杀气腾腾”的东北印象书写中显得特立独行!小说再现了一个闯关东的农村家族从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的变迁史,围绕章家内部抵牾、与土匪的矛盾、与日本人的抗争展开叙述,人性异化、家族解体、抗日斗争等事件交替映現,从中可以窥见人生百态和20世纪的
东北日常情状。津子围也有通过写家族史折射大历史的史诗性追求,但笔下的历史多了对土地情结的传统文化深描,描绘的东北乡村在粗野中保留了一份细腻的温情。这得益于对主人公章文德的形象塑造,这类平凡而懦弱的劳动者不断被驱逐,却始终坚持开荒、执守大地,最终在绝境中爆发,奋起反抗侵华日军,是无数良善坚强的中国人的生动写照。章文德是当之无愧的土地守卫者,用温情与温暾唤醒了人与大地久远的血肉羁绊,强调了守“根”的重要性,反映了津子围对社会生活体验的深度思考——个体生命的代代传承无法离开土地的滋养,所有理想主义的张扬,必须扎根于脚下坚实的大地。小说再现了传统美德的力量,并重点刻画了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与执着,为突破“野蛮东北”旧有刻板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营造了淳厚温和的阅读美感。
这种特殊的阅读体验首先源于津子围对小说意象的选择与构建。小说题目“十月的土地”有两个要素:“十月”鲜少出现,是一种美好朴实的期望,代表平安富足。章文德所代表的劳动人民盼望的正是安全稳定的平凡日子,而小说尾声交代了1945年8月日军投降,就暗示着广大劳动者在经历了血泪苦痛的斗争后,即将迎来真正的丰收十月。“土地”则贯穿全文,指代人类赖以生存的温馨家园。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土地都象征着自然之母,哺育万物,在此也不例外。小说开篇就写到了“腥丝丝的泥土味儿”,所用的比喻是“好像女人生孩子后,丈夫在炭火铁盆烘焙子宫时散发的、那种令人钻心入肺的腥味儿”。这里显然赋予大地以母亲的形象,将泥泞的土地比作生育孩子的子宫,而处于濒死状态的章文德回归了母亲温暖的子宫,陷入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梦境中。这种描述并没有使人感受到面对死亡的恐慌,反而带来奇异的镇静与安抚,并且这种与生育相关的腥味儿也暗示着章文德生还的可能性,奠定了小说中土地作为养育者的角色,也解释了章文德为何会成为坚定执着的大地守卫者——因为他就是大地的孩子。
其次,主人公身上的传统美德力量,特别是他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情谊,也为小说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小说中一共有三次土地开荒,涉及三代人。后两次开荒都是章文德被本家、被日本人驱逐而被迫进行的,这意味着他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只能通过开辟新的土地来谋生。津子围安排三代人开荒的用意在于强调“土地”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开拓新土地并扎根于此,才能开创家园建立羁绊。“活着就要找土地。找土地不是为了活着。”培根的名言在此得到了更丰富的诠释。章文德是被逼无奈参加革命的“平庸者”,乱世使他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无处容身的悲哀与恐惧对他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沉重压迫,无根的失重感战胜了懦弱怕事的本性,逼至绝境就爆发了勇敢的血性。父亲章兆仁的遗言“只有守住了地,咱的子孙后代才有落地生根的泥土”,更是他永不敢忘的教诲。“我的命没了地也不能没了。”透露出章文德骨子里的坚韧,与土地的坚实厚重一脉传承,这种内在的联系是小说对人物形象的补充与完善。他并非一味只懂得退让,只是良善的本质促使他选择容忍,正如同广袤的大地一样沉默。但章文德的特殊,就在于他身上同样流淌着大地的野性,被挑衅的愤怒被压抑积累,就会反过来支配他的身体。这种抗争,目的是守护,而不是争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温和本性。为了守卫自己辛苦开荒出的土地,章文德几次冲锋陷阵,九死一生,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击败他,这种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令人惊叹。两次失去与重建,无形中加强了章文德与土地的深刻联系,使得他更加重视“家园”的重要性,所以他对大地的深情厚谊是别人难以企及的。而且每次被驱逐时,章文德都没有换一种谋生方式——说明是潜意识做出的选择,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信赖与依恋,这就是农民的本能。此外,小说中章文德、章文海兄弟均从土里死而复生,结尾处也揭秘二爷章秉麟附魂在章文德身上与他共存。这种颇为奇异的与土地有关的“复活”,既接通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大母神崇拜,我们的先祖从作物周期性荣枯中,认为大地母亲具有掌握死亡和再生的超验力量;又暗合古老东方“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轮回思想,世界和生灵都在一个圆环上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故而在章文德的潜意识中,人属于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能割舍与土地的联系,人的灵魂与肉体都受土地的限制与保护,要寻求土地的庇护,必须以开荒为起点,从而延续生命的希望。开荒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劳动,也代表着对人类物质与精神家园的拓展、壮大,所以开荒者也是“开路人”。
除了开荒守土,章文德的温情与温暾还体现在即使处于各种特殊情境下也始终坚持种地。一是他去看守被土匪盯上的金矿。“可出于本能,章文德见不得土地被糟蹋了,他自己也闲不住,遇到下雨天不能出工,他都觉得浑身直痒痒……目的就是种地,只管耕种,没想收获……”经年累月的耕作早已融为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变成本能的习惯。津子围在塑造章文德时,有意识地将人物与土地这个意象相结合,把个人命运完全与土地绑定,将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安置在有泥土的环境里,而“土”的厚实、沉稳也相应地转化为章文德性格的组成部分。作为大地的执守者,章文德身上具有和现代人格格不入的执拗与单纯,是极其典型的守本分的旧式农民,这点在与堂哥章文智(接受了新派思想的“先进代表”)的对话场景中更为明显。小说结尾处,堂哥认为土地是“盘剥人、捆绑人的”,追求解放,不愿被土地束缚;而章文德的愣怔正是对这番言论的反驳。章文德就像一个从远古时期穿越而来的人,他虽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历史变革的重要时刻,却难以接受时代的迅速转换以及思想的剧烈变更。他身上具有明显地落后于时代的错节感,这种落差注定了章文德最后会回归大地的怀抱,也暗示了他下半生的归宿就是与土地为伴。二是章文德在被迫随土匪逃难的岁月里也不忘耕作。有一个情节是他哼唱歌谣:“老鹞鹰,嘭嘭飞,飞到东,飞到西,飞到高,飞到低,快快飞到你窝里。”土匪们都一起哼唱并伤感起来。“鹞鹰”指代这些离开家乡漂泊的人,正是因为割舍了与故土的联系,才会有无处可归的迷茫。这份伤感是想回“窝”的渴望,是对乡土的思念。章文德是一个与传统东北文学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异类:他生性懦弱胆小,对土地具有忠诚的信仰,并没有土匪姜照成等人“像个大男人那样志在四方”的豪气,只想“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富即安”。津子围在塑造章文德时,并没有打上英雄的烙印,而是注入极为深厚的人民性——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因此,章文德的意志表达就具有深刻的代表性,而他的权利诉求即“拥有自己的土地安稳度日”被两度打破时,正说明了普通百姓同样面临生存困境,这也是当下许多游子失重心态的真实反映。在时代规则制约下,章文德是极少见的能从大地那里获得慰藉的人,是看透了命运轮回与生命痛苦本质的智者。小说接近尾声处,章文德从二爷留下的木盒里找到了七粒谷种,用儿子的童子尿育出了嫩芽儿。这无疑是一道生的启示,说明了章家的血脉将代代传承,如谷种一样落地生根,坚强生长。
除了人物塑造突出,小说在叙述上也颇具特色。譬如叙事上主要采取内视角,而且视角切换繁杂、迅速,将各个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细致地展现出来。津子围安排章文德作为主要视角的承担者,在第一章利用他的记忆“闪回”,引出了对章家主要成员的介绍,使我们对重要人物堂哥章文智、二爷章秉麟有了初步认知,奠定了章文智喜欢钻研、学识丰富的形象,而章秉麟“神秘、古怪、和善”的脾性也可以略知一二。除此之外,小說的语言极其生动,具有贴近底层劳动人民的“野味儿”。主人公章文德是个地道庄稼汉,所以在农事上头头是道,预判天气和分享耕地经验时往往以谚语开头,“扑地烟,雨连天”等层出不穷。小说还刻画了一个老光棍“老庄头”,张口即来“四大白、四大急、四大小……”插科打诨的乡下瞎话极具生活气息。后文情节写到土匪胡子,还涉及了一些黑话:抹尖子(尖耳朵)、插了(杀了)、喷子(鸟枪)、海青子(大刀)……打磨语言需要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进行锤炼,信手拈来的大量农谚、歌谣、俗语、黑话,对农家用具、房屋、耕作细节的勾画,都说明津子围在写作前期的深厚素材积累,所以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地层温度的人民文学。
当然,小说的后半部分节奏过快,相比于前三分之一细致描写家族矛盾、田园生活,后面与土匪、日本人的交锋就有些潦草,处理各人物的道路选择上缺少细节,而且对于部分女性譬如章韩式的刻画不够深入,导致一些原本与男性角色一样充满闪光点的女性沦为配角……除了这些小瑕疵,《十月的土地》总体上是一部代入感极强的饱含深情与眷恋的小说,修正了对东北文化的记忆偏差,展现了主人公章文德温和淳厚、有如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并揭示了人与土地互相守护的羁绊情谊。正因如此,《十月的土地》才会具有一般描写东北乡村的小说所欠缺的内在柔和之美,给我们带来绵长悠远、鲜活感动的阅读体验。守土才能寻根,寻找人性的归处,寻找心灵的栖息地。章文德的形象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他的懦弱与勇敢分别是个体灵魂的一体两面,而他的执着与温情正是津子围追寻并想展示的崇高品质。津子围用自己的创作对抗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试图用文字追溯古老而遥远的理想桃源。这种脱离了现代“高飞”意识的守根心态,是一种对传统文化与质朴人性的怀旧情怀与真挚呼唤。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长篇小说文体发展史”(20BZW1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宜宾学院文艺学部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周雨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