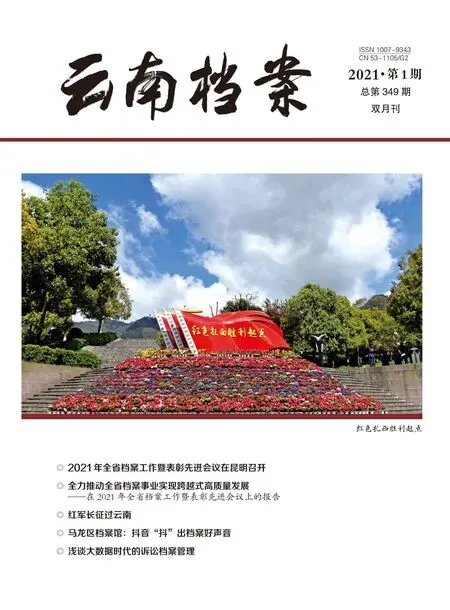西南联大组织特色探析
■ 史晓宇
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在抗战全面爆发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挽救大学的命运,保持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保存中华文脉,在战时状态下对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种治理模式选择。
1937年8月,《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中第一条即说明了组建联合大学的目的,内容写道:“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1]这切实说明了临时大学的筹设,实质上是在抗战中,为了避免全国高教系统被破坏,需要对其全力保存和恢复有效秩序,同时在特殊时期高校也应继续培养人才以应国家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对于这所特殊时期组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学,它的组织性质和特色,有必要作一些分析和阐释。
一、组织性质
关于西南联大的组织性质,我们所熟知的是,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所临时的联合大学,是三校合组而成,即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是容易忽略的是,西南联大的成立,实际上是成立了一所新校,这所新校并非三校的实质性合并,因为政府并未取消三校的原有建制。对于三校来说,不是谁并入谁的关系,而是在这所新设立的大学中平行的联合、合组关系,即三校是参加西南联大,是立足本校、服务联大,而三校亦有各校的建制、机构和事业。
关于这一点,清楚地记录在由联大人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1942年12月21日)》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等史料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1942年12月21日)》的开篇“学校沿革”中一语道破,系“联合筹设新校”:“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平津陷于倭寇,北方各大学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于长沙联合筹设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2]而在另一史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是这样描述的,“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平津陷于倭寇,北方各大学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迁于长沙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于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离长沙,四月二十八日到昆明,并奉教育部命,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于五月四日恢复上课。”[3]
而三校的建制存在的痕迹,我们举个西南联大内部的“三校办事处”的例子可知,西南联大史料中分别记录有“国立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机构、人员名录(1942年)”[4]、“国立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机构人员名录”、[5]“南开大学昆明办事处机构人员名录”[6]。
关于这一点,也可从联大的英文名称知照。1938年2月,联大第49 次常委会决定的长沙临时大学的英文名称为“Lin- shih- ta- hsueh(The Associated National Universities: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7],Lin- shih- ta- hsueh系民国时期经常用到的邮政式拼音,系指“临时大学”;而括号中的英文名称很长很特别,特别之处在于明明白白写着三校的校名,三校是“Associated”,是复数形式的“Universities”,是大学联盟的关系,这才是组成这所大学的三校之间关系状态的原初反映和真实表达。当然,仅仅过了3个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名就改为了“The National South- 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8]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都有“Associated”,但三校独立建制的痕迹在这一校名中已经被自然遮蔽。
三校在西南联大的内部存留,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西南联大组织的认识和态度非常明确而具有代表性,“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9]。在国民政府主管负责人的表述中,联大是“维持”的状态,组成联大的“各校”是单独存在的。
二、常务委员的身份
从西南联大常务委员的角度理解,一方面,在1928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中明令“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10]而西南联大常务委员是“聘”而非委任或任命;另一方面,常务委员与西南联大的关系,是“兼职”而非实职,其本人的实际职务还是某所大学的校长,就是说,三常委原来的三校校长身份依然存在。
这可以从史料中的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方面,西南联大1945年10月24日的常委会会议记录显示,“(一)梅主席报告:蒋梦麟先生为业已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所有本大学常务委员兼职,自应一并解除,即希察照来函。(二)梅主席报告:教育部为聘傅斯年先生为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除置聘外,仰知照训令。傅常委并已到校”。[11]由记录可知,蒋梦麟辞去的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而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只是属于兼职。另一方面,这也清晰地显示在“南开大学昆明办事处机构人员名录”中,1938年,张伯苓的信息是“张伯苓 常务委员 校长;黄钰生 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兼秘书长”,及至1946年5月,在同样的名录中记录为“校长办公室 校长张伯苓”,[12]说明南开的校长办公室、校长、秘书长依然存在。所以,联大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四所学校:联大(在常委会记录中称“本校”)、北大、清华和南开。
三、管理人员的身份
以这种模式延续下来,推而广之,三校人员依旧保留在原来学校的职务;联大的各处处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职务在联大皆为兼任职务,而非专任,身份都是教授。这可以从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中一目了然,“一九四五年年四十七岁 依阳历新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秘书长、文科研究所副主任,兼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总务长、校务会议书记。”[13]
四、师生管理
原三校的教师人事管理权在各自学校。他们是在各校聘任基础上由联大再为加聘,是参加联大服务,非属联大编制,也不由联大负责管理。参加西南联大服务的教师,不止服务于本学科所属的学院,也被其它学院加聘,如师范学院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兼任。参加服务联大的教师如有特殊情形不需继续服务,是由联大通过致函该教师所属的学校解除聘约,聘约解除即意味着此人同时丧失了参加联大的服务的机会。联大后来聘任了一些教师,其编制又属于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职员是借调或调到联大。这一点,在“国立北京大学参加西南联大服务之教职员名单”、[14]“南开大学教职员参加西南联大工作人员姓名表”、[15]“国立清华大学参加西南联大服务教师名单”[16]。这些史料的标题中即可获知;另外,在联大教职员名册和各校机构人员名录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和痕迹,如“国立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机构人员名录”中,“技师 周蓁(1939年2月起为联大借调)”[17],“注册部 主任 朱荫章(1943年2月调联大)”,[18]资料显示,类似调到联大的还有4 人。
三校各自的学生进入联大在表述时也称“参加联大”。我们看到,到了1942年,在“国立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教务会议”的记录中,还有“本校三十年度参加联大学生(共卅三人)”的表述。[19]
五、联大组织内部隐含的变数
及至抗战即将胜利之时,西南联大一路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联合到底,联合成功,已为世所共知。反倒是由于长期战乱和人员的变化更迭,组成联大的三校之于教育部而言,已是一种若隐若现的状态存在。这种维持和联合的情态,在联大三校复员北返时就变得不那么简单:此时三所学校在国家学校制度层面上的位置、意义和作用究竟是什么?三校北返后能顺利复校吗?还会是有预算、有补助的独立的三所学校吗?国民政府会进行重新考量和设计吗?这种种的问题,自然引发了身处其中的、熟稔西南联大内部管理样态的办学管理者的不少焦虑和危机感。
身为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员,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此事的思考是非常深邃的。他在1945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枚荪昨日还,据谈教育部本年可拨北大特别费五十万,骝先对于北大复校甚关心,愿在战事结束前作一法律上定案,其意愿加设农、工、医三院,嘱余等筹之,余意第一步应先由教育部承认三校地位与各校一律有预算、有补助乃可也”。[20]在当月10日的日记中又再次表达了这种忧虑,“九时旋舍。作书复孟真,谈复校事,大意有十点:……二、请教育部承认北大、清华、南开之存在,一切权益与他校等;……”。[21]而郑天挺先生对此种不确定性的忧虑,伴随北大校长蒋梦麟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的传闻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继而与当时仍然留存的西南联大的领导体制是否发生变化紧密关联在一起,并于1945年7月8日的日记中流露出来,“同人所鳃鳃过虑者,在恐联大改校长制,故由。托蒋太太上第二书,请维持常务委员制,……”[22]。好在此后联大依然维持常务委员制,三校如愿北返,一切尘埃落定,归于平静。
值得关注的是,西南联大虽然采用的是委员会制,但其决策及实施是高度内聚统一的。西南联大的本质不是三所学校的简单集合,而是三所学校精神融合基础上大学联合体的集成彰显。虽然三校人员的身份是多元的,但只要是参加西南联大的教职员,都凝聚在西南联大的旗帜之下,认同于学校的精神文化并形成一种信念,而作为西南联大“代理校长”梅贻琦的心里是装着这四所学校的。
结语
西南联大相对于在实施联合以前的北大、清华和南开这三所独立建制的大学来说,是一所结构上更为复杂也更为松散的大学联合体,是一所类似于联邦结构的大学联合体;但其精神上是一所爱国、团结、民主、科学、进步的大学联合体,是一所一体化的联合大学。
作为一种大学组织的特殊样态,西南联大这种大学联合体,留给我们思考和研究的空间是很大的。西南联大的组织系统,内部治理结构,组织运行的特点和方式都将受此影响而产生出更多的变化。这也从另一种角度诠释了《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23]所蕴含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