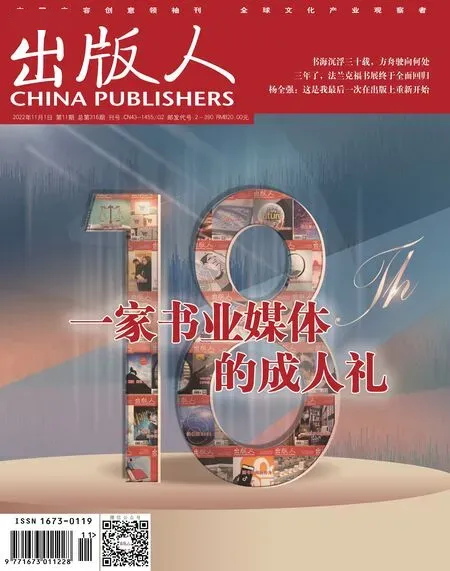杨全强: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出版上重新开始
记者|谭予
成立出版品牌“新行思”是杨全强作为出版人的“最后一搏”。
“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再失败,我就没有任何借口重新开始。”经历多次重启的出版生涯后,成立出版品牌“新行思”是杨全强作为出版人的“最后一搏”。
做出版的前20 年,杨全强辗转待过三家国有出版社,安心在体制内出版社做一些小众的严肃图书,而不必承受经营的压力,是他理想中的工作状态,就算“因为经济效益表现普通而难以更进一步晋升”,他也没有想过离开体制。
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子品牌上河卓远的最后两年,由于社内业务的调整,杨全强的出版生涯几乎陷入停滞,无法自主决定业务的存续,这虽然让他感到沮丧和无力,但他丝毫不曾想过改变自己。好友也是他现在的搭档杨芳州很早就劝他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但直到鲍勃·迪伦的《编年史》到期,这本曾经让杨全强自掏腰包也想做出来的书后续版权最终流去了其他出版社,他才同意采取行动,注册了行思。
很快,有投资方找到他,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杨全强想,既然对方知道自己这些年来做过哪些书,就说明他们还是认同他这些年所坚持的出版领域与方向的,杨芳州也认为有团队、有资金,迅速做出一个品牌,才能发挥出他的能量,所以鼓励他接受投资。毫无“江湖”经验的杨全强因此交出了“行思”的控制权,以雇佣关系成为自己创立的品牌行思的总编辑。
直到资方资金链断裂决定结束出版业务时,这两个搭档才意识到,尽管跳出了体制,关键时刻到底还是不能自己说了算。
在掌控出版业务、为所有图书涉及的作译者设计师等负责到底方面,杨全强不想再跌倒第三次,新行思成立后,虽然仍有新资方的加入,但他和搭档终究把握住了图书业务掌控权。
正式转入“商业赛道”的第二年,杨全强似乎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面对《出版人》记者关于新行思可能再次遇到不可预知的挫折的发问,他虽然做出了文章一开头的回答,但话锋一转,他不容置疑地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肯定不会有问题。”
想从数字上来认识一下自己
一年前,当杨全强选择跳出体制以一个独立出版人的身份开始做书,并接受投资方提出的年度生产码洋目标时,他就注定无法像以往那样在出版业的经济效益层面继续“含混”下去了。
在体制内度过了出版生涯的前20 年,花上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慢慢“养”一本书,是杨全强做书多年坚持的一贯战略。只要认为一本书有价值,他就会去做,“数字”很少是必须列入考量的因素。在业界看来,小众、学术且不赚钱似乎成了杨全强所做的书身上撕不掉的标签。即便印象如此,拉长时间来看,这些书中的大部分其实也并没有让出版社赔钱。
做思想人文、社科文学这类书想要获得市场、渠道和读者的认可,往往要经受比一般大众书更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须承担起人力、版税预付等成本。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赔钱”是不可避免的,谁也绕不过去。杨全强在上河卓远甚至是更早之前的南京大学出版社时,前面的几年从账面上看也都是负的,因为有体制的支撑,杨全强并不着急摆脱这种状态。“慢慢你会越做越好,到了一定阶段,就开始赚钱了。”他说。
可是,当资本的审视取代了体制的庇护,行思却不得不因为赚钱不够快而在短短一年后就被迫终止。这一年中,仍在磨合期的行思团队做了十几本新书,还有近20 本卡在了合作出版社的流程而没能出来,资方期待的生产码洋目标最终没能完成。
资本“无情”撤离,刚刚有点习惯了在体制外做出版的杨全强,却不打算就此终止自己的出版生涯,他和团队从原公司脱离后,就地成立了“新行思”品牌。这一次,经历过来自资本的评判后,杨全强决定开启一场自我检验,“我确实也想从数字上来真正认识一下自己”。
尽可能地缩短前期的资金投入阶段,利用有限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收支平衡,这是新行思当下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以杨全强过去的经验看,达到这一平衡可能需要三到五年,但现在,喊出了“必须赚钱”的他想要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提一点。
“有两到三年,到明年底或者后年,各方面应该都循环起来了,就不用再担心到哪里找钱了。”为此,一向不擅长经营的杨全强和搭档没有少做盘算。按照目前的人员规模,再刨去各种办公成本,新行思一年的销售码洋达到3000 万元的时候,两个人就可以不用再为钱的事发愁了。这一数字落到具体的图书产品上,在明年年底前,新行思的编辑们要做出50 种以上的新书。
3000 万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想要“轻轻松松、愉快地做书”,杨全强私下里给自己定下的年销售码洋目标,其实不止5000 万元。
并非白手起家
两年时间,让一个出版品牌能完全依靠自己活下来,这是杨全强过去不曾考虑过的。放在一年前,他或许也还不敢说自己就能做到。
做独立出版对杨全强来说完全是一个新事物,无论是团队内部的磨合,还是与合作出版社在流程的协调上,行思成立后的第一年都必然只能是一个摸索阶段。编辑们的做书偏好要与整体的品牌调性融合,同时还要尝试各种营销动作,等到终于顺利把书做出来,出版社内部的流程也有可能影响出书的速度。这个过程里,来自资本的压力始终悬在杨全强和编辑们心头。
回头看过去的一年,杨全强感受更多的是磨合和压力带来的积极一面。“我觉得去年一年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炼,整个团队形成的这种趣味,包括做事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甚至是跟出版社之间的磨合,都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杨全强说。
不用重新开始打地基,除了书出得不多,新行思具备了杨全强以往做出版时没有过的基础和便利。不管是在南大还是上河卓远,杨全强几乎是都是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品牌或产品形象,而出版又是个极度依赖整条系统循环配合的行业,即便他从选题角度做得无懈可击,社内原有的发行和营销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书堆在仓库里,读者买不到,“你不赔钱谁赔钱”?
如今借助合作出版社在市场上的可见度和出版形象,包括对方成熟的渠道发行能力,杨全强不需要再重复以前“白手起家”的老路。“我把合适的产品放到它们的系统里,就一定会有效果。”杨全强说。
新行思今年新增了两家合作出版社,目前看,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合作都进行得比较顺畅,没有出现书长时间被卡住出不来的问题。如此一来,能否在短时间内靠自己活下来终究还得看图书本身。
集中在杨全强身上最大的争议,除了能否赚钱,就是他做的书看起来太过小众,诗集、哲学、文艺评论,能卖多少呢?一定程度上,业界正是从他的小众做书偏好而判断他并不能真正赚到钱。
每次有媒体采访,都不免提到类似“做小众书很难”的看法,听得多了,同事Phoebe 不禁想,做大众书就不难吗?“大众书可能更难,你卖两三个月,可能网红博主也不推了,抖音也没人带货了,就真的卖不掉了。但我们做的这些书不一样。”
总有人要读文学,要读如何理解文学,总有人想了解艺术是怎么回事。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就很可观,每年都会有新的读者被生产出来。“比如说我今年上高中,没有读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但到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读这本书,我的上一级可能比我早一年读到了这个书,无非就是这样而已。”
在杨全强深耕的这一小块人文社科领域,一本书在一年的销售周期内卖出4000~6000 本,是一个“可以基本保证的量”。这个自信的根源,在搭档杨芳州看来,在于图书出版始终有一个主流。“只要书还在,最后剩下的买书的人就是会买这类书。科普、经管什么的可能很容易被公众号、视频的内容所替代,而诗歌、文艺类的读者,他们喜欢的就是书。”杨芳州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类书心里就特别踏实。”
活下去的逻辑
“每本书都卖五六千册,我就不可能活不下去。”杨全强告诉《出版人》杂志,这是他这么多年做书的直觉,也是这个行业的基本逻辑。
卖出首印绝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杨全强希望有相当一部分书,“至少要保证1/3 甚至1/2”,能过万、两万,甚至是有十万几十万的书。
从原行思去年一年的表现看,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定价400 元的詹姆斯·伍德全集首印4000 套,一个月就加印了,到春节前,《三只忧伤的老虎》也卖过了5 万册。“如果没有去年年底的变化,今年我们《三只忧伤的老虎》肯定是要过10 万的,伍德也要卖到2 万套。”杨全强说。
抛开这两本书自带的作者光环或口碑积累不说,单从“价值”的层面判断,他认为这些书迟早也能卖到这个数字。“我做了20 年的出版,很清楚哪些书大概有多少读者,虽然不能叫出每个读者的名字,但我知道中国肯定有这么多人要读这些书。”他表示。
而在杨全强所做的图书类别里,他的搭档认为,前者在对选题价值的判断和最终呈现出来的图书品质方面无疑是一流的:“这个话说起来非常自负,其他出版人就是知道这个作者、知道这个类别,可能也做不出我们做出的那种感觉。”
去年7 月,晦涩难懂的拉美文学作品《三只忧伤的老虎》出版,杨全强等了8 年时间才做出这部让不少出版人望而却步的书。今年即将出版的安托南·阿尔托文集《对诗歌的反叛》同样让杨全强等了近8 年。阿尔托是20 世纪初的法国诗人、剧作家,此前,因为翻译的难度和选题的小众,国内极少有出版社译介过他的作品。在资深西方文艺理论学者尉光吉的主持下,7 名译者参与到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中来,最终完成了这部近千页的作品。
时隔100 年的文本,当杨全强和编辑们再读到它,仍惊叹于作者的功力,觉得他写出了“我们可能有几十年都读不到的东西”。和《三只忧伤的老虎》这类可读性更高的小说类别不同,阿尔托的这套文集更厚,“也更挑人”,但基于新行思目前的团队营销能力,包括杨全强对市场可能性的了解,他还是表现出了极强的信心:“960 页、30 个印张,定价180 元,你看看一年之后我们到底能卖多少。”
对更多的书而言,要卖上过万的量,甚至更多,仍然需要“养”。把书做出来,放在市场上慢慢培养读者,这是杨全强过去相当熟悉的节奏。2015 年在上河卓远做的《文学阅读指南》首印4000 册,第一年首印消化完后,第三年到期之前,还能以每年4000 册的销量持续滚动,如果不是业务停摆,没能续约,他估计至少再往后至少3 年,每年4000 册仍然没有问题。“如果再扩大一些宣传的范围,往高中语文阅读方面去努力,实际上还可以有更大的量。”他说。
耐心养书的同时,杨全强也在主动调整自己。选题上,他已经尽量减少那些市场反应更漫长的严肃学术类图书。原先几乎由他一人决定做哪些选题,现在,他的决定至多占到50%,经过了一年磨合,在选题趣味、调性上已经充分相互信任的编辑们越来越多地提出更多样而有价值的选题。因为有编辑对漫画感兴趣,新行思今年还首次尝试签了几部漫画,其中一部西班牙的漫画在发给译者范晔看后,对方非常感兴趣,进而接下了它的翻译。
小而美是成立的
从各方面看,让新行思活下来好像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这里面有杨全强和搭档十几二十几年做出版的经验作为支撑和参照,也有基础条件转变带来的利好,杨全强主动调整自己以适应“商业赛道”的规则更是让新行思的前景越发清晰起来。
尽管杨全强的自我调整和观念上的转变足够让人惊喜,可透过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他实际上也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人。
杨全强不是那种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出版人,从南大社时期开始,他一直颇为重视图书的营销工作。只不过,在营销上有些底线是他始终坚持的。从去年到今年,新行思的编辑们解锁了多种营销玩法,对于营销节奏的把控也因为在《三只忧伤的老虎》踩过坑而更有经验,但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那样把书推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读者面前去,让本来就可能对某本书感兴趣的人知道这本书就足够了。“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反复教育一个读者,就是告诉他一个信息,他看到就知道这是他会买的书,这才是我们的核心读者。”
如同在卖书问题上,不求把书卖给尽可能多的人,杨全强也不希望新行思未来扩张到多大规模,“我们现在的10 个人,最多再加两三个足够了,做到轻轻松松地养活大家,就很好了。”关于未来的设想,伽利略、子夜、新方向、Verso 这些国外文学与社科社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出版机构:体量小、人员精、有自己独特的出版方向,且要做到这个方向最好的作者。对标这些出版社,他认为新行思也能活得“小而美”。
除了体量、人员和出版方向,新行思的“小而美”可能还要包括杨全强和搭档为团队营造出的有趣而正向的氛围。在原行思出现问题,已经停发工资的情况下,编辑们每天还能开开心心干劲十足来上班,直到三个月后原班人马宣布成立新行思,两个合伙人感觉到这个经历了一年磨合与摔打的小团队正有着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现在的新行思是一个略带乌托邦色彩的团队,虽然杨全强和搭档会一遍一遍算账,给自己定下“活下来”的码洋目标,但他们没有给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提出码洋或毛利的考核,搬到新的办公室后,连打卡这一最基础的约束也都取消了,日常的管理也是以正面引导为主。因为热爱自己所做的工作并珍视这样的团队氛围,编辑们表现出来一种非外力约束的自觉和勤奋。反过来,这又让杨全强对他的团队有着超越以往所有时候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