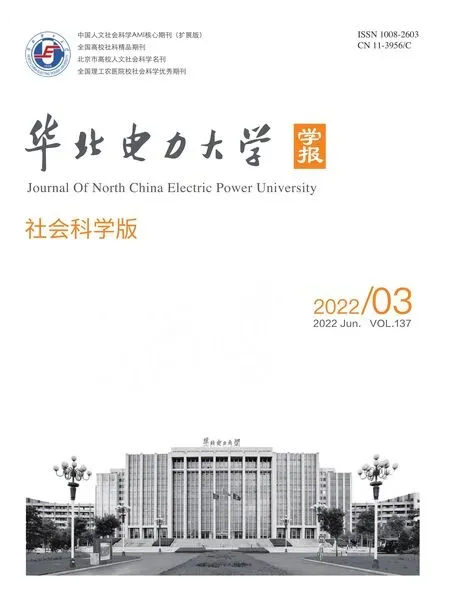唐集贤学士“分掌制诰”考述
——兼涉其性质与影响
王冰慧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00)
唐代集贤院主要职能是“刊辑经籍”,并开展教授生徒、议政献猷、酬唱侍从等活动。又集贤院与“分掌制诏”之说主要出现在有关翰林院建置的介绍中,如《翰林志》《新唐书》。而开元时期,唐代集贤院亦短暂地行使过“分掌制诰”的权力。然而,在研究集贤院职能的时候,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以下几点:教授生徒、编纂书籍、议政献猷、酬唱侍从等。(1)日本学者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之《盛唐之集贤院》(《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71 年)较早地关注文馆的问题,论文主要涉及到集贤院的沿革、省舍、职能、人物考述等方面的研究。随后,中純子《中唐の集賢院--中唐詩人にとっての宮中蔵書》(《東方学》,1998 年07 期)涉及到相关问题。国内较早关于集贤院的研究是傅士真《唐代集贤院之研究》(明雄出版社,1977 年)。此后,学界又有从书院史角度讨论集贤院,如陆新朔《丽正书院与知院事张说》(《洛阳大学学报》,1995 年01 期)、刘畅《唐代东都集贤殿书院的沿革及特色》(《现代教育科学》,2006 年)。杜海斌《唐代集贤院新探》(《唐史论丛》,2016 年02 期)对集贤院的制度沿革、职能变化、位置变迁等又进行了探索。另外,黄光辉《唐代宗朝集贤院十三待制考》(《唐宋历史评论》2019 年第2 期)还谈及到了集贤院待制的三个系统。近年来,学者对唐代集贤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对于集贤院的“分掌制诰”的基本细节等仍有可研究的余地。实际上,“分掌制诰”活动出现,是学士获得内制草制权的一种尝试;其活动存续情况,是对学士制度整体构建的一种反馈。因此,唐集贤院“分掌制诰”问题研究,有助于研究“亚制度”的存在模式,有助于理解学士制度(甚至其他制度)的自我反馈机制。
本文拟对开元时期集贤学士的临时职能(更确切说是活动)—“分掌制诰”展开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翰林志》《新唐书》《全唐文》等中分析“分掌制诰”的存在情况,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此问题考察的另一方面,即厘清学士掌制诰的初置动机。二是考述集贤学士草诏的撰写场所、草诏权的存续时间、草诏内容范畴等细节。这为后之学士撰写制诰情况提供了参考。三是结合前文分析,探究“分掌制诰”活动的性质与特点,进而明了其出现及消失的背后原因。这反映了学士制度的一种自我调整策略。
一、“分掌制诰”的初置与潜在动机
“分掌制诰”之“制诰”内涵主要指王言,“旧制,册书诏敕,总名曰诏。天授元年(690),避讳改诏曰制”[1]9 2 6,制书的功能是“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敕宥降虏”[2]274。至于“分掌”之说,自然是指集贤学士与该时期的中书省(主要是中书舍人)、他官兼知制诰之间的职能分配关系。目前将唐代集贤院与“分掌制诰”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典籍记录主要为《新唐书·百官志》《新唐书·吴通玄传》《唐会要》《翰林志》等。文书记载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况,因此有必要对集贤学士是否参与撰写制诰进行考察。“分掌制诰”的直接语源为《新唐书·百官志》: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3]274
首先,此处提到“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与《唐会要》所谓“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1]1146,李肇《翰林志》说的“至玄宗,置丽正殿学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后改为集贤殿,亦草书诏”[4]1 等内容都相契合。又结合《旧唐书》《集贤注记》并无记录集贤草诏一事,但与其他记录也并无龃龉之处。尽管《翰林志》《唐会要》《新唐书》等典籍之间有史源上的联系性,即便不能完全达到互补的绝对证据力,但其论述的一致性至少证明了唐时人对此的情况认知。这是集贤学士参与撰写制诰活动的直接书面证据。
其次,制度规定的落实仍需文本证据的证明。结合《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等相关内容,笔者收集开元时期集贤学士名录,并统计了其文章创作情况。(2)部分借鉴《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唐代文馆学士任职及出身简表”。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年。该群体(3)该群体所涉人物众多,主要包括以下若干人:(1)赵冬曦,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2)孙季良,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3)咸廙业,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4)吕向,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5)李子钊,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6)陆去泰,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7)毋煚,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8)余钦,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9)赵玄默,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0)侯行果,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1)敬会真,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2)冯朝隐,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3)陆坚,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4)张说,开元十三年入,十六年致仕,十七年复入,十八年卒。(15)徐坚,开元十三年入,开元十七年卒。(16)徐安贞,开元十三年后入馆,二十三年、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有在馆记录。(17)贺知章,开元十三年入,十四年出。(18)康子元,开元十三年入。(19)韦述,开元十三年左补阕入馆,十八年在馆,二十八年出馆复又入。此后未详。(20)王迥质,开元十六年入,十八年在馆。(21)陈希烈,约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天宝四载有学士在馆记录。六载、九载、十三载有在馆记录。(22)李锐,开元十九年前入。(23)张九龄,开元十九年有在馆记录,后因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复入,二十四年在院,后罢。(24)万俟馀,开元二十二年在馆。(25)崔沔,玄宗时期在馆。(26)尹愔,开元二十五年入,后不详。(27)李林甫,至迟开元二十五年入,后为集贤院大学士。(28)萧嵩,开元十九年、二十年有学士在馆记录。二十一年罢。(29)施敬本,开元时期在馆。(30)陆善经,开元末、天宝五载为直学士,后为学士。(31)于休烈,玄宗时期在馆。(32)徐峤,开元中有在馆记录。(33)卢僎,开元时期有在馆记录。(34)包融,开元中有在馆记录。(35)崔藏之,玄宗时期在馆。(36)李融,玄宗时期在馆。(37)韦逌,玄宗时期在馆。(38)王择从,玄宗时期在馆。(39)郗纯,玄宗时期在馆。(40)殷践猷,玄宗时期在馆。(41)韩覃,玄宗时期在馆。(42)杜慤,玄宗时期在馆。(43)史惟则,玄宗时期在馆。(44)严从,开元中在馆。(45)马利徵,开元八年补修书直学士。有文本者,如李林甫现存《全唐文》存其天宝八载(749)敕牒;徐安贞现存《全唐文》存其为中书舍人时所为制诰及为集贤学士时所作的哀册文;徐峤现存《墓志汇编续集》存奉敕志铭;陆去泰,《玉海》有开元十二年(724)奉敕铭文;张说,《全唐文》存其为集贤学士时的奉敕碑文;张九龄,《全唐文》有其为集贤学士时制诰等。
此类群体创作诗文中属于“制诰”占比较少,且可明确归为集贤学士期间所作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其代表为张九龄之文。张九龄两次在馆:一次是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入,后因丁母忧出;一次为开元二十二年(734)至二十四年(736)。开元十九年(731)至二十年(732)前,其作品主要是表、状等臣子进奏之文。此中属于制诰类的是开元二十年(732)张九龄(在秘书少监兼集贤学士副知院事任)《慰勉清夷军使虞灵章书》、《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一)[5]186。此时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学士,副知院事”(《旧唐书·张九龄传》)[6]3099,其中秘书少监掌管古今图籍、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等,与集贤院之职务有切合之处。如此任命倒也是顺理成章。但在此期间所作之敕文,若不是以“分掌制诰”的统治者命令而作,则有越权之嫌。笔者认为将其断为出于集贤学士临时活动而作较为恰当。可见,集贤学士撰写制诰的活动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此处提到集贤学士掌草诰的直接动因为“书务剧,文书多壅滞”。“文书壅滞”是官方意志基于实际情况作出的判断。尽管此判断很有可能参杂着官方意志改革学士制度的主观想法,但此足已构成集贤学士参与撰写制诰活动的合理动因。考各类唐史记录,开元十三年(725)至二十六年(738)之间,暂无说明“文书壅滞”的直接证据。然而,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何不用“知制诰”来解决此处的“文书壅滞”之忧?实际上,此时原本可掌制诰的群体主要是中书舍人以及他官兼知制诰,其他个体偶尔参与制诰撰写。中书舍人一般为六人,即“六人分押尚书六司”(4)(唐)李林甫撰:《唐六典》“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卷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1 月,第276 页。。六人之数,确实不算多。但是“他官兼知制诰”设定本身就是具有弹性的制度,其人数并没有规定上限。故而,笔者以为集贤学士“分掌制诰”是官方意志对学士制度构建的一种尝试。在已存在制诰撰写系统中,增加另一群体作为执笔者,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利的重新分配。笔者以为或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出于有意分散中书舍人的职权;二是出于任命的便利性。
二、“分掌制诰”的细节及试行情况
不同于中书舍人等已有群体,集贤学士参与草诏活动情况自成一套体系。尽管此体系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已有制诰撰写系统,且借鉴已知的行文流程,但其本身是学士群体参与制诰撰写的一种尝试。其活动场所、存续时间、制诰内容等,皆可反映出此次“分掌制诰”的试行情况。
(一)“分掌制诰”的职能场所
一般情况下,撰写制诰地应在集贤院。根据《集贤注记》记载:开元五年(717),“始有制于东京之乾元殿之东廊排写四库书”。开元十年(722)春,“始移书院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后之东京集贤院)”。开元十一年(723),归京,“始于大明宫光顺门外创建书院(后之京师集贤院),依旧称之为丽正书院”。开元十二年(724)冬,“车驾入都,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亦以丽正书院为号”。开元十三年(725),“改集贤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开元二十四年(736),“驾在东都(兴庆宫集贤院)”,“张九龄遣魏光禄先入京造此院”“在和风门横街之南”。开元二十八年(740),造华清宫集贤院,“在宫北横街之西”[7]207-223。可见,唐时有若干处集贤院:(1)东京之集贤院,开元十年(722)移书院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开元十二年(724)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2)京师集贤院,位于大明宫光顺门外,本命妇院的其中一部分。(3)兴庆宫集贤院。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遣魏光禄先入京造此院。(4)华清宫集贤院,开元二十八年(740)建,位于宫北横街之西。由此推之,集贤学士有其自身常驻场所,那么撰写制诰的场所亦大概率在此。此为常例。
又开元二十年(732)夏末,张九龄奉拟敕书《慰勉清夷军使虞灵章书》、《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一)。根据其《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字韵》提到“天津桥”(天津桥横跨于穿城而过的洛河上),可见其人身在洛阳,而且同年十月,张九龄随驾发东都北巡。结合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年(732)的行程,五月玄宗于应天门受信安王李祎所献的奚及契丹之俘,冬十月壬午,玄宗发东都。可见,两者行程一致。作为集贤学士的张九龄随驾帝侧,那么此时撰写制诰地点很有可能是东都集贤院。同理推之,集贤学士的撰写制诰之所随着帝王之驾有所改变。若当地无固定场所,则是随驾而写。此为特殊情况。
可见,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场所是以君主为中心而发生变化的。一般情况下,集贤学士在集贤院;特殊情况中,集贤学士随驾君主所在地。前者给予集贤学士归属感;后者隐约有翰林学士“职亲地近”的影子。这也是学士群体与皇权密切相关的实践之一。
(二)“分掌制诰”的存续时间
“分掌制诰”的存续时间,是履行职能情况的一种反映。“集贤学士”之称起于开元十三年(725)。此点与《翰林志》“后改为集贤殿,亦草书诏”[4]1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此是否意味着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上限为开元十三年(725)?值得注意的是,前引文章提到“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3]1183。此处提到“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可见部分翰林供奉亦曾参与撰写诏书。翰林供奉的存续时间成为关联性问题,其存续时间上限可能影响集贤“分掌制诰”的情况。据《新唐书·儒学下》开元初提到“翰林供奉吕向”,而吕向开元十年(722)“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文艺中·吕向传》),换言之,“翰林供奉”之称于开元十年(722)已有(5)翰林供奉可能是开元十年正式建置的。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宁:辽海出版社,2005 年,第184 页。。但若是翰林供奉成于开元十年(722),与此处集贤学士成于开元十三年(725),又是否矛盾?笔者以为,“集贤”之称可能后来史官以“集贤院”指代丽正院,正如此处提到的开元十年(722)吕向为集贤校理,固不能排除此时丽正书院存在撰写制诰的可能性。此处亦是聊备一说。而翰林供奉、丽正院等人员参与撰写的可能性,暗示了对草诏权的分配情况并不是一直处于稳定状态。
“分掌制诰”存续时间下限,是集贤学士草诏权消失的重要节点。名义上,集贤学士撰写制诰的结束时间是相对明确的。据《翰林志》载:“至翰林置学士,集贤书诏乃罢”[4]1,即开元二十六年(722)翰林院成立之时,集贤学士草诏之举停止。结合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上限时间,其存续时段非常短暂。那么,此后集贤学士是否再无撰写制诰之举?笔者以为集贤学士撰写之举的消失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趋于湮没。
首先,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之句后,黄鹤注曰:“制诰本集贤学士领之,今翰林学士得分掌,故曰兼绾”。[8]206-207笔者以为此注源于“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6]1845与“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3]1183 之说。但张垍在馆时间为天宝四载或五载(745 或746),此处“兼绾”对象应以中书舍人为主,而非集贤学士。又据《翰林志》言:“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苏味道、韦承庆,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则薛稷、贾膺福、崔湜。玄宗改为翰林待诏,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改为翰林供奉。”[4]2此段虽是写翰林学士院成立之事,但这里盘点此类文官与撰写制诰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兼绾”的情况是一直存在的。例如李德裕不是翰林学士,但可撰写“诏意”。这亦可作为开元二十六年(738)之后,集贤学士(或其他文士)偶尔参与撰写制诰的旁证,但此时撰写制诰不属于该类群体的正常职能范围。
其次,据《旧唐书·陈希烈传》记载:“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6]3059此处提到“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以情理推之,其“撰述”包括对大型文化典籍的编纂,亦包括对王言的撰写。那么,其是否包括“制诰”类文本呢?结合典籍可知,陈希烈作为集贤学士,其在馆记录约开元十八年(730)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天宝四载(745)、六载(747)、九载(750)、十三载(754)有作为大学士的在馆记录。可见,其在馆时间较长。陈希烈具有“分掌制诰”的可能性。陈希烈存文不多。目前《全唐文》有陈希烈文两篇,即《道士萧从一见元元皇帝奏》《修造紫阳观敕牒》。前文为奏议一类,属于臣子向帝王上书陈述事情、议论是非之文,非属于“撰述”的范畴。后文为“敕牒”,是《新唐书·百官志》所言的王言之制之一—“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於旧则用之”[3]1210。此时陈希烈为具有多重身份,“左相兼兵部尚书崇玄馆大学士集贤院弘文馆大学士”。在天宝时期,左相指门下侍中。敕牒是诏书的一种。而此文作于天宝八载(749),已超出开元时期“分掌制诰”时间段。由此可知,“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非仅是虚言。陈希烈在担任侍中兼集贤学士等职时,曾参与王言的撰写工作。集贤学士作为使职,影响其他官职职能活动的开展。
综上,“分掌制诰”时间上限可至开元初期,下限为开元二十六年(738)。然而,各类群体因出于职务之便或偶参与制诰撰写活动。个别文书的草诏权,并未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群体完全瓜分,如敕牒、册书等。换言之,撰述活动的群体并不是完全局限于法律规定的若干类群体。
(三)“分掌制诰”的制诰内容
“分掌制诰”的制诰内容,是职能具体分配的一种反映。典籍中“分掌制诰”之“制诰”范围包括“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敕宥降虏”[2]274。但集贤院的“分掌制诰”范围比较限制,主要集中在敕文,如张九龄《慰勉清夷军使虞灵章书》、《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一)。此敕文内容和形式与中书舍人敕文并无二致。
就《敕渤海(郡)王大武艺》[9]579而言,本篇比较朴素并无甚典故,但在措辞上非常注意恰当与否、公正与否。这是对已有制诰撰写体系的直接借鉴。其一,对已有形式体制的直接引用。唐初形式体制尚未完全固定,但存在大致规范。文章以“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艺”起,最后以“秋冷,卿及衙官首领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寻挹同往,书指不多及”为结。中间是具体事件的呈现、态度的表明、措施的落实等。敕文中间主体内容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所占篇幅长短不一,但“发语辞”、“结语辞”、文章结构大抵是相似的。总的来看,它与该时段的中书舍人之敕文并无根本上的区别。
其二,对已有内容结构与行文基调的参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内容表达基于事实。该敕文基于史实,即大武艺与其弟大门艺(亲唐派)内战之后,大门艺败而入唐,大武艺穷追不舍誓要诛杀其弟,而玄宗遣大门艺到岭南以避风头之事。文中的“昆弟之”“门艺穷而归我”“处之西陲”之语是此事实的反映。二是思想主题符合官方立场。敕文是王言的一种,其文要公之于天下。在敕文实际撰写过程中,自身想法与官方意志可能存在偏差。如若行文不能正确处理此偏差,很容易影响到政治集团对撰写者水平的评价。而此文强调了儒家的“孝悌”之风,同时体现出敕文接受对象与发敕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品德的高低。这实为可取的作法。三是行文需有明确的行为措置。敕文要明赏罚、寓褒贬,不能行之无文。四是行文情感基调需结合国情。由于受敕对象是外交个体,整体语气基调还是比较缓和。此篇中有较多的散句、反问句,这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自然与强烈,既显得“谆谆善诱”,又显得言之有物。例如第一部分引入阐述的对象,第二部分以体恤对方的态度婉转地表明自己态度,紧接着言自己的处分。
可见,集贤学士所涉敕文与“中书制诰”存在一定的类似性。这是对已有制诰撰写体系的直接借鉴。然而,集贤学士所写制诰较少涉及“除XXX 官制”。张九龄有开元二十年(732)《授卢绚裴宽御史中丞制》,开元二十一年(734)《除韩休黄门侍郎平章事制》《诸王实封制》,但此时他亦兼知制诰,不应将其归于集贤学士职能。可见,中书舍人撰写权限更高,所涉文书更为多样。
综上可知,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场所是以君主为中心而发生变化的。一般情况下,集贤学士在集贤院;特殊情况中,集贤学士随驾君主所在地。“分掌制诰”时间上限可至开元初期,下限为开元二十六年(738)。集贤院“分掌制诰”之“制诰”所涉范围主要集中在敕文。诸多试行情况皆暗示了集贤学士对草诏权的重新分配,又反映了“分掌制诰”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有限性还体现在哪里呢?
三、“分掌制诰”的特性及实际影响
从上文集贤学士“分掌制诰”设置与潜在动机、细节与试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措施实施的背后政治逻辑。但是,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距离,“分掌制诰”亦是如此。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反馈机制。
(一)学士认知与撰写活动的疏离
集贤学士与草诏权行使处于疏离状态。疏离指两者之间的距离,此中包含客观成分和主观成分。客观成分即其制度规范与实际行动,主观成分指集贤学士的自我认知。
就制度规范与实际行动而言,集贤学士“制”草诏权并不全面,即以敕文为主,“诏”的文本较少。这从“除xxx 官制”仍多由中书舍人撰写即可看出。而相较制诰文本,集贤学士其他文本占据了较大比例。这说明集贤学士文本撰写并不是以制诰为主,而存在其他自由发挥的空间。集贤学士其他创作,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与一般臣子相同性质的文章,如章、表、奏、议、疏等。例如目前《全唐文》有陈希烈文两篇《道士萧从一见元元皇帝奏》。这是臣子向帝王上书陈述事情、议论是非之文,非属于“制诰”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此可归类于集贤学士的其他职能,如议政咨询等。第二类是侍从宴游的诗文。这主要是涉及各类应制诗、奉和诗等,如《奉和圣制送张说赴集贤学士赐宴》。结合《集贤注记》可知,开元时期,此类文会参与主体为集贤学士。这属于集贤学士职能的附带活动。第三类是奉敕创作的文章。此类文章属于奉皇命而创作的撰述,其类型可涉及挽歌、神道碑、墓志铭、颂、铭等,如张九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张说《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十九首奉敕撰》、张说《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碑奉敕》、张说《道家四首奉敕撰》、陆去泰《唐游仪铭》。第三类与第二类有一定的相似处,亦属于集贤学士职能的附带活动。可见,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条例规定内容,并没有成为集贤学士的主要活动。部分奉敕应命诗文虽与集贤学士职能相涉,但并不等同于职能性文本。在条例规定与实际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集贤学士与“分掌制诰”并不是彼此紧密相关的事物。
就集贤学士的自我认知而言,制诰之外文本内容,反映出集贤学士并非是“分掌制诰”为主的角色。开元十三年(725),以“送张说上集贤学士”为主题诗歌反映的就是这个现象。其中张九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是以集贤之庭,更为论思之室矣”[7]234与李隆基《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10]35 奠定了此次创作基调,而奉和之作中的集贤院多被比拟成“东壁”“西园”“东堂”“文殿”“石渠”“金殿”“策府”等,或为图书之秘府,或为文会之佳所。这些都是集贤院本身主要职能。另外,诗歌中还提到“西学垂玄览,东堂发圣谟”(贺知章《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谟字》)[10]1146,“忝同文史地,愿草登封书”(徐坚《奉和圣制送张说赴集贤学士赐宴赋得虚字》)[10]1111。此处“圣谟”,可指代集贤院可负责撰写的王言,亦可指代皇帝要求写的其他文书;“登封书”指登山封禅的文章,可指代集贤学士可以奉敕撰写的文书。而“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11]188 亦表达了相似内容。综合来看,此时的集贤院以图书整理、文会侍从等为主要活动,亦有代笔行文之职能,如开元十三年(725)诏说改定乐章,“令太常乐工就集贤院教习”[1]696。由此可知,集贤院一直履行着“掌书籍”(《集贤注记》)[7]221,“续俭志以藏秘府”(《新唐书·马怀素传》)[3]5681,“分库检校”(《唐会要》)[1]1118 等活动。而诗文对集贤院的定位亦以“石渠”等图书藏馆为主,其集贤学士形象特征也主要是“儒”“礼”“学”等特质为主。至于“分掌制诰”,行文中少有提及。我们虽不能否认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举,但相较于后之翰林学士,其对自己学士活动之定位不在于撰写制诰。
简言之,制度规定的不完整性、学士自我认知的主观性等,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分掌制诰”的不可行性。尽管君主有意地分部分草诏权给集贤学士,但因缺少强契机与政策的有力支撑,故而集贤院草诏权颇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这最终导致集贤学士与撰写活动之间疏离感的产生。而这种现象反馈到学士制度整体中,使得实际制度及相关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分掌制诰”状态的不稳定性
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正当性,不仅仅源于官方意志,也源于与所带其他官职间的联系性。而后者职能间联系与混同,影响了“分掌制诰”的正当性认证,进而导致状态的不稳定性。这是“分掌制诰”之举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张九龄而言,开元二十年(732)八月张九龄在工部侍郎、集贤学士副知院事兼知制诰任;开元二十二年(734),丁母忧,起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开元二十三(735)年至二十四年(736),任中书令。实际上,知制诰、中书侍郎、中书令本身亦牵涉到“制敕、册命”之事,因此张九龄撰写制诰之举,很难将“分掌制诰”的权力正当性全部归于集贤学士的职能范畴。以系列制诰文本《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为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张九龄亦敕拟《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二);开元二十四年(736),有《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三)、《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四)。此时,张九龄任中书令之职务。据《通典》载:“(中书令)掌侍从,献替,制敕,敷奏文表,授册,监起居注,总判省事。”[12]562此时若言其出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权,终究缺少点名义上的正当性。因此,集贤院的草诏权,或多或少借着中书省内草诏权的“光辉”。集贤院与中书省的草诏权之共存现象,于徐安贞身上亦有出现。例如徐安贞在《册信成公主文》(737)、《册永王侯莫陈妃文》(738)等自言官职,即为“副使中大夫守中书侍郎(正四品)集贤学士上柱国徐安贞”。
可见,本官与使职的兼职与共存状态,给集贤学士撰写制诰以正当性。实际上,中书令虽有曾参谋诏令,但实际上较少参与起草,而中书侍郎自开元时候开始亦需要“知制诰”之称。[13]54这看似两属职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给予集贤学士的撰写制诰行为以方便,亦是给集贤学士撰写制诰以正当性。换言之,可撰写制诰的集贤院群体除了集贤学士这个头衔外,往往还有中书侍郎、中书令等官职或兼知制诰的任命。与其说集贤院“分掌制诰”是对“文书壅滞”境况的补救,不如说本官与使职的兼职与共存状态是一种新的尝试。
同时,正是因为这些人物本身具有撰写文书的便利,如徐安贞、张九龄等,使得集贤学士“拥有”了草诏权。集贤院主要职能终究是“撰集文章、校理经籍”[6]1852,因此为保证制诰撰写的有效性,对学士身份与学士文书能力多有考虑。不少集贤学士曾任中书舍人,如萧嵩(约开元四年至约十年)、张九龄(开元十年至十四年)、陆坚(开元十一年至约十三年)、赵冬曦(开元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徐安贞(开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吕向(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三载)、韦斌(天宝元年至三载)、徐峤(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3]282-321。换言之,并非是集贤学士的头衔使得其可以撰写制诰,而是这些人物使得集贤院人物看似“拥有”了草诏权。只不过这两者间不管孰先孰后,呈现结果都是集贤学士撰写制诰,所以我们对此难以进行明确区分。
正是上述疏离感、不稳定性导致制诰系统又另生出翰林学士一职。集贤学士存续时间短,但并非毫无意义的。正是有了北门学士、集贤殿学士“分掌制诰”的经验,翰林供奉存在被逐渐认可,加上统治者的制度构建与态度的支持,开元二十六年(738)才可以形成集贤书诏罢、而翰林学士“专掌内制”(6)內制与外制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据《翰林志》《唐会要》《册府元龟》可知,元和时期,涉及朝臣除命的白麻内制,其行用范围包括三公、将相等的除免及皇后、皇储的授命等方面,而在其他政事处理场合,包含赦文、德音、批答等的起草,招讨不庭、抚恤灾祸、宣慰军旅等诏令的草拟,皆归翰林学士承担。这一惯例在整个中晚唐时期基本得到贯彻,尽管其中也有例外者。《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第二》载,中晚唐以后,两制在官员除命范围上的分化并未就此停止。至五代,朝廷曾以诏令形式划定宋代对内外制的草诏权的分割,采取吸收为主,微修以适应时局为辅的策略。参见毛蕾著:《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11 月,第97-98 页。张祎著:《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杨芹著:《宋代制诰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06 月;吴晓丰:《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史学月刊》2020 年01 期:第29-42 页。的局面。
结语
《翰林志》《新唐书》《唐会要》等记录是集贤学士存在“分掌制诰”的直接书面证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等相关内容,则提供“分掌制诰”的实例,如张九龄。在进一步考察集贤学士“分掌制诰”制度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是集贤院存在多处藏书之所,但草诏之所却未必确定。学士或于集贤院撰写制诰,或随驾写制诰。二是集贤学士“分掌制诰”存续时间上下限是模糊的。一般情况上,集贤院因“文书壅滞”而“分掌制诰”,因翰林院的出现而罢撰写制诰之权。实际上,集贤学士草诏权理论上的存续上限,可至翰林供奉存在之时;情理上的存续下限可至翰林学士成立之后。这是因为制诰撰写者除主要群体之外,仍存在其他人员。三是集贤学士草诏范围相对有限,主要以敕文为主,较少涉及到除官制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的制敕等。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集贤学士草诏权具备以下特点:集贤学士与撰写制诰活动之间存在疏离感、“分掌制诰”状态具有不稳定性。就前者而言,这种疏离感可从其诗文以及实际行动反映出来。例如诗文对集贤院的定位多是“石渠”等图书藏馆为主,而其创作文本亦是以制诰之外的文本为主。就后者而言,集贤学士与本身其他官职之间联系与混同导致了“分掌制诰”状态的不稳定性。正是这不稳定性导致制诰系统又另外生出翰林学士一职。可见,集贤院参与撰写制诰是形势所决定的,其消亡也与所处的环境有关。
“分掌制诰”是集贤院研究中一个小问题。通过对集贤院草诏权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窥探唐代三馆之一的集贤院职能演变过程的一部分。尽管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情况只是制诰撰写史上的支线,但是存续时间并非毫无意义。“分掌制诰”活动出现是学士获得草制权的一种尝试,其活动存续情况是对学士制度整体构建的一种反馈。这为我们研究“亚制度”提供了一个启示。另外,我们可将集贤学士将其放在整个唐代制诰制作系统中,探寻集贤学士制诰的所处位置,补充学士制诰文本生成机制的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