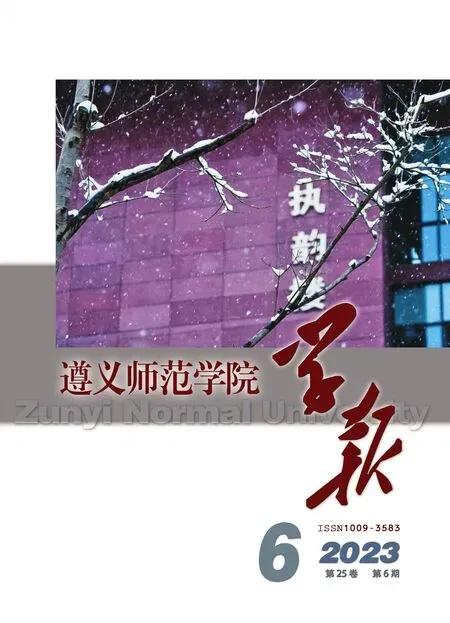《百川东到海》的“文化”书写
孙建芳,蒲 实
(1.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6;2.重庆外语外事学院,重庆 401120)
郑欣的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以42 万字的鸿篇巨制,展示了从1919 年至1949 年的历史画卷。三十年的风云际会,作者借助全能视角,结合时代背景与地域特色,通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描绘,形象勾勒出那段波澜壮阔、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仔细品读作品,不但可以了解世纪风云的沧桑巨变、领略乡风民俗的淳朴厚重、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可以进一步探索“百川东流”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源,寻求在“大浪淘沙”冲刷中的民族性格与精神品质的文化基因及心理动因。
文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内涵丰富且广博深邃。作为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以广阔的历史背景、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优美的语言文字,为我们徐徐开启了一个勤劳智慧却灾难深重民族的“文化”大幕:大气磅礴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诗情画意的语言文化。展卷细读,精彩纷呈——栉风沐雨的革命斗争、大浪淘沙的改朝换代、出生入死的英雄传奇、一波三折的浪漫爱情、婚丧嫁娶的烟火市井、琴棋书画的唯美风情……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如和风穿柳、春雨润物,让人不知不觉陶醉其中。
一、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百川东到海》的封底,以高度凝练的文字概括道:“这是一部浪漫、传奇的革命史诗,以1919-1949年为时间坐标建构宏大的叙事框架,腐朽黑暗的军阀统治,风雨飘摇的社会时局,人物命运一朝颠覆,众生百相波诡云谲……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徐徐展开。”
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透视过去,也可以照见未来。《百川东到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生动历史画卷,几乎所有的时代重大事件,都被作者款款叙述、娓娓道来。这是大手笔书写的大时代,正如《人民日报》的精准评价:“书写大时代,需要练就通达古今、直抵人心的苍劲笔力。只有守住人民这个‘根’,笔下的人物形象才能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真实鲜活的质感。”[1]
江河奔流,泥沙俱下,但是,百川东到海,一路浪淘沙。“身在大潮流中,却企图独善其身,生在乱世却期待开辟桃源净土,又怎么可能,这些年来,中国有识之士坚持的各种主义与牺牲,为的早已经不是让哪一股势力占上风,最源头最根本的是为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和道路。历史给我们以警示,而只有未来才能证明一切。就好像无论是哪一条河流,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得泥沙俱下。向东流,入大海,才能从入海口的汇入和消失中,获得真正的永恒的安全。因为只有大海才是永恒存在的。”[2]P292小说中这段议论兼抒情的文字,可以看作题旨,既点明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概括了作品的主题。
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可以脱离时代而不朽。《百川东到海》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精心安排了几对复杂的“爱情”线索——罗丹与王中南从激情幼稚到分道扬镳,最终与淳袏志同道合而成为同志爱人;敏之与淳祐从一见倾心到血浓于水的生死相随;淳袏与惠茗始而甜蜜浓稠终究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一拍两散;蕙茗与王中南彼此贪欢各有所图利益失衡后的劳燕分飞;当然,还有唐炳铨夫妇、孟学士夫妇举案齐眉的夫唱妇随;淳衷与端芬旧式婚姻的貌合神离;淳衷与翠仙、翠仙与奎栗各怀心事的一厢情愿;山口医生“男主外女主内”嫁鸡随鸡的日式婚姻;桃叶“女大三抱金砖”的“小丈夫”婚姻……这些或隐或显、或详或略的婚恋关系,并不局限于才子佳人恩怨情仇的情感纠葛,而是借助个人命运的沉浮荣辱展现时代浪潮,否则,小说就会沦为无病呻吟的失败之作。毕竟,历史上这类鸳鸯蝴蝶、风花雪月的娱人故事数不胜数,但终究湮没于时间的洪流,了然无痕。
网上有句被高赞的流行语:时代的一粒灰,压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没人可以脱离时代而独活,即便是逃进深山不食周粟的商朝遗臣伯夷、叔齐,到底也做了时代的牺牲品。滚滚洪流泥沙俱下,革命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选择过程,只有烈火才能炼得真金,就如小说主人公之一的罗丹所说:“创造一个新世界,必须打碎这个旧世界,这个过程必是一个流血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道路,为之付出一切而不悔的道路!”[2]P233
可是,动荡不安的时局,变幻莫测的社会,理想的实现任重道远:征途遥遥、歧路漫漫、荆棘密布、暗流汹涌。在某些特殊的历史关头,信仰的坍塌使人类精神大厦土崩瓦解,群体的迷茫和个体的异化,成为一种焦灼不安的时代情绪,同时也成为小说艺术集中展示的深刻主题。这充分体现在作品的人物形象上:普通群众、革命者、进步者、观望者、投机者、叛敌者、随波逐流者,等等。非常典型的人物有罗丹——集富家小姐、进步学生、时髦青年、顽强战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革命者;敏之——看似弱不禁风、隐忍退让的大家闺秀,实则刚强娴淑、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惠茗、王中南——一对叛节蜕变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淳祐、淳袏兄弟的成长成熟……时代大潮中,此起彼伏的波峰浪谷,清浊难分中的浑水摸鱼,纵良莠不齐,神鬼莫测,经自然选择与淘汰,终究大浪淘沙,百炼成钢。
历史不容假设。作为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百川东到海》强烈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其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的真实性。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他的名篇《希腊古瓮颂》中有句名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3]P126小说除细节、环境、氛围等的真实外,还有一种更高的真实,那就是说真话,并用最大热情描绘心中的理想,人类的共同梦想。
罗曼·罗兰说:这世界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敏之与惠茗这对表姊妹的不同人生道路,是个体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命运的选择。罗丹、敏之、淳祐、淳袏兄弟,顺境中善待他人,逆境中善待自己,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在革命的烈火淬炼中,坚守信仰,坚持目标,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也成就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二、丰富生动的民俗文化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俗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背后是悠远的历史沉积和日渐趋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民俗经地域切割和时间发酵,逐渐演化为绚丽多姿且独一无二的地方性与民族性,沉淀在语言、艺术、饮食、服饰、建筑、节庆、信仰、心理等各个方面,种子般被时间风干、窖藏、传播,成为一种柔韧的文化基因,嵌入群落骨血并一脉刻录传承,锻造出专属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性格。
中国古典文化中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等民间俗信,就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集体心态的外化、固化和物化。不计其数的诗词歌赋都在书写描述天涯海角的游子和浪迹江湖的侠客,终不甘背井离乡的漂泊,冲破凄风苦雨的羁绊,“宦海沉浮终是客,解甲归田养天年”,说到底,他乡再好难为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这是汉民族对“故土”的一种普遍认知,也是走遍世界都难忘家园的强大心理动因。
从时间维度和地理范畴来看,《百川东到海》长达半个世纪,横跨半个中国,时空纵横交错,勾勒出一帧帧浩大的动态历史画面,也描摹着一幅幅鲜活的现实生活图景。郑欣说:“在故事之外,为写出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的历史文化特色,我铺陈了很多文化场景,比如市井街头、园林建筑、书法绘画、戏曲歌舞等等,以此增加时代质感。当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谙熟文化背景及诸多细节后,我感到‘下笔如有神’,虚构的人物置入真实的历史画卷,别具一格的故事场面呼之欲出。”[4]
作者所言非虚,她的笔下的的确确“铺陈了很多文化场景”:豪门望族轰动一时的世纪婚礼,军阀权贵雕梁画栋的山水园艺,八旗子弟玩物丧志的文玩烟酒,贵族小姐描金绘彩的凤冠霞帔,花街柳巷倚门卖笑的吹拉弹唱,文人雅士夸才斗艺的琴棋书画……从钟鸣鼎食的侯门大户,到引壶卖浆的贩夫走卒,无论富贵锦绣还是颓败破旧,都有一股浓浓的艺术质感,都是无可替代的民族文化。例如,小说开篇即让人不能小觑、必须高看一眼的“三希堂青莲诗文铭白羊脂玉方壶”“两盅桂花莲子银耳汤”,那是富贵之家的钟鸣鼎食、风雅闲适,而“锔盆锔碗锔大缸的营生”,无非是平民百姓的养家糊口,虽也衍生为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但“技”与“艺”终究是卑贱与高贵的分野,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质”的天壤之别。
小说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唐太太自杀一节的细微描写。比之前文高朋满座的热闹婚礼、车水马龙的盛大葬礼,唐府盛极而衰的凋零颓败、墙倒众人推的分崩离析,更让人过目难忘,唏嘘不已。曾经呼风唤雨的豪门权阀,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击碎,瞬间四分五裂,众叛亲离,“忽喇喇似大厦倾”“好一个飞鸟各投林”,恍惚间,树倒猢狲散的悲凉感油然而生,很有点读黛玉葬花、焚稿时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强烈的共情产生强烈的共鸣,悲剧的震撼力就在于此。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浪潮汹涌滔滔,没有谁能阻止历史前进的脚步,无论是指点江山的一代帝王,还是改朝换代的一众英雄。
就传统观念而言,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最大程度地深入浅出,因为“深入”易、“浅出”难,这需要极高的写作功力,包括观察想象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语言组织的能力和文字表达的能力。也就是说,真正好的小说,并不是把故事编造得多么离奇惊悚,把背景渲染得多么紧张神秘,也不是把人物刻画得多么神出鬼没,把语言铺排得多么漂亮华丽,而是能够以小见大,小中见大——繁琐细碎的衣食住行,一日三餐的油盐柴米,酸甜苦辣的婚丧嫁娶,生离死别的爱恨情仇……这些日常生活的庸常琐细,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寻常日子,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间烟火。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随着各民族不断地交流融合,民俗文化也在悄然变化;而从民俗文化到民族文化,呈现为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但铭刻在集体记忆深处的历史和文化,却愈加鲜活生动。历史不能忘记,文化不会忘记。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尼采说:“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5]P4
文化附着于历史长河的每一朵浪花,光华灼灼、熠熠生辉。那么,关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记忆”与“遗忘”,特别是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寻找历史、当下与未来三者恰当合理的精神坐标,便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没有过去就难以拥有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无数精彩纷呈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曾经辉煌的遥远记忆,张扬着不断进取、永远超越的理想和自信。
三、诗情画意的语言风格
语言的书写与思想的传达,是考验一位作家真实水平的“硬功夫”。《百川东到海》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语言的诗化。细腻传神的描写,古朴优雅的表达,灵动有趣的思维和活泼浪漫的想象,都仿佛在与读者进行情智对话。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生活的审美化,即主体脱离理性判断和功利目的,对世界有一种无声的鉴赏和审美,表现为透视的质感、非理性的逻辑、令人舒适的比例和恰到好处的比喻。此所谓“文笔”,往往为学者型作者所偏爱。
毋庸置疑,郑欣的古典文学修养深厚,根基扎实,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上,就是妙笔生花,古意盎然,特别是修饰语的两两对应,颇得骈文神韵,不仅节奏上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行文也是排列有序、美观整齐。
《百川东到海》的语言之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名字、句子、文字。
1.唯美名字
名字是人或物的指称性符号,多数还兼具象征意义或文化意义。作为一部背景广阔、结构宏大的长篇小说,众多个性鲜明、关系复杂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一个辨识度高、又有特定含义的名字来称谓。这是一个基础性同时又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不能太随意,也不能太刻意,就像年轻父母给孩子取名,寄托着全部的爱和梦想,包含了无限的祝福和心愿。
不难看出,《百川东到海》的取名颇为巧妙,特别是女性名,用字考究,寓意美好,无不彰显其主人的蕙质兰心:敏之、蕙茗、桃叶、菊香、梅筝、素琴、锦瑟、红珠、晚柳、宛淇、宛漪、续春花……梅兰竹菊,琴棋书画,桃红柳绿,花团锦簇,唯美画面呼之欲出,仿佛一个个诗词中的古典美人,一路款款行来,仪态万方、风华绝代。作者借人物之口向读者解释这番良苦用心:“素琴,锦瑟,都是前一个字是颜色,后一个字是从玉的,那么还是从玉红珠。红色最辟邪;珍珠,又是圆满和富贵的意义。”[2]P401
书写新时代,怎能缺席新女性?罗丹,便连名字也透着几分“洋派”:一身衣着“斑斓得像一只蝴蝶”,象征着人物不拘一格、特立独行的爽朗率性,“一位时髦女郎,一身青翠色西装与玫红洋绸旗袍中西合璧式服装引人侧目,大红大绿在她身上倒也杂糅出一些别样的味道。”[2]P17年龄、身份、教养、语言都在不动声色地配合着这个“洋气”的名字,彰显其热情洋溢的活泼性格和热烈如火的革命激情。
至于其他名字,也都各具特色,如淳衷、淳祐、淳袏三兄弟,左中右显然煞费苦心;项伯亦、方可为,透着几分书卷气;山口医生、菲堤医生,充满异域气息;小滴答、段大挑,显出俏皮劲儿;还有唤作“蕉雨轩”的餐馆、“袅晴丝”的烟馆、“止远堂”的书画店、“辰轩榭”的方亭水榭,顿时让人对“文化”心生敬意;“小花枝胡同”里出现妓院“浮光美”,有个名妓叫“翠仙”,似乎也都再贴切不过;而正正经经的“坪林山庄”,则是大户人家看似低调实则笃定的四平八稳、成竹在胸。
总之,这些人名地名,既可以“雅”得高山流水、仙气飘飘,也可以“俗”得市井烟火、“痞气”十足。这不能不看作是作者的十分功力和百分用心。
2.对称句子
对称是形式美学的一个基本法则,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特别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突出地体现在中国独有的楹联艺术以及诗文中的对偶、对仗,基本要求是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词性相对、词义相反等等。
《百川东到海》非常明显地运用了对称原则,许多句子都是两两相对:“多愁多病的身,怜香惜玉的心。”“检查一下人口,核对一下良民。”“千万不能有闲杂人等混进来,也不能有吃里扒外的混出去。”“朗朗世界,母子不得相聚,夫妻不得团圆。”“列位的马褂长袍,西装革履,珠环翠绕,云鬓香影,一幅人间富贵繁华的景象。”“戏台上出将入相,仙魔毕至,丝竹盈耳,锣鼓喧天。”“什么主义,什么名分,一切不过都是梦幻泡影,惟有声色犬马和真金白银,才是世上最稳妥的安身立命之所。惠茗一面挥汗,一面挥泪。”
还有大量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天光水影,碧波荡漾;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应对合宜、大方得体;宦海沉浮,飘摇不定;皓月高升、月华如练;放马归田,安享晚年;喧嚣熙攘、高朋满座;凄风苦雨、阴阳相隔;红烛照影,喜字高悬;红烛美人,挽发梳妆;艳若桃李、冷若冰霜;亭台楼榭、花草树木;湖光山影、水禽飞鹤;风云变幻、诡谲莫测。
惯常的四字结构,语义明确,节奏铿锵,雅俗共赏,为小说一大亮点。而众多诗文的高频次现身,既言简意赅又画龙点睛,亦为小说增色不少。
3.诗性文字
传承数千年的方块汉字自带诗性,形音义三者的完美结合,仿佛诗乐舞的三位一体,灵动、柔媚、唯美,动感十足、魔力无限。《百川东到海》语言的诗性特质,在小说中不用刻意寻找,随时随地就“跳”将出来:
“浮光美那间熟悉的小阁楼里,奎栗静默地坐在一把圈椅上,手里拈着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待喝待不喝地举着,微微眯着双眼,在想着什么心事。翠仙也是没有话,静静地撮了一炉香点上。片刻过后,香气似松柏林中扫过的清风一样,若有若无地飘浮在房间里。翠仙端端地坐在琴凳边,调了一下弦子。刹那间,十指兰花初绽,那乐音也就恰似那新莺出谷、银瓶乍裂。”[2]P32
“红霞白塔,桃花流水,霞光中天空慢慢转成靛蓝色,湖水沉淀成青蓝色,北海公园里也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西仔在水边桌台点燃了盏盏油灯,烛火隐约摇曳着,湖水慢慢变成深蓝。”[2]P20
例子太多,不胜枚举。“单看这戏楼,却是说不出的金碧辉煌,正中写着‘盛世和声’四个大字,两侧联对‘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2]P7-8简简单单几十个字,现实中有虚幻,虚幻中有现实,存在与虚无,在联中彼此映照,这恰好就是语言文字难以言喻又不言而喻的绝妙之处。
通读小说,单就语言来说,也不难看出作者的温婉气质。即便表现血雨腥风的军阀混战、表现生离死别的爱恨情仇,都难见文字的气急败坏、咆哮呐喊,而是一如既往的平心静气、典雅端丽,在交代背景、叙述故事、塑造形象、烘托气氛的从容淡定中,历史大潮的“刚”与诗化语言的“柔”相互映衬又彼此中和,刚柔并济,诗画一体。这种“魔性”贵在日常修为的“定力”,恰如白居易诗:一勤天下无难事,一静天下无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