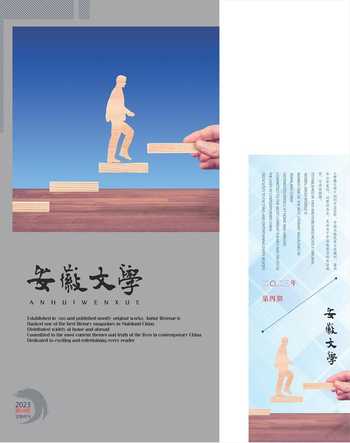养育恩
董晓英
对于父亲,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养恩大于生恩,你们一定不能忘记了。
母亲说的养恩,是指养父对于我们的养育之恩,而生恩,指的是生父对于我们的生育之恩。
母亲1976年离婚后,带着不到四岁的哥哥和两岁的我,千里迢迢从甘肃陇南一个边远的山区,坐汽车,转火车,再坐手扶拖拉机嫁给在南疆某水库工作、比母亲大17岁的养父。生父彻底割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对我们从来不曾有过只言片语的问候,更不要谈经济上的资助,他去世了,我们还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所以生父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虚无缥缈的称号。
我们从生父那里没有得到的父爱,养父全部给予了我们。
为了迎接我们,父亲将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笔巨款——200元钱,交给一个关系很铁的老乡,请他帮忙到夏克(当时阿瓦提的一个集市)买点米面粮油回来,结果,老乡拿上钱就跑没影了。手上没有一分余钱的父亲抓狂了,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我们和接下来的日子。
“既来之,则安之。”父亲接到我们后,首先将我们带到了连队食堂。一路长途跋涉的我饿极了,抱起案板上的一条生鱼就开始啃,眼疾手快的父亲一把抢下鱼,他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把一个馒头迅速塞到我手里,又打了一缸子肉菜,尽着我和哥哥吃个够。父亲看着狼吞虎咽的我们,心疼地说:“看把我娃给饥得!”
从父亲工作的食堂出来,母亲走进了父亲所谓的“家”,发现真的是家徒四壁,除了用两张小床拼凑在一起睡觉的大床,一方小桌,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米桶里也看不到几粒粮食,母亲那个愁呀!
好在父亲人缘不错,街坊邻居到了饭点,就把我们叫过去吃饭,或者送一些做好的馒头、饼子、咸菜过来。挨到父亲发工资,母亲拿着贰拾捌元捌角肆分钱,还还人情,剩下的全部買成苞谷面(白面和大米价格太高吃不起)。母亲做搅团、打糊糊,连续吃了好几年,这个家才勉强缓过来,后来也偶尔买点大米白面润润我们的肠胃。很多连队的职工看了我家的境况,都一个劲地摇头说:“老董家迟早过不下去!”
平时,父亲宁可自己不吃、不穿、不用,也要让我们吃好、穿好、用好。他甚至打消了要自己亲生孩子的想法,原因是母亲曾经小产了一对双胞胎,身体一直很虚弱。他看着我们对母亲说: “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共同把他们两个拉扯成人,难道不是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吗?”直到现在母亲都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你真是个老好人,又不是亲生的,何必呢?差不多行了!” 面对闲言碎语,父亲总是一笑置之,待我们依然如故。“老好人”的名头却越叫越响。
记忆中,我和哥哥整天不是喝苞谷面糊糊,就是吃苞谷面搅团、苞谷面饼子,偶尔用苞谷和捡来的麦粒做成醪糟煮着吃,一家人高兴得就像过年。每顿饭我们总是把碗舔得比洗的还干净。看着其他小朋友拿着白面馍,端着白米饭,甚至咔嚓咔嚓啃着充满冰碴子的胡萝卜,我们都是满眼的羡慕。
母亲总是说父亲,饭都吃不饱,不要给孩子满足一些其他愿望。父亲总是笑笑不说话,照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五六岁的时候,我迷上了看小人书。可是,那真的是一种奢侈。看见几个小朋友手里拿着小人书,聚在山墙下看,我就靠着墙根,眼睛往他们的书页上瞟,只看到零星的画页和未被完全遮挡住的线条,就已经很满足了。也许是脖子伸得太长,被他们发现,感觉不舒服,他们就往远的地方挪,我也跟着挪到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眼睛却还在往书页上瞄。拿小人书的小朋友气急了,拔起屁股向远处跑去,身后跟了一群他的同伴,只留下我失神地怔在原地。
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的,有一次,居然带回了几册小人书,递给正在烧火做饭的我。我看得入了迷,等到煳味飘出,从小人书的故事情境里回过神来,才意识到灶里的火太大,菜已经变成了炭色,惹得母亲劈头盖脸地对着我和父亲一通骂。父亲只是笑了笑,用筷子搛起惨不忍睹的菜,一边吃一边赞道:“莫啥的(没什么),好吃,我们家闺女做啥都好吃!”气得母亲直跺脚。
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照着我们的身形,往大两三岁的趋势做的,一件衣服真的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合身?不可能!有得穿都不错了,哪有条件挑三拣四?
稍微大一些,在父亲的提议下,母亲也觉得应该给我们置些像样的行头了,就到夹河子(集市)给我们买了身新衣服让我们换上。而父亲却秉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很少有新衣服上身。用他的话说,自己是大人,每天都要干活,穿新衣服糟蹋了。
父亲把我们刚接过来的那几年,一头乌发都愁白了。为了多挣钱,他不得已辞去了人人羡慕、能吃饱肚子的食堂班长职务,下到连队,一年到头在外打梢捆、防洪、护堤、修涵洞、修渡槽等,经常不在家,肉眼可见地消瘦、憔悴了许多。
每天不见油星的饭菜,寡淡得我们胃里仿佛住着一群饿狼,稍微有点荤腥,就馋得直流口水。记忆里,我们总是吃不饱,每天饥得就像“饿鬼投胎”,一到家就开始翻箱倒柜找吃的。
哥哥上了初中后,喜欢跟着连队里的小伙伴模仿电影《少林寺》里的动作练“武术”,活动量增加,饭量陡然增大。有一回放学回家,刚吃完一小盆面条,到了晚上12点,又吃了一个跟平底锅一样大、10多厘米厚的甘肃大饼,还觉得没吃饱。父亲吓坏了:“不害怕你吃,就害怕把胃给撑坏了,这可怎么得了?”最后还是下了小半盆面条,让哥哥吃下才放心。
随着我们日渐长大,父亲的工资涨到一百多块钱。本想着可以松一口气,但随着我考上中专,要到一百公里外的阿克苏上学,家里银根又一次骤然吃紧。除去柴米油盐正常支出外,家里还要承担我每个学期500元的学费,每个月最少50元的生活费,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
为了给我筹措各项费用,每年年初,父母都会买几头小猪,抓些鸡苗,再养一头牛,起早贪黑地为这些牲畜割草、煮食等。每个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就卖掉一些鸡,甚至将养得半大、正在长膘的小猪处理掉,换取很少的钱款,才勉强不欠账。
那几年,父亲一直有胃病,可为了我上学,一直瞒着。1993年,我还没毕业,实在扛不过去的父亲住院了,化验单出来的那一刻,全家都蒙了——胃癌晚期?——怎么可能?妈妈这才后悔不迭地回忆起,父亲这两年胃病加重了,却从来不肯到医院就诊,疼得厉害了,就用被子或者硬物死死地顶住疼的部位,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到门诊找两片止痛片吃上。
母亲一直后悔自己大意,有时发现父亲疼得脸色发白,让父亲到阿克苏医院好好诊治一下,父亲却总说没事,母亲也就没有深究。可怎么会是胃癌晚期呢?我们谁都想不通!细细想来,一定是父亲心疼医药费,不愿意在一百多公里的路途上来回折腾,病情才一步步恶化的。
父亲患病半年多,其间一直嚷著要出院,他对母亲说:“你们把远亲近友的钱都借遍了,谁看见你们不是躲着走?住不起啊,一万多块钱的债,我要走了,你没有工资,两个娃娃都没有工作,拿什么还喔!”我们都鼎力坚持给父亲治病,直到医院下了回家静养的通知,才回到团场。到了第七天晚上,父亲的口、耳、鼻突然大量喷血,母亲、哥哥和我吓坏了,借了辆拉车,拉着父亲就往营部的门诊跑,只为留住父亲……
到了门诊,也许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父亲黯淡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呼吸急促,胸口剧烈起伏,嘴唇嚅动着想说什么,却已经发不出声。哥哥赶紧将耳朵凑在父亲嘴边,却依旧什么也听不清。
父亲的脸色逐渐灰暗,眼中的星光渐渐变弱,他一瞬不瞬地盯着我们娘仨,星子一点点减弱,直至散尽,他眼中所有的担忧、难舍、眷恋……在流下一行热泪,脑袋向右一侧后,骤然消失不见……
黑暗中仿佛有什么轰然倒塌……
顿时天愁地惨、星月无光……
无尽的绝望、撕心裂肺的痛楚如山呼海啸般席卷而来……
“老董……”
“爸……”
我们娘仨匍匐在父亲的病床上撕心裂肺地恸哭!如一串串惊雷,炸裂了死寂、可怕的暗夜!
三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养育之恩我们时刻铭记。我们每年都要回水库祭奠父亲:清除杂草、培土、烧纸钱,燃一路鞭炮,告诉父亲——我们回来了。我们虔诚地跪下,告诉他,我们现在也像他当年庇护我们一样,长出了枝繁叶茂的华盖,接过他老人家的接力棒,尽心尽力地孝顺母亲、福荫儿女,在这一片他曾经热爱并付出青春与热血的地方,替他活着,努力工作,不让他老人家失望。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