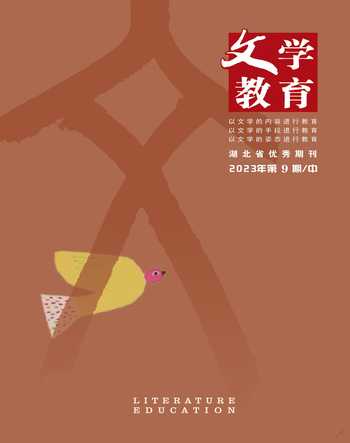大谷光瑞及其《放浪漫记》中的宁波印象
王涵
内容摘要:近代以来,大量日本人来华,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游记,这些游记以纪实的形式对中国近代社会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录,是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但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大谷光瑞是近代日本知名宗教界人士,曾于1914年进行中国之旅,甚至到过浙江宁波,并留下游记《放浪漫记》。宁波是近代中国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担任交通要塞的重担;古代宁波与日本交流来往也十分密切,尤其在佛教方面,天童寺、阿育王寺都是日本佛教人士寺院巡礼的重中之重。本论文通过对日本代表性的佛教人物的分析,管窥其时日本人认识中国路径的一个侧面,对把握当时的中国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大谷光瑞 佛教 亚细亚主义 宁波印象
1871年中日正式建交之后,日本人怀着各自目的大量涌入中国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并以游记,书信等方式记录下所见所闻。这些游记中出自个人之手的为数最多。按照撰写者的身份来看,大致分为:学者及记者、作家或艺术家、宗教界人士、儒学者等等。而对于这些撰写者,目前的研究者们大多将目光聚焦在作家的作品上。许多作家抱着对古典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来到中国考察,并对中国文化充满期待和憧憬。但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实难免令他们感到失望,进而在各自的游记中表达出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不屑与蔑视。研究者们则针对这些日本作家对华的认识进行深入的考察。而对于其他身份,尤其是宗教人士的撰写者,关注度则相对较低。
大谷光瑞,是近代日本知名宗教界人士,曾到中国旅行考察。大谷光瑞于1914年开启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海外“放浪”之旅。期间,除游山玩水之外,他时刻关注中日两国乃至国际政治局势,同时对日据地区进行殖民规划,与相关人物频繁交流来往,这些经歷都记录在其著书《放浪漫记》中。大谷光瑞的中国之旅呈现出多重目的。虽与作家们观察中国的视角略微不同,但对当今学者来说也是一部有助于窥视近代中国的现状,并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近代日本人对华认识。
本文将通过《放浪漫记》中大谷光瑞对于宁波的记录来考察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本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第一部分是关于大谷光瑞的简介;第二部分论述其游记《放浪漫记》中的宁波印象;最后第三部分是总结。
一.大谷光瑞简介
大谷光瑞(1876-1948),法号镜如,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任法主,致力于宗务、教团实力的扩张;继承了父亲大谷光尊的“开国进取”的思想精神;于明治35年(1902年)-大正2年(1913年)期间,曾组织多次大规模的“中亚·西域探险”,遍访敦煌、吐鲁番、楼兰等地区盗窃中国文物;并于1919年创立“光筹会”且自任总裁,同时发行《大乘》杂志。该杂志除研究佛典外,还意在鼓吹国家主义。大谷光瑞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其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全境,国内许多地方如上海、大连、青岛、台湾等地他更是多次前去,甚至长期旅居。著作方面,主要有《清国巡游志》、《放浪漫记》等。其游记《放浪漫记》是其于大正3年(1914年),因财政失败和贪污事件辞去法主之职后,在中国、南洋等地进行海外之旅时所作的记录。
二.《放浪漫记》中的宁波印象
1.呈现“亚细亚主义”色彩的宁波印象
对于大谷光瑞此次海外之旅的目的,纵观整个《放浪漫记》,以“怡神适意,逍遥放浪”的心态而体验的游山玩水之旅只是大谷光瑞此行的一个侧面,在激荡的历史风云中保持对政治的高度敏锐,对日据地区的殖民规划以及与相关人物的交往等,在他的“放浪”之旅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根据《放浪漫记》的目录可知,大谷光瑞此次“放浪”之行,在来中国之前首先去了朝鲜半岛,之后再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在中国由北向南进行考察旅行,考察完大陆之后又去了香港,随后前往南洋地区,结束在东南亚地区的旅行后又从新加坡返回上海,再次在中国大陆南北各地进行旅行,最后为了避暑选择在普陀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
在其著书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正4年(1915年)4月,大谷光瑞在上海停留期间,遇到了当地的“排日”运动,便声称上海人大多数来自宁波,因此在总领事的劝告下,他放弃了去山阴、四明、普陀等地的漫游,转而去了西湖。此言显然是对宁波的偏见。尽管大谷光瑞在4月因受上述“排日”运动的影响放弃前往宁波地区,但其在同年6月为了避暑经过一番搜索后还是选择从宁波中转前往普陀。大谷光瑞于6月23日午后4点,乘坐轮船离开上海,于翌日早晨6点半到达宁波。
关于宁波,大谷光瑞如是说道:“宁波从唐代开始到明代,都作为中国与日本来往的交通要塞,和今日的上海一样。并且,天童、育王等古寺在历史上都与日本有着密切联系。(中略)如果要以宁波为中心在其附近探访名胜古迹的话,三月的温度最适宜。而如今湿热难忍,并非游玩的最佳季节。因此还是直接前往普陀。”
此前,大谷光瑞虽对宁波抱有偏见,但此次途经宁波作出的评价还算中肯,并无体现其民族侵略意识。大谷光瑞坐船离开宁波后,先到象山中转,随后再坐船到达沈家门。途中,大谷光瑞对于其所见景色也进行了一番描述。大谷光瑞将其看到的海景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进行比较,作出评价:“海上大大小小的岛屿很多,酷似濑户内海;山貌大都十分险峻,最高处却也能耕耘;山林茂盛有许多竹林点缀,色彩浓淡恰到好处;唯独海水浑浊偏红色,不如日本的海水那样呈深蓝色;并且,来来往往的船只都呈现出暗褐色,在晴天却看不到白帆之美;若除去这两点,那这片大海便可比肩濑户内海。”
此处,大谷光瑞将两物进行比较,得出“若除去这两点,那这片大海便可比肩濑户内海”如此结论。除上述将海进行对比之外,大谷光瑞还写了“桃花岛的山顶最高但和濑户内海相比还差一千多尺”类似的描写。此番描写看似只是对沿途景色的描写,实际却对普陀山海域的景色处处贬低,在贬低的同时又不忘赞赏日本的景色,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感。
此番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大谷光瑞表面上看似只是对景色进行比较,实则赤裸裸地表露出其“大日本主义”的优越感,由此产生日本从精神上“帮助”中国乃至亚洲的错误认识。而所谓的“帮助”实际是其帝国主义侵略并吞并中国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此处提到的“亚细亚主义”是1917年3月,大谷光瑞在其“放浪”之旅即将结束之际,于《中央公论》当月首篇发表《帝国之危机》一文中提及日本当前面临“内忧外患”之危机时所提出的理论。大谷光瑞认为“内忧”主要是对于国民反叛天皇的担忧;至于“外患”,则最主要的是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其中在谈到对华关系时,他声称,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已经无法以大国自存,且屡遭列强蚕食,国内骚乱不止,已成东洋和平之大患。作为邻国,日本必须予以干预,直至其“独立自存”。
在谈到如何解决“外患”问题,大谷光瑞指出:“亚细亚主义是治理外患的妙方,它既可以增进亚洲人的和平与福祉,还可以防御别国欲对亚洲实施的侵凌暴虐之举。这是日本民族的天职,也是使命。如果不能推行,则我民族将不复存在。”
此处,大谷光瑞首次提出“亚细亚主义”的概念,不但将其视为“治理外患的妙方”,还看作当时日本的“天职”和“使命”,甚至认为关乎日本的存亡。很明显,大谷光瑞提出的“亚细亚主义”就是希望亚洲国家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务,但同时又认为日本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来“指导”“干预”中国,以此共同对付和抵抗欧美。大谷光瑞甚至在同年4月发表的《慨世余言》文章中,直呼“亚细亚主义,乃天赐日本民族之使命。”对此,他也详细说到:“亚细亚主义即大日本主义,而推行该主义,乃大乘的使命所在。此乃我常年内心牵挂之事,即使造次颠沛亦未能忘却。不肖自幼顽钝,学无所成,行事不成,常受世间指弹,蒙受诮笑,而犹蠢蠢乎贪生者,原因之一就是想看到该主义能够实现。不肖七岁,始见父亲所给之世界全图,慨叹我帝国乃一蕞尔小岛,深感必须使小日本变成大日本。尔来三十余年,连做梦也未曾忘却。”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大谷光瑞将“日本民族”和“个人”共同努力“领导亚洲”从而实现“亚细亚主义”联系起来。由此,《帝国之危机》、《慨世余言》两篇文章也成为其“亚细亚主义”论的开端。
与大谷光瑞的“亚细亚主义”论相呼应,当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亚细亚主义”思潮。该思潮在形成初期作为一种日本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的集合体,包含了兴亚论、合邦论、保全论等诸多不同的形态。各种理论都在“西力东渐”的环境下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的口号。然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要求充当亚洲盟主并取代西方列强向大陆扩张的论调开始稳稳地占据“亚细亚主义”论调的主流地位,使其从本质上表现出了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对此发展趋势,我国学者盛邦和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的亚洲主义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亚细亚主义”从最初的亚洲协力共同对抗欧美的主张演变成了带有侵略性质的对外扩张本质,由最初的亚洲团结变成日本一国领导管理亚洲,从而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此处的“共荣”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幌子,本质却是日本无限对外扩张侵略亚洲各国,其中最具代表性行为就是侵华战争以及侵略朝鲜半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战争进入了包括军事能力、资源、武器、军需产业的综合战斗力阶段,对于国土面积小且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来说必须通过海外扩张来保证军备资源充足,而大谷光瑞所坚持的“亚细亚主义”思想正好迎合了日本的海外扩张政策。并且,大谷光瑞认为中国人的存在妨碍了日本帝国的繁盛。于是,他宣称军备扩张是出于和平的目的,为摆脱日本帝国的危机只能执行军国主义。所谓出于和平而实行军备扩张海外侵略,此番言论是荒唐的,违背世界和平。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理论本质上以实现日本利益为首要目标,将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表现出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海外扩张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以致反噬最终彻底战败。
2.具有佛教色彩的宁波印象
《放浪漫记》中,除了对从宁波前往普陀途中海域的描写之外,大谷光瑞在登陆普陀本岛之后,也进行了一番描述:“登陆普陀山岛后,借住在圆通禅林的寺院。透过房间的窗户,视野十分开阔,东西至南160度的景色尽收眼底。濑户内海般的奇景与天籁般的波涛声搭配的十分和谐,简直和仙境一样。”
他甚至还使用“天然的奇胜”“美轮美奂”来描写该禪林的景色。对于此处描写使用的词汇简直和之前描写那片海域时使用的词语大相径庭。
探其缘由,终是由于普陀与日本之间的佛教渊源。尤其是普陀山的观音信仰对中日两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放浪漫记》中,大谷光瑞也提到关于普陀观音信仰,他称“日本的僧人入唐、入宋时,都往返普陀的寺院拜访,向观音大士祈愿航海安全。”此处被提及的“向观音大士祈愿航海安全”是与观音信仰有关。唐朝时期,日本僧人惠萼从山西五台山请来观音像,途经宁波后置像于普陀山,守护过往的船只与人们。观音由此演变成海上保护神。此后落户于普陀山的普陀观音影响越来越大,远远超出宁波本地观音信仰的范围,遍及整个东南沿海及东亚地区。而观音信仰在日本也是十分流行。观音信仰最初传入日本时并无特别之处。后随着密教和净土的观音信仰传入,观音信仰开始带有现世利益和来世利益的作用。随后,观音信仰上升到国家层面,被赋予“镇护国家”的意义。对于贵族而言,观音信仰具有作为地方守护神来守护家族的功能;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观音信仰能够保佑他们现世利益与来世利益。并且,观音信仰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信仰相互融合,甚至在日本神社中也占据一席之地。随着视观音为“圣”的信仰者进行大量布教活动,日本各地建造起许多的观音灵场。由此,观音信仰成为日本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基于普陀的观音信仰对日本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作为佛教徒的大谷光瑞定是对普陀充满向往之情,将其作为圣地来膜拜。因此,在对于普陀山的寺院描写时采用“仙境”“天然的奇胜”“美轮美奂”等具有褒义色彩的词语也不足为怪。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大谷光瑞在寺院的房间里听到波涛声时使用的是“天籁般的”,他在形容奇景时使用的是“濑户内海般的”,大谷光瑞在潜意识里就把濑户内海等同于天籁,此处再次暴露了他作为日本人所带有的优越感。由于身为佛教徒,大谷光瑞对佛教寺院充满憧憬仰慕之情,其笔下之文尽显夸奖赞赏之意。这不禁令人遐想,假若大谷光瑞的身份并不是佛教徒,他又会如何形容寺院景色呢?根据其描写中国海域时尽显鄙夷之感的性格来推测,大概也是偏向贬义吧。
本文考察的文本,从文体上看是随笔游记,随时记录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受。一般而言,一边旅行一边记录的游记更有史料价值,后人也能更为直观地对其进行研究。大谷光瑞带着日本帝国主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来俯视中国,借着“帮助、同情”中国的噱头实则响应日本政府海外扩张侵略的政策。尽管大谷光瑞的“亚细亚主义”是在其中国之旅即将结束时才提出的,但这种思想却始终贯穿着他的整个“放浪”之旅,尤其在中国旅行期间表现的淋漓尽致,企图侵略呑占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这是近现代日本人来华旅行时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感受,带着日本政府鼓吹的“帝国主义”思想,是近现代中日国力逆转后的必然现象。即便是宗教者,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政治意识色彩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但由于如今关于近代日本人访华游记,对宗教界人士的研究资料少之又少,使得大家对近代日本宗教者的中国观了解甚少。
近代日本人访华游记所记载的中国形象,是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珍贵史料,而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日本人作者的中国观更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中之重。葛兆光曾说过,要重视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这样既可以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丰富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只有深刻了解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审视那段历史,对“现实中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王美平.小寺謙吉の大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その中国観を手掛かりに―[J].アジア太平洋研究,2019(35):116-128.
[2]大谷光瑞.慨世余言[M].東京:民友社,1917.
[3]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M].東京:勉誠出版,2010.
[4]大谷光瑞.放浪漫記[M].東京:民友社,1916.
[5]范宏涛.大谷光瑞的“放浪”之旅与“亚细亚主义”[J].史志学刊,2009(03):20-30.
[6]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1-14.
[7]李广志.宁波海神信仰的源流与演变[J].民间文化论坛,2011(05):31-37.
[8]刘峰,田波.日本大正末期的“亚洲主义”浪潮与中国的回应―兼论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J].世界历史评论,2020,7(02):177-190.
[9]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J].历史研究,2000(03):125-135.
[10]张明杰.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张荣堃.观音信仰在日本的变容研究[D].山东大学,2022.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