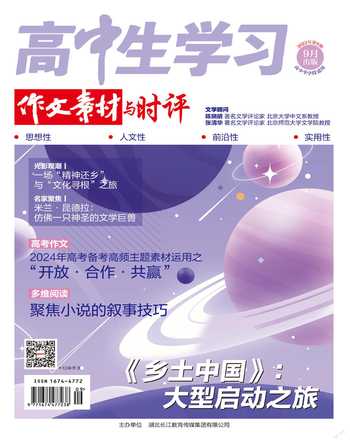作者专论:极富思想洞见和人文情怀的大学者
与其他20世纪的思想者一样,费孝通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中国找寻现代之路。他早年对乡土中国的论述如今成为了中学生的必读书目;而他晚年对文明与文化的诸多思考与提炼出的一些说法,如“多元一体”“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几乎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各方都耳熟能详;不仅如此,费孝通还是世界性的社会科学家,他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了中国式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世界性问题的独创性思考。
——三联书店总经理肖启明
⊙ 徐平(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首先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吴文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在当时世界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都算得上领先。1936年,吴文藻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马林诺斯基。他向这位功能学派大师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
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林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同时也知道了正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因此马林诺斯基一回到英国,便从他的大弟子弗斯手中接管了费孝通,亲自指导其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林诺斯基一首一尾的两大弟子。
费孝通原本想以大瑶山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弗斯却认为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对中国研究更有代表性,由此也奠定了费孝通成功的机缘。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 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結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
(来源:光明日报2017-11-22,原题《费孝通:从实求和 志在富民》,有删改)
⊙ 王乾荣
脚勤:“真知亦自足底功夫”
费孝通脚勤,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1935年夏,清华研究院毕业,将远赴英国留洋的青年社会学者费孝通和同行、新婚爱人王同惠,结伴赴广西大瑶山实地考察。社会学实地考察,当年中国鲜有人为。费氏夫妇此举,并非蜜月之旅,而是一次学术之行。小两口晓行夜伏,一路攀悬崖,跨激流,在“山壁峭立处竟疑无路”,披千里月色,借住于“码头上的大帆船中”,双双生出“不知今夜宿何处”的奇异感慨。不幸的是,费孝通在崎岖山路误踏陷阱,王同惠女士在求援的路上遇难了。费孝通忍着极度悲痛,暗下决心,以一生走田野考察学术道路的行动,来继续爱妻的未竟事业。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并在这里启蒙。后他外出求学、工作,1936年首返离松陵镇不远的祖居地开弦弓村实地考察,正式走上中国独特的社会学研究之路。开弦弓村后被费先生命名为“江村”,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一个名播全球的乡土“学术村”。
1980年,国家走过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几段弯路后,终于盼到改革开放。费老从严寒中伸臂展腰,从另册喷薄而出,重振并引领社会学研究。费老的主要研究方式,即是“田野考察”。他迈开大步,四处探访。“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他说他这匹“健硕的老马”,还想走更多的路,来试试自己的脚力。
东西漫行,南北穿梭,或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或徒步翻山越岭,费孝通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均在路途当中,行色匆匆,跑遍除台湾、西藏之外的祖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方从敦煌还,又上麦积山。老马西北行,关山视等闲。”路漫漫其修远,遥遥行程几许,无以数计。不舍春夏秋冬,无论天南海北,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他不为游山玩水;莺归燕去,山立水转,行行重行行,他双脚不曾歇息。费老的“脚力”,果然不凡。
行者费孝通在路途书赠友人小赋一则道:“兼容并济,山川入怀,满天星斗,古今一瞬。”这是他“行”出来的胸臆,颇富仙风道骨韵味。
他有一本文集,书名《行行重行行》。他给自己记叙访问家乡的两本文集,分别起名《吴江行》和《故里行》。一个“行”字,尽道高龄行翁的“脚勤”功夫。
脑勤:“事迹易见,理难相寻”
费孝通脚勤,缘于他的脑勤——脑指挥脚嘛。
1936年清华研究院毕业那会儿,他完全可以赋闲等赴伦敦,然而他抽这个空当去了大瑶山,为的是做土著民族状况的调查。
在大瑶山考察时受伤,他“意外得到两个月‘余暇’”,也不静养,而是跑回家乡江村,作“除获得知识之外毫无其他目的及责任”之访——后来事实证明,他这次获得的知识,恰恰用在了他一贯追求的“富民”这一明确“目的”上;而他的一生,也正是以实现这个目的为己任的。
综观费老一生学术成就,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他赴伦敦之前在江村所做调查报告的一个结晶,被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即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创译)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
此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
费老晚年复出后研究新时期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写下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总结出新锐的“苏南模式”,也无不体现着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发展道路这一基本理念。
费老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但是他没有像有些“海龟”那样,把学问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而是将它“中国化”“乡土化”,使之变成改变穷困中国的一件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贡献。
在费孝通先生那里,学问就是有用的知识,他始终虔诚地使他的知识学以致用。有人因此把他绵延半个多世纪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誉为“江村学”,以彰显他的卓越成就,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说,《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对现代乡土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做了最早图解,那么《乡土中国》的主旨,便是着眼于中国整体社会的结构和特质,高屋建瓴地审视社会,试图把握中国文化的脉搏。它不因循西方社会学法则,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浅出以例释理,娓娓道来,妙趣横生。比如我们可以从中见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山杠爷”式人物,使读者于愉快的阅读享受中,蓦然领悟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原来如此”的真相。这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学解析,既反映出国民性中朴实、美丽的一面,也挖掘出民众蒙昧和深受宗法理念束缚的另一面。费老得出的结论是,“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因为前者是“争权利”,后者则是“攀关系、讲交情”。
在对国民性的探索上,费老“从制度到精神”的社会学分析,与鲁迅“从精神到精神”的文化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强调的是,人們如何行动起来,把一个“乡土中国”变成“现代中国”,使之融入世界,步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且不失中国特色——这才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终极使命。
后来费老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世界各民族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的设想,便是他自《乡土中国》开始一贯持有的学术思想的延续。
费孝通这些前无古人的研究成果,得益于他的“脚勤”加“脑勤”,而以脑勤为主——“事迹易见,理难相寻”嘛。他把他一生不落窠臼的考察结果不断升华为新的理论,才开创和丰富了独特的“中国社会学派”,才有了对于国民性的深刻挖掘,才促生了概括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变迁的“苏南模式”,才唤起了国人在文化方面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意识,也即敲响了国人“文化自觉”的警世钟。
(来源:北京日报2011-12-27,原题《脚勤、脑勤、笔勤的费孝通》,有删改)
《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
⊙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觉得《江村经济》绝不下于《乡土中国》。完成前书时费28岁,后书时38岁。跨越十年的这两书实为姊妹篇。一个微观,一个宏观;一个是对某一村庄生活的面面俱到的事实勾画,一个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融会贯通的理论思考。
两相对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定位《乡土中国》。笔者以为,《乡土中国》是一本理论著作。我相信同行的师生中会有不赞同者。不得学问真谛者常陷入两个误区,须棒喝纠正。其一,哲学史不是哲学,理论史不是理论。其二,理论未必是高度抽象和艰深的。什么是理论?从现象的层面提升到概念和道理,就是理论的形成。不论水准高下,中国哲学史家、理论史家多得是,哲学家、理论家少得很。准确地说,《乡土中国》是一本通俗的理论著作,它形成了概念,讲出了自家的道理。通俗的理论也是理论,艰深的理论史也不是理论。而《乡土中国》是通俗理论著作中的精品。
我定义《江村经济》是经验研究、田野研究。我一向不接受“实证”的说法,尽管费孝通也说“实证研究”。我以为“实证研究”属于自然科学,一方面社会学高攀不上,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现象也不是可以实证研究的东西。经验和理论是对应的。汉语“田野”的概念精妙。“野”对峙于“文”“文献”;“田”以其象形,道出边界性、局限性,拒绝泛滥无边、大而无当。费曾说:他做学生时就不喜欢《定县调查》式研究的肤浅。他日后的研究在两端上反其道行之,《江村经济》在深入调查一端,《乡土中国》在理论思辨一端。而二者在他那里发生了关联,没有《江村经济》和魁阁的六年(1939-1945)的乡村研究,就不会有《乡土中国》的宏观思考。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离开村庄整理调查20天后,返回村庄补充调查10天。就是如此短时间的调查托举起这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语)的研究。第一,当然在于他天分高。第二,他是本土人,他在该县的另一村庄生活到十岁,离乡后少不了听说乡间的事情。因此调查的效率一定高于地道的外乡人。第三,他对这项调查的巨大热忱。他在调查刚刚结束后撰写的《江村通讯》中说:“虽说我是个本乡本地的人,而回去一看,哪一样不是新奇巧妙得令人要狂叫三声。这一个月紧张工作,只令人愈来愈紧张。”如此状态,不出成果都难。有人类学家反对回本乡做人类学研究,说视野早被成见扭曲。有一部分道理,未离开本乡的人调查本乡确实有这个问题。但笔者觉得,离开本乡若干年,见识过另一天地,学习过理论反思,回过头来研究本乡,非但可以,且有其优势。费的成功即其证明。
《江村经济》当初的副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这副标题起得“好”。好在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的雄心,另一方面,因标题与论文内容的反差所势必引发的批评——一个村庄可以概括中国社会吗?我们有缘听到费孝通在方法论上的辩解。他说:
把一個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同一整体中的个体有点像从一个模式里刻出来的一个个糕饼,就是这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他引用当年他的一位老师、最早赏识《江村经济》的弗思(Firth)教授的话说:
我想社会人类学者可以作出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依然就是这种微型社会学。
我很同意费的辩护。其一,社会的某个局部,与大象的某个局部,迥然异趣。单纯从象牙、象尾,不可能认识大象。而文化在时间上先于每个在世的个体,从空间上传播到广阔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导致一个局部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总体,虽然子文化和小传统也决定了局部不可能完全反映总体。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共性与个性。其二,因为巨大体量的事物难以把握,深入的理解,几乎必然来自可以把握的局部,特别是在迄今为止“大数据”的伟力还未全面释放的社会历史中。
其实,费孝通的姊妹篇的成功就是以上辩护的证据。《乡土中国》论述的不是社会的局部,而是整体。而他此前的主要力量是花费在一个个乡村,即社会局部上面的。在概括中,他扔掉了他判断为局部的个性,整合出各局部的共性。从局部推断整体,当然不能说不会失误,但是舍此该如何认识整体呢?不是每个研究者,甚至不是多数研究者,可以完成从局部推断整体。但是能完成“微型社会学”研究的人较多。他们的成果,为理解中国社会之整体准备了基础。况且,为理解整体做准备,只是“微型社会学”的功能之一。如果认为微观研究的功能仅限于帮助理解庞大的中国,便是头脑僵化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中。一个村庄的研究,可以直接服务于该村庄,以及同类型的村庄的改善。还可以服务于若干小专题。其功能不一而足。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9-16,原题《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有删改)
士不可夺其“志”
⊙ 刘友梅
费孝通特别强调“志”对于人生的意义,“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要知道,要明白……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他曾经写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认为自己能够看出他老师那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他以曾昭抡先生为例,曾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已经很出名了,是系主任。曾先生穿的鞋是破的,他想不起来要穿好一点的鞋,还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换一双。别人可能评价他不修边幅,但在曾先生的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的。费孝通说:“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费孝通是在1938年回国的,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外国人觉得奇怪,问还在打仗,为什么要回去。费孝通说,就是因为打仗,所以得回去,“我们当时很多在外国的朋友,很少因为在外国生活好一点,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流落异乡,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
费孝通早年在东吴大学读了两年医预科,目的是想治病救人。后来,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亡国的问题,于是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下决心研究中国的社会。
费孝通说:“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从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1938年秋,费孝通抱着救国的信念从英国学成归来。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他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费孝通的一生都是“志在富民”,他有一种“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
1938年11月15日,他刚抵达昆明两个星期,就奔赴西距昆明约100公里的禄丰县,在一个村子里开始了调查。他为这个村子定的学名叫“禄村”。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费孝通写道:“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首先就要认识农民,懂得农民。”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1938年至1942年,他带领学生和助手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要补课”的要求,这项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费孝通的肩上。费孝通重新创建的社会学,是要从中国土地、中国人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此,学科建设成为他的重要使命,而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他的第二段学术生命开始于江村。他将江村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8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又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提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进而从块状的发展模式提升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包括黄河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影响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是他大半个世纪苦苦追寻之所在。
尽管费孝通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来源:上观新闻2020-12-01,原题《费孝通:坚守知识分子风骨与情怀》,有删改)
“志在富民”的深刻意蕴
⊙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管仲《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熟悉或不熟悉费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费先生把自己的人生志向归纳为四个字:志在富民。在我的头脑中一直保存着一幅清晰画面,即先生手书的“志在富民”。
如果我们以为“志在富民”的“富”只是指经济,或许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面。我以为,“志在富民”可以作两层理解:第一层是改变中国的面貌,另一层则是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前者是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讲经济生活,《行行重行行》讲经济发展。在这些著作里,费先生有一个由下向上的发展思路,主張富藏于民。第二层是改变中国人的落后面貌,是大家不讲的。落后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所指,内涵社会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指思想落后、精神落后。合起来理解,“志在富民”的“富”,一层是经济富裕,一层是精神富有。在费先生那里,精神和财富的双重富有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本质,社会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面。这个追求,早已呈现在费先生14岁时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中。
在精神富有之中,“志在富民”的又一层含义是希望在“富”的进程中不让中国变成西方那样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人与物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费先生曾反复强调说,中国向现代转型要经历“三级两跳”。
第一跳是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中国人口和资源分布得极不均匀,东部资源丰富、人口密集;中西部资源相对贫瘠、人口相对分散稀少。人口与资源分布的非均匀性导致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跳跃中会出现地区之间的非均衡性。为此,他提出过两个方案。第一是在东部发展乡村工业,推动城乡一体化;第二是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发展大工业,推动城市对乡村的带动。大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是费先生的第一个方案,却忽视了他的第二个方案。其实,费先生在第二个方案上花费的精力并不少,他带着学生去了不少大型企业考察,探索大企业带动地区富民的路径。
第二跳是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在第二跳中,有经济富裕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精神富有。对此,费先生重拾早年对中西社会、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讨论,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士绅》《留英记》到《美国与美国人》,把中国和中国人放在更长远的历史和更大的社会格局中,分析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探讨中国“富了以后”怎么办。费先生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在向信息社会的跳跃中,中国与西方相遇、中国人与西方人相遇是世界潮流,不可避免。既然如此,中国和中国人又如何自处及与西方相处呢?费先生问自己,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历经十年,在《孔林片思》中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倡导世界各国的文化自觉。
(来源:光明日报2021-01-02,原题《费孝通:破茧欲飞舞 行行重行行》,有删改)
费孝通的十六字箴言
⊙ 丁元竹(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费孝通先生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探索中国发展问题,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2001年10月,费孝通在演讲中说:“我反复申说这四个字(“和而不同”),包含着我个人对百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诸多努力的一个总结,也隐含着我对人文重建工作基本精神的主张,更饱含着我对人文世界未来趋向的基本盼望和梦想。”
在赴英国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之前,费孝通已在姐姐费达生开办的丝厂开展实地研究。他从丝厂所在的吴江开弦弓村开始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乡村手工业和城乡关系,20世纪30年代留学英国和40年代访问美国,则使他有机会在东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中深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此外,20世纪30年代初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费孝通深受吴文藻的影响。吴文藻向费孝通介绍了帕克的社区理论,也介绍了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讨论的“社区”,主要用以说明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另外一种社会类型,是一种欧洲经验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可以看到滕尼斯理论的影子。“共同体”理论是包括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在内的多位学者对时代变革的共同反应。
如果说18、19世纪的思想家们试图用共同体理论来回应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乡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变,那么20世纪末提出这十六字箴言,则是费孝通基于历史积淀,把对现状与长期社会进程的思考结合起来,对百多年来世界层面的工业革命、城市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新变化所做出的新的历史性回应。这十六字中的“天下大同”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大同”进行了改造,并延伸了社会学中的“共同体”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战国时代,人类必须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实现“天下大同”。
当前,人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一个不同于19世纪的时代节点上,必须在一个更高层面上重塑共同体愿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共同体,正是这十六字箴言的历史逻辑。
(来源:文汇报202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