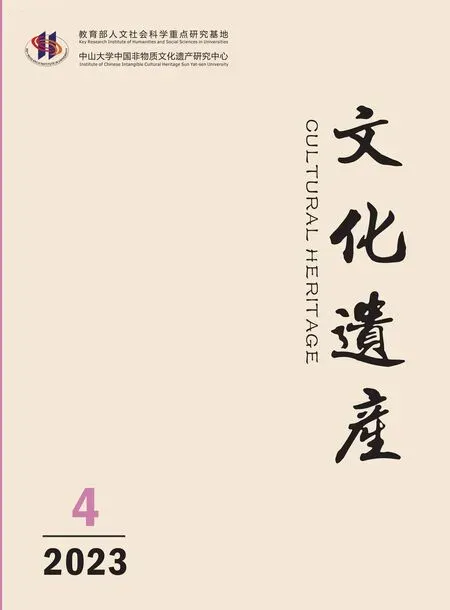神话与迷信之争的知识溯源:以1920年代世界考证潮流为中心*
杨明晨
引 言
1950年代初期,中国曾就如何界定、处理文艺作品中的神话与迷信问题展开讨论,传统戏曲尤为关涉其中,田汉、周扬、黄芝冈、马少波等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都发表了相关观点。(1)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田汉全集》第17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74-198页;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71页;马少波:《迷信与神话的本质区别》,《戏曲改革论集》,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64页;黄芝冈:《论“神话剧”与“迷信戏”》,《从秧歌到地方戏》,上海:中华书局1951年,第 51-71页。改革传统文艺中的神鬼内容是新中国初期建设新文艺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神话与迷信的讨论正是出现于此背景中,当代不少学者也是在1949年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特定脉络中理解这一现象。(2)代表成果有:张炼红《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王英《无鬼之国:中共与陕西地区的“鬼戏”之争》,《二十一世纪》(香港)2016年12月号,总第158期,第51-66页;Maggie Greene,Resisting Spirits:Drama Reform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n Arbo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9)等。
不同于目前主流的研究思路,本文试图从知识史溯源的角度重新反思1950年代这场神话戏与迷信戏之争,即追问中国现代思想史或知识史中何时把神话与迷信的范畴联系在一起,使得神话有了迷信的意义?这种知识在怎样的文化实践中形成?又如何扩散至文艺、政治等其他领域为其提供认知基础?在此意义上,本文将1950年代的论争视作1949年以前神话/迷信知识在当代的回响和变奏,其中1920年代中后期一批民俗学知识分子的神话考证成为重要历史事件。当时顾颉刚、容肇祖等学者以文献考证的现代学术实践考证神话传说,并汇入到从西方汉学流转到东亚中国学的世界考证风潮中,这不仅在知识观念上将神话传说归为实证科学的对立面,而且与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风俗改革和戏曲审查管制互动呼应,奠定了日后缠绕在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的神话/迷信关系命题。本文通过追溯1920年代这段从西方现代学术实践到中国文艺政治的知识跨界之旅,以期重新理解神话/迷信在中国现代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与意义。
一、神话传说作为迷信的表述
现代汉语的“神话”概念在晚清就已出现,以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文为代表,“神话”意涵在引入中国之初便与欧洲19世纪以来流行的比较神话学、文化人类学话语密切相关,世界各地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被视为人种分布和人类文明进化的依据。(3)梁启超:《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梁启超著、林毅点校《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第21页。同时期日本知识界对西学的接受加速了进化论人类学在东亚的流行,以精灵魔术信仰为特征的神话往往被定义为原始初民的历史范畴(4)如19世纪后期日本出现了模仿西方文明史、人类学的畅销文化专著,把神话问题结构在进化论的文明史框架之中。参看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东京博文馆1898年,第21页;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东京博文馆1900年,第8页。,中国从晚清民初的思想启蒙论述到1920、1930年代的神话研究皆不乏对这种认知的回应。(5)前者如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鲁迅《破恶声论》等;后者如黄石《神话研究》(开明书店1927年,第2-9页),玄珠(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世界书局1928年,第4-7页),谢六逸《神话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第32-35页),林惠祥《神话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0页)等。
尽管在进化论人类学的知识结构中,神话意味着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非理性范畴,但并未被明确定义为“迷信”,也正是与此脉络相对,中国1920年代直接将神话传说等同于迷信的观点就显得十分突出,容肇祖《迷信与传说》一书便是代表之一。该书以“传说”而非“神话”为题,但针对的内容是传说中与神话密切关联的超自然因素,在此意义上神话与传说难以分离。(6)关于神话(myth)与传说(legend)的关系,民国学者在有意区别两者的同时又强调两者在神的故事和超自然信仰方面的相似、相通和相关性,如周作人《神话与传说》、茅盾《神话的意义与类别》等文。本文也是从此意义出发,将神话与传说连在一起讨论,它们共同含有的超自然信仰元素是本文“迷信”议题所讨论的对象。《迷信与传说》由容肇祖在1920年代不同时期写作的文章汇编而成,在1929年被纳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出版。虽然书中不同文章所讨论的对象各不相同,但主线以明确的姿态将民间神话传说定义为迷信,并且宣称该书的目的便是通过专业的研究而破除迷信:“我们就所知的材料,求所得的结论,这也不是徒然的。在广大的范围的学问中,我们要研究民俗学,在民俗学范围中我们要研究迷信,我们因材料的便利而研究中国的迷信。”(7)容肇祖:《迷信与传说》“自序”,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第3页。在此,容肇祖把“材料的便利”投向中国古典文献中的神话传说,他所谓的反迷信实践便是破除中国的“神话迷信”。
具体而言,容肇祖为何会把神话传说视作迷信?又如何通过研究而达到破除迷信的目的?他在《传说的分析》一文中写到:
传说既然成立之后,人们便把增生和演变的解释当作事物的源起,假如你要说他不对时,他们就会发问“何故会有这事物呢?”你答不通时,便见仍然不能破他们的迷信,他们仍是说他们确凿的证据。(8)容肇祖:《传说的分析》,《迷信与传说》,第139页。
在容看来,传说之所以是迷信,是因为人们“把增生和演变的解释当做事物的源起”,而所谓“增生和演变”的内容往往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灵与神迹,人们对之深信不疑而不知道他们信奉的对象其实是在后世流传中添加虚构而成。针对此现象,容肇祖指出破除迷信的方法便是向世人揭露神话传说的本事和演变过程,这样故事中的神灵主角便原形毕露、不攻自破。他在序言中写到,对待神话传说应当“讨寻他的来源和经过,老实不客气地把他的真形描画出来。”(9)容肇祖:《迷信与传说》“自序”,第2页。例如书中《二郎神考》一文,容肇祖详细爬梳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相关记载,梳理出汉代蜀守李冰在后世逐渐神化并与其他历史人物混淆而成二郎神的演变轨迹,以此达到容肇祖破除二郎神祭拜“迷信”的目的。(10)容肇祖:《二郎神考》,《迷信与传说》,第142-171页。
将李冰视作二郎神的原型是容肇祖的一家之言,譬如胡适在同时期还主张北宋人杨戬是原型(11)胡适:《关于封神传的通信》,《民间文艺(广州)》1927年创刊号,第32-33页。,容肇祖在考证李冰线索之外也受其影响。(12)容肇祖除了考证李冰演变线索,还整理了其他与二郎神名有关的人物原型,并认为胡适的观点甚可参考。容肇祖:《二郎神考》,《迷信与传说》,第170页。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容肇祖与胡适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却在根本方法和目的上相一致,即试图以考证文献材料、辨析神话传说发展演变的方式呈现某一神灵偶像的起源与形成,以揭开后来人们深信不疑的神话或神明的神秘面纱。事实上,考证神话传说的学术实践在中国1920年代的民俗学中一度流行,这不仅在研究方法与治学风格上与追随文化人类学的神话研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神话传说不再仅仅被视为蛮荒或原始的范畴,而是在历史考证的真假辨析中被视作不符合实证事实的虚构。它们明确被定义为附会、衍生之物,人们对它们的迷恋与崇拜就成为了缺乏科学依据的迷信。
容肇祖以文献考证而破除神话迷信的学术实践直接来源于他的老师顾颉刚。顾早在1924年《东岳庙游记》中便提出神话是迷信的观点,文中指出:“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神话,有史书,笔记,图画,铭刻等等供给材料。要研究现代的神话,有庙宇,塑像,神祇,阴阳生,星相家,烧香人等等供给材料。”(13)顾颉刚:《东岳庙游记》,《歌谣周刊》1924年6月29日第61号,第1版。而该文具体针对的北京东岳庙及道教便属于顾所谓的现代神话,这被他毫不客气地称作迷信:“北京的东岳庙的规模,固然不能及玄妙观大,但至少可以说是北京人的迷信的汇总。”(14)顾颉刚:《东岳庙游记》,第3版。顾颉刚的神话研究虽然涉及田野,但更体现为与容肇祖一样的历史文献学,也是将神灵与神迹视作历史流传中添枝加叶的衍生之物。他在发表《东岳庙游记》的同年便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著名长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其后经过不断发展形成孟姜女研究系列,收录于1928-1929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其研究考证了《左传》中的杞梁之妻如何演变为孟姜女传说和孟姜女庙的供奉信仰习俗。由于顾颉刚在1920年代后期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影响,直接带动了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为中心的神话考证风潮。例如魏应麟的《福建三神考》是一部密切追随顾、容神话考证的著作,作者将自己考证福建三神——临水夫人、郭圣王与天后的研究称作对顾、容的天后考的延续。(15)魏应麟:《福建三神考》“自序”,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第2-3页。而魏应麟强调福建三神的形成是后世不断增添虚构成分的结果,这更与顾、容二人的话语方式别无二致。
1920年代中国民俗学者的神话考证,与其说是以各自研究来破除中国既已存在的神话传说迷信,不如说他们正是在文献考证的现代学术实践中,才将神话传说等同于迷信的知识建构出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文献学并非完全建基于中国的文献学传统,而是与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学科互动共振,这种以实证科学为精神的学术实践将神话传说文本化,并以事实判断为依据重构神话传说的逻辑意义。正是在此认知体系中,神话传说才逐渐被视作迷信。
二、从西方到中国的世界考证风潮
1920年代中国民俗学同人中流行的神话考证,直接与顾颉刚的史学革命有关,即他著名的“古史辨”。顾在1926年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收录了此前他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论伪书的文章,并以长篇自序阐明其“疑古辨伪”的主张,以层累说为模型,“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16)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3页。在这辨伪史的过程中,就包括考证古史中所混入的神话,例如顾颉刚最为有名的研究之一是对史祖“禹”的考证,提出大禹治水神话中广为流传的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17)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63页。
顾颉刚从史学研究的脉络进入民俗学和神话考证,加之他自身并未有过留学或翻译西方著述的经历,又不想承认西学对他的影响(18)在《古史辨》第一卷中,顾颉刚基本只承认中国传统学术是他疑古史学的来源。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1-13页。,因此其对神话的历史考证容易被视作中国本土的话语实践。但事实上,顾颉刚所表现出来的似乎十分传统的文献考证,仍然是与欧美现代学科进行跨文化互动的结果,是19世纪后期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东亚的历史考证潮流的一部分,这一全球化网络联结起欧美东方学/汉学、日本中国学以及中国1920年代与民俗学学科建设几乎同时期开展的“整理国故”等不同地区的现代学术实践。顾颉刚对神话的历史考证正是出现于这一全球脉络之中,与他响应胡适号召而参与其中的整理国故运动相关联,可以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民俗学学者在1920年代中外多重现代考证学术脉络的汇流与碰撞中建构起神话/迷信知识。
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胡适,自称是受启发于在巴黎“敦煌烂纸堆里混了十六天”(19)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而准备整理中国传统,所谓的“敦煌烂纸堆”,正是当时正兴起活跃的欧美汉学研究,特别以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为代表。胡适将欧美汉学的语文学方法视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可以帮助他“把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打出来”(20)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第117页。,神灵的原型考证达到他所谓“打鬼”“捉妖”的意义。而顾颉刚不仅与胡适有所交往,1920年代前期他所处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就是在“国学”与海外“汉学”的交缠中建立起来的机构。当时国学门聚焦团结的重要人物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周作人、黄侃等都是章太炎弟子,而大力支持国学门的蔡元培更是对欧洲东方学/汉学有所了解,他在1921年提出西洋各国研究中国典籍的现象。(21)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后来1932年北大发布的国文系课程指导书中,更是明确指出国学门和国故整理运动直接受到欧美汉学(Sinology)和日本“支那学”影响:“近数十年来,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去所谓‘支那学’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尤多可观。老实说,近年提倡国故整理,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22)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李森《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续编》第一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329页。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具体设置了“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几个分支,考古、风俗、方言等研究正是其时海外汉学的重要领域。而事实上,1920年代国学门确实在积极与欧美和日本的相关学者联系交流,将诸多汉学家列为国学门的通信员,包括[法]伯希和(Paul Pelliot)、[日]今西龙、[日]泽村专太郎、[丹麦]吴克德(K.Wulff)、[法]阿诺德(Therese P.Arnould)、[德]卫礼贤、[日]田边尚雄。(23)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页。这些汉学家大多都在语文学和考古学方面取得成果,其中伯希和在今天更为著名,他继承法国著名汉学奠基者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的中国文献考证,出版了诸多敦煌文献研究著述,涉及语言、宗教、考古等多方面,还在1922年通过罗振玉向研究所国学门捐赠了二十篇论文,(24)《伯希和先生赠书》,《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11日,第2版。其中一篇关于东方古语言学和历史的文章在1923年被王国维翻译成中文后发表。(25)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王国维译,《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3月16第3版;3月17日第2版;3月19日第2版;3月20日第1版。顾颉刚在北大时期并没有专事于某一部门,而是担任研究所国学门的助教和干事,直接受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指派负责学会各类出版物编辑和活动筹办(26)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84页。,这种经历使他更容易接触到上述诸多汉学家及其研究。
尽管顾颉刚未承认自己受到海外汉学考证研究的影响,但他却在1939年中国出版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书经中的神话》(LégendesMythologiquesDansleChouKing)前言中表达了西方汉学的了解,并宣称他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是“精密的头脑,科学的方法”。(27)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冯沅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页。这正是“整理国故”运动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想象和接受方式,即欧洲汉学的文献考证启发中国学者将中国文献考证的学术传统进行现代化革命,并使之成为服务于科学启蒙事业的工具。马伯乐也是沙畹的学生,《书经中的神话》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相似,指出神话传说被列于中国上古史迹之中并被《尚书》尊为正史,他致力于辨析出不同的神话传说类型,在其划分的“洪水的传说”中就包括禹的神话。(28)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第21-22页。实际上,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汉学界普遍出现了考证中国上古史和尧、舜、禹(特别是禹)的趋势,(29)西方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早在晚明耶稣会士来华之际就已出现,耶稣会士重绘中国上古史在神学版图中的位置以传教,也开启了后来欧洲启蒙时期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及争论,成为近代汉学家文献考证研究的先行。可以参看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汉学家常常从《尚书》等上古史的后世汇编情况出发,提出尧、舜、禹如何被书写进上古三王的谱系,并强调他们作为传说的性质。不过,一些汉学家在论证尧、舜、禹的超验神话特质时,也并未简单否定他们曾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例如上述马伯乐在解释大禹神话时便未明确表态;再如,将《尚书》翻译为英文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其译本的前言介绍中首先指出尧、舜、禹的神话传说和后世演义性质,随后却又在结论中认为人们不应当怀疑他们是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30)James Legge.The Shu King,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879),14-19.;其后Thomas W.Kingsmill、John Chalmers、沙畹等不少著名汉学家都曾加入相关讨论。(31)Rudolf G.Wagner,“The Global Context of a Modern Chinese Quandary:Doubting or Trusting the Records of Antiquity”,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67(2019):457-61.
西方汉学界关于上古三王的文献研究,在历史编年与神话考证的史学原则上与顾颉刚对“禹”的疑古相似,但他们与顾颉刚宣称大禹是动物的观念不尽相同,而最像顾一样直接否定禹作为历史人物的声音来自日本的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白鸟库吉的一位重要老师利斯(Ludwig Riess)是德国著名东方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学生(32)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al: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25.,白鸟从欧洲东方学中习得现代考证方法并重新应用于对中国上古史材料的整理,提出尧、舜、禹是战国后人们为宣扬儒家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33)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页。,其尧舜禹抹杀论成为西方汉学和顾颉刚考证大禹之间的重要过渡和中介。不过,尽管顾颉刚的方法和结论与白鸟有相似之处,但两人背后的思想体系和文化意图根本不同。顾强调大禹虚假性的主张与他论“伪书”、质疑儒家正统的姿态有关,根本上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把任何有权威的偶像都冲倒”(34)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第1页。的思想启蒙事业。
尽管很难直接判定顾颉刚受到特定某位西方汉学家或语文学家的影响,他与白鸟库吉的关系也为不少学者和文化人所争论(35)如王汎森、刘起釪、李学勤认为顾颉刚没有受到过白鸟库吉的影响;而胡秋原、廖名春认为他受到了白鸟的影响。李孝迁:《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史学界的影响》,《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61-62页。,但他的确处在中国国学与海外汉学相互动的脉络中,其考证神话、古史辨伪的话语实践是其时全球流动风潮的一部分。1920年代从事神话考证的民俗学学者以顾颉刚为中心,在了解、汲取、汇入欧美与日本现代学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跨文化实践,与“整理国故”运动一道重新发明了文献考证的传统。在文献考证所彪炳的现代科学精神中,神话与传说不再以信仰价值所衡量,而是在现代实证逻辑中被辨伪、去伪。如此一来,像福建三神、二郎神以及孟姜女神这些隶属于完整地方宗庙体系的神话传说,被剥离开其原本所属的文化体系,而作为文献被重新归类进一种“文本化”的历史。文本化的信仰对象在现代技术中被“辨伪”分析,神灵权威和信仰的合法性由此被解构,神话作为迷信的知识也逐渐形成。
三、学术实践与文艺管制的跨界互动
1920年代后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学术实践与其时南京国民政府的风俗改革出现了交织与互动,其中也包括“神话迷信”的建构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紧全国“训政”和秩序清洁,在此氛围中开启了包括干预民间信仰在内的风俗调查改革,通过削弱民间信仰以建立张倩雯所说的“民族世俗主义”(national secularism),这在当时是加强国民党政权权威、塑造现代国家共同体的方式之一。(36)Rebecca Nedostup,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4-16.这一过程不仅牵涉到宗庙习俗等社会事务,并且对表现神话内容的文艺也进行审查,审查机构将迷信话语应用其中。
1929年广州“风俗改革委员会”(简称“风改会”)的建立和运行,是联结民俗学与政治实践的一个明显例证。风改会响应南京国民政府整改社会风俗的计划,于1929年七月由广州市国民党党部成立,其核心工作便是“改革风俗,破除迷信”(37)风俗改革委员会编:《风俗改革丛刊》,广州: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印1930年,第3页。。风改会成立后首先整治了广州地区七夕节烧衣拜仙的习俗,随后波及庙宇活动、宗教信仰、旧历体制、妇女健康、卜噬星象等不同方面,还涉及到民间戏剧,如当时一篇为风改会撰写的文章写到:“民间的戏剧,端阳节的竞渡,清明踏青,中秋赏月,重九登高等习俗,都无一不是祀神祭鬼的举动。把很优美而且有意识的民众艺术,白白地糟蹋在迷信的观念里面,演成了鄙俗秽陋的风俗。”(38)冰浪:《改革风俗与提倡艺术》,风俗改革委员会编《风俗改革丛刊》,第54页。风改会自觉寻求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合作,上文提到的容肇祖就被选派参加风改会的工作,容特意针对风改会和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之间的关联撰写了《改革风俗与民俗研究》一文。(39)容肇祖:《风俗改革与民俗研究》,风俗改革委员会编《风俗改革丛刊》,第36页。巧合的是,除了容肇祖,另一位考证神话的学者魏应麟也在1929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第二次会议中被派选出席广州市国民党党部风俗改革会案,在这次学会会议中,学者们还就与风改会合作的事情进行提议。(40)《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30年,第81-82页。风改会的出现和运行直接表明了1920年代民俗学知识生产与政治实践发生了关联,“训政”通过借用现代学科话语以对自身进行科学化、合法化地表述。
正是在1920年代民俗学知识与政治实践联结互动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发现神话作为迷信被建构出来的历史节点:学院派形构神话/迷信知识的几乎同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将涉及神怪或神话的舞台与荧幕表演视作迷信活动,并在全国范围内审查禁演。以国民党1928年的审查活动为例,传统戏曲、海派京剧、电影等诸多表演类别中的神怪或神话内容都牵涉其中,各地教育局或其他审查机构认为它们宣传迷信,这与其时正开展的风俗整改潮流紧密呼应。在当时的海派京剧舞台和电影产业中,“西游记”“封神榜”题材最为流行,舞台新技术推进了超验神话的奇观刺激,上海市教育局就此指出“此类神怪戏剧,对于社会风俗有不良的影响,无形中促使观众引起迷信观念,妨碍文明进步”,提出“不许各舞台再行开演”的禁令。(41)稳:《禁演神怪剧》,《锡报》1928年10月7日第4版。而同年遭到审查禁演的“迷信戏”远不止于新兴风靡的表演形式和题材,更涉及诸多传统曲种曲目,既包括主流唱腔京剧,也包括地方戏,它们往往改编自古代典籍中的神话逸闻,不仅鬼仙形象突出,更是隐含着民间宗教信仰的意义。如1928年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要求禁演十六部浙江京剧,认为“流行旧剧,内容类多诲淫诲盗及提倡迷信者,此种剧本,殊足以影响革命建设之进行。”(42)十六部被禁之戏分别是《劈山救母》《新斗牛宫》《阴阳河》《黑风帕》《盗仙草》《探阴山》《七星灯》《九花娘》《宝蟾送酒》、二本《虹霓关》《双珠凤》《少华山》《纺棉花》《双摇会》《梵王宫》。参看《浙省禁演之剧目》,《小日报》1928年8月9日第2版。这些禁戏中明显具有神话与信仰色彩的是《劈山救母》《新斗牛宫》《阴阳河》《盗仙草》《探阴山》《七星灯》。如《阴阳河》一剧,主要讲述了山西商人张茂深与妻子李桂莲因中秋月下交欢而秽犯月宫,妻子因此暴病失魂,张茂深后来在阴阳河看到已经嫁给地府鬼役的妻子,最后妻子还魂夫妻重圆。(43)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第301页。戏剧中作为故事发展动力的秽犯月宫、地府勾魂等情节具有民间道教信仰的痕迹。
上述禁戏中的《盗仙草》格外引人注目,该戏是著名白蛇神话故事的京剧演出剧目,而本文开头提及的参与1950年代神话戏与迷信戏论争的田汉,恰恰在1950年代重新改编了京剧《白蛇传》。田汉曾在1952年呼吁区分迷信与神话,他以神话表现古代人民对旧世界的抗议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为由,为一些神话题材辩护(44)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田汉全集》第17卷,第181页。,第二年他便改编了京剧《白蛇传》,通过突出白蛇对法海的反抗而将神话戏合法化。(45)可参看田汉编写的《白蛇传·京剧》,北京宝文堂书店在1953年出版。虽然田汉在1950年代使得白蛇神话的戏曲免遭迷信之名,但我们可以早在1920年代国民党的戏曲审查中就看到相关问题的源头,1928年的戏曲审查风潮将包括《白蛇传》在内的一系列传统神话题材与民间神灵之戏推入迷信话语的漩涡,直接开启了日后关于神话戏与迷信戏的困惑。这不仅在1928年浙江的戏剧审查中有所体现,《白蛇传》在同一年武汉戏剧委员会的禁戏名单中同样上榜,武汉禁演的所谓迷信戏,除了《白蛇传》外还有《打城隍》《打灶神》《大游寺》等。(46)老鸽:《武汉禁演之剧目》,《小日报》1928年11月2日第3版。
南京国民政府对神话戏的审查与此前的旧戏批评和禁戏传统形成对比。一方面,尽管晚清以来知识分子不乏以是否合乎现世理性为依据批评传统戏曲中的鬼神内容,但他们更多化用传统儒家“不合情理”“不事鬼神”的旧有说法,这与1920年代后期知识界和南京国民政府所强调的现代迷信知识明显不同。(47)如陈独秀《论戏曲》中提倡“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戏”,三爱(陈独秀):《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期,第5页;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上批评旧戏“淫、杀、皇帝、鬼神”(周作人、钱玄同:《通信: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新青年》1918年5卷5期,第527页)等。另一方面,从政府禁戏的历史脉络看,此前北洋政府更多沿用了近代以前官方禁戏传统中“风化”的表述,对“淫戏”的整改是其强调风化道德的重要内涵,而绝少涉及神话/迷信的面向。(48)北洋政府对戏曲表演的相关管理,可以参看《直隶教育司关心风化》,《教育周报(杭州)》1913年第13期,第18-19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0-174页等。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治管制中,戏剧与电影最突出地纳入审查中,这不仅因为此类舞台视觉实践较之其他文艺形式更为流行,更重要的是它们容易激发社会情感和认同,特别是传统戏曲中的神话,不仅仅起到娱乐作用,更是隐含着鼓动信仰的可能,而神话信仰也正是神话考证的学者们所致力于解构的。1920年代神话考证的学术实践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神话戏管制相呼应,两者的互动进一步使神话传说成为反迷信的对象而进入科学启蒙话语中。
总之,中国在1920年代中后期明显出现了神话/迷信的现代知识建构和与之呼应的文艺政治管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学术实践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戏剧审查并非简单一致,两者的运行逻辑并不相同。神话考证不是将神话现象从社会中清除,而是通过整理、展示乃至保存历史中的神话使之成为没有信仰效用的“死物”;南京国民政府在风俗改革中却是以直接消除和压抑部分神话为旨归。其时民俗学学者并非没有意识到知识建构与政治管制之间的分歧,容肇祖在参与风改会时就提出,风俗改革是从实际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以废除或建立某种风俗,而民俗研究是以客观眼光探问民俗的因果关系(49)容肇祖:《风俗改革与民俗研究》,风俗改革委员会编《风俗改革丛刊》,第36页。,他在此所说的风俗改革与民俗研究的不同也对应着禁演神话戏与考证神话的不同。尽管1920年代的知识与政治都将神话引向迷信的范畴,民俗学学者与南京国民政府也在此基础上相呼应,但两者的差异决定了知识在介入文艺政治的过程中遭遇意义的改写,原本在学科实践中可以保留的神话文本却在现实的风俗整改和戏曲管制中被清除。民俗学与国民党风俗整改的合作热潮将“客观”知识导向权力实践,1929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第二次会议一度提出,在调查研究和整理风俗之外应当“严厉取代欺诈取财的神棍及占卜鬼婆的事情”(50)《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82页。,这更与风改会的态度相似而非民俗的客观探问。1920年代民俗学知识在政治实践中的协商构成了从神话考证“祛魅”到神话查禁的流变背景,也折射出从西方到中国、从知识到政治的沟通、越界和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