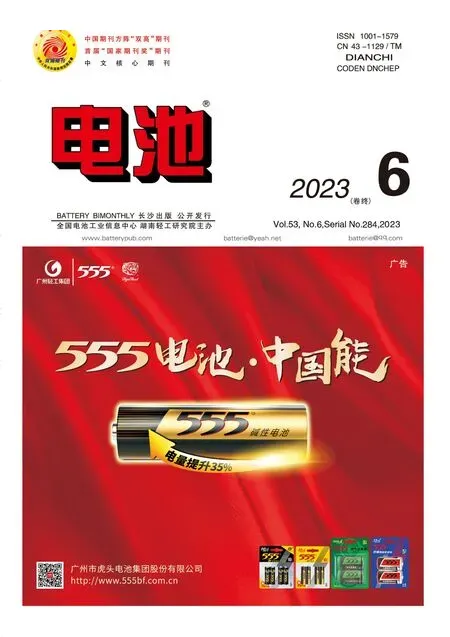动力锂离子电池规范回收利用的效益及对策
刘 宜,尚 闽,2*,谭 刚,刘海鲨
(1. 四川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中心,四川 成都 610031; 2.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锂离子电池生产、使用、回收、处置情况受到广泛关注。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一般使用年限为5~8 a,对容量的要求较高,电池容量衰减至70%~80%时,将不再适用于新能源汽车。 2020-2021 年,我国迎来第一批动力电池“退役”高峰,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及资源化循环利用成为关注重点[1]。
动力锂离子电池以含锂的活性成分为核心材料,主要由外壳、正极、负极、电解液和隔膜等组成。 常用正极材料有镍钴锰酸锂、镍钴铝酸锂、磷酸铁锂或锰酸锂等,负极材料以碳为主,如石墨,也有铜箔、硅碳合金和钛酸锂等[2]。 退役后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仍有较高的回收再利用价值,可进行梯次或再生利用[3]。 如得不到有效回收处理,可能会对土壤、水体乃至人体健康产生危害[4]。 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19 年本)》[2]规定了再生锂、镍、钴的回收率分别不得低于85.0%、98.5%、98.5%。 为促进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循环再生利用,2022 年1 月1 日实施的欧盟新电池法规要求,到2030 年,电池生产中钴、镍、锂的再生材料使用量占比分别不得低于12%、4%、4%[5]。 目前,我国电池行业钴的回收量仅占消费量的20%左右,锂的回收量约占5%[6]。
本文作者对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效益价值进行定量评估,分析我国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 减污降碳综合效益评估
1.1 经济效益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国内累计退役的动力锂离子电池约32×104t,到2025 年我国动力锂离子电池累计退役量预计约78×104t,可从中回收锂1.43×104t、钴1.76×104t、镍4.68×104t 和锰1.76×104t,分别占相应金属需求量的27.7%、55.5%、28.7%和47.9%,充分使用再生金属,可节约大量原矿资源开采和进口[7]。 据统计,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市场规模在2022 年为154 亿元,预计2025 年将达350 亿元,2030 年将超过1 000 亿元[8]。
1.2 减污效益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内含有电路板等废物,正极材料含有大量镍、钴、锰等重金属,电解液含有碳酸二乙酯、碳酸二甲酯等危险化学品,以及六氟磷酸锂等含氟盐类,易分解形成氟化氢、氟化锂、五氟化磷等物质(见表1)。

表1 相关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9]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evant hazardous chemicals[9]
研究表明,4 000 t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可拆解产生1 100 t 重金属和超过200 t 的电解液[11]。
按照2025 年预计退役量78×104t 计算,我国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将拆解产生21.45×104t 重金属和3.90×104t 电解液。 这些有毒物质难以降解,必须规范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利用,才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环境风险。
1.3 降碳效益
从原矿中获取动力锂离子电池所需的高纯度金属盐,提取难度大。 以镍为例,我国储备最多的红土镍矿,镍含量仅为2%~3%[12]。 动力锂离子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并不会消耗锂资源,且能够通过废旧电池回收环节分离出高纯度锂原料,锂再生过程的碳排放量远低于原矿提炼。 P.Nuss 等[13]发现,从矿石原料开采生产1.0 kg 的锂、钴、镍和锰,将分别排放7.1 kg、8.3 kg、6.5 kg 和1.0 kg 的CO2。 李建西等[14]发现,1 GW·h 容量的废旧三元锂离子电池再生产出的锂、钴、镍和锰等材料,原生生产过程中的CO2排放量为2.43×107kg,废旧三元锂离子电池回收、拆解和再生利用产出再生材料过程产生的CO2排放量为0.72×107kg,废旧三元锂离子电池材料的再生利用可减少CO2排放1.71×107kg。
对以上数据分析计算可知,废旧三元锂离子电池材料再生利用过程,CO2的排放量比原生生产过程减少70%。 假设锂、钴、镍和锰等材料的减排比例都是70%,则从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中再生回收1.0 kg 的锂、钴、镍和锰,对应CO2减排量分别为5.0 kg、5.8 kg、4.6 kg 和0.7 kg。 根据预测退役量计算可知,2025 年从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中回收利用锂、钴、镍和锰的CO2减排潜力分别为7.2×104t、10.2×104t、21.5×104t 和1.2×104t,共可减少40.1×104t CO2的排放。
2 回收利用存在的问题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得到广泛关注,发展速度也很快,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2.1 生产处理能力不匹配,区域布局不均衡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市场前景广阔,大量企业纷纷涌入,包括电池用户、电池生产企业、材料企业、储能企业、设备制造商和车企等。 有数据显示[15],截至2023 年2 月底,全国现有与拟新建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处理企业共145 家,规划建设产能987.5×104t,环评批复产能469.2×104t,回收利用产能已超过退役量。 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收集和运输距离长、数量少等因素,规范开展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存在困难。 截至2022 年11 月,工信部公布的88 家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白名单企业)[16],西部地区仅6 家。
西部地区锂矿资源丰富,动力锂离子电池产能发达,目前,四川省动力电池总产能达到186 GW·h,全国六分之一的动力电池产自四川省[17]。 利用处置能力分布不均,导致西部地区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链回收利用环节薄弱,未实现从上游到下游的纵向整合,不利于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化学特性活泼,遇高温、挤压和撞击时,极易失控、着火甚至爆炸,长时间贮存、长距离运输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2.2 利用标准不完善,技术储备不充足
梯次利用是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首选的高效利用方式。目前,动力锂离子电池型号标准不一,一致性较差,导致对退役电池进行检测和分类的难度和成本较高。 电池剩余寿命及一致性评估等技术不成熟,梯次利用的安全性、市场成熟度等因素,困扰着统一标准的制定。
再生利用技术尽管已有一定应用,但存在工艺稳定性不强、多种电池处理技术兼容性不高等问题,有价金属高效提取等关键共性技术和装备有待突破。 如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沉淀所得锂盐纯度难以控制;70%企业采用湿法回收工艺,但仅回收金属锂,未回收磷酸铁(含量95%)等主要成分;三元材料锂离子电池成分复杂,工艺稳定性不足;再生利用须有萃取、蒸发等针对性工艺,流程较长,处理成本较高等。
2.3 规范处置率低,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锂离子电池产业的强势发展,带动锂原料价格大幅上升和剧烈波动。 以碳酸锂为例,2021 年初,电池级产品的价格为5 万元/t,2022 年10 月突破52 万元/t,到2023 年6 月又回落到约15 万/t。 在价格刺激下,“低成本、高竞价”模式将扰乱市场秩序,挤压白名单企业的生存空间。 流入不规范处理渠道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主要采用简单的拆卸处理方式,回收锂盐等有价物质后,其他部分多作为垃圾丢弃。 随意丢弃动力电池,会污染土壤和水源,而焚烧将导致有毒气体逸散。 部分电池包拆解成电池模组后,未按梯次利用标准规范进行检测评估,而是组装成不同规格的“新”电池,用于低速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家庭储能和备用电源等,导致安全隐患突出。 白名单企业却面临回收数量不足、货源供应不上等困境,大量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得不到规范再生利用。
3 对策建议
促进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处理行业规范发展,应加强部门间联动,与“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近零碳示范区等工作有机融合,凝聚合力,共同发力。
3.1 引导行业有序发展,补齐区域处理能力短板
借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建设契机,在西部锂矿资源丰富地区合理布局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可增强区域产业链薄弱环节,打造形成“锂矿-锂盐-锂离子电池-再生锂”的闭环产业链,实现资源高效循环。 深入开展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报废产生量和回收利用能力调研,可进一步优化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处置利用能力布局,避免盲目投资行为。 将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纳入“无废城市”建设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体系,列入重点任务或重点项目清单,形成可落地、可实施、有保障的建设任务。 根据废旧铅酸电池、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等“资源型”固体废物报废、回收、环境风险的共性,整合回收处理渠道,构建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等“一站到达”的综合利用企业模式,培育“城市矿山”再生利用基地。 鼓励就近进行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减少环境风险,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共建环保产业的亮点。
3.2 完善利用标准体系,提高再生利用效率
推动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梯次利用、再生利用等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实现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处理标准化、绿色化、产业化。 按照梯次利用、物理分解、化学处理的梯次推进原则,提高废旧电池再利用、再循环效率。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经检测和性能评估,能够梯次利用的,用于电力系统储能、通信基站备用电源、低速电动车和小型分布式家庭储能等领域;不能梯次利用的,优先通过物理破碎分选的方式,分离收集电极材料、塑料隔膜、电池外壳等组件;难以物理分选的部分,可通过化学处理技术,提取锂、钴、镍和石墨等有价资源,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提高低碳指数。
支持龙头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平台开展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再生利用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加大瓶颈技术攻关、技术集成示范和科技成果转化。 重点研究适用于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的材料再生技术,支持对有价元素高效提取、残余物质无害化处置等关键瓶颈技术攻关。 推广安全环保高效的协同处理新技术,如结合水泥行业生产设施及技术特点,利用低含氧量的水泥窑高温烟气对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焙烧处理,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含氟有机尾气等,降低处理运行成本和设备投资,同时降低环境风险。
3.3 健全回收处理体系,防范环境安全风险
进一步完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处理体系,促进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处理行业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在国家政策层面,出台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快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等,重点推动宁德时代等“链主企业”开展自主回收。 鼓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动力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等设定回收目标,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大型城市群分散建立区域性处置利用设施,或与白名单企业合作。 试点推行电池回收“押金制度”和奖励制度,建立线上回收交易平台,适当补贴通过规范渠道交售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的车主和企业,多效合力促进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流入规范回收处理渠道,减少非法拆解,增加回收资源并消除环境风险。 依托国家、省级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平台,构建电池强制备案信息清单,加强溯源管理,实现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去向可追、节点可控、责任可究。
4 结论
我国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迅速。 由于相关政策措施技术标准配套不及时、不完善等原因,目前,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行业存在生产处理能力不匹配、区域布局不平衡、利用标准不完善、再生技术储备不足、规范处置率低、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利用具有巨大的环境和社会效益,预计到2025 年,可从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中回收锂、钴、镍、锰共9.63×104t,减少CO2排放40.10×104t。 迫切需要完善回收、利用处置、政策保障体系等制度措施,挖掘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利用价值,打造特色“近零碳排放产业”,实现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的目标,并起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作用。
致谢:感谢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调研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