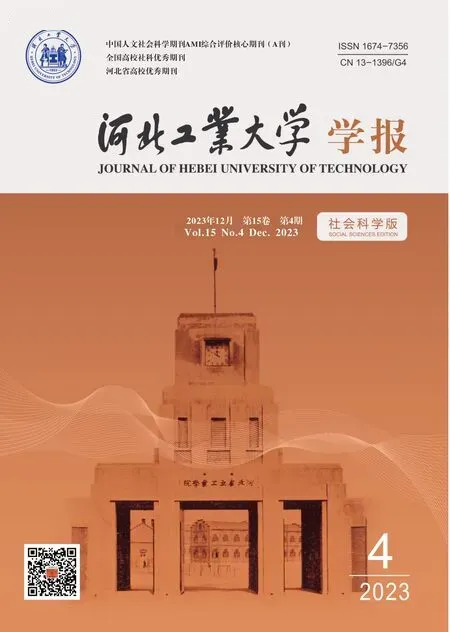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高露洋,梁晓晓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51)
1942 年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深刻改变了解放区文艺的创作生态,座谈会成为划分解放区文艺发展的关键节点。座谈会前的解放区文艺是有待调整、修正的,“不完全的党的文学”[1];座谈会后的解放区文艺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统摄下的文艺实践。这种对解放区文艺的历史本质主义表述无形中遮蔽了各根据地之间因地方风貌、交通阻隔、战争环境、政治需求而形成的文学生态差异。无论是《讲话》前自主的文艺探索,还是其后对《讲话》精神的实践,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实践都明显区别处于“后方”的延安,显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必要予以独特关注,从而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解放区文艺地方路径的价值内涵在于打捞长期被忽视的地方文艺实绩,思考地方经验如何推动整体的发展变化,中央如何影响地方文艺实践,揭示地方与中央、局部与整体的互动关系,通过深描地方文艺进一步阐释解放区文艺的共同性问题,而不是解构解放区文艺的整体性。正如李怡所言,“‘地方路径’的提出则是还原‘地方’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名为‘地方’,实则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可谓是以‘地方’为方法,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2]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亦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思考《讲话》与晋察冀文艺的动态关系,梳理出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探究地方经验如何通达革命中国。
一、晋察冀文艺实践与《讲话》的发生
通常对《讲话》的溯源往往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党的文艺政策方向,而较少关注到各根据地文艺实践对《讲话》产生的影响。李丹以“延安风尚”与“华北立场”区分解放区文艺的地域差别,强调解放区文艺的“华北根性”,认为在1942年以前,一种内容上服从于现时需求、审美上契合华北农民心理,极具群众动员能力的文艺创作在华北已经极为成熟,并且这种地方经验在《讲话》中得到肯定,上升为中央政策[3]。李丹的论述对《讲话》前解放区文艺内部多样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对“延安风尚”与“华北立场”之间关系的界定失之笼统,其论述中也提及延安民众剧团与华北各革命根据地文艺“同声相应”,华北各剧团亦赴延安学习演“大戏”,显然延安与华北之间的文艺趋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此,所谓“华北立场”的生成逻辑,延安与华北之间的互动关系,“华北立场”对《讲话》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分析。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作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成功实践文艺大众化,产生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集中体现了地方文艺创作与中央政策导向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艺大众化是中共文艺政策的重要内容,左联成立之初便强调文艺大众化,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并未取得满意的结果。鲁迅当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4]。1938 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强调,“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5]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存在下去,文艺工作者常常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这就为文艺大众化提供了实践的可能。1939 年,聂荣臻《在边区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的大众化、政治性,“我们的作品要求与边区军民的战斗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今天迫切的问题……我们希望作家深入到群众之间,反映他们的抗日热情,在政治经济动员上边,更要作家们积极参加活动,从文艺方面启发其民主运动的发展,帮助战争动员。”[6]合于战争形势,突出文艺的宣传功能奠定了晋察冀文艺的基调:在创作方法上,作家需要深入群众,反映边区的实际生活;作品内容上,要激发群众抗日的热情;作品主旨上,要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晋察冀文艺在贯彻文艺大众化、强调文艺政治性的方向上同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并与《讲话》精神暗合。
文艺政策在晋察冀的地方实践需要文艺工作者的探索。晋察冀边区位于战场一线,需要文艺宣传来动员群众;只是受制于战争环境与文艺人才的匮乏,边区初期缺少足够的宣传力量。晋察冀根据地开创初期,部队系统的文艺工作便紧迫地开展起来,抗敌剧社、火线剧社先后成立,很多县成立了民众剧团,《抗敌报》 也开辟了文艺副刊《海燕》,但当时很多作品、剧目是从延安传过来的[7]。“边区三省七十二县十万方公里一千两百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出版物。”[8]直到延安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总政前线记者团、东北干部队铁流社等团体先后到达,边区聚集了田间、邵子南、雷烨、魏巍、钱丹辉等文艺工作者,初步构建了一支文艺队伍。可以说,延安为晋察冀文艺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到来充实了晋察冀文艺队伍,同时也使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演“大戏”等问题的论争进一步在晋察冀展开。由于晋察冀处于前线,时刻面临战斗风险,文艺工作者大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战争状态直接决定了晋察冀文艺的核心内容,也构成其区别于延安的地方特色。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实践始终同抗战需求相一致,并未使相关论争干扰到宣传工作。例如,在如何实践“艺术大众化”的问题上,西战团倾向于批判旧戏,创制新的形式。但是,“以‘乡村动员’为首务的晋察冀文艺界对旧形式相当欢迎,主流舆论始终吁求旧戏抗战”,西战团在形式问题上不得不进行妥协[9]。在演“大戏”问题上,沙可夫指出“大戏”不通俗,不能普及,如果总是演“大戏”将会影响边区戏剧大众化的工作,“使戏剧活动限制于狭小的圈子里而脱离了广大群众……我们应以更大力量给戏剧深入群众的工作,给产生大量反映边区斗争与生活的大众化的剧本。”[10]这些内部讨论以及对文艺工作方向的明确判断,避免了争论的扩大和创作的犹疑,有利于文艺工作更好地服务于边区建设。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创作风格,适应晋察冀客观环境,实践艺术大众化方针。这从侧面为后来的文艺工作者下乡提供了合理性证明。
在明确的文艺方针引导下,晋察冀文艺在创作上取得突破。1941 年冀中地区开展“冀中一日”写作运动,记录5 月27 日这一天发生的大事小情,冀中军民无论识字与否广泛参与到运动中。据统计,在这一天亲自动笔的写稿者就达十万人[11]。《冀中一日》全面展示了侵略者的暴行,部队作战,根据地民主建设,群众生活等多个方面。“冀中一日”运动不仅团结教育了群众,还培育了群众的阅读兴趣,带动根据地各学校、机关进行一日征文活动。孙犁称“《冀中一日》 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艺运动”[12]。而像号召春耕的街头诗诗集《粮食》在晋察冀销售达到七千份,“这是证实了街头诗的威力与信仰以及前途。”[13]小说创作方面,《誓死和鬼子干到底》《张二嫂送夫参军》《缝棉衣,送前方!》《张大嫂》等作品书写了动员参军、军民鱼水情等不同主题,全面反映根据地建设。正如孙犁所描述的那样,“战斗的园地培植灌溉了文艺,而文艺便反过来协助耕种了这战斗的园地。”[14]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方针,内容贴近具体政治任务,形式迎合大众审美需求,诱发群众的创作热情,使群众成为文艺的表现主体、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显然区别于同时期延安盛行的演“大戏”、暴露“阴暗面”的文艺风尚。
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实践也引起了中共领导的注意。1940 年,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作报告时总结华北宣传工作经验,“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15]报告肯定了华北宣传工作同广大群众相联系,使党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并指出艺术要面向群众,艺术家要深入生活。可以说在座谈会之前,部分中共领导了解晋察冀文艺宣传实际,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而且也正是贺龙、王震等前线指战员对延安文艺现状的不满[16],促成了座谈会的召开。
在座谈会召开过程中,先后到晋察冀、晋绥工作的欧阳山尊在第一次会议后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加强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毛泽东回信称“你的意见是对的。”第二次会议上,欧阳山尊讲,“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17]欧阳山尊曾回忆:“听周扬同志说,当时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对他说,到底是从前方回来的。”[18]朱德在第三次会议上发言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接触工农兵,多反映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19]。朱德和欧阳山尊的发言显然是以他们对前线文艺的了解为基础的。在座谈会后不久,周扬也反思:“我们是身在延安,而心仍然留在上海的亭子间。这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艺术和政治结合了,而其实并没有结合得好的来由。”“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由于战争环境的直接经历,是已经正确地把握了方向。”[20]前线基于战争环境的文艺创作,更好地实践了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在文艺与政治、文艺大众化、文艺工作者下乡等方面为《讲话》内涵的生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和路径借鉴。
由此可见,在座谈会前“延安—晋察冀”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一方面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为晋察冀文艺实践提供政策上的指导,并输送大量文艺工作者,帮助晋察冀边区组建文艺队伍;另一方面晋察冀的现实情况要求文艺实践与抗战具体任务紧密结合,文艺工作者必须调整创作风格,将文艺与政治结合在一起,适应群众审美需求,完成政治宣传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这种成功的地方文艺经验为《讲话》的合理性提供了现实依据,并最终被吸纳进《讲话》的精神内涵中,上升为具有权威性、全局性的党的文艺政策。
二、《讲话》精神在晋察冀边区的传播
座谈会仅仅是《讲话》精神在地性生成的一部分,《讲话》的开花结果仍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和文艺实践。正如有论者所言,延安文艺体制正式建构的起点可溯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讲话》的发表,《讲话》落实执行最终进入“体制化”还有赖于其间进行“文艺界整风运动”“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和“秧歌剧运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对《讲话》精神的补充和延伸,党务广播《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经验介绍》中对延安文艺经验的肯定、推广,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党印发《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21]。
众所周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目的之一是讨论延安文艺创作中存在的轻视工农兵、脱离实际生活、暴露阴暗面等问题,参与者也多为身处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传播方面,《解放日报》1943 年10 月19 日方刊发《讲话》全文,《讲话》单行本传播范围也有限,而《晋察冀日报》 正式刊发《讲话》则要迟到1944 年1 月30 日。座谈会召开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对《讲话》内容并不了解。座谈会后,由于缺少对《讲话》背景的完整认知和中央明确指示,晋察冀文艺工作者无法把握《讲话》的重要性,只能在文艺界整风运动中通过零散的消息感知文艺政策的转变。
在座谈会前,晋察冀边区文艺界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1942 年5 月,边区文联主任沙可夫指示要重新学习三风文件,“严整三风——在今天就不能单单看成是共产党机关和党员的事,同样也是摆在一切革命团体和工作者面前的最迫切的工作。”[22]随后,边区成立了文化界整风委员会,并要“检查过去强调演‘大戏’以提高艺术,而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偏向”[23]。此次针对演“大戏”的批评要比以往更加激烈。同时《晋察冀日报》也对“延安剧作者决定从事小型创作”“鲁艺文学院开始党风学习”等消息进行报道,了解到延安文艺创作风向的变化。边区文化界文风委员会编印的《整顿文风参考资料》将“近日延安《解放日报》所刊载的各作家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斗争王实味等文章”[24]作为选取内容。 8 月5 日召开的晋察冀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聂荣臻作报告时主要的理论、政策依据仍是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并针对延安《解放日报》上有人主张“超人”的艺术,特别强调“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有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我们的艺术也是如此,有阶级性,有党性……如果离开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哪怕他写得再好,也是没有价值的。”[25]报告针对晋察冀文艺创作实践而发,在主旨精神上与《讲话》 一致,但没有直接提及《讲话》,核心概念表述也有差异。“文艺界整风运动”在延安与晋察冀是同步开展起来的,只是当时晋察冀对《讲话》的具体内容并不了解,侧重于在具体问题上调整工作方向;而不会像延安文艺工作者那样自觉将文艺整风与《讲话》联系在一起,并在“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开启之前便主动要求下乡[26]。
1943 年3 月10 日中央文委、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鼓励文艺工作者参加前方或后方的群众实际斗争。凯丰在会上发言,“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次要根本打破宾主的界限,去的人不以客自居,群众也不以客相待,要直接的长期的老老实实去做工作。”[27]《解放日报》报道此次会议时公开介绍了《讲话》精神,并明确这次“文艺工作者会议”是“实现毛泽东同志在去年文艺界座谈会上所指示之新方向的有决定性之前奏”[28],是对《讲话》精神的实践。《晋察冀日报》3月31 日转载了这篇报道,这也是晋察冀首次了解到《讲话》精神。4 月24 日至27 日,中共北岳区党委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集中批判了艺术至上主义[29]。5 月6 日至10 日召开的边区文联第二届代表大会,沙可夫总结了文联两年来的工作,指出今后的具体任务包括继续整顿三风和实行文艺工作者下乡[30]。随后,边区文协将工农兵通讯员培养,开展街头、集市、庙会的文艺活动,出版通俗读物列为重点工作;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田间、邵子南、林采等分配到县、区工作,孙犁、丁克辛、邓康等下乡承担实际工作,沃渣、钟惦菲、劫夫等分配到宣传出版机关工作[31]。经过文艺整风及下乡运动,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对土地分配、劳资关系、妇女解放等乡村具体问题有了切身的了解,进一步将创作与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为以后创作风格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作为对《讲话》精神的地方实践,《解放日报》特别报道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整风,“晋察冀的经验证明,文艺界脱离群众的倾向即在敌后直接战争环境中亦有发展的可能与清算的必要。按党中央的文艺政策,在华北各地先后均已有所反映,而且联系当地实际,经过深刻的讨论,借以彻底改造工作者,当以晋察冀的经验为最值得重视。”[32]处于“直接战争环境中”的晋察冀文艺整风是对中央文艺政策的地方回应,表明了文艺整风的紧迫性、普遍性与合理性,是建构一体化文艺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察冀文艺整风的示范效应,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文艺整风在各根据地的开展。
经过文艺界整风、文艺工作者下乡等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以《讲话》精神指导文艺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1943 年10 月19 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的《讲话》,11 月7 日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全党的文艺工作者研究和践行《讲话》的指示。1943 年深秋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已经接触到《讲话》的油印本[33]。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晋察冀日报》到1944 年1 月30 日才转载《讲话》全文。2 月15 日,边区文联举行第三次会议明确提出工作任务:“进一步开展文艺界整风运动,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政策的决定,深入有效的检查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和工作,进一步克服艺术至上主义的思想偏向……”[34]至此,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的学习和实践全面铺展开来。
在座谈会之初晋察冀边区对《讲话》的信息所知不多,对《讲话》 的了解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但在“文艺界整风”“文艺工作者下乡”等运动上,晋察冀边区与延安地区基本是同步的,并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被中央作为典型进行宣传。可见在“延安—晋察冀”间存在着“中央指导—地方落实”的权力关系,并且晋察冀作为地方典型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央政策的落地,从而证明了《讲话》“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
三、《讲话》对晋察冀文艺实践的影响
随着《讲话》精神的传播及文艺工作者下乡、批判“艺术至上主义”等活动的展开,尤其是《讲话》 全文的正式刊发和对《讲话》 指导地位的明确,晋察冀文艺工作者自觉学习《讲话》,以《讲话》指导自身的文艺创作,《讲话》开始全面影响晋察冀文艺实践,深刻改变了晋察冀文艺风貌。
首先,《讲话》结束了长期以来边区存在的关于演“大戏”的争论,引发了文艺工作者的自我反思,促进了文艺工作者的理论学习,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信念。晋察冀边区在文艺政策上虽然强调文艺的大众化,批评演“大戏”的倾向,但是没有完全统一思想认识。一些文艺工作者并不反对演“大戏”,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认为使用旧戏的形式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演“大戏”,一方面可以满足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自身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村剧团等小团体的文艺工作者渴望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和表演技巧。小剧团的工作者观摩了“大戏”,不免相形见绌,觉得自己“太土气”,产生“提高”的需求。这些都为演“大戏”思想的萌发提供了土壤。但是大戏不符合广大工农兵群体的需要,难以被他们接受,起不到宣传的效果。当时像群众剧社这样的小文工团,成员大都是当地的农民,初中生很少,演出剧目与抗日工作紧密配合。“征收公粮时演《缴公粮》,扩军时演《送子参军》”,这些戏在艺术上十分粗糙,但因为演员熟悉当地情况、有抗日激情,语言又是群众的语言,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35]。一些文艺工作者在追求艺术品质与宣传效果之间摇摆,而《讲话》则在理论层面和政治层面肯定了小剧团与工农兵结合的创作方向,使文艺工作者能够从理论出发,自觉投入群众戏剧工作中。
例如在深入学习《讲话》后,邵子南曾反思,“从前,我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群众工作,实际上是个人英雄主义,认为群众不沾,要自己教育他……下乡中,我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群众某些方面,了解了劳动……由于立场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创作上也有了新的特点……写的时候,就像有一个老乡在告诉我,我在记录一样。”[36]西北战地服务团贯彻深入群众的理念,将创作与实际问题紧密联系:因为敌人计划在繁峙川抢粮十二万吨,川下群众十分关心粮食,他们就紧急排演粮食斗争的戏教育群众;《活捉王家祥》一剧本来是演到王家祥被活捉便闭幕,但群众强烈要求当场处死王家祥,就又增加了公审的情节。这种紧贴现实斗争,形式灵活多变的戏剧节目更容易被群众接受,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次,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晋察冀边区产生众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丰富了解放区文艺的内容,进一步推动了《讲话》精神在地性的生成。这些经典文艺作品产生于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一类是延安文人根据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内容进行创作。歌剧《白毛女》的生成就源于“延安—晋察冀”的互动。1944 年邵子南从晋察冀边区返回延安并创作关于白毛仙姑传说的叙事诗,而周扬也收到了林漫的短篇小说《白毛女人》。周扬意识到白毛女故事题材的重要性,决定以歌剧的形式进行表现,并否定了邵子南的初稿,起用贺敬之作词[37]。在故事主题上,否定了“神怪故事”或“破除迷信”的观点,明确“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38]流传于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传说经延安文人有意识地改造,明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形成了“新”的白毛女故事。同样,1946 年滞留在张家口的丁玲参加土改工作队,参与怀来、涿鹿一带的土改工作,尤其是在温泉屯的经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产生了“把这个阶段的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的想法[39]。写完初稿后,丁玲又对小说中顾涌、黑妮等形象进行修改,并请周扬、胡乔木、艾思奇等人看稿,努力贴合《讲话》精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方最终成形。此类创作模式以专业作家为创作主体,在《讲话》精神的规训中明确主题导向,创作过程及最终文本也呈现出艺术自由与政治导向相互纠缠、斗争的状态。
另一类则是由长期工作于晋察冀边区的作家创作,经由延安的肯定、宣传,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品。相较于陕甘宁边区以“新秧歌剧”反映生产建设,晋察冀边区则反映前线的战斗生活,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解放区文艺的内容。艾思奇看过新闻报道剧《李殿冰》后指出,“在陕甘宁边区,自从文艺座谈会以来,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依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用秧歌剧以及其他形式,表现了工农兵们以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英雄事业……在前方,对敌斗争是直接的中心任务,因此,在文艺中也必须表现工农兵们在战斗中以及战斗与生产结合中的英雄事业……希望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晋察冀的经验,使新的文艺运动在前方各地大大开展起来。”[40]艾思奇的评价显现出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在文艺创作内容上的不同,肯定了晋察冀文艺在落实《讲话》精神中的地方价值。1944 年5 月西战团从晋察冀边区返回延安演出了反映敌后人民斗争生活的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周扬评价“以它所描写的内容的新鲜和它的艺术力量,以及它的大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程度来说,它在抗战以来产生的剧本中,算是最特殊的,非常优秀的一个。”[41]晋察冀文艺的地方经验得到艾思奇、周扬等人的肯定,并作为有益的“经验”经由《解放日报》宣传到各解放区,无疑会推动《讲话》精神的落地,表明“延安—晋察冀”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再如产生于晋察冀边区的《穷人乐》 由群众和知识分子集体创作,取材真人真事,并由当事人出演,知识分子在舞台设计、戏剧动作等方面提供指导,又贴合农村实际情况;群众参与到戏剧编、排、演的全部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成为群众文艺活动的新范例”[42]。与延安文人根据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内容进行创作不同,这些作者对晋察冀边区的生活情态更加熟稔,在与群众相结合中也更为自觉。正如胡可所言,“晋察冀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的指引下自觉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方面,我们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我们处于敌后的战争环境之中,衣食住行时时处处都离不开群众……《讲话》中所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执行起来也就更为自觉。”[43]
最后,由于“延安—晋察冀”实质上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讲话》成为解放区文艺的核心内涵后,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晋察冀文艺的地方特色,尤其是遮蔽了《讲话》前晋察冀文艺的实践价值。在文艺整风与学习《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边区针对自身的文艺问题进行了过火的自我否定。通过《中共中央文委与中央组织部召开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详情》了解到《讲话》精神后,晋察冀文艺界迅速开展自我批评,指出整个文艺工作发展极不平衡,不全面,不深入;原因就在于“与工农兵结合还不够,文艺工作者对实际情况了解的差”,存在很严重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44]。沙可夫在《晋察冀新文艺运动发展的道路》 中便以《讲话》为界来分析晋察冀文艺,指出1940 年冬至1941 年秋许多文艺工作者不满足于群众文艺运动,争相演“大戏”,出现艺术至上主义,给敌后新文艺事业造成损失;《讲话》后,经过文艺整风,晋察冀文艺创作走向繁荣,证明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45]。实际上,晋察冀边区一直对演“大戏”倾向持谨慎甚或批评的态度,更加鼓励“大众化的剧本”[46];而且1937—1942 年的晋察冀文艺实践也为《讲话》提供了事实支撑。此类自我否定的出现自然包含着中央与地方间权力关系的影响。这种以《讲话》后边区文艺矮化、否定《讲话》前边区文艺的评价方法,进而形成了以《讲话》为核心内涵的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叙述模式。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文艺经验的推广突出延安经验,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晋察冀及其他解放区的地区经验[47];以至于在相关文学史表述中,解放区文艺由《讲话》前的知识分子个性主义表述和《讲话》后的工农兵方向两部分构成,遮蔽了以晋察冀文艺为代表的地方经验与《讲话》生成的互动关系,尤其是《讲话》前晋察冀文艺在践行文艺大众化方面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叙述以《讲话》 为核心内涵,遮蔽了晋察冀地方经验在《讲话》 在地性生成中的作用。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丰富的互动模式,对《讲话》在地性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环境形塑了晋察冀文艺的基本风貌,其践行文艺大众化的地方经验为《讲话》所借鉴、吸收,从而影响了解放区文艺的整体生态;在文艺界整风、文艺工作者下乡等运动中,晋察冀积极落实中央政策,是对《讲话》精神的地方回应,推动了《讲话》精神的落实;《讲话》的指导促进了晋察冀文艺创作的繁荣,也因其权威性遮蔽了《讲话》前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因此,解放区文艺地方路径的提出正在于补充解放区文艺的研究视野,丰富关于解放区文艺整体生态的研究,尤其是“中央—地方”互动关系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