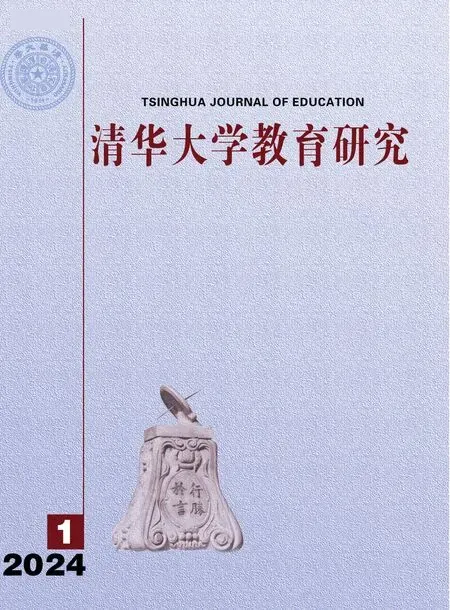德国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跨学科协同发展
王世岳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36)
科学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和高等教育研究(higher education study)在英语世界中拥有各自较为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科研群体。但是在德国,研究者常常以“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Wissenschafts-und Hochschulforschung)并称两者,并亲切地简称它们为Wiho。两个领域的研究者之间惺惺相惜,在2012年出版的德文版《科学社会学手册》中专门开辟“友谊”(Freundschaft)一章讨论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对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1)Georg Krücken,Hochschulforschung.Handbuch Wissenschaftssoziologie(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2012),265.与之相应,最新出版的德文版高等教育研究专著亦不忘将“科学学研究”纳入其中。(2)Otto Hüther and Georg Krücken, Hochschulen-Fragestellungen,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d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Hochschulforschung(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2016),299.最近二十年,德国政府和第三方资助机构以课题委托、共建数据库、建立研究中心等方式,有意识地用“有形的手”整合两个学科的研究力量,制度性地为德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发展服务。特别是2013年成立的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DZHW),已经成为德国最大的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学学的协同发展,反映出德国科学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间的不断融合,体现着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和科学技术强国对于科学和高等教育两者间关系的认识。
文献综述: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
德国的科学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时,德国科学技术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一些科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反思科学研究活动。例如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就比较了戴维(Humphry Davy)、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等六位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并从社会背景、成长周期等角度讨论“伟大科学家”的成长共性。科学活动中的社会性因素,逐渐成为德国研究者关注的对象。(3)W.R.,“Grosse Männer,”Nature 81,(1909):121-122.其后,科学学经历了“科学的科学”“科学理论”等称谓,直到当下“科学学研究”成为通用概念。尽管名称不断变化,但是科学学研究内部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问题意识和演绎逻辑,关注社会与科学工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相比之下,制度化的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相对较短。20世纪60年代,进入扩张阶段的德国高等教育急需满足发展需要的科学规划,众多研究者参与到和高等教育相关的智库研究之中。其后六十年中,德国经历了“68学生运动”、两德统一、欧洲一体化等社会变革,促使德国高等教育不断进行改革。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吸引了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之中。
回应现实问题的需要,使得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一开始就和高等教育实践紧密联系,展现出智库研究的特征。(4)王世岳.“成果丰富”与“理论匮乏”: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悖论[J].高等教育研究,2022,(8):52-60.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通常是以报告、政策评价的方式呈现。与之相比,科学学研究的成果则以传统的专著形式呈现。有研究者认为,两个领域的参与者之间也存在差异(5)Otto Hüther and Georg Krücken, Hochschulen-Fragestellungen,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d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Hochschulforschung(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2016),300.,科学学的研究者更多是接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研究者,而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则接受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训练。(6)Julian Hamann,“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ihr Bildungsdiskurs. Zur Kartierung eines vernachlässigten Gebiets der Wissenschaftssoziologie,”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44, no.3(2015):180-196.
差异之外,两者间的共性愈发凸显,甚至有研究者将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视为“共生”。(7)Susan E.Cozzens, The Research System in Transition(Wiesbaden: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2012),3.在2012年出版的德文版《科学社会学手册》中,“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学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被定性为:“社会学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在内容上高度交汇。抽象而言,两者都关注知识和社会间的联系。具体来说,关注知识的认证,前提条件和结果”(8)Georg Krücken,Hochschulforschung.Handbuch Wissenschaftssoziologie(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2012),265.。共同的研究对象为两者间的相互交流奠定了基础。“高等教育学与科学学这两个学术领域已经通过相互征引、相互吸纳、科研合作、学术互聘等形式开始了比较密切的互动,对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9)沈文钦.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交集与互动——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1):72.国内一些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呼吁加强高等教育学和科学学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10)阎光才.科学的社会运行与大学组织变迁[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1):36-52.实际上,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促进两个学科间的合作,德国就是其中一例。
对于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的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观点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出发,将两个学科视为“两种功能”。这一观点以泰希勒(Ulrich Teichler)为代表,他认为大多数“高等教育研究”集中在教学功能上,而高等教育的研究功能则属于另一个领域——科学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11)Ulrich Teichler,“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0, no.4(2005):447-469.“两种功能”的观点划定了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之间的界限。另一种观点则将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视为“不同机构,同一功能”,克吕肯(Georg Krücken)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由不同的机构进行研究,“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其差别仅仅是在不同机构中进行研究。唯一不同的是,在科学学研究中,大学的地位并不清晰”(12)Georg Krücken, Hochschulforschung. Handbuch Wissenschaftssoziologie(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2012),265-276.。
带着泰希勒和克吕肯对于两个学科关系的不同解释,我们不禁会提出问题,近二十年中德国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协同发展是机构的杂糅拼接,还是功能的有机融合?继而我们还要尝试解释,为何德国的研究者如此重视加强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之间的联系,什么力量推动了两个学科的协同发展,两个学科之间又能从彼此之间学习到什么?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学科间的协同发展,反映着德国科学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愈发亲和的联系。
一、如何协同发展:构建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协同发展,首先来源于德国的决策系统对于科学研究的需求。德国教育和科研部在其资助指南中这样解释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功能:“(德国)科学政策和管理的决策与行动,还大多数是靠前科学(vorwissenschaftlich)的知识完成,极少以科学知识引导。无论是教授和机构的数量,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内容之间的网络,以及理论成果之间的转化都是不足的。”(13)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Über den BMBF-Förderschwerpunkt,”https://www.wihoforschung.de/wihoforschung/de/bmbf-projektfoerderung/ueber-den-bmbf-foerderschwerpunkt/ueber-den-bmbf-foerderschwerpunkt_node.html.为了提高两个学科服务实践的功能,凸显科研成果的应用性,德国政府和第三方资助机构采取课题委托、建立科研机构的方式,有意识地构建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促进两个学科的协同发展。
1.建立研究机构和数据库
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在德国同属于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讨论科学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结构和运行机制。与实践工作紧密联系使德国的科学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一直受到德国政府和第三方资助组织的高度关注。支持一个学科发展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成立独立的实体研究机构。2013年,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正体现了德国政府有意识地加强两个学科的协同发展。
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体是由之前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汉诺威高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和专门从事科学学研究的科研信息和质量保障研究所组成。在合并之前,两个机构已经在其领域中颇具影响力。汉诺威高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从事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数据收集工作。1998年,该公司收集了德国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信息。(14)Hochschul-Informations-System eG, HIS 50 Jahre(Hannover: Hochschul-Informations-System eG,2019),6.专门从事科学学研究的科研信息和质量保障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其主要任务包括“收集德国和国际科研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相关信息;分析科学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关于科研支持和治理结果的优缺点分析;基于研究成果,为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和政策提供建议支持”(15)Wissenschaftsrat, Institutionelle Perspektiven der empirischen Wissenschafts- und Hochschu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Berlin: Wissenschaftsrat,2014),53.。
新研究中心的建立是为了提升两个学科的整体科研水平,增强机构科研能力,提高两个学科解决战略问题的能力,构建学术网络,培养集体性的身份认同,与国际专家一起,建立更为密切的网络。时任科研信息和质量保障研究所主任的霍恩伯斯戴尔(Stefan Hornbostel)在中心成立时说:“具有决定性的,是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学学研究,在‘科学的科学’这一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设计开发研究工具。”(16)Institut für Forschungsinformation und Qualitätssicherung,“Neu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 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 in Berlin und Hannover erhält grünes Licht, Wissenschaftsrat befürwortet Zusammenführung von iFQ und DZHW. Pressemitteilung,”https://www.prmaximus.de/102808/neues-zentrum-fuer-hochschul-und-wissenschaftsforschung-in-berlin-und-hannover-erhaelt-gruenes-licht.pdf.
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总部位于汉诺威,同时在柏林和莱比锡还设有分部。在成立十年后,中心现有研究员六十名,主任为社会学研究者荣包尔-甘斯(Monika Jungbauer-Gans)。中心的研究取向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和科学系统中进行应用导向的经验研究……其研究是由理论引导,与实践相关”(17)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e-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DAS DZHW,”https://www.dzhw.eu/gmbh/index_html.。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中心分为“教育过程和成果”“研究系统和科学动力”“高等教育和科学治理”以及“研究设施和方法”四个分支部门。2019年,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建立了研究数据中心,系统性地采集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相关的量化和质化数据,并向外界开放。
2.科研项目引导
除了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德国现有十余个专门从事“科学学研究”或“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包括卡塞尔高等教育研究国际中心、哈勒-维滕堡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此外,还有一百余家研究机构不定期参与和高等教育相关的研究。(18)Rocio Ramirez et al.,“WiHoTop-Elemente einer Topografie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s-und Hochschulforschung,”die Hochschule 30, no.2(2021):9-80.为了引导研究机构加强学科发展,德国教育和科研部有意识地向两个领域投入资金,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些研究领域,提升两个学科的研究能力。
在科学学领域,2001年到2013年,科研项目“科学、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研究”获得了德国教育和科研部1210万欧元的资助,其中480万欧元用于子项目“决策程序的知识”,730万欧元用于子项目“科学的新型治理”。专门从事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获得了两个子项目中9%和27%的资助份额。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包括“高校教学专业化”在内的五个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获得了6390万欧元资助,专门从事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获得了其中 3%到26%的资助。(19)Wissenschaftsrat, Institutionelle Perspektiven der empirischen Wissenschafts-und Hochschu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Berlin: Wissenschaftsrat,2014),22.无论是科学学领域还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在应用导向的课题研究中,高等教育研究者扮演着更为主动和积极的角色。
科研项目在激发学科发展,赋予研究动力的同时,也会影响两个学科研究的视域。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让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更强的本土意识。2014年,德国科学委员会在评估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学学的学科发展时,讨论了应用导向对两个学科产生的“本土化”影响:“项目委托方更加希望能够解决本土性、地区性和国家的问题,因而经验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以及一部分经验性的科学学研究,都是与自我高度相关,从国际视角而言,被视为‘向内看’(inward looking)”(20)Ibid.,20.。
3.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在建立研究实体,完成科研项目的通识,德国的科学学研究者和高等教育研究者有意识地构建学术共同体。在德国教育和科研部的网站上,收录了80位活跃研究者的简历。其中有47位从事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研究,22位从事与科学学相关的研究,另外还有8位研究者的方向明确横跨两个专业。这代表着兼顾两个学科的研究者共同体已经逐渐形成。学术共同体产生的条件是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身份和相似的个体身份,能够执行的合法实践,相关的标准和规训体系,以及相关的公共交流。(21)Jochen Gläser, Wissen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meinschaften. Die soziale Ordnung der Forschung(Frankfurt: Campus,2006),259.2017年,汉诺威大学专门组织会议,讨论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此次讨论的结果,最终发表在德国社会学学会会刊《社会学》上。(22)Julian Hamann et al.,“Aktuelle Herausforderungen der Wissenschafts-und Hochschulforschung,”Soziologe 47, no.2(2018):187-203.
培养学术工作的后继者是构建学术共同体最为重要的方式。当下德国一些高校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如比勒菲尔德大学的“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汉诺威大学的“科学与社会”,柏林洪堡大学的“科学学研究”硕士项目。此外,一些学校的教育管理专业也涵盖了高等教育和科学学研究的内容。但是这两个学科的博士培养一般都是由第三方资助完成的,大学中没有设置固定的培养项目。究其原因,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在德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就业去向,因而没有出现制度化的博士研究生培养。
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于人的认识活动的自我反思。德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与科学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德国研究者对于高等教育和科学间关系的探索。研究者对于两个学科的理解,蕴含着德国研究者对于两种认识活动的理解。
二、当科研与高等教育相遇: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议题
2020年,哈勒-维滕堡高等教育研究所对德国的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者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涵盖了目标、机构、人员、成果等与两个学科发展相关的问题。(23)Rocio Ramirez et al.,“WiHoTop-Elemente einer Topografie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s-und Hochschulforschung,”die Hochschule 30, no.2(2021):9-80.调查中,530位长期从事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者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内容。笔者通过人工分类的方式,将这些研究内容划分在六个集群之中,包括科学技术研究、科学中的合作与转化、大学教学法、学术职业、高等教育治理以及研究方法。
如果将德国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主题放置在一个坐标之中,坐标的一头是教学,坐标的另一头就是科研。科学的转化工作,例如科研网络(占总受访者的21%,下同)、科学交流(19%)和科学转化(12%)等就体现出了科学工作独有的特征。与之相比,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加关注大学中教与学,诸如大学教学法(21%)、教学评价(15%)、能力建模和测量(14%)以及课程开发(11%)等议题。各具特色并不意味着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相互独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主体、制度和组织高度重合,成为两者共同关注的对象。
1.主体的多元特征

在德国,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组织中。依据德国统计局的估算,2006年德国的科研人员约有10万人,其中有70600名科学家在大学之中工作,应用科学大学占科研人员的3.4%。(24)Marianne Kulicke and Thomas Stahlecker,“The Role of Research in Germa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in The Research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utside the University Sector, eds. Svein Kyvik and Benedetto Lepori(Dordrecht: Springer,2010),167.兼具科研职责和高等教育职责,也赋予了大学教师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科学系统中,他们是“科学家”;在发表领域中,主体是“作者”;在大学中,他们是“教授”;在第三方资助系统中,他们是“合同方”;在科学界之外,他们是“专家”。(25)Julian Hamann et al.,“Aktuelle Herausforderungen der Wissenschafts-und Hochschulforschung,”Soziologe 47, no.2(2018):187-203.学术从业者所具有的不同社会角色,为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性。
将科研纳入高等教育之中,改变了高校中学生的地位。对于学生而言,“听课只是副业,重要的是,人们在一个兴趣相投、年龄相仿的紧密集体中,在一个汇集了致力于提升和传播科学的经验丰富的学者的地方,有意识地为自己和科学生活几年”(26)Wilhelm von Humboldt,“Der Königsberge und der Litauische Schulplan,”in Werke in fünf Bänden(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69),191.。尽管教师和学生在知识储备和能力上处于不同阶段,但他们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具有相同的地位。教授通过让学生参与到自己的科研之中,使得学生学习到科学的原理、方法和技术。而学生也要从教授者参与科研的工作中,了解如何从事科研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让性别问题成为德国研究者特别关注的话题。在学术领域,女性一直以弱势群体的形象出现。重点大学资助政策“卓越战略”特别强调女性在科学系统中的地位,是否塑造了女性友好的成长环境,开始成为评价大学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27)Anita Engels et al., Bestenauswahl und Ungleichheit. Eine soziologische Studie zu Wissenschaftlerinnen und Wissenschaftlern in der Exzellenzinitiative(Frankfurt: Campus,2015).
2.组织与制度设计
科研与高等教育的相互融合不仅体现在主体承担的多重任务,也受到了组织和制度的保障。20世纪70年代,德国大学已经开始提倡“基于科研的教学”,1976年,德国大学校长理事会就曾经这样阐述大学中的教学:“大学中的教学必须基于最新的知识,判断谁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知识”(28)Westdeutsche Rektorenkonferenz, Arbeitsbericht(Bonn: Westdeutsche Rektorenkonferenz,1976),205.。
高等教育经费是以学生人头费的方式发放到各个学校,科研经费则是采取项目制的方式进行申请和发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学几乎无法为大学带来更多的收入,大学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科研工作,这就激发了高校的科研动力。近年来德国最为重要的科研政策是“卓越战略”,科研由过去以课题项目的方式资助个人,开始向资助学校转变。表1展示了德国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德国科学基金会的科研资金有88.9%被投入到大学之中。大学既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获得了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

大学聚集了德国3/4的科研人员,获得了德国科学基金会近90%的科研资助,自然就成为了科学技术治理和高等教育治理的共同对象(22%)。研究者从组织社会学(20%)、管理学(17%)和法学(3%)的视角出发,讨论德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治理形式的改变特别体现在评价实践中(13%),同行评议、基金资助和项目制成为当下科学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特征。
如果我们将经验、理论和方法理解为构成一个学科的支柱,那么德国的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不仅经验对象相互重叠,研究方法还相互通约。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是人类独有的活动,对于两者的研究采用了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2%)。科学计量学(10%),如文献计量、信息计量和网络计量等方法,就被大量运用到政策和管理研究之中。研究方法的融合,意味着两个研究领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其结果可以彼此认可和交流。尽管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重合,研究方法通约,但是不同的研究目的,使得两个学科遵循了不同的学科范式,表现为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偏重。
3.和而不同:学科经典与理论选择
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模式,使得两个学科遵从了不同的发展逻辑,直接体现在两个学科范式之中。如果我们借用科学学研究自身的成果加以解释,那么科学学的学科发展遵循了知识生产导向知识生产“模式I”。与之相比,高等教育研究自产生之日起,就直接进入了“模式II”状态。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完成的,研究主题与现实问题高度相关,质量认定不是以科学作为评价标准,而是要考虑实践应用的情境。也就无怪乎德国科学委员会在对两个学科进行评价的评估报告中将两个学科发展特征评价为:“高等教育研究更多是通过研究对象相融合,与科学学研究相比,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进步较小……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还不充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不是因为研究能力缺乏;而是因为现有研究结构的范围过于狭窄,有关的研究没有制度化。”(29)Wissenschaftsrat, Institutionelle Perspektiven der empirischen Wissenschafts-und Hochschu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Berlin: Wissenschaftsrat,2014),13.
德国科学委员会对于两个学科发展范式不同的判断,可以体现在两个学科的学科经典之上。在2010年的调查中,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在德语的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相关出版物中,什么著作对您的工作最重要?”在481份有效问卷中,共有485本著作被提名,其中有21本著作的提名者超过3人。这些著作可以被理解为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范式,反映了两个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经典方法论。科学学研究在学科内部形成了知识再生产机制,其经典著作既是学科研究成果的积累,也是后续研究的经典“范式”。与之相比,高等教育研究主要为智库性研究,研究成果服务于现实需要,因而缺乏学科“经典”文献。
早期的科学学研究从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讨论“科学方法”如何被社会建构。弗莱克(Ludwik Fleck)于1935年发表的《科学事实的产生和发展》被视为第一本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讨论科学知识生产的著作,研究通过梅毒的发现过程,讨论了社会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的科学》、史迪威(Rudolf Stichweh)的《科学、大学、职业:社会学的分析》等著作都延续了这一视角。
在研究社会如何科学研究的同时,科学如何影响社会成为科学学研究的另一个母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科学家“走出象牙塔”,开始广泛参与大众传媒,向公众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特别是在核能利用、转基因技术运用等议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温佳德(Peter Weingart)在《真理时刻?——科学社会中的政策、经济、媒体与科学》中提出德国科学系统出现了政治化、商业化和媒体化的趋势: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科学不能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但是能增强决策结果的合法性;与之相似的是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要求的实用性影响了科学的自主性;在大众传媒领域,如果大学倾向于吸引公众注意力,就会降低自己的专业性。
宏观视角下科学学研究关注科学系统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微观视角则考察科学系统内部的科学秩序。格莱瑟(Jochen Gläser)的《科学生产共同体:研究的社会规则》提出了“科学生产共同体”的理念,关注“科学共同体中的社会秩序如何产生,如何维持?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相互之间并不充分了解的科学家,能够在一起制造科学知识”(30)Jochen Gläser, Wissen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meinschaften. Die soziale Ordnung der Forschung(Frankfurt: Campus,2006),11.。
与科学学相比,高等教育研究更偏向于实践应用,缺少公认的理论性著作。在21本著作中,高等教育研究著作仅有4本,其中被提名最多的著作是2016年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问题、成就与展望》。另外被提名3次以上的著作包括社会学家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的著作《寂寞与自由:德国大学和德国大学改革的理念与结构》,施耐德(Michael Schneider)的《优质教学:循证指导的助力》和徐特(Otto Hüther)的《从共同体到层级制:联邦州高等教育法中的新公共管理主义》。这就意味着,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还没有像科学学领域那样产生系统的“经典文献”,作为后来研究的范式。
由此可见,偏向应用性,还是偏向学术性可以被理解为两个学科之间最大的差异,“当下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有社会科学理论相配套,这一差异是因为产生历史的差异。这一差异使得两个学科在不同的智识层级上产生和发展”(31)Georg Krücken, Hochschulforschung. Handbuch Wissenschaftssoziologie(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2012),267.。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为学科之间的相互学习具有了可能性。克吕肯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消费理论主要来自专家为高校和政策的决策者服务。科学学则和应用语境保持着清晰的界限。应用语境通常要伴随着较高程度的自我反映和对基础(认知)理论的讨论。”(32)Ibid.,275.对于应用导向的高等教育研究而言,科学学体现出高等教育相关研究中蕴含的巨大理论可能性。与之相对应,高等教育研究则向科学学研究展示了如何服务于现实发展的需要。
2014年,德国科学委员会在对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两个学科进行调研之后,发表了题为《制度化视角下的德国经验性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意见书,建议增强科学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之间的合作:“科学系统,和学校、高等学校、高校外的研究机构、工业企业组成的令人激动的教育和就业系统之间应该建立问题网络和研究需求……因此,在经验性的科学学研究和经验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之间,应该增强合作”(33)Wissenschaftsrat, Institutionelle Perspektiven der empirischen Wissenschafts- und Hochschu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Berlin: Wissenschaftsrat,2014),10.。
三、讨论:科学与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了解德语区的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也是在说明一个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对于科学和高等教育的理解。两个学科的协同发展,反映了德国科学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不断亲和。当我们从高等教育研究的角度再次审视两者的协同发展时,可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独特意义:作为科研组织,大学的独特性在于教学;作为教育组织,大学的独特性在于科研。
在公共政策引导下,德国的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协同发展的特征,以思想的力量促进科学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于中国而言,德国的经验同样具有意义。科学学研究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发展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社会学》《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社会组织》等著作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领域的基本文献。其研究范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德国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协同发展,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和科学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启示。
第一,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和科学学拥有各自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和学术组织,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学研究分布在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和情报学等学科专业之中。伴随着“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为中国顶尖大学的主流政策话语,科研成果已经成为衡量“研究型大学”办学效果最为重要的标准,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组织科研”等理念的提出,更要求作为组织的“高等教育”和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研究”两者之间有机联系。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学和科学学之间也必然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为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作为两者反映的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学学更应该相互协调,相互补益,并形成有效地交流,更好地为“有组织科研”活动提供服务。
第二, 德国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协同发展,反映出德国政府对于学术研究“科学引导”的重视,也体现出政府和第三方资助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学和高等教育研究是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再认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科学活动和高等教育活动的理解,继而提高科学活动和高等教育活动的自觉性。加强科学学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服务于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学产生的“初心”。因此,高等教育学和科学学仍然应该注重自身的学术成果对于现实工作的积极影响。
第三, 科学学与高等教育研究间的亲和,体现出了学术共同体在现代学术系统中的重要功能。想要更好发挥两者的合力,就需要建构科学学-高等教育学的共同体,促进两者之间更多的对话。因而期待国内的高等教育学和科学学领域可以就现实问题,诸如学术评价、研究生培养、学术职业发展等,展开更多对话,以期获得更多研究成果,并最终服务于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寻求学术性和应用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