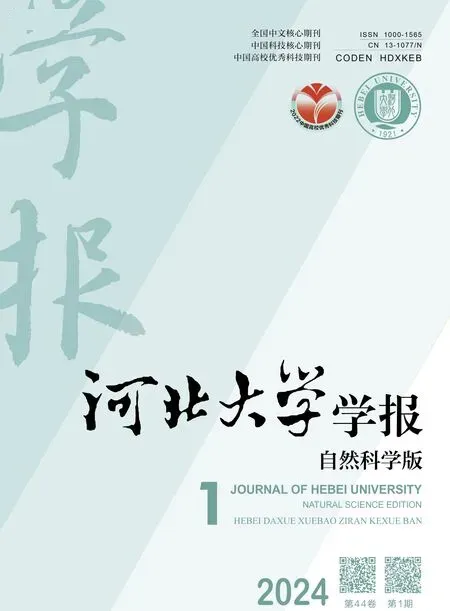姜黄素与抗肿瘤药物联合应用的研究进展
刘文清,杨莎,刘明松,徐志栋
(河北科技大学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河北省药用分子重点实验室,河北 石家庄 050018)
在临床上,单一用药有时不能完全治疗疾病,存在一些缺陷.为此,临床上会采用联合用药的策略达到治疗目的.联合用药是指为达到治疗效果而采用2种或2种以上的药物同时或先后使用的用药策略[1].由于许多疾病涉及多种复杂发病机制,联合用药可以通过多条途径、多个靶点治疗疾病,有明显的疗效优势[2].目前,联合用药方案是感染性疾病、消化性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肿瘤等多个系统的常用治疗模式.采用联合用药的策略,在临床中通常可达到以下治疗效果:其一,对抗耐药性[3],如将链霉素、异烟肼和利福霉素三者联合使用,可有效防止单药产生耐药性,改善治疗效果.其二,增强疗效,如将硫酸镁和硝苯地平联合用药能降低妊娠患者高血压,减小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疗效[4].其三,减轻不良反应,如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和甲硝唑的三联法已成为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的一线疗法[5],可显著降低克拉霉素导致的副作用. 2021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6]提出,不同形式的联合用药方案是抗肿瘤药物研发的重要方向.
联合用药往往会在体外和体内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药物在体外直接配伍使用时,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称为配伍禁忌,其结果可影响药物疗效,应注意避免.药物在体内发生的相互作用是药效学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协同或拮抗作用.1984年美国学者Chou和Talalay[7-8]建立了用于评价药物联合应用的中效原理(Chou-Talalay联合指数法).根据此原理对实验数据用软件绘制指数曲线,得到联合用药的联合指数(combination index,CI),用于评价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当CI<1,两药合用为协同作用;CI=1,两药合用为相加作用;CI>1,两药合用为拮抗作用[9].联合指数法已广泛应用于抗癌药物的联合治疗中.姜黄素(curcumin,CUR)是一种从中药姜黄中提取的天然抗肿瘤活性成分[10-11](图1),已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列为第3代癌化学预防药[12-13].姜黄素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阻断信息传导通路和增强化疗敏感性等[14-15].尽管姜黄素具有良好的抗癌前景,但由于其水溶性差[16]、生物利用度低、半衰期短以及不能通过血脑屏障等缺点,限制了姜黄素在临床中的应用.姜黄素在溶液中是以酮和烯醇的互变异构体形式存在,烯醇式是其快速降解的主要原因,导致姜黄素在生理条件下的化学稳定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其药理活性.为提高姜黄素的治疗效果,科研人员对姜黄素与其他化疗药物联合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文对姜黄素与其他抗肿瘤药物在不同癌症中联合应用进行了综述.

图1 姜黄素的结构Fig.1 Structure of curcumin
1 姜黄素与生物烷化剂抗肿瘤药物的联合应用
顺铂(cisplatin,CDDP)是最早应用于临床的一种生物烷化剂类抗肿瘤药物[17],可抑制肿瘤细胞DNA复制,阻碍细胞的分裂[18].197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顺铂用于临床治疗膀胱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睾丸癌、头颈部癌、恶性淋巴癌和乳腺癌等[19-20].该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有肾、胃肠道毒性,耳毒性及神经毒性,长期使用还会产生耐药性.
姜黄素与顺铂联合使用对肺癌A549细胞增殖生长有抑制效果[21].作用24 h后,姜黄素(5~40 μmol/L)对A549细胞的增殖抑制率为6.5%~27.93%;顺铂(1~4 mg/L)对A549细胞的增殖抑制率为7.12%~26.88%;姜黄素(20 μmol/L)与顺铂(1 mg/L)联用对A549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可达到28.37%.由此可见,姜黄素与顺铂联用对肺癌细胞的增殖抑制率明显高于单药组,并且联用浓度低于单药使用浓度.研究发现:以反相微乳液联合膜分散的方法制备的脂质体作为载体,将姜黄素和顺铂按(物质的量比8∶1)同时递送至病灶部位,其对肝癌HepG2细胞的IC50值为(0.62±0.72) μmol/L,顺铂和姜黄素单独用药时的IC50值分别为(2.56±0.58) μmol/L和(20.33±0.68) μmol/L相比,顺铂和姜黄素联用对肝癌HepG2细胞的作用较强,能够协同增强抗癌疗效,如图2[22].在大鼠卵巢癌模型中,也证实了采用离子凝胶法将姜黄素负载到壳聚糖-三聚磷酸钠中制备的纳米姜黄素与顺铂联用能增加顺铂治疗卵巢癌的敏感活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卵巢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达到协同抗癌效果[23].近年来,乳腺癌大鼠模型的研究数据表明[24],姜黄素可通过减少炎症标志物、增加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的表达以及降低乳腺肿瘤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表达,增强顺铂的抗肿瘤活性,减轻其肾毒性.

图2 在HepG2细胞上处理不同比例的CDDP和CUR后的联合指数与分数影响(FA)曲线Fig.2 Combination index vs. Fraction affected (FA) curve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CDDP and CUR on HepG2 cells
综上所述,姜黄素和顺铂联合用药在细胞及动物模型中均表现出对多种癌细胞的生长增殖有协同抑制效果,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诱导肿瘤细胞死亡的信号通路有关,但具体机制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姜黄素和顺铂联用,能够降低顺铂剂量,减轻顺铂的细胞毒性以及提高药效.同时,新的姜黄素递送系统如共负载脂质体及纳米粒的应用也提高了姜黄素的生物利用度.
2 姜黄素与抗代谢抗肿瘤药物的联合应用
5-氟尿嘧啶(fluorouracil,5-FU)是一种半衰期短的抗代谢抗肿瘤药物[25].5-氟尿嘧啶是通过抑制DNA合成中所需的叶酸、嘌呤、嘧啶及嘧啶核苷途径,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存和复制所必需的代谢途径,导致肿瘤细胞死亡.5-氟尿嘧啶是临床上常用的化疗药物,对肝癌、食管癌、胃癌、肠癌、胰腺癌及乳腺癌疗效较好.但5-氟尿嘧啶在临床应用中有严重的副作用,如胃肠道毒性、神经毒性、心脏毒性及骨髓抑制等[26-27].
已有的研究表明[13]:姜黄素和5-氟尿嘧啶联用对人结肠癌细胞株HT-29生长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较高剂量下,姜黄素和5-氟尿嘧啶二者联合使用可以定量观察到对HT-29细胞的协同抑制效果.此外,姜黄素是一种选择性环氧化酶(COX-2)抑制剂,与5-氟尿嘧啶组合应用可使COX-2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二者联合应用可协同抑制HT-29细胞的增殖及HT-29细胞内COX-2的表达.另外,姜黄素和5-氟尿嘧啶分别作用48 h后,姜黄素对肝癌SMMC-7721细胞和Bel-7402细胞的IC50值为(89.06±11.85) μmol/L和(94.74±4.03) μmol/L;5-氟尿嘧啶对2种细胞的IC50值分别为(21.90±1.54) μmol/L和(38.48±2.27) μmol/L;当两者联用(物质的量比为1∶1)时,其对肝癌SMMC-7721和Bel-7402细胞IC50值分别是(4.95±1.20) μmol/L和(19.30±2.29) μmol/L[28].由此可见,姜黄素和5-氟尿嘧啶联合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药物剂量,增强疗效.除此之外,二者合用干预,还能抑制食管癌细胞EC-9706和EC-109的细胞活性,并增加5-氟尿嘧啶对该类细胞的化学敏感性及杀伤力,如图3[29].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与单独使用5-氟尿嘧啶相比,姜黄素和5-氟尿嘧啶联用还能够显著抑制食管鳞状细胞癌TE-1细胞、TE-8细胞和KY-5细胞的增殖[30].

与0 μmol/L姜黄素组比较,**P<0.01
由此可见,姜黄素与5-氟尿嘧啶联合应用能够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及转移,诱导其凋亡,有协同抗癌作用.同时,姜黄素还能增强5-氟尿嘧啶对不同肿瘤细胞的化学敏感性,并降低癌细胞活性,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蛋白表达及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有关.与此同时,姜黄素和5-氟尿嘧啶联合应用,能减少5-氟尿嘧啶长期使用引起的胃肠道和血液系统的毒副作用及耐药性,为临床使用提供了初步的实验依据,但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3 姜黄素与抗生素抗肿瘤药物的联合应用
阿霉素(doxorubicin)是一种常用的抗肿瘤蒽环类抗生素[31-32].阿霉素是通过嵌入DNA碱基对,干扰转录过程,阻止mRNA的合成,从而杀灭多种肿瘤细胞产生抗癌效果[33].阿霉素作为广谱抗肿瘤药物,临床上主要用于急性白血病、淋巴瘤、乳腺癌、肺癌和肝癌等肿瘤的治疗.阿霉素有较强的副作用,如心脏毒性、性腺毒性和肾毒性[34].
姜黄素(16 μmol/L)与低浓度阿霉素(0.16 μmol/L)合用,对人白血病细胞株HL-60的细胞抑制率可达99.0%.二者联用的作用机制可能是与两药合用增加HL-60细胞对阿霉素的敏感性、下调生存蛋白(survivin)和X-相关凋亡抑制蛋白(XIAP)的表达水平有关,从而促进细胞凋亡[35].相关研究表明,利用薄膜法制备的姜黄素脂质体和阿霉素联合应用对人乳腺癌阿霉素耐药株MCF-7细胞的抑制有协同增效作用(CI<1)(表1)[36].姜黄素脂质体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人乳腺癌对阿霉素的耐药性,其分子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miRNA的表达来影响相关信号通路,进而增强人乳腺癌细胞对阿霉素药物的敏感性.采用亲水性聚合物凝聚法,以高分子纳米材料mPEG-b-P(Glu-co-Phe)为载体,将阿霉素和姜黄素制备成纳米颗粒(L-阿霉素+姜黄素)共同递送至细胞内,与单独用姜黄素和阿霉素相比,L-阿霉素+姜黄素纳米颗粒对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细胞的毒性更大,诱导细胞凋亡率增高,能够提高疗效并具有协同作用.同时,L-阿霉素+姜黄素还具有表观遗传效应,可能是通过下调miR21和miR-199a,上调miR-98和miR-200c,进而有利影响miRNA水平[37].研究发现[38],在小鼠体内共同释放利用高压微流体方法制备的阿霉素/姜黄素脂质纳米颗粒与阿霉素/姜黄素相比,前者IC50值是0.42 μg/mL,后者IC50值为1.26 μg/mL.因此,阿霉素/姜黄素纳米颗粒对抑制肝癌细胞生长增殖的作用更强.

表1 不同组别中阿霉素对MCF-7/ADR的IC50值[36]
综上所述,姜黄素与阿霉素在低剂量下合用,以及新型纳米材料和脂质体所承载的姜黄素和阿霉素联合应用,不仅能够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还能降低阿霉素自身的细胞毒副作用,这可能是通过降低蛋白表达水平及调控miRNA途径来发挥抗肿瘤活性.因此,姜黄素和阿霉素联用的新剂型更加有利于对癌症的治疗,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4 姜黄素与天然抗肿瘤药物的联合应用
紫杉醇(paclitaxel)是从红豆杉科属植物中分离出的一种具有手性的二萜烯类天然抗肿瘤药物[39-40].手性药物是指分子结构中存在手性中心的药物[41],其空间立体结构的差异会对药物的理化性质、药理活性产生影响.人们开始认识到手性在药物中的重要性,可能源于沙利度胺“反应停”事件,其R-异构体有镇静作用,而S-异构体有较强的致畸作用.紫杉醇侧链结构中的手性单元是其发挥药效的重要组成部分.紫杉醇是通过打破微管和微管蛋白二聚体之间的动态平衡,诱导和促进微管蛋白聚合,使其不能形成纺锤体,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而使细胞阻滞于G2/M期,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紫杉醇是临床治疗卵巢癌和乳腺癌的一线药物,对其他实体瘤也有一定疗效[42].
姜黄素(3.9~62.5 μmol/L)单独处理卵巢癌细胞系OC3,可明显抑制OC3细胞的生长,抑制率为9.3%~47.2%[43].将半量血药质量浓度为50 μg/mL的紫杉醇分别与15.625、7.8125、3.9 μmol/L的姜黄素联用,OC3细胞的抑制率分别可达到75.3%、76.3%和78.8%.由此可见,二者联合应用产生的效果明显优于单独使用姜黄素.姜黄素和紫杉醇联用制备为纳米乳,能有效提高药物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进而显著抑制卵巢癌细胞生长,起到延长患者寿命、增强疗效的作用[44].相关研究表明[45],姜黄素35 μmol/L、紫杉醇1 μmol/L以及联合使用作用于人舌鳞癌CAL27细胞48 h,抑制率分别是(51.40±2.98)%、(50.70±2.42)%和(77.30±3.41)%.因此,姜黄素和紫杉醇联用与单一用药相比,联用对CAL27细胞有较强的协同抑制和促进癌细胞凋亡的作用.二者合用的机制可能与下调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和Bcl-2/促凋亡蛋白(Bax)的表达比例,上调Bax和活性半胱天冬酶(caspase-3)的表达有关.在体外细胞实验中[46],通过乳腺癌MDA-MB-231细胞的迁移距离评估,紫杉醇组(69.45±14.63) μm、姜黄素组(50.89±13.22) μm以及姜黄素/紫杉醇联用组(38.10±15.21) μm相比较,联合用药组具有更强的降低乳腺癌MDA-MB-231细胞迁移浸润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蛋白表达的能力.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姜黄素和紫杉醇两药联用还可能是通过降低转录因子NF-κB的表达,促进乳腺癌细胞凋亡,发挥抗肿瘤效果[47].
综上所述,手性药物的对映体在药理活性上往往有所差异.手性药物在今后药学研究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对提高药物的活性和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非常有利.姜黄素和紫杉醇联合用药比单一用药有更加显著的抗癌效果,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MMP-9蛋白、NF-κB表达以及Bcl-2/Bax的表达比例,进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促进其凋亡.姜黄素除具有抗癌效果外,还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保护身体器官,减少紫杉醇的副作用.此外,若采用纳米乳给药,还可以提高姜黄素的口服生物利用度,是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5 姜黄素与新型靶向抗肿瘤药物的联合应用
肿瘤靶向药物是一类通过调控以细胞分子水平为靶点,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造成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但不影响周围正常细胞组织的药物[48].靶向药物具有不良反应小、毒副作用低及疗效显著等特点.
靶向抗肿瘤药物主要包括抗体药物和小分子抑制剂2类.小分子抑制剂是以细胞信号转导通路中关键激酶为靶点的药物,代表药物有索拉非尼(sorafenib)和吉非替尼(gefitinib)等[49].索拉非尼是一种多激酶抑制剂,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肝癌[50].吉非替尼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主要用于治疗局部晚期或非小细胞肺癌[51].相关研究表明[52],针对肝癌细胞株MHCCLM3,姜黄素纳米粒单药组的凋亡率为(17.40±0.18)%,索拉非尼单药组为(15.39±0.14)%,而两药联合组为(22.85±0.25)%,显示出较强的协同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姜黄素纳米粒与索拉非尼联合应用是通过抑制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1/2)磷酸化,下调MMP-9表达,从而发挥抗肿瘤协同作用.采用包埋技术制备的脂质体姜黄素(10 μmol/L)和索拉非尼(0.1 μmol/L)联用作用于人肝癌Huh7细胞,显示出比单药组更强的协同抑制效果,如图4[53].另外,还有研究表明[54],对肝癌HepG-2细胞,姜黄素和索拉非尼两药联用比二者单独使用,诱导晚期细胞凋亡更加显著,并呈现细胞周期G1、G2期阻滞作用,从而明显增强抑制效果.近来,研究人员还发现姜黄素(10 ng/mL)联合吉非替尼(0.1 mol/L)对耐药肺癌NCI-H1975细胞系的增殖能力表现出更显著的协同抑制效果(相对细胞增殖≈0.2%)[55].二者共同治疗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下游通路蛋白磷酸化而实现的.此外,姜黄素也能逆转非小细胞肺癌对吉非替尼的耐药作用,引起癌细胞自噬诱导和凋亡,从而显著降低EGFR活性[56].

NC: 阴性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0.05;与索拉非尼组相比#P<0.05
由此可见,新型抗肿瘤靶向药物具有对靶点针对性更强、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优势,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之一.姜黄素和新型抗肿瘤靶向药物联合应用可能是通过调节蛋白激酶磷酸化以及降低NF-κB表达,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迁移,逆转抗肿瘤药物的耐药性,从而达到协同抗癌作用.尽管姜黄素与新型抗肿瘤药物联用有很大的优势,但靶向药物还面临诸如成本较高、治疗范围有限等问题.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未来姜黄素和新型抗肿瘤药物联用将为临床应用提供更加可行的治疗方案.
因此,姜黄素与生物烷化剂、抗代谢药物、抗生素药物、天然抗肿瘤药物以及新型靶向抗肿瘤药物联合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化疗药物的毒性,对多种肿瘤细胞产生协同抑制作用(表2).

表2 姜黄素与抗肿瘤药物的联合应用总结
6 总结与展望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机构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数据显示,中国癌症新发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均位列全球第一.化疗是目前恶性肿瘤治疗的三大疗法之一.单一化疗药物可能因只能阻断某一信号通路而易产生耐药性,导致治疗效果下降.采用联合用药的方法,将2种或2种以上的抗癌药物联合应用,发挥多种药物杀伤癌细胞的协同作用,减少耐药性,降低毒性,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研究表明,姜黄素和临床抗肿瘤药物联合应用能抑制多种癌细胞的生长增殖、促进其凋亡,具有协同疗效.两者合用的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细胞通路、降低蛋白表达、作用于转录因子、调节细胞增殖及凋亡的相关基因等有关.今后对于姜黄素与抗肿瘤药物联合用药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抗肿瘤药物的联合应用能提高疗效,扩大化疗范围,但由于联合用药也存在如药物之间的配伍禁忌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潜在风险,因此要遵从联合用药的合理性原则.
2)尽管姜黄素的抗肿瘤活性备受科学家的青睐,但其水溶性差,生物利用度低,制约了姜黄素在临床上的应用.除对姜黄素进行化学分子结构修饰和改造外,还可以采用新型的制剂技术手段进行载药,如制备纳米粒子、脂质体、胶束和纳米乳剂等,促进姜黄素更好地在体内释放,进而提高其水溶性和生物利用度.
3)目前有关姜黄素与临床化疗药物联用的大量实验是在体外细胞和动物模型上进行的,尽管研究结果显示其具有良好的临床治疗前景,但实际应用还需更详实更全面的临床数据,以充分证实联合应用的协同机制.
综上所述,对姜黄素与抗肿瘤药物联合用药进行更加系统且全面地深入研究,以期实现其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将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