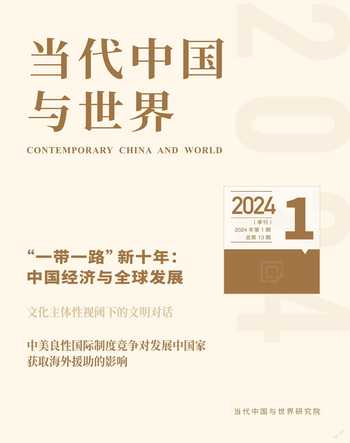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思想根源与传承发展实践
谢清果 韦俊全
【内容提要】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是国之要事。立足于文化传承与发展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了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内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廓清了方向,锚定了基准。若要更好地开展文明传承与传播活动,须对五大突出特性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解读和重返基源式的梳理。本研究回到文明的历史与当下现场中,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深蓄五千多年的典籍文化与文明交流传播事件,进而对五大突出特性的深层内涵与生成逻辑进行考查,从观念与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并通过探讨五千多年的文明实践何以在漫长的文明时空中历久弥新,以回应未来的文明发展之问。
【关键词】五大突出特性;中华文明传播;文明气质;文化传承与发展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泽被天下,泽养万物,是推动着个人生命秩序与价值建构,形塑国家社会治理与情感认同的命脉。文化之发展离不开内外双向传播,亦是在内部传承与外部交流的双向传播活动中,中华文明才得以行至更远,行之更稳。文明传播对内呈现为传承的中华文明自我传播活动,对外则呈现为交流互鉴的文明国际传播、对外传播活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一直是国之要事,古往今来便有“盛世以修文”之举,文化的传承、延续与活化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每个朝代都有实践,从结绳记事、甲骨金文,再到竹帛简牍等,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媒介中承载着、建构着、传承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亦牵动着中华民族之心。从1956 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2013 年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再到2023 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召开,国家一直关注与推进着文化事业的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a 文明发展虽有断代史,但却无法仅仅通过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判读来实现对中华文化全局的了解。因而需要全面、深入地审视中华文明,才能更好地发现自身文明气质与特性,厘清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进行设想与指导。基于对中华文明深入而全面的审视,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式地提炼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也从根本上总结出了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入手处与切入点,给未来的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之实践活动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指引,亦成为未来文明实践与文明研究的重心。同时,这五大突出特性也暗合、对照着中华文明内生之气质。在中华文明传播实践中,“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亦是重要发力点,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最终效果诉求与行为归属。若要更好地贯彻五大突出特性下所廓清的文化发展方向,必然需要充分地对五大突出特性的内涵生成、道理蕴藉、实践理路进行深入了解,这便需要回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历史现场当中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并发掘其内在要义。本文尝试回归到中华典籍之中,分析五大突出特性的内涵生成,以期通过对五大突出特性的深入读解,为未来的文化传承发展活动提供些许可供借鉴之见解。
一、连续性:“慎终如始”的观念与“久久为功”的实践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悠久历史产生的基础,也是建构文化自信的主要根源。《论语·子罕》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与《周易·乾·文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b 均在强调着一种时间演进中的连续,“连续性” 亦是一种整体时空的超越,是时间与空间的延续。但“连续性”作为一种特性,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的形成与建构,既需要观念上的“慎终如始”,还需要传播实践上的“久久为功”。“慎终如始”与“久久为功”深刻地表征着中华文明的时间偏向,两者在知行合一中共同建构并生成“连续性”的中华文明。正是华夏文明传播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实现了中华文化跨越千年的文明传承。c
(一)以“慎终如始”之精神缔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品质
首先,“连续性”的产生来自中华民族所含蓄着的“慎终如始”精神观念,这亦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之始由,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延续之基源。在中华典籍中有着不少关于“慎终如始”的思想阐述。“慎终如始”最完整表述出现在老子《道德经》中。《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说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d 便强调了干事情、做事業要保持一种持续谨慎的精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亦说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也在强调着“连续性” 的重要,强调着要从始至终保持一种奋斗感。而《诗经·大雅·荡》亦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也在强调着能做到“慎终如始”而不断绝实属不易。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慎终如始”的敬畏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连续而不断绝,成为世界几个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而传承至今的文明。
(二)以“久久为功”的实践夯实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气质
“连续性”还需要民族共同体坚守着“久久为功”的实践意识。“久久为功”是“慎终如始”的内在要求与精神延续。如果说“慎终如始”是一种全过程的文明发展目标,是“态度”层面的话语,那么“久久为功”便是方式与手段,是“行为”层面的表述。在中华文明中流传着很多“久久为功”的典故, 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等,在《荀子·劝学》中亦有言“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皆强调通过时间的累积与演变,逐渐成就自我生命、逐渐形成沉积厚实的文明内涵。其中“积”与“不舍” 便内隐着中华文明的时间观念, 而以“久”为大的时间偏向与追求实现了文明自身的延续性与超越性。
二、创新性:“趣时而变”的观念与“日新日进”的实践
创新之精神是流淌在中华文明血液里的, 也同时衍化成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实践。正如《诗经·大雅·文王》所言“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e 中国历朝历代俨然将改革与创新视为国之天命,从封建历史到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盛大的变法与改革,中华民族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社会制度,逐渐走上了实现民主、奔向大同的道路。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在传承、发展中始终秉持与贯彻着求新、求变、求进之精神。任何文明都是群体应对环境的综合性成就,而群体在面对不同变化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时,其所进行的种种行为实践是无法一成不变的。正所谓变则通,因而创新内化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文明实践中。可以说,“创新性”同“连续性”一样,呈现着明显的时间偏向,而“连续性”与“创新性”也有着深刻的互文性: 創新是连续的创新,文明也是在不断创新中得以实现连续发展、传播。而历史上那些失落的文明,正是没能应对各种挑战而最终消亡的。如果说“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与样态的总结,那么“创新性”便是其基底,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够不断地实现文明的迭代优化,创造出文明的流动性与活力,进而实现文明的源远流长。
(一)以“趣时而变”的创新精神保障文明的连续
创新体现在文明的变通智慧上,以变求通的意识与能力是文明不断传承、发展之关键。因而,“创新性”的观念层面便可归结为“趣时而变”,强调不守于一时、因时而变通。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多次出现“趣时而变”有关的表述。《周易·系辞上》有言“日新之谓盛德”f 便将创新喻为德之盛, 足见创新在中国文明深层气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在《周易·系辞下》中有“变则通,通则久”,将创新之“变”与“久”联系在一起, 可见创新在内在理论上便呼应着“连续性”。同时,《周易·系辞下》也提到“变通者,趣时者也”,g 而《周易·随》也有言“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h 里面将“趣时”“随时”称为创新的本质,也是天下之义,更是将创新活动镀上了一层时间偏向。
(二)以“日新日进”的实践锻造创新的精神特性
在传承发展实践上,“趣时而变”便是要在整体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坚持拥抱时代新质, 并细化为“日新日进”的具体行为。在“日新日进”的创新性行为层面上,《礼记·大学》便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i 将创新视为日常之行为要求,要求要做到每日不间断。而在北宋程颢、程颐的《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的第二十五卷中有言“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j 其中便完整表述出了“日新日进”,提出创新不是保持,只要一天不创新便相当于落后。由此可见,“趣时而变”的观念与“日新日进”的实践是相生的。“趣时而变”之理念呼吁着一种细化的文明实践——每日都求新求进,在不断地自我迭代与发展过程中真正实现文明的创新。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创新支撑着新中国实现了一项又一项突破,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上天,从高铁网络到超级计算体系,创新无疑是文明发展的深层动力。在当下的中华文明传承与传播活动中, 更需要坚持思想内容与方式路径的双重创新, 既要立足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生态演变,革新文明的发展理念,做到“趣时而变”“日新日进”;也要积极融入媒介语境与传播技术发展,创新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方式,做到技术与方式均为我所用,亦是“创新性”作为突出特性对当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启示与要求。
三、统一性:“天下为公”的观念与“和合共生”的实践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在文明的发展、传播中呈现为,“天下为公”的观念与“和合共生”的实践。“天下为公”是中国儒家体系的重要思想表述,“天下为公”之“公” 也是当下中国文明气质的最佳注脚——中国所强调的统一并非一种和谐外衣下的霸权重塑, 而是以和平之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与共治。同时,“统一性”在实践进路上可以用“和合共生”来界定。在当下的文明传承发展实践中,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合共生”的实践逻辑,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不同的国际活动中,中国一直坚持着“和合共生”的实践逻辑, 并形成“共生交往”k 的实践理路,以期达成“天下为公”的命运共同体形态。正如习近平 外交思想所阐述“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l
(一)“天下为公”的观念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气质
“天下为公”的观念自古便在中华民族中代代相传。中国历史上对一统的表述异常丰赡。最早可以见于《春秋·公羊传》,其有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m 董仲舒评论《春秋》的大一统时也提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n 颜师古在对《春秋》作注时也提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o 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一统不是一个阶段性的话语,而是一种融结古今,具有超越性的时空观的表述。同时,一统又是一种社会的至高形态,而非狭隘的霸权政治体,是一种各民族共生、共治的天下交往智慧。至《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p“天下为公”便正式提出并成为中国人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它所构建的是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共治、共享,各有所依,各有所用的社会图景。其深刻地影响着之后的政治文明所不断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共同体话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 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所指出的:“支撑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q 同时,“天下为公”的理念亦并不仅仅指向中国,它也承载着中国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求大同的担当,如赵汀阳在《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所说“天下固然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却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特殊概念,它所指向的问题都超越了中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问题。”r
(二)“和合共生”的实践追求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特性
2017 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s 这里面所提的“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便暗合着“和合共生”的“统一性”特性,也最终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和合”与“共生”相接,“和合”是整体的文明气质,“共生”是具体的传承发展实践,基于“和合”的内在气质,文明主体之间可以寻找、发展出共生传承的外显理路,“和合”与“共生”共同建构着共生传承的理论。“和合”的思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文明思想共生传承的结果,里面蕴藉着儒、释、道以及墨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菁华,彰显着独特的中国式气质底蕴、思维方式与传承智慧,而“和合”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追求。在《国语·郑语》中完整地提到“和合”之表述,并称之为“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t 其中的“和合五教”便是在諧和“义、慈、友、恭、孝”五种礼仪教化中使得百姓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其便是通过实践来指向“统一性”。发展到当下,“和合共生”不仅仅是指向政治体的建构,亦深入形塑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和合共生”的传承理路上,它既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同时还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与“和光同尘”的境界观,而由“和合共生”发展而来的这几个观念整合着从国际、到人际、到个体的各种传承发展实践,也以“共生”贯通, 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厚的文明共生之图式。
四、包容性:“美美与共”的观念与“交流互鉴”的实践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注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论语·为政》有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作为中华文明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便阐明了中国不可能走向“攻乎异端”的冲突对立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u 这一思想提炼出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宽阔的格局、积蓄起如此丰富的内涵,便得益于其“包容性”。在中国历史中,民族交流与国家交流时有发生,不管是胡人入唐还是郑和下西洋等,这些历史上的传播交往实践都极大促进了当时国家文明的发展。在中国的文明交往实践中,无论是张骞出西域、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都没有产生文明霸权行径与文明殖民现象,而是以一种“包容性”去进行文明交流,以求形成一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局面。因而, “美美与共”也可以说是“包容性”在文明传承与发展上的观念体现。而将“美美与共”的观念贯彻在实际行动中,便成为“交流互鉴” 的文明实践。“交流互鉴”是“美美与共”观念的实践表征,也是体现与深化中华文化“包容性”特性的有效方式。
(一)以“美美与共”的包容胸襟开拓人类交往的新高度
“美美与共”之所以成为“包容性”的观念体现,源于“包容”与“共”的互照。关于“共”的思想阐述,在中国历代典籍中层出不穷。《说文》中将“共”称为“同也”,《庄子·庚桑楚》有言“共其德也”,“共”从字义上,大致为共享、共有之意。“美美”就是从“包容性”的角度,认为各种文化、各个文明都有其美的形态,承认不同文明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因而,“美美与共”的传播观念阐述着:文明在发展、传播过程中是可以相互共生,甚至是可以彼此互构的。而“美美与共”的“包容性”观念也彰显着中华文明的德性底色,《尚书·君陈》中“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v 便直接将包容与德性进行接轨,包容与德性是共生的一体两面,包容观念也是中华文明德性观念的一个浓缩式展演。同时,这种“包容性”也演化在中华文明不同的层面上,既是整体文明层面“包容性”的德性展现,也是民族个体层面“包容性”的德性修炼,如《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提到的“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以及冯梦龙在《增广智囊补》中所言的“能容小人,方成君子”,均是指向个体层面的“包容性”的修炼,但同时亦是经由个体升华成民族集体的“包容性”德性观念的修炼。可以说,“包容性”既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气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气质。
(二)“交流互鉴”的实践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具体体现
在“美美与共”的观念层面下是具体化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交流互鉴”是指不同文明之间相互鉴别、比照,从而在传播交流、融会贯通中彼此借鉴与学习,以他山之石来实现本体的超越,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与进步,这也体现着文明交流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作为与担当。而“交流互鉴”的实践也在彰显着中国文化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以“包容性”胸怀去实践文明之间的共通往来与共生传播。在中国历史中,中华文明的整体跃迁离不开“交流互鉴”的实践。从佛教的传入、利玛窦的传教,到近代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利器,再深化到如今的“两个结合”,使得中华文明不断展现出更活跃的面貌,也激发了自身的理论自信。这一切,无不是在“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因而“交流互鉴”是实现“美美与共”的“包容性”观念的重要理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w 在“美美与共”的“包容性”价值理念与“交流互鉴”的“包容性”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中华文明才能进一步实现自身更加流长、更加博大的发展,人类文明共同体才能不断展现出更多元、更丰富的样态。
五、和平性:“和衷共济”的观念与“和平发展”的实践
“和平性”作为中华文化五大突出特性的最后一个,占据着重要的压轴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 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x“和”一直以来也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追求与共同气质。《说文解字》中有言“和,相应也”, 《广雅》则称“ 和, 谐也”。在《礼记· 中庸》中则将“和”言之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和”之意大体可界定为居于理之“中”,不偏不倚,周全方正之和谐。可以说, “和”是华夏先贤们在长期文化传承与发展实践中总结的,用以规约与完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结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一种理念,也显化为具体的礼乐制度。同时,“和”的理念与气质,也成为促进中华文明实现天人沟通、民族交流、国家往来、文明互鉴等文明传播活动的基本准则与关键法门。和平承载着全人类共同的企盼,是全人类通约的价值、共通之情感,也是中华文明讲好自身故事、阐发文明气质的重要支点。
(一)“和衷共济”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理想观念
2021 年10 月25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 周年纪念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y 其中将“和衷共济”的理念摆在了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前面,“和衷共济”将人类视为一个共同体组织,在共同体的组织传播中彼此同心同德、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发展、传播活动在“和平性”观念层面的贴切注解。“和衷共济”的文明观念,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也有深厚的思想资源。关于“和衷”,在《尚书·皋陶谟》便提到了“ 同寅协恭和衷哉”,z 意为“同僚之间恭谨事君,并且共襄政事之典”, “衷”表示内心,而“和衷”便可理解为内心之和善、和美之义。而之后“和衷”便有了鲜明的共同体指向,更多意指群体之间的同心, 如在《明史·邹元标传》中便有提到“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ヒ《上大学士书》中也有“与满侍读和衷办事”フ都是指齐心协力之意。“共济”可见于《国语·鲁语下》,其中便提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ヘ同时,《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三年》中也提到“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ホ“济”有舟之意,即共同体内风雨同舟。因而,“和衷共济”便是倡导一种大家发自内心的同心同德,也在组织上形成同舟共济之体。由此可见,“和衷共济”阐扬着“和平性”突出特性的理想观念。
(二)“和平发展”的实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基
“和衷共济”的观念催生出“和平发展” 的文明传播实践。“和平发展”已然成为中国当下的文明发展与传播实践重要模式,它是对中国整体文明文化发展进行深层反思后所提炼出来的道路形态。从文明传承发展来看,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突出特性可理解成由“和衷共济”理念与“和平发展”实践所共同谱就, “和衷共济”的文明理念需要“和平发展”的实践道路来实现。在当下,“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历史不可逆的大潮流,而“和平发展”的理路也是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当下国情全面深刻审视后作出的选择。在历史上,通过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活动,中华文明展现出了只交流传播而不殖民侵入的和平本色,也形成了中国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国际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坚持奉行并不断深入演绎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将自身和平发展的内循环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循环相结合,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均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是如何坚守和平发展的信念,如何为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全人类共同愿景贡献中国方案。而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制度、价值理念、发展成就等汇集而成,涵盖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不同层面中国式智慧的中国之治也渐为世界瞩目,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传播支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マ
结语
在新的文化发展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中华文化的五大突出特性,为未来的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廓清了方向,也锚定了目标。中华文化的五个突出特性并不是简单罗列与断裂存在,正如五大突出特性中的“连续性”所强调的一样,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全景。五大突出特性作为一种凝练式文明话语,是“在一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以语言及媒介使用为特点的社会交际实践”,ミ它们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整体性的探照、梳理与重释,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深入性的精准提炼与整体总结,也是未来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活动的切要命门。要准确而深入地了解五大突出特性,对其思想根源进行探源,就必须先回到文明现场,回到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文化关系及古代的相关文明实践案例中去。对五大突出特性进行重返基源式的梳理,既能更好理解其本质内涵与生成过程,又能以此为切口探照出中华文化的整体思想风貌与精神气质,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要义,以求更好开展文化传承与传播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22&ZD313) 研究成果。
【注释】
a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 2023 年第17 期。
b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0 页。
c 谢清果、王婕:《与时偕行:华夏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 载《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 年第3 期, 第41—47 页。
d【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第166 页。
e 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367 页。
f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71 页。
g 鲁洪生著,赵敏俐总主编:《细读周易》,北京:研究出版社,2017 年,第547 页。
h 陶新华:《四书五经全译》,北京:线装书局,2016 年, 第467 页。
i 李世忠、王毅强、杨德齐编著:《〈大学·中庸〉新论》,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8 页。
j 李敖主编:《周子通书·张载集·二程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438 页。
k 谢清果:《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载《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2 期,第5—13 页;谢清果:《共生交往:全球抗疫實践的人类交往方式审思》,载《教育传媒研究》,2020 年第5 期,第1 页。
l 习近平:《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央视新闻网,2021 年10 月25 日,https://news.cctv.com/2021/10/25/ ARTIcKoYiOdA1fTGhk8pDPHT211025.shtml,访问时间: 2023 年7 月9 日。
m 毛峰:《中国梦的文化诠释:大一统文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年,第24 页。
n 马勇:《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5 年,第87 页。
o 张耀南著,王守常总主编:《中华理想人格》,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 年,第198 页。
p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414 页。
q《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网,2017 年12 月1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01/c_1122045499. htm,访问时间:2023 年7 月1 日。
r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2 页。
s《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讲话》,新華网,2017 年12 月1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01/c_1122045499. htm,访问时间:2023 年7 月1 日。
t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6 页。
u《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网,2023 年6 月 2 日,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6/02/c_ 1129666321.htm,访问时间:2023 年7 月1 日。
v 陈戍国导读,陈戍国校注:《尚书》,长沙:岳麓书社, 2019 年,第176 页。
w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人民网,2019 年3 月26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326/c1001- 30996745.html,访问时间:2023 年7 月10 日。
x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 2023 年第17 期。
y 习近平:《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政府网,2021 年10 月2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5/ content_5644766.htm,访问时间:2023 年7 月9 日。
z 陈戊国点校:《四书五经》(上),湖南:岳麓书社,2014 年,第221 页。
ヒ 李凤梧主编:《中国历代治吏通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292 页。
フ【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325 页。
ヘ【 春秋】左丘明著,刘长江译注:《国语》,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 年,第44 页。
ホ 陈虎总主编,李宝、唐黎明校注:《资治通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94 页。
マ《 为何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这样阐述》,新华 网,2022 年3 月29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 03/29/c_1211626544.htm,访问时间:2023 年7 月9 日。
ミ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26 页。
(截稿:2024 年3 月 责编:季哲忱)
作者简介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
韦俊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