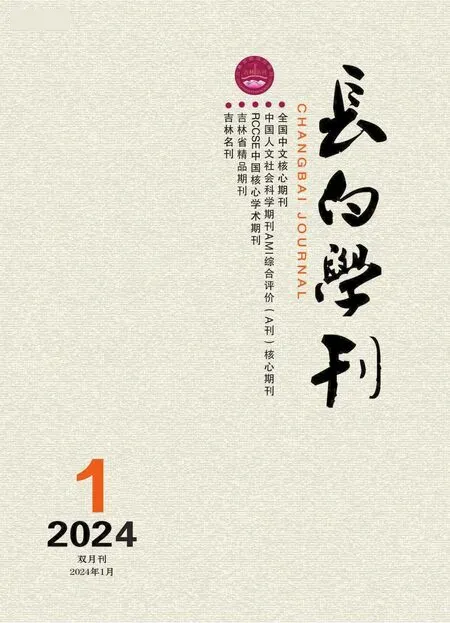清代州县司法中的具结状:辨义、类别与性质借鉴
——以巴县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档案为蓝本
申 巍
(山西警察学院,山西太原 030401)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18—2022 年的统计数据,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90%”[1],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强化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程序价值。与此同时,也有诸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显现。其中,关于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及效力的认识分歧,引发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为此,需要追本溯源,从历史渊源上探究具结书的本义及适用,以期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认罪认罚具结书中的“具结”源于何时,无从考证,但至少宋代已经存在甘结①南宋宋慈《洗冤录·颁将新例·检验法式》:“仍取苦主并听一干人等,连名甘结,依式备细开写当日保结。”。至我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极致的清代,具结已经成为州县司法实践中的常见行为。作为《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一种独特司法制度,具结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甘结文书中的具结状(以下简称“结状”)。依据台湾淡新档案①淡新档案是清朝在台湾的淡水厅、新竹县与台北府城三个行政单位的行政与司法档案,所涵盖时间自乾隆四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776—1895年)。,台湾法律学者戴炎辉从清代台湾的诉讼手续角度讨论了结状[2];日本学者滋贺秀三从诉讼文书类型角度讨论了结状的产生、功能、种类等[2]。笔者主要利用四川巴县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初编档案,并辅以清代江西万载佚名讼师秘本、台湾故宫博物馆藏的军机处档案等珍稀文献,结合学者对南部档案、淡新档案等研究成果,辨析清代法律制度中的“具结”“甘结”“结状”等词义,系统分析讨论结状的类别与性质,以期为正确认识当代认罪认罚具结书提供可能的分析视角。
一、“具结”与“甘结”辨义
古汉语中的“结”本义是“绳索打结”[3]787,上古时代“结绳而治”、后世“易之以书契”[4]389,说明“结”在记录信息方面具有广泛认可、值得信服的证明意义。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记载:“具结”一词中,“具”为动词,准备、备办之意。“具结”就是出具、取具或加具甘结的意思;“甘结”,即指具结时所制作的各种保证文书,“甘”是情甘、情愿、自愿的意思。
清代的具结是基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保证行为,主要有两类情形。一是保证负责。清代司法活动中,时常需要对有关主体的身份、财产、品行、家庭成员、婚姻状况、身体状况、诉讼行为等进行查验核实。因而地方官府、机构、宗族或个人便负有了出具相关保证的义务。比如,清查官员赔赃后的财产状况、检验尸体、验明稽留囚徒是否患病等客观事实,须由官方出具保证文书;而流犯是否婚配、其妻年龄与健康状况、官员是否有匿丧恋职等事实,则需要地方宗族、乡约、邻里配合调查,并予以书面保证。如《大清律例》“流囚家属”之例15.05:“凡律应定拟佥遣之犯,承审官于审讯时,即取本犯确供,将伊妻姓氏年貌,即于招详内声明,如无妻室,即取具邻族甘结,随招申送……倘有捏结情弊,将具结之邻族杖一百,犯妻立即补解。”[5]42即是规定,邻族要出具甘结,以保证发遣罪犯确实没有妻室。又如,“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之例77.06:“令地方官查明僧道中之实在焚修戒法严明者,具结呈报上司。”[5]245意思是,地方官要保证,经查明确实存在严格遵守戒律的僧道人员,然后呈报给上司。除律例规定外,中央档案中亦多见各种甘结,情形多样。有官方的具结行为,比如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河南直隶汝州鲁山县知县沈诗李,具结奏报该县教谕宋益谦,“于乾隆三十一年国子监肄业之时,实与逆犯冯王孙并不认识,亦未见五经简咏书籍”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故机026154号。;也有民间的具结行为,如乾隆四十八年,生员万邦伟、万邦和在限期内清偿其堂兄万邦英因山东任内犯事欠下的赃款后,出具甘结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故机035466号。。地方档案中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具结便具有了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愿意负责的实际意义。二是了结案件。清代州县府衙号称“一人政府”[6]28,自理辖区一切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治安案件。州县官员审理自理案件虽然并无系统的法定程序,却以“息讼止争”为最终旨要。因此,在能够接受的前提下,认可官府的审断结论或接受乡约、亲族、邻里的居中调停,结束诉讼、尽快结案,是具结者的心愿。
受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的文化影响,各种甘结文书应运而生。日本学者内藤乾吉将“甘结”解释为:“凡官府断案即定,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写花押,谓之甘结。”[7]15,16我国学者李鹏年、刘子扬、陈锵仪对“甘结”的解释是:“旧时向官府出具的保证书,称‘甘结’。清制,官府审理案件时,在审讯过程中和审结之后,由犯、证人等出具的保证证言事实无虚,或对判决表示服判的书面保证书,即为甘结。一般民人,遇有事故,向官府出具书面保证书,证实事实真情,表明本人态度,亦称甘结。”[8]41这两种解释共同体现了甘结的保证作用,此类文书在清代地方档案中大量存在。
清代的具结类似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有关当事人签署某种文书的行为,如: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行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的行为。甘结则类似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有关当事人签署的具结文书,如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签署的具结书。古今比较而言,清代的具结与甘结并不仅限于认罪认罚,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二、结状的种类
清代地方州县的甘结种类繁多,根据作用不同,甘结可分“结状”“息状”“领状”“保状”“缴状”等不同种类。其中,“结状”文书的名称与律例中的一致,如《大清律例》“虚出通关朱钞”之例123.07:“如无缺少,一并出具结状。”[5]333结状文书的标志比较明显,文书开端处常有“具结状人某某某……今于太(大老)爷台前”,中间区域有非常明显的“准结”字样,结尾处还常有“某年某月某日具结状人某某”等类似语。滋贺秀三认为“结”有宣誓之意[2],具结状人在结状中或明或暗都传达了承诺所言属实并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思。这类文书多出现在案件的审理或完结阶段,是为了结案件由原告、被告、或其亲族、乡邻、地保等第三人上呈地方州县官府的保证文书。从现存清代州县档案来看,结状并非上呈、准批一次就能奏效,有的案件需要两次以上方可结案。比如在裴彦凤报其妻裴慕氏自缢身死案内,各方当事人虽然在道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都上呈了结状并被准结,承诺不再滋事,但是该案并未当即了结,而是拖到当年十月才最终结案[9]64-67。相对于作用单一的普通结状,实践中还有“缴结状”“领结状”“保结状”“悔结状”等叠加作用的特殊结状。
有清一代,官司一旦以“告”开启、诉至官府后,双方当事人均不得随意撤案或私下自行了结,即不得“冒结”,待到州县衙门在法定期限内对自理案件作出审断或者经民间调解和息后,双方当事人、调解人等必须书面叙写结状,并上呈官府,表示服判、息讼或其他意思。因此,结状一般又可划分为如下五种类型。
(一)服判类结状
服判类结状是因服从判决而甘愿了结案件的保证文书,其中常有“遵依结状”等语。如光绪十年,徽州绩溪民人程德安与程梓陞因“梯下间门”的开关问题引发纠纷,经过知州审理,最后断令:该门平时关闭,只有遇到“喜哀正事”的时候,双方沟通进出事宜,该结状正文有语:“饬令具结完案。身依遵断心平,并身所呈当契一纸,赏给领回。所具甘结是实。”[10]107,108
服判类结状是案件当事人在听从州县官员对案件的审理意见后制作的。由于州县官员对自理的刑、民事案件的处罚均可适用笞、杖、枷号等刑罚处罚方式,因此在部分服判类结状中,常常存在清晰的类似当今认罪认罚的服判内容。比如乾隆三十二年,在巴县禀报拿获江津县恶匪彭全一等盗窃耕牛案内,最初彭全一曾在巴县出具结状,承认自己“无知误招贼犯”,才得到巴县县令批准因而“省释”[11]2。乾隆五十六年,在界石场廖松山控徒弟秦正爵不听教诲逞凶伤人案内,经巴县官府审理,抱告人廖松山于四月初九日出具结状,表示认可官府对徒弟的责罚,并承诺:“日后再不得招留正爵滋事。”被告人秦正爵于四月初十日也出具结状,不仅承认其师所控“属实”,而且接受了官府对自己的“责惩”,并承诺:“日后再不至廖松山家往来滋事。倘稍有滋事,自愿甘罪戾。”[11]226双方当事人在结状中都明确表示服从官府最终的判决结果。道光二年,在重庆府札委巴县审理铜梁县民曾世麟控刘纪等案内,曾世麟、曾世辅于当年七月二十六日出具结状,承认自己“不应越控”,并因此接受官府做出的“掌责”处罚;刘纪出具结状,承认自己“不应率人撵赶世辅转衙”,并因此接受官府做出的“罚钱补修城楼”的惩处[9]28,29。江西万载县民人刘文锦控告童生巫正南偷税丢粮,官府经过一番审理后,发现其中原委复杂,梳理清楚事实后,最终裁断刘文锦交粮钱3675文整、巫正南罚40千文资助东洲书院。最终,巫正南遵从州县判决,上呈了结状文书[12]628-631。这些内容的存在,明确反映了某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罪与罚的认可与案件的完结、出具结状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
与当代司法人员秉持“依法裁判”不同,清代州县官员在审断自理案件时,有较大幅度的自由裁量权[13]。邓建鹏认为,“自清中后期以降,州县官的司法实践偏离体制规定日益明显”[14],只要有助于息讼止争、维持社会秩序,州县官员很多情况下不会僵硬地守文据法,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行政角色决定地方官员缺乏依法裁判的思维;二是受制于司法资源不足与人口剧增带来的审案压力;三是层层向上负责的官僚制度对司法体制的冲击[14]。在这些因素推动下,州县官员对自理案件进行自由裁量,常常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以“薄惩”结案,从宽处罚,当事人大多也认罪服判。
(二)和息类结状
和息类结状是指因服从民间调解而甘愿了结案件的保证文书,常有“遵依允服”“自愿休讼”等语①据日本滋贺秀三先生对台湾淡新档案的研究,“遵依结状”一词也是和息类结状中的常用语。。这类案件先在官府具控,后经民间调解和息具结,当事人往往在具结时会表示不愿再继续打官司,因此在程序上需要调解人向官府出具息状,然后再由当事人双方分别出具结状。这里的息状是指当事人虽然已向官府具控,但之后双方在亲族、乡邻等居间调解情况下,愿意私下和解以息讼,继而由调解人向官府递交的保证文书。此类情形大量存在于清代地方档案中,比如,道光元年,在张殿彦告张明德等痞搕凶伤案内,当事人双方先是分别向官府出具告状、诉状,然后又接受了约邻熊钰宗、郑德胜、李维芳、罗德儒四人的居间调解,在调解人向官府递交息状后,当事人双方在官府以出具结状了结了案件[9]2-20。再如,江西万载某民人先是向官府控告巫开德用假契约骗钱,后经亲友“逐一言明、劝息”,自愿休讼,出具结状[12]735。
结状不仅在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在民事领域也有适用。清初康熙年间,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记载乡民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主动邀请弓手、里书、乡长、邻人等作证,丈量土地、划清边界、出具结状[15]180。民间调解自古有之,发展至明清,调解时以情理为据,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拥护与支持[16]82。调解并不是要分清泾渭、分毫不差,而是让当事人双方相互妥协、和息相安,以取得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正如汪辉祖所言:“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17]318,反映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般价值取向。因此,在这类结状中所体现的是非曲直并不一定会与案件事实完全相符,更多是双方相互妥协的合意体现。即便日后再起诉讼,也极少见到因不守先前的结状而定罪处刑的情况。
(三)担保类结状
担保类结状是指案件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以个人信誉向官方表达自己知悉某状况真实存在的保证文书。这类结状内容丰富,类型多种。有邻佑认可死因的结状,比如,道光四年,在裴彦凤报其妻裴慕氏自缢身死案内,同年三月二十四日团邻李培福等五人向巴县官府出具结状,以证明裴慕氏“畏质自缢身死,并无他故”[9]65。有到场亲属指认伤情的“指伤结状”,据滋贺秀三先生研究,淡新档案中可见到指伤结状[2],该结状添附在诉状中。
在审转复核程序案件中,如果有担保类具结申请,地方州县官员需奏请上级后,依奉准结。比如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山东曹州府郓城县黄德辅提出具结申请,声称其父黄道煚在任内滥用军需银3507 两8钱4分,因旨意要求亲属凑钱代为偿还,故具结保证在三年限期之内照数完赃,不敢有延误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故机035469号。。该县知县张光熙复查后没有发现异常,加具印结后,遵旨议奏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故机035470号。。
(四)检验类结状
所谓检验类结状,是指与检尸、验伤相关的结状,包括仵作检验后出具的结状、亲属提出免检尸体或尸体某些特殊部位的“免检结状”等。如道光四年三月初八日,巴县的裴彦凤向官府提交了申请免检尸首下身的结状[9]51。
(五)收据类结状
所谓收据类结状,是指案件当事人从官府领走涉案钱财、物品或尸体而制作的结状。比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从官府领埋尸身。道光四年三月初八日,经巴县官府批准,裴彦凤得以领埋其妻尸身,出具了结状[9]60。这类结状主要发挥收到某物、立字为据的作用,相当于领状。
从现存清代州县档案来看,结状中包括大量“缴结状”“领结状”“保结状”“悔结状”等特殊结状,似乎是“缴状”“领状”“保状”“悔状”等分别与“结状”两种文书的结合,因而保证作用和执行力度更强。例如,嘉庆十八年,在罗恒发控告谭龙腾等积欠银两案中,经巴县知县审理断定,罗恒发、谭龙腾等当事人之间的债务属于“情债、并非利债”,驳回罗恒发收要九百余两利钱的请求,最终以谭龙腾当堂呈缴欠银三百两、罗恒发当堂领银三百两结案[18]189-200。此案中,“缴结状”“领结状”不仅联合发挥了结状的作用,而且以当堂执行保证了结状的效力。乾隆四十七年,在巴县拿获天主教经书案内,族邻王朝士、熊志元二人为熊同朝、熊同海、刘世位、刘璧等四名人犯作保求结(在此之前,这四人已经被处枷号且限满),上呈保结状,承诺这四人日后再不私藏、阅读天主教经书,巴县知县批示“准开枷、交保严行管束”[11]72。此案中,因有族邻作保才使得人犯出狱、结束囹圄之苦。乾隆三十六年,在仁里七甲白天奇具禀三妹身死不明案内,最初白天奇到县衙告状是为了追查其妹白氏死因,后在提出请求检验尸体的第二天又反悔,于是以出具悔结状、承认七妹白氏因病而亡故而甘结[19]32-41。与普通结状相比,特殊结状是在缴纳或领取钱物、或领取人、或乡邻作保、或表达反悔等同时保证服判或息讼的意愿。
综上,结状一般出现在清代州县自理的民事案件或轻微刑事案件中,根据内容不同主要有服判类、和息类、担保类、检验类和收据类五种,其中前两种主要反映案件当事人对官府判决或民间调解结果的服从、承认,后三种主要反映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涉案事实或结果的保证、鉴定、认可等态度,以及对涉案物品认领等情况的确认。结状形式上,特殊结状比一般结状的执行力与保证力要强烈。从现存清代司法档案来看,结状的种类与意义较之律例规定更为丰富。
三、结状的性质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农民聚村而居,安土重迁,因彼此熟悉而产生信任[20]1。基于这种信任,具结的效力得以实现,因此沈玮玮认为,出具甘结是“由传统社会中注重信用的心理和文化因素演化而来的传统管理方式”[21]。清代地方档案中,巴县档案以诉讼为重,大多诉讼案件以当事人向官府递交结状、了结诉讼而告终,意图彰显矛盾纠纷由此消弭,社会重归和谐,儒家“无讼”理想社会得以在小范围内实现。因此,结状所蕴含的证明性、合意性与保证性是无可置疑的。
(一)突出的证明性
结状首先是一种证明文书。从其内容和种类上分析,它可以对如下事实进行证明。第一,证明官府的审断,或调解后各方一致认可的结论,或阐述的事实真实存在,并以“所具甘结是实”等语发誓。这是结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有在此前提之下,停止诉讼、了结案件才有意义。尤其是涉及刑事案件的结状中常明确包含结状人认罪认罚的内容。第二,证明案件在特定时间、空间和众人的见证下得以了结。服判类和息讼类结状的末尾处,都写清楚了具结时间和具结人姓氏,可以作为息讼止争的证据。第三,证明结状人出具甘结时自愿,并对甘结内容负责。如结状正文的后段,常有“愿甘一体治罪”“倘有滋事,自甘……”等语。
(二)复杂的合意性
结状中常见表达结状人意思自治的表述之语,如“再不滋讼”“中间不虚,结状是实”。但是仔细研读包括禀状、刑房拟传唤人证票稿、诉状、刑房讯问笔录、息状、领状等诸多文书后,会发现结状的合意程度存在不同。
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官府审断清明,当事人因而服判,这种服判类结状的合意性就比较真实饱满。比如,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家住直里一甲的惠先向官府报案,称其姐自缢身死,尸体两条胳膊上明显有伤。作为死者的亲弟弟,自然要搞清楚死因。经巴县知县派人验尸、询问相关证人,最终断定:死者惠氏因家庭琐事与丈夫伍大和发生口角,被伍大和责打后,用麻绳自缢身亡,依照《大清律例》之规定,对伍大和应处以杖八十,最终以折责三十板了结。七月二十七日,惠氏的胞弟惠先在巴县衙门出具结状,邻佑、乡保也出具了结状,均表明承认仵作验尸后的结论确实是“殴后自缢身死,并无别故”,因而息讼[19]8。
但是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凿,或官府听讼与情理不相允协的案件也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所作的结状的合意程度就比较低,清代循吏汪辉祖称这种情形为“两造曲遵”[22]217。一个“曲”字,道尽了至少有一方诉讼当事人的无奈。嘉庆六年,家住巴县孝里十甲的刘正龙到官府报案,说他的妻子刘徐氏被卢祥廷客栈寄住的徐文福拐逃。而卢祥廷辩称,刘正龙靠其妻吃软饭,其妻被拐逃是咎由自取。事实起因如何,一时争议不下、无法查明,幸运的是不久后徐文福被拿获归案,刘徐氏也一同被押回。最终查明徐文福与刘徐氏二人勾搭成奸后逃跑,但是巴县知县并没有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定罪处刑,而是以刘正龙领回其妻管束、徐文福上呈领结状低调处理了事[18]20-42。为何徐文福拐逃妇女的行为不按照律例严格追究?在案件的审理中,刘正龙为了推动官府寻找其妻,囿于清代盛行的“陋规”被收了多少钱财①明清时期衙门胥吏会从诉讼当事人那里索取不少“陋规费”。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修订译本),范忠信,何鹏,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72—78、100—104页。,刘正龙的真实所想究竟为何,有无隐情,都留下了不少疑惑。
和息类结状,因民间调解系统或双方当事人言明已经和解后才向官府上呈结状,这种结状的合意程度也不能一概认为都是真实饱满的,只能说是一种多方妥协的结果。其一,从社会治理角度分析,凡是对簿公堂的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息,官府一般不会干预与追究。吴佩林通过对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研究,曾指出这是州县官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普遍遵循的思路,也就是说,案件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当事人是否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官府并不深究,一般只是采取尊重其选择的态度[23]356。黄晓霞根据淡新档案中的“陈耀宗为板责学生触怒陈阿五而致殴辱”一案,亦指出司法实践中有“被具结和息的可能,既有在背后捏息而完全不自知者,也有在刑讯之下被迫具结者”[24]。其二,从经济角度分析,从最初告禀到最终判决、执行,整个诉讼期间的费用不菲,因此不少诉讼当事人会采取“官司打半截”的方式,即先去衙门告上一状,给对方施加压力,然后在乡邻地保族人等调解说和下再和息、具结销案[25]。这类情形并非偶然,而是明清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诉讼策略。正因为“中间不虚、结状是实”之语背后复杂的合意性,才为之后的反悔、翻案埋下了隐患。
(三)不充分的保证性
《大清律例》“诬告”之例336.10:“词内干证,令与两造同具甘结,审系虚诬,将不言实情之证佐,按律治罪。”[5]1000根据这一规定,令当事人与证人出具甘结,是为了保证其所言为实、所愿为真,而按律治罪的前提则是所言为“虚诬”,即说假话,甚至诬告他人。据此,部分学者认为结状的性质是保证书[26]。所谓“保证”而非“契约”,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必须遵守、违者应受责罚,前者则在一定条件下可反悔且免责。
首先,无论是淡新档案,还是巴县档案,或清代其他地方档案,其中多起案件卷宗里的结状,都有必不可少的誓言,如“再不滋事”“倘后违犯,自甘坐罪”“倘若……甘愿杖毙”等。滋贺秀三在研究淡新档案的基础上,得出一个观点,即结状属于证文书类[2]。笔者认为缺乏法律信仰、仅凭信用支持的誓言难免会被推翻,这也应了戴炎辉对结状的一个认识,即一次遵依结状很难彻底了结一起案件。这样的承诺之语,仅仅具有一种起誓作用,一旦违反,并未见到真的就此实施杖毙之刑的事例,更何况杖毙也不是法定正刑,或者就真的定罪。
其次,两造当事人事后可能违背具结中的承诺。道光年间,时任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曾积极倡导和坚持使用“具结”策略,即要求外国人出具甘结,承诺其来华遵守中国法令,“永不夹带鸦片”。学者李毅明确指出,林则徐所使用的“具结”,其属性是保证书,“具结”策略是在不违背道光皇帝所主张的禁烟这一基本宗旨前提下的一种变通措施。林则徐相信来华外国商人出具保证书之举,既能够贯彻朝廷禁烟的决定,又保证了正常的国际贸易[27]。但是道光皇帝在禁烟派的支持下禁止了“具结”政策,明确指出:“即使此次具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28]243这至少说明,在皇帝的认知中,结状有被推翻的可能。
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结状虽然上呈至“父母官”,但也不是不可反悔。有的反悔是事出有因、无法兑现。乾隆五十八年,渝城陈奇亡故,其妻陈周氏与妾陈谭氏因当房屋的价银三十六两发生争执。经知县审理,妻妾各分一半,双方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遵依具结。不料,陈周氏与其子陈思明不仅不遵守结状内的承诺,而且逼着陈谭氏改嫁,陈谭氏只得于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向县衙控禀。陈谭氏的做法当然违背了之前“再不滋生事端”的具结保证,但是事出有因,在知县的主持下,乾隆五十九年正月二十日,陈思明在县衙缴银十八两,陈谭氏当堂领取,了结了纠纷[19]94-111。
有的反悔是为了取得双方更为满意的结果。嘉庆十五年七月,四川巴县审理了一起鸡奸未遂、反遭被害人敲诈勒索案。起初,知县当堂责惩了企图鸡奸许楮的傅正柏和敲诈勒索者刘应彪,双方当事人均遵依具结。谁知九月初十日,许大顺将儿子许楮从泸州带回,重新发起控案。经过审讯,完全推翻了最初的审断,即傅正柏没有企图鸡奸许楮,刘应彪、许楮等也没有对傅正柏及其父傅良彩敲诈勒索。最终双方当事人再次“遵依具结备案”[18]104-146。知县之所以没有对反悔之事进行深究,估计是顾及最初的审理结果有损许、傅两个家族声誉,作为治理者,更乐于见到有助于长久消弭纠纷、维护正常秩序的解决方案。
但是翻供不实、逆行诬告,往往会遭重惩。雍正八年,安徽怀宁县县民赵荣泽、汪南川和王行所三家因祖坟问题发生纠纷,诉至怀宁县县衙。一开始经中间人赵既宾等人居中调解,平息了纠纷,各出具甘结,送交县衙存档。不料两个月后,赵荣泽又跑到安庆府翻供,控告汪家。安庆府知府徐士林仔细查验卷宗内所列证据后,认定赵荣泽“抗断悖息,刁词翻供”,违背甘结,翻供诬告,最终将其重打二十五板[29]152,153。
官府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主动推翻已经批准的结状,而且不受任何追究。在乾隆三十二年巴县禀报拿获江津县恶匪彭全一等盗窃耕牛案内,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巴县知县已经批准了彭全一、李三多二人上呈的结状,准其具结归家,耕牛原主人冯文学也于当日从巴县县衙当堂领回被盗的耕牛一头,不料接收人犯移送的江津县知县认为彭全一与彭尚礼属于同堂弟兄、常相往来,“恐其结交为匪”,因此请求巴县差拘彭全一并移送。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同年八月巴县又应要求将李三多等人也移送至江津县。后来此二人作为窝留盗窃耕牛重犯彭尚礼的同案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追究[19]2。
综上,清代司法实践中的结状,虽名为“甘结”,但是其中蕴含当事人复杂的合意,无论当事人还是官府,都有可能反悔,尤其是当官府在准结后又主动提起诉讼时,不会因之前的准结行为而被上司追究。因此,综上述情形来看,结状的效力具有不确定性。
四、对规范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借鉴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重要成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切实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理论界对于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等基本问题仍存在不同看法。其中,“具结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保障认罪认罚实质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具结”一词来自古文,具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古老中华法系的基因。研究清代具结行为和具结状,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体现法治人文关怀、追本溯源、传承中华法系法治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清代的具结状与我国目前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无论在适用主体还是适用范围上都存在很大不同,但其性质又存在某些共性,在适用过程中也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
首先,围绕保证的性质,完善和规范认罪认罚具结书。其一,是对具结事项的真实性予以保证,即所谓“中间不虚,结状是实”,否则就要受到责罚。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对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予以保证,但从相关的条文完全可以推出其应当承担具结内容真实性的保证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这说明,在开庭初期阶段,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是审理的重点,自然可以得出被告人应当保证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而不许作虚假具结的结论。为此,需要至少在认罪认罚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对此予以明确。其二,是明确表示“服判”,保证“日后再不滋事”或者“不越控”。在清代,有关人等签署具结状后,是对官府表示自己希望“案结事了”,不再缠讼的一种意思表示和保证,否则也会受到责罚。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如果认可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就应当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法院判决时,也“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具结书的签署,不仅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认可,也意味着被告人未来对人民法院按照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所作判决的认可。建议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相关内容,审慎确定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应尽可能具体、明确,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诉权的前提下,减少反悔和不必要的上诉。
其次,二者都体现出某种合意性,可能出现只追求形式真实,而放弃对案件实质真实追求的有害倾向,这是在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环节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清代具结过程中,官府为了追求“和息”效果,每每偏离律例规定进行裁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司法资源有效配置的具体问题,关涉公、检、法、司等多个部门。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主动协作,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标准,对少数被告人没有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或者量刑建议未被采纳,但符合抗诉条件的,鼓励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尽责。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秉承的客观真实主义应当坚持,不可如清代那样偏离事实真相而片面追求“和息”目的,更不应迷信美国等国家的辩诉交易,只注重纠纷的解决,而罔顾事实真相。为此,在要求嫌疑人签署具结书的过程中,应当同时要求其如实坦白案情,尽量收集能够印证口供的各种证据,而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口供的获取和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
最后,清代具结过程中虽然每每偏离事实真相的做法绝不可取,但其以追求“和息”为目的、对反悔的当事人施行某种处罚以体现具结神圣性的理念有其可取之处。在完善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中,为实现诉讼的效率价值,在保证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应当考虑赋予认罪认罚具结书一定的效力,以约束嫌疑人的反悔行为。比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出于尊重嫌疑人自愿性考虑,固然可以允许其撤回具结书,但在案件移送法院之后,应当对其撤回具结书的行为进行限制。为此,应当在移送起诉前告知嫌疑人最后的撤回机会,并在审判阶段禁止其撤回具结书,彰显具结书的法律效力和认罪认罚制度的权威性,实现认罪认罚制度的效率价值和程序公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