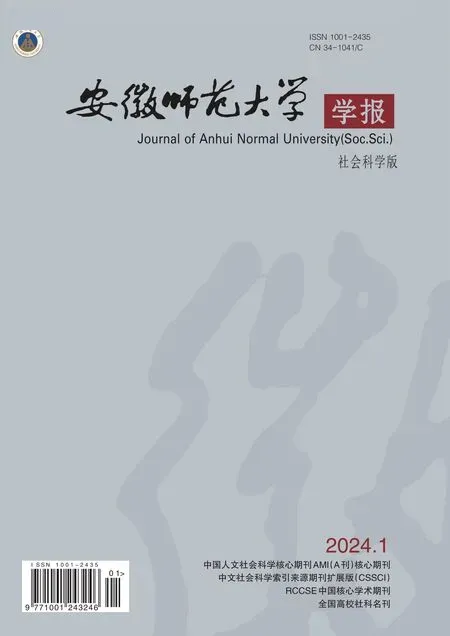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潘炜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戴望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是晚清咸同重要的经学家。早在戴望生活的咸同时代,同代士人就盛赞其经术深湛。如薛福成肯定戴望“才高学博”①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载《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15页。,施补华评价其“学术成就卓卓”②施补华:《戴子高墓表》,载《施补华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135页。,汪士铎称赞其“声名早在公卿之间”③蒋启勋修,汪士铎纂:《同治续纂江宁府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戴望逝世后,刘师培、章太炎、缪荃孙、梁启超、钱穆等学人亦重视其学术思想,给予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以重要的位置。
在戴望的学术思想中,其与乾嘉汉学的关系是不可绕过的话题。咸丰年间,戴望北上苏州问业陈奂、宋翔凤,奠定了其对汉学及其发展趋向理解的基础;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展开训诂考证工作、发挥汉学别派常州公羊学、承续戴震建构的新义理,意欲推进太平天国战后晚清汉学之重振。不过,细察学界围绕此议题展开的探讨,往往更加关注戴望对汉学别派常州公羊学的发扬,①参见郑卜五:《常州公羊学派“经典释义公羊化”学风探源》,载《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郭晓东:《宋翔凤与戴望:以〈公羊〉释〈论语〉》,载《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潘炜旻:《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海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忽视其对戴震等其他汉学义理的继承。②张舜徽先生最早注意到戴望对戴震义理的钦慕,谢弟庭先生则开始对戴望与戴震关系展开初步研究。参见张舜徽:《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3页;谢弟庭:《戴望及其〈论语注〉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57页。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戴望与谭献的交游出发,结合函札、日记、文集、经著等史料,勾勒戴望研习戴震义理的历程、分疏《戴氏注论语》对戴震义理的化用,以期深化学界对戴望学术思想、晚清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等问题的认知。③长期以来,咸同时期的戴震接受状况,没有得到系统梳理。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咸同时期宋学家对戴震的批判。参见乐爱国:《晚清朱子学者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批评——以夏炘、朱一新为中心》,《学术界》2022年第3期。
一、函札辩论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进攻湖州,戴望避难城南东林山。咸丰十一年(1861),戴望久居山中、饥困无所得食,遂依从寡母之命,南下福建投靠至戚。咸丰九年(1859)秋,谭献应徐树铭侍郎之招,随其视学福建。咸丰十一年(1861)2 月,太平军攻占杭州,谭献再次迁徙福州,入福建学使厉研秋幕府,期间历经“乡井再陷,音书断绝,心志瞀乱”④谭献:《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7页。的惨恻。
由于太平天国军进攻江南,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流离中的戴望与谭献得以在厦门偶遇。两位好学胪古者相见后立谈倾倒,遂在荡析流离中同游书肆、商量旧学。同治元年(1862)九月,戴望返乡迎接困居东林山的母亲,并慷慨答应谭献为其访求妻儿讯息。抵达湖州后,戴望发现府城早在五月已经覆灭,其彷徨求母而卒无所遇,⑤施补华:《戴子高墓表》,载《施补华集》,第133-135页。遂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复入福州客游。是年九月,戴望又从福州迁转邵武以就周星诒之聘,谭献赋《戴生行送子高之邵武》依依送别。⑥谭献:《戴生行送子高之邵武》,载《谭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此后,两人虽身处异地,但仍时时书信往返、研讨经术。
同治四年(1865),清军收复江南,谭献、戴望相继离开福建。3月,谭献携妇子从福州登舟返回杭州;7月,戴望亦离开邵武,在俞樾引荐下进入苏州洋炮局。离开福建后,二人仍然保持音书往返与学术往来,如同治六年(1867)、同治七年(1868),戴望曾向谭献描述其转入金陵书局的境况、结交的知友。⑦钱基博整理编纂:《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116-118页。此后,戴望因规劝谭献太过,与谭献产生嫌隙,三年不相通问。⑧赵之谦曾对唐仁寿这样谈到戴望与谭献的交恶:“囊时戴君与谭子甚密,后因谏谭大过,遂决裂。有书已赠谭子,复假归而匿之者(属弟假来而戴君取去),弟于中颇受其难也。”参见赵之谦著,戴家妙编:《上海图书馆藏名家墨迹:赵之谦尺牍》,西泠印社2020年版,第131页。
在戴望与谭献相交的1862至1868年间,二人围绕戴震展开学术论争是重要的事件。《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新收录了戴望的一封信札,展现了戴氏与谭献关于戴震学术最早的论争,现将该手札录示如下:
仲仪足下,昨接凤州札,即作复函,仍从尊处寄去,何如?沪上竟音信杳然,魂神飞越矣。岳氏之事,何以处之?《汉学商兑》二册,奉去秋归陈氏,弟一时不能忍性,涂抹数处,既而悔之。此辈人无足重轻,谬悠邪说何足致辨。东原之学虽出江氏,而未尝师事(但看段氏《年谱》,约略可见),然所作《江氏行状》,固已极口推尊,称为自先师康成后二千年第一人。而王述葊为《江氏墓志》云“吾友戴君东原,盖今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而自述其学盖得之于江先生”云云,可见东原之推本所得如此。而惟其未尝师事,故称之为婺源老儒。而平定张氏及娄、姚、桂辈,群诋之为背师,此何说乎?江氏论礼,则多本朱氏(《礼书纲目》体例本于《仪礼经传通解》);推算,则惑于西人(见钱詹事《潜研堂集·与东原书》);《乡党图考》,体例未善;《群经补谊》,讹谬更多;又其言《易》,宗尚邵氏;又著《近思录集注》一书,核其所得,疵多醇少。以东原较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惟所为《杲溪诗经补注》《毛郑诗考正》,均属未善。《考工记图》甚精,《水经注校正》与全、赵出而合辙,慎密处则又过之。(《水地记》以山川之脉络定郡县之向背,奇作也,惜仅成一卷耳)《声类表》《方言疏证》皆未尽善,而以先觉觉后觉,段、王之于《说文》《广雅》,郝氏之于《尔雅》,体大思精,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后之人日受其惠而不自知,岂非饮流忘原乎?《学礼篇》一卷,取《礼经》大者若干事,各为一篇,考之以详,出之以简,毛公诂诗之法也。使不能文者为之,则连篇累牍,皆注疏体矣。至其《原善》及《孟子绪言》,天人之故,经之大训萃焉。是以段大令、孔检讨、洪舍人、江征君推之于前,焦孝廉宗之于后。汪拔贡亦言国朝儒者顾、阎、梅、胡、惠、江接二千年沉沦之绪,而东原集其大成,为定大儒七人,通人十九,以诏来学,东原与焉。段大令则称其学贯天人;孔检讨则感其崇阐汉学,而不终其志以殁;洪舍人则谓欲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江征君则以能卫东原者为卫道之儒;焦孝廉则谓其疏性道天命之名,如昏得朗。诸君子皆非漫然无学术者,而交口称之,且再三称之。足下何见乃欲置之第二流,而以慎修为过之。江戴相等,犹之可也;乃使之一居上上,一居上中,岂以其名高而有意抑之乎?其意见可谓重矣。
足下论诗不喜少陵,论文不喜退之,此自有所得,不得附和世俗之言,以足下为非,而其论学遂诋及孟子。夫孟子之言常若有可疑者,而其大端则皆本孔氏之微言,未尝少有差失。故其言性、言心、言仁、言天道,与孔子若合符节,而荀、杨、韩氏偏与立异,此儒之未闻乎道者也。宋之儒者,阳宗孟子而阴取荀、扬、韩氏以助之攻,且杂糅西域胡人之语,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举万事万物以内之恍惚无象皆归于一理,而道始大贸乱矣,而其流弊遂以心之意见为理,以理杀人,无异于申韩之以法杀人。自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言之深切著明。其忧如此,其大者乎。故《原善》《疏证》之作,虽谓之功在万世可也。
足下不信孟氏,遂致不喜东原之书。盖即其书而反覆求之,周详思之,平心易气,矜庄以莅之,而毋以私见参焉,则所谓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达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将旦莫遇之矣。泾包世臣尝言,东原虽不见用,然由其言而知其用之之无弊也,其亦以是书信之乎。况乎二百年以来,其能身通六艺、兼综群言以能折中于至圣者,曾不数人。若东原者,可谓得其全矣,世无孔子,当亦游、夏者流。足下轶才,绝辔而驰,弟所深畏。敢更少抑贤知之过,以受刍荛之言,使弟得随时而取衷焉则幸甚。大著论议杂文,褒为一编,付我手钞可乎。苟能以汪、龚之文,加以习斋、东原之学,则它日吾党之斗杓宜专归足下矣。弟望手启。六月六日①钱基博整理编纂:《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上》,第113-115页。
这封函札的落款时间为六月六日,可以断为是同治二年(1863)。是年,谭献在日记中记录了戴望对戴震学术的推崇:“子高前日有一书与予,争东原为本朝儒者第一。予不答。此事非一人私言,予故品东原为第二流之高者。”②谭献:《谭献日记》,第7-8页。谭献日记所言之书札,很可能即是这一封,因书函与日记内容相贴合。细察戴望的这封函牍,其重要性有如下数端。
一、再现了戴望与谭献关于戴震学术的第一次论辩。透过书信可知,戴望与谭献对戴震与江永关系、戴震义理、戴震学术地位的判断存在分歧:戴望反对谭献把江永推为“上上”而把戴震贬为“上中”,申言戴震与江永虽有学术渊源,但不仅未尝师事江永且学殖远迈江永;戴望批评谭献轻视戴震的义理,盛赞戴震义理不仅还原了三代圣人之道,而且不会产生政治实践的流弊;戴望也拒绝谭献将戴震仅仅视作二流学者,推举其为清朝二百年来集大成的学者。
二、见证了戴望对戴震学术的深入研究。透过书函可知,戴望曾在1863年对戴震学术展开系统研读,研习范围包括《考工记图》《水经注校正》等考据著述,亦涉及《原善》《孟子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义理著述。①戴望还阅读、抄写了戴震晚年的著作《中庸补注》。《戴震全书》中的《中庸补注》,即是以戴望长留阁的抄本为底本:“《中庸补注》乃戴震未竟之作,只注至‘所以怀诸侯也’为止。此书原稿为戴震嗣子中孚所藏,后邮段玉裁。此后至清道光年间,德清戴氏长留阁又据稿本传抄(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清末,上海《国粹学报》又据戴望(子高)抄本正式刊行。邓实在抄本题下批曰:‘此德清戴子高先生抄本,内有校记及圈识,皆先生手迹也。’中缝有‘德清戴氏长留阁正本’字样。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戴望长留阁抄本为底本,参校《安徽丛书》本。”戴震著,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第2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49页。通过这番研读,戴望颇为服膺戴震的学问,既盛赞戴震的训诂考据之作,更称颂戴震的义理之学。戴望对戴震的双重嘉许表明,其认为乾嘉汉学不仅在训诂考据且在经之大训上功绩卓著;经学的目标并非是训诂考据而是义理建构。
三、展现了戴望反理学思想演进的轨迹。早在道咸时期,戴望及周遭士人即对理学颇有微辞。②参见潘炜旻:《道咸时期的湖州学术——戴望早期学术、交游之钩沉》,《区域史研究》(总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太平天国战后,戴望对宋学愈加不满,并在入闽前夕写作的诗作中,最早表达了对理学的批判,主张破除理学对儒学的垄断性阐释,复原出真正的圣人之道。③戴望:《将游闽中别费生襄四十二韵》,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谪麟堂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从戴望思想演进的脉络出发,其在1863年6月对戴震的考据与义理展开如此深入的研习,无疑会加剧其对宋学的抵排。而后,1863年12月,谭献记载戴望曾“寄示所著书曰《微言》者”,“大辨宋人为伪儒为非圣”,④谭献:《谭献日记》,第197页。表明戴氏已开始整合各家之说突破宋学义理、重构三代圣人之道。戴震的义理,日后成为戴望这一构想中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一点,透过戴望手札“苟能以汪、龚之文,加以习斋、东原之学”的说法,可见端倪。
但是,谭献收到书函后却并不认同戴望的判断,因此在同治二年(1863)六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叙道:“东原虽博大,不得为第一流,而子高顾笃信其《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附和前哲,必推为集大成之贤。其与升朱熹为十哲之见相去几何?”⑤谭献:《谭献日记》,第193页。可见,谭献反对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推重,诟病戴望过分抬升戴震的学术史地位。不过,虽然谭献并不认可戴望的识解,却始终记挂这场争论,因此决定于同治三年(1864)放下偏见再次研习戴震的义理:
五月初六日阅戴东原《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子高服膺最笃,予徇其意,乃一究心。东原所学,校之俗儒信有原本,而持之有故,尚未足以推见天人之事。终不能附和耳。⑥谭献:《谭献日记》,第199页。
复思夙昔疏于东原,未尝卒业。其书子高盛推之,往复三四矣。发子高书箧,有《戴集》,因先检段若膺《年谱》阅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辨正宋明鄙说,信有催陷之力,然为空言一也。剖析穷于豪芒,语多则不能无得失。其《说命》《说才》,予亦未遽谓然。杂文朴僿,不免腐木湿鼓,非庄、汪诸家比。⑦谭献:《谭献日记》,第21页。
可惜这次研读仍然没有改变谭献对戴震义理的失望,其断言戴震虽然能对理学有所针砭,然“未足以推见天人之事”。翻检《复堂日记》,谭献对戴震的失望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如十月朔,谭献再次记录道:“暇更当撰《国朝经师别传》以正其失,在阮伯元、江藩之后出者皆在焉。憾此事无可商定,中白、子高皆奉戴震为圭臬者,与予异趣,其他更无论矣。”不过,虽然谭献不赞同戴望的学术见解,但在《师儒表》中却有意识地将戴望视为戴震的继承人:
经师六(专经著撰别见)
江慎修先生一传:戴东原氏再传:段茂堂氏金檠之【斋】氏三传:陈硕父氏四传:戴望子高同学:胡竹村氏胡墨庄氏别出:凌仲子氏程让堂氏①谭献:《谭献日记》,第29页。
二、经训化用
出于对戴震义理的高度认同,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广泛化用了戴震的义理。下文尝试比读《孟子字义疏证》《戴氏注论语》《论语集注》,对此做出分疏。
(一)天理观的破除
《孟子字义疏证》列理(15条)、天道(4条)、性(9条)、才(3条)、道(4条)、仁义礼智(2条)、诚(2条)、权(5条)共8个条目,本节选取该书诠释“理”的内容进行讨论。
其一,《戴氏注论语》继承《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天理观的批判。诸多学者指出,天理是程朱理学的最高范畴。②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2页。但是,《孟子字义疏证》却对程朱“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天理概念进行了批判。首先,戴震运用语义学方法重释理之概念:“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③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页。称条理、分理是“理”最重要的含义,指客观事物固有之规律。其次,戴震批评程朱理学的天理观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将“理”视为在人心之物,往往使得“理”度越于事情、人伦之外;二是将“理”视为具于心之物,往往易使个体断事时流于心之意见,导致以理杀人。④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载《戴震集》,第175页。针对程朱的天理观,戴震提出理义观,申言个体当在人己关系与日用饮食中探索理义的存在,运用自我心知,条分缕析事情以求取人情、物理之通则。⑤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第3、6、8、15条等,载《戴震集》,第267页。
戴望颇为欣赏戴震对程朱天理观的批评,如其曾寄函谭献,不仅推许戴震对宋儒天理观的否定,而且赞许戴震对宋儒天理说流弊——“以心之意见为理,以理杀人”的观察。⑥钱基博整理编纂:《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上》,第113-115页。与此同时,戴望将戴震对宋儒的批评转化到《戴氏注论语》中。比如,与《论语集注》详言理、天理不同,《戴氏注论语》绝口不提天理、绝少言理;与《论语集注》纵谈“天理”之“理”不同,《戴氏注论语》使用的“理”接近“人情事理”意涵。⑦如戴望阐释“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曰:“《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此“理”意指“事理”。再如戴望阐释“何以报德”(《宪问》)曰:“施行得理为德,反德为怨”;阐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曰:“我无之求诸人,与我有之非诸人,皆人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名为义”,此“理”意指“人情事理”。戴望:《戴氏注论语》,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96、206页。
其二,《戴氏注论语》继承《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理—气”天道结构的批判。诸多学者指出,理气论是程朱理学的重心,⑧钱穆:《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6-45页。关涉其对天道、人性的理解。但是,《孟子字义疏证》亦对宋儒“理—气”二元的天道结构作了批判。首先,戴震批评程朱“太极/形而上/理—阴阳/形而下/气”二本的天道结构,混入了佛家“神识—形体”二本的观念,与六经、孔孟之说貌合神离。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第2、3、4条,载《戴震集》,第266-269页。其次,戴震提出新的天道观,认为天道的实体不是理、气,而是阴阳五行。而这样气化的天道才是人道和人性的本原,所谓“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①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第1条,载《戴震集》,第287页。可见,通过重构天道,戴震否定了宋儒划分宇宙界为理、气,歧人性为理之性、气质之性的构想,认为秉承气化天道生成的人性是一元的。
《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宋儒天道结构的批判。比如,戴望阐释“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曰:“天地合和其气,故生阴阳,陶化万物”②戴望:《戴氏注论语》,第68页。,摒弃了《论语集注》以理气为主体的天道构架,坚持气化论意义上的天道观,将阴阳五行作为天道的实体。再如,戴望阐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曰:“性者,人所分于阴阳五行,有仁、义、礼、知之等”,③戴望:《戴氏注论语》,第71页。强调个体秉受阴阳五行之气获得了人性;而且这种人性是一元的,气质之性之外别无理之性。可见,戴望对天道、天道—人性结构的认知与戴震颇有渊源。
其三,《戴氏注论语》继承《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理—欲”对立结构的批判。学者曾指出,天理人欲之辨是程朱理学的重心。④钱穆:《朱子学提纲》,第92-97页。但是,《孟子字义疏证》却批驳了宋儒构建的天理、人欲对立框架。首先,戴震反对宋儒以天理为正、以欲求为邪,把理欲关系视为正邪对立关系。如戴震指出,情欲根植于人之血气,是人性中的自然构成部分,因此,个体不能没有情欲,但需节制使之无过情。⑤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第10、11、15条等,载《戴震集》,第275-276页。而理与欲形成的也并非是正邪对立关系,而是互相依存关系⑥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第166页。——理就存在于饮食日用之中。因此,个体求索理义,不能于人性情欲之外求之,不能强制压抑自我情欲。其次,戴震批评宋儒理欲之辨思想引发诸多社会流弊。如在戴震看来,古代圣人推行仁政,往往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充分体恤民情民隐。但是,宋儒却推崇与圣人相悖的灭欲观,遂使治理者往往漠然于天下人之生道穷蹙。⑦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第273-275页。
《戴氏注论语》注意并转化了戴震对宋儒“理—欲”观的批评。如朱熹《论语集注》阐释“颜渊问仁”(《颜渊》),典型展现了其理—欲对立的思维框架: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闻夫子之言,则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请其条目也。非礼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辞。是人心之所以为主,而胜私复礼之机也。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⑧朱熹:《论语集注》,载《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3页。
朱熹注解该章,将心之全德的实现、天理的流行,视为行仁的至高境界;强调仁者为了抵达仁境,须时时提防人欲的诱惑、日日反躬自省,以使自我克尽私欲、复归于本心之莹然。由此,朱熹将天理论述成规范、压抑个体私欲的对立物。但是,戴望却这样推阐“颜渊问仁”(《颜渊》)曰: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责也。复,反也。能责己反礼,然后仁及天下。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反礼以正身,不能正身,虽有善政教民,不以仁名归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取譬于己。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仲弓皆具君德,故以天子、诸侯之仁告之。①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67页。
戴望提出了与朱熹判然不同的求仁目的与求仁取径,称仁者行仁的目标并非是向内求索具于心中的天理、完善自我的德性,而是要推行善政教民、仁及天下。因此,仁者行仁的取径并非是日日反躬、净尽私欲,而是要一面反礼正身,一面推行善政、向外事功、仁达天下。可见,戴望与戴震的观点相一致,皆否定朱熹的天理观及其对理—欲之界的辨析。
(二)性、才说的重构
戴望对戴震义理的继承,也表现在《戴氏注论语》对《孟子字义疏证》人性论的继承。
其一,《戴氏注论语》继承《孟子字义疏证》对人性的解析。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性”作为连结天道与人道的中介,是颇为重要的概念。对此,戴震首先批评了宋儒的二性说,指出宋儒歧人之性为理之性、气质之性,断理之性为善、气质之性为恶,实则是阴取荀子、老庄、佛家而叛离孟子性善说。②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性”第8条,载《戴震集》,第300-303页。继而,戴震提出一元的人性说,指出继承阴阳五行天道的人性,只有气禀之性,并无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而这一承天而来的气禀之性不仅是良善的,而且需要个体不断扩而充之。但是,个体达至性善不能依靠宋儒的克欲复性工夫,而是要使其人性中的欲情舒展至不逾无失的状态。③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性”第9条,载《戴震集》,第305-306页。
戴望对戴震一元的人性说颇为厝心。如同治二年(1863),戴望致函谭献,肯定戴震批评宋儒的人性论“阳宗孟子而阴取荀、扬、韩氏以助之攻”,赞许戴震恢复孟子的性善说、整合孔孟性说于一途。④钱基博整理:《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第114页。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在几处论述了其对人性的看法,与戴震的性善说相一致。比如,戴望阐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公冶长》)曰:“性者,人所分于阴阳五行,有仁、义、礼、知之等”;阐释“子路问成人”(《宪问》)曰:“人受性于天,不可变易”;阐释“性相近”(《阳货》)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强调作为天道与人道中介的人性,本于以阴阳五行为实体的天道(而非理气)。⑤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00、137、221页。再如,戴望阐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曰:“性者,生之质也。民含五德以生,其形才万有不齐而皆可为善,是相近也。至于善不善,相去倍蓰而无算者,则习为之,而非性也。故君子以学为急,学则能成性矣”,⑥戴望:《戴氏注论语》,第221页。否定《论语集注》划分性为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坚持一元的性善论,认为得之于天道的性是一元的,且无不善、无不相近;因此,《论语》言“性相近”与《孟子》言“性善”并无不同,皆是指明气质之性为善。可见,戴望吸收了戴震“后天型气学的人性观”,⑦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页。尤其是戴震批评宋儒二性说、合孔孟性说于一的论断。⑧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00、137、190、221页。
其二,《戴氏注论语》继承《孟子字义疏证》关于才质的认知。“才”是戴震人性论中的关键概念,《孟子字义疏证》曾专列三条予以剖析。首先,戴震定义了才的概念——“才者,人与百物各如其性以为形质”,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才”第1条,载《戴震集》,第307页。认为才质是伴随天性生成的产物,是外在可见的具体形质。其次,戴震辨析了性与才的关系,强调才与性具有一体性的关系——“由成性各殊,故才质亦殊,才质者,性之所呈”。⑩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第273-275页。为此,戴震批评宋儒歧“性”与“才”为二、以不善归“才”,申言与气禀之性相生相随的才质无有不善。
《戴氏注论语》化用戴震关于才质的论述,从而使其义理阐释与《论语集注》别异。如朱熹这样推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①朱熹:《论语集注》,载《四书章句集注》,第176-177页。强调理之性无往不善,但气质之性、人之才质却有美恶之分。由此,朱熹将“才”与“气质之性”相连,将理之性转恶的缘由归结为气质之性与才质之恶。
但是,戴望却这样注解“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性者,生之质也。民含五德以生,其形才万有不齐而皆可为善……上知生而知之,下愚困而不学。降才各殊,不相移易。”②戴望:《戴氏注论语》,第221页。指出人性中只有气禀之性,而无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才质伴随气禀之性而生,“才以性殊则德殊”,虽然“降才各殊”③戴望这样阐释“子路问成人”(《宪问》):“人受性于天,不可变易。才以性殊则德殊,圣人制礼乐,使人各尽其才,就其德以善其性,故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90页。,但本质皆善。因此,导致天性转恶的原因并非气禀之性与才质为恶,而是因为个体困而不学。
三、絜矩之道
除了天道论与人性论,《戴氏注论语》亦高度重视《孟子字义疏证》的情欲观与絜矩观,并对之做了大力的阐扬。
首先,《戴氏注论语》继承了《孟子字义疏证》的情欲观。细酌戴震的情欲观,其包涵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将情欲视为人性中的自然之物。如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一元的人性论,并将人性划分为血气与心知,认为二者主宰了个体在人道世界的欲望、情感与伦理,私欲因此是个体“血气之自然”。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第305页。由此,戴震以性善论为基点,确认了个体私欲的合理性与不可压抑性。二是将情欲作为个体与他者相处的中介。⑤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第164页。如戴震相信,个体欲望的扩张未必会导致强者胁弱、众者暴寡,反而可以成为个体与他人良性互动的道德基础。为此,戴震反对宋儒封闭地求取天理,主张个体将情欲作为勾连自我与他者的媒介,在人己关系与日用饮食中,“以己之欲通天下人之欲”“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三是将体恤民众的情欲作为仁政的重要内容。如戴震指出,古代圣人推行王道,往往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因此,当今为政者整顿民情,亦当充分体察饮食男女的生道欲求。
《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人欲的解析,如对比《论语集注》《戴氏注论语》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章的读解,二者对人欲的理解截然殊致。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而愈远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⑥朱熹:《论语集注》,载《四书章句集注》,第91-92页。
朱熹认为,学人不应将“博施济众”作为求仁的方法,而应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作为求仁的方法。学人在立人、达人时,当注意在人己关系中锻造自我“以己所欲譬之他人”“推其所欲以及于人”的能力,时时向内循省自我心意与欲求是否出于公意,从而臻至胜人欲之私、全天理之公的人生止境。可见,朱熹对个体欲求做了公与私的区分,以私欲为恶,主张个体节制私欲。但是,《戴氏注论语》却这样针锋相对注解道: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设言充仁之量。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读当至“必也”绝之,犹言若何从事于仁,必能如是也,虽圣如尧、舜,犹以为忧。病,犹忧也。忧其不能遍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立,定。达,通也。欲定人之生,谓制田里、廛宅以富之;欲通人之道,谓设庠序、学校以教之,皆近取诸身而喻之于人。行仁之道,务此而已。①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15页。
与朱熹推崇律身自治的仁道不同,戴望推重向外践行的经世之仁,认为博施济众即是仁者求仁的理想。由于《戴氏注论语》《论语集注》对行仁目标的设定不同,二者对“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行仁方案的设想亦不相同:在朱熹看来,立人达人是个体训练自我“求取天理、克尽私欲”的道德修炼方法,个体需要向内严审自我欲求是否出于公意;在戴望看来,立人达人乃是仁者践行仁政的基础,仁者需要反躬静思其生命欲求,并将人己同欲心落实在政教行动中,致力于富民教民的工作。可见,戴望一面消弭了朱熹人欲观念中公私的划分,视性之欲具有正当性;一面批评了朱熹克制欲求的工夫论,主张个体在社群中推扩欲求。
概言之,《戴氏注论语》对《孟子字义疏证》的情欲观有较深的接受,诸如皆强调性之欲的合理性,批评宋儒克尽私欲的工夫论,主张个体推广欲求等等。
其次,《戴氏注论语》继承了《孟子字义疏证》的絜矩观。考察《孟子字义疏证》的絜矩观,其具有以下几个内涵。一是戴震认为絜矩之道是个体锻炼心性、求取理义的重要途径。如戴震这样论述道:
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恶既形,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②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第265、266页。
可见,戴震将以情絜情、恕之道作为伦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主张个体体味自我内在释放、施诸于他人的情欲;相信个体通过此反躬过程,既能维持合理的生命欲求,又能避免跌入逞欲的状态,从而达至情得其平、好恶有节的理义境界。二是戴震认为絜矩之道是为政者敷治天下、实现王道的重要法则。如戴震曾反复论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民谋其人欲之事”“使天下无不达之情”③戴震:《与某书》,载《戴震集》,第188页。,申言王道的目标在建立遂欲达情的社会,相信絜矩之道可在其间发挥巨大功用。④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第168页。戴望对戴震的絜矩说颇为倾心,因此在《戴氏注论语》的多处踵事发挥: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欲立立人,欲达达人。顺事恕施,无非法者。(《为政》)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极仁之量,尧舜犹病,故人疑其远,莫能致也。立人、达人、取譬于己,好仁而仁斯至矣。(《述而》)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者,以身为度,可施于彼,然后行之。《传》曰:“以其所愿乎上交其下,所欲于下事其上。”(《卫灵公》)
子贡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己欲立而立人,故立之斯立。通达之以德,斯行矣。德礼不易,能安人则莫不怀来。动之以礼,使民有父之亲,有君之尊,则莫不和顺。(《子张》)①戴望:《戴氏注论语》,第71-72、124、207、243-244页。
在这些注解中,戴望格外重视《论语》“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的说法,内涵即是絜矩之道、恕之道,法则则是“取譬于己”“以身为度”。戴望的这些疏解,与戴震“以情絜情”的感通相恕之道相近,皆主张个体反躬自我,以我絜人、推己及人,推展自立自达的欲心。而在《戴氏注论语》的其他注解中,戴望则发挥了戴震絜矩之道政治的面向。如戴望这样阐发《宪问》: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故不行是四者,可以为难,未可以为仁。②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87页。
朱熹注释该章强调,仁者通过克制自我情欲,勉力做到不行“克、伐、怨、欲”,仍然不够,因为仁者的至高境界是自然而然抵达至无纤毫私欲、天理浑然的状态。但是,戴望却认为,仁者做到不行“克、伐、怨、欲”之所以不够,是因为仁者的最高境界应是“以己之欲通天下人之欲”,关怀到天下人的整体欲求。可见,戴望与朱熹之别在于,其认为仁的终极目标在于向外实现人人遂欲的社会,而非向内成就自我内在的德性。再如戴望这样阐发《宪问》: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人谓臣也。择德而任官,度材而定次,百僚称职,天工不旷,是谓安人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视百姓之身犹吾身,百姓之妻、子犹吾妻、子,不以天下害所养,是谓安百姓也。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病其难则必求所以安之。③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99页。
朱熹强调,“修己以敬”比“修己以安百姓”更加重要,因此孔子勉励好强的子路能够反求诸己,通过治己完善自我德性。但是,戴望却强调,“修己以安百姓”比“修己以敬”更加重要,因此孔子勉励子路效仿尧舜,既注意内在的心性修养,更注意民众生养与天下治理,竭力实行仁政、抵达王道。
概言之,戴望注解《论语》展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认为儒家的终极理想不仅仅在于求得内心天理的浑然、道德的完善,更在于构建人人遂欲的理想世界;二是认为仁者当把“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作为重要法则,从体察其生命欲求出发,满足民众的生命欲求,践行富民教民的仁政。戴望渴望仁者能够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渴望建构人人遂欲的理想社会,与《孟子字义疏证》的絜矩之道相通。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戴震的理欲观表明,其推许的是“在人伦格局下具有道德同情力量”、能够“与社群人士共振”的社会性人格;④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第183、299页。其追求的是以“遂欲达情”为目标的王道仁政。
最后,统括前文可知,戴震通过重诠儒家理、人性、才的内涵,构建出与宋儒殊异的“天道—人性—人道”秩序;通过辨析人欲与天理关系,提出絜矩之道,建构出区别宋儒的个体在人世修为、与社群相处的行动准则。戴望对戴震义理的这两个面向皆有继承,表明其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是系统性的。同时,戴震对宋儒展开结构性批判,背后托寓着现实关怀,用意在提出与宋儒不同的个体修养模式、伦际相处之道与理想王道世界。如戴震曾在《与某书》中抨击宋儒之学容易造就“冥心求理”“学成而不知民情”的“迂儒”;希望新义理能够培植出睿智明理兼能事功的学人,最终实现达情遂欲、天下大治的王道世界。①戴震:《与某书》,载《戴震集》,第188页。就此而言,戴望不仅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结构性的反叛,而且接续了戴震对儒家理想人格、人伦相处模式、王道世界的构想。
四、结 语
释读戴望手札,剖析《戴氏注论语》与戴震义理关系,可以勾勒出戴望接受戴震义理的历程。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围绕戴震学术展开争论,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第一流的学者;1860—1870年,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的义理。
将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接受置于清代汉学发展脉络、汉宋对立学术格局、戴震学接受图景中加以考察,或可增进学界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认知。
就清代汉学发展脉络而言,戴望不仅是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而且推动了清代汉学的转型进程。咸丰年间,戴望通过问业陈奂、宋翔凤,奠定了其对汉学及其发展趋向理解的基础。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不仅做了浩繁的训诂考证工作、发挥了汉学别派常州公羊学义理,而且尝试承续戴震开创出的新义理体系。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晚清光宣之前,戴震义理并非乾嘉汉学的主流,常州公羊学实则是乾嘉汉学的别派。那么,戴望学术工作的意义在于,其处在清代汉学发生重要流变的时代,大力发扬了乾嘉汉学别派的义理,由此推动了晚清汉学别派逐步占据主流位置的学术转型过程。
就清代汉宋对立的学术格局而言,戴望是咸同时期具有崇汉抑宋学术取向的学人。而戴望之所以坚持汉宋门户,一方面源自其对训诂考据这一历史化、追复三代圣人之道治学方法的坚持;一方面源自其对天道—人道—王道体系的理解与宋儒不同,即其推许的理想学人是“以己之欲通天下人之欲”的学人,其推许的理想社会是遂欲达情的王道世界。进一步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选择,与其置身的时代密切相关:经历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的动荡,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强逼,谋求中国的国强民富成为咸同时期政治思想界的时代课题。②参见《(六○四)薛焕奏洋务掣肘须在自强中国练兵不可稍缓折》,《(一一四七)毛鸿宾郭嵩焘奏敌国外患所当豫筹请饬整饬纪纲申明法度折》等文,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4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1、1351页。正是在这一时代氛围中,留心时务、深悟“许衡治生为急”③戴望:《戴东原、戴子高手札真迹》,“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6年版。之言、主张富民的戴望,④《戴氏注论语》曾在多处表达富民的思想。如戴望阐释“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曰:“知者务民,富、教之,宜不黩鬼神”,强调为政者当注意富民、教民;阐释“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曰:“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欲定人之生,谓制田里、廛宅以富之;欲通人之道,谓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同样强调为政者当注意富民、教民。戴望:《戴氏注论语》,第113、115页。选择了与时代精神更契合的戴震义理,既表达了其对体情遂欲王道世界的渴望,也表达了其对富裕民生的强烈诉求。因此可以说,戴望批判理学、承续戴震义理的深层目的,乃是要调整中国儒学使其得以有效应对咸同时期变局的挑战;重述三代圣人之道以为咸同时期的富强之道奠定经学的学理基础。
就清代戴震学接受图景而言,戴望是咸同时期大力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自戴震撰成《孟子字义疏证》后,清代学林不乏嘉许戴震义理的学人。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皆被视作是乾嘉道时期戴震新理学的传人。⑤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9-103页。进入民国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亦纷纷撰文阐扬戴震的义理,以期重构清代学术史版图。在这种清代学术史描述中,咸同学林对戴震学术的接受图景变得不甚明晰。如学者梳理戴震“学术形象的变迁”,认为宋恕、蔡元培、王国维、刘师培是清末民国较早对戴震义理展开研究的学人,没有注意到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推尊。⑥邓林:《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就此而言,梳理戴望与戴震义理的渊源关系,可以丰富晚清至民国的戴震接受谱系。
——以一则正统十一年商人家庭阄书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