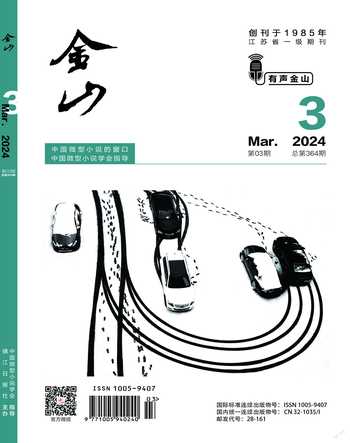亲人三题
蒋静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市奉化区文艺季刊《雪窦山》编辑。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星星诗刊》《小小说选刊》《文学港》《四川文学》《安徽文学》等刊,出版有散文集《静听心声》《时光和野草》和微型小说集《表达方式》《童年花谱》等,两部微型小说集均入选宁波市文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多篇作品入选散文和微型小说年选。
哑 伯
哑伯死了。
堂兄告诉我,哑伯临终前,突然开口,整整说了一天一夜,说得嗓子都哑了。婶婶捂住哑伯的嘴,让他以后慢慢再说。那嘴却像决堤的渠口,怎么也关不住。关了几十年的话,如湍急的流水,哗哗哗,流个不停。最后,婶婶和堂兄听得打起了瞌睡。等到他们醒来,哑伯的嘴还大张着,人却没了气息。
哑伯是我父亲的兄长,其实不哑。年轻时,因说话犯了事,被打断一根肋骨,打落两颗门牙后,还被抓了进去,一关五年。出来后,他说:“以后,我再也不说话了。”他真的说到做到。渐渐地,同辈便叫他哑子(哑巴),小辈则在原来对他的称呼前加上一个“哑”字。他也不恼,仿佛那就是他的名字。
起初,婶婶很伤心,也不明白: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成了哑子?哑伯在药箱里找到一袋麝香追风膏。那是家庭常备的一种伤膏,遇到风湿关节痛、肌肉酸痛、挫伤扭伤时,人们一般不去医院,就用这种伤膏在患处贴一张,基本能消肿止痛。不过,不到十分难受时,人们一般不舍得用。
哑伯取出一张伤膏,贴在嘴上。伤膏像一个巨大的创可贴,将嘴巴和下巴牢牢地蒙粘住。浓郁的麝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在婶婶惊诧的目光中,哑伯走向外面。
人们见到哑伯,不管是熟悉的或陌生的,都吓了一跳。谁见过伤膏这般用法!有人将哑伯当成了精神病人,离他远远的。
除了吃饭和晚上睡觉,哑伯的嘴一直不离伤膏。起先,婶婶试着开导他说话。他就指着像贴着封条的嘴,摇摇头。婶婶拿他没办法。一天早上,婶婶得意地说:“昨夜你说了好多梦话,响着呢。”堂哥也说:“对,我在楼上也听到了。”
哑伯似乎受了惊吓,浑身颤抖,脸色灰白。那天晚上,他没将伤膏取下。
几天后,哑伯的嘴边和下巴因伤膏引起过敏,一片红肿,起了疹子。他改用纱布和胶带蒙嘴。纱布比膏药小一些,露出了下巴。两个月后,哑伯的嘴巴像是结了痂的伤口,不用包扎或蒙住了。他已习惯了遇到任何事情也不发出一点声音。
哑伯从灰堆里掏出一块石板和一支石笔。石板黑色,A4纸那么大,石笔白色,这是哑伯上小学时学写生字的学习用品。遇到必须交代事情时,哑伯就在石板上写字,如:“我去赶市了,下午回来”“某人葬事,全家都去”等等。石板上的白字,抹布一擦就没了。
后来,石板碎了,哑伯只好改用纸笔。不过他用得很少,能不写的尽量不写。他将写了字的每一张纸都亲自收起来,划根火柴烧成灰烬才放心。
哑伯的脾气倒是好了许多。以前,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不管何时何地,他会当场发作,骂娘,或挥拳头,得罪了好多人。现在,遇到同样的情况,他最多黑着脸,别过头,匆匆离开,一副与他无关的样子。这一点,倒是让婶婶省心多了。
当地结婚有一项很重要的仪式——端茶(敬茶)。喝喜酒前,新娘子得一一向男方的长辈端茶。新娘边双手敬茶,边恭敬地说:“爹、娘,请喝茶。”长辈大声应一声,喝几口茶,奉上一份茶钿(红包)。堂哥结婚前,曾托我父亲说服哑伯,新娘端茶时,做公爹的总得应声。哑伯应承了。到了那一天,新娘子端茶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最大的兴趣其实是来看哑伯怎么开口说话。新娘子向哑伯奉茶,哑伯动了动嘴唇,谁也没听见他的应声。事后,哑伯在纸上写道:“我真的应了,自己听见了。”
有一段时间,哑伯学过哑语。他天天走五六里路,去一个聋哑人家里学。回家后,哑伯两只手像玩石头剪子布游戏一般,翻来覆去做动作。他示意婶婶和堂哥跟他学,他俩不理。堂哥直接对哑伯说:“我们又不是哑子,学什么哑语。”哑伯很失落,只好放弃。自己对自己做手势,有什么意思。
哑伯比真正的哑巴还哑。我认识的一个哑巴,虽不会说话,但若谁犯了他,哇啦啦哇啦啦地叫得山响,三四里外也听得见。可哑伯却哑得无声无息。有一天半夜,婶婶去解手,发现哑伯在床上爬来爬去,大汗淋漓。问他:“怎么了?”哑伯指指右下腹,龇牙咧嘴。婶婶问:“很难受吗?”他点点头。
堂哥急忙叫救护车。到了医院,医生说:“马上动手术。”并责怪家属,“阑尾都穿孔了,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要出人命的知道吗?”婶婶、堂哥辩解:“病人没说,我们不知道。”医生说:“阑尾穿孔很痛,起码痛了一天了,病人怎么会不说?”
婶婶、堂哥怎么也不明白,痛到这样地步,他为什么不叫一声。
棺柩在堂前停了三天两夜。按当地风俗,死者的老伴不必守夜。可是,那两夜,婶婶一直从夜晚守到天明。白茫茫的月光照在清静的堂前,婶婶注视着那张微微张开的嘴,感觉那里随时可能会发出声音。
姑婆的“他们”
姑婆出了车祸。母亲火急火燎地拉着我去医院。
我一个激灵,突然问:“妈,你猜,这一次,姑婆会不会再提‘他们?”
母亲瞪我一眼,没好气地说:“姑婆差一点就被轧断了腿,你还有心取笑。”
真是冤枉,我只是出于好奇,绝没有取笑姑婆之意。
姑婆很能干,既精于女红,又烧得好菜,家中里里外外料理得井井有条。她有个习惯,每当下结论或表态时,总以“他们”作为开路先锋,譬如:“他们说,你这件衣服太老式了。”“他们说,这电影不好看。”“他们说,隔壁家的孩子不学好。”……
这样的说法,让人模棱两可。姑婆到底在转述“他们”的话呢,还是想借此表达她的意思?也许,对于姑婆来说,更重要的是,话中掺进了“他们”,就好像有了金字招牌或者强大后盾,即使说错了,追究起来,也与她无关吧。
一次,我好奇地问姑婆,“他們”到底是谁呀?姑婆怔了怔,闭着嘴,没开口,好像嘴里关着什么秘密,不能让它跑出来似的。
姑婆要求她的儿女,即我的表姨、表舅,说话时也要拉上“他们”。表姨、表舅在姑婆面前极少说话,有时候,开口若是冒出“我觉得”“我断定”诸如此类的话,就犯了忌,姑婆的脸一下子拉长变色,伸手去捂他们的嘴,好像这话一经流出,会大祸临头似的。后来,他们说话磕磕绊绊,都落下了口吃的毛病,很可能跟此事有关。
姑婆的记性极好。别人说话时,她一边听声音,一边看说话的人,耳朵和眼睛同时运转。她如一台录像机,将一切录了进去。将来,什么时候若要引用这些话,就会从“他们”的引领下,一一蹦跳出来,几乎一字不漏。有一次,一位族人忘了自己某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事关家族间的利益。几位族里长辈就和当事人一起,到姑婆那里求证。姑婆眼睛也不眨一下,就说出几月几日几时,在某个地方,当事人的穿着、动作、口气以及说过的每一句话。当事人不得不服。
姑婆像一个谜,我们从来不知道她的真实想法,甚至很难分清,什么时候她代表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她又将自己排除在“他们”之外。她与我们之间犹如隔着一道屏风。姑婆的丈夫也说,他们中间,总隔着“他们”。除了亲戚,少有人到姑婆家去找她。即使有事上门,开门的总是她的丈夫或儿女。若她的家人不在,姑婆也懒得开门,只回说:“他们不在。”
在她面前,我们早已免疫,任她说多少个“他们”,我们基本不吭声。这情形,比课堂考试时的情形还严肃安静。有一天,姑婆庆生,我们同坐一桌,吃生日宴。姑婆兴致很高,一连串的“他们”,像一个个水泡从嘴里吐出。她吐她的水泡,我们吃我们的食物。突然,一个响声,从桌子底下响起,接着臭气弥漫。姑婆停止了吐水泡。我们兴奋起来,寻找屁源,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我往桌下一钻,一嗅,指着姑婆,大声说:“姑婆放屁。”姑婆的脸红红的,嘴巴哆嗦着,再也吐不出一个水泡。整桌的大人小孩都大笑起来。那是多么轻松的时刻。她的生日,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每当姑婆再提“他们”时,我总是盼望着那个可爱而浓烈的响声再次从桌子底下响起、升腾。
我发现,姑婆口中的“他们”,有时候并非真的确有其人。比如,姑婆会将“他们”的话综合起来,剔除对自己没用的,留下有用的,加工成“他们”说。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已变成了她自己,但她从不承认。
此时,姑婆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两只大腿打了石膏,悬吊着。她皱着眉头,一副痛苦状。
母亲上前,问:“受罪了,疼不疼?”姑婆答:“他们说,很疼很疼。”
我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但却禁不住大笑起来,就像那次找到了屁源一样。我想,“他们”一直住在姑婆的身体里头,好像姑婆是他们的代理人,只是我看不见而已。
金 姨
金姨是我母亲的姐姐。金姨出生时,外公替她算了一卦:五行缺金。于是,她便有了一个带“金”的大名,奶名(乳名)叫小金子。
金姨爱她的名字,也爱金子(黄金)。可是,金姨二十多岁了,还没见过金子。金子多金贵呀,那个年代,一般人哪能见到。
有金子的人家,讲究的是代代相传。金姨到了适婚年龄,不愿轻易出嫁,她决定要物色一位金主——有金的人家才嫁。直到她三十岁了,还没有调查出结果。为了扩大概率,金姨同时找了三位疑似金主。相处了几个月,三个小伙子的父母都不见动静。金姨使计,同时答应三个小伙子的求婚,成亲的日子也定在同一天。成亲前一天,就在金姨不知所措时,一个小伙子的母亲终于按捺不住,将一只金戒指戴在了金姨白皙的手上。第二天,三顶花轿同时出现在我外婆家的门口,上演了一场抢亲大战。金姨仓皇又不无失骄傲地坐上了金主家的花轿。
婚后,金姨一直戴着金戒指,这为她赢得了许多目光。姨夫警告她:“当心你的手指。”那时传闻戴着金戒指的女人夜里走路若遇抢劫,不配合的话会被人剁掉手指。金姨晚上一直不出门。
等到大家都公开戴金饰品的时候,金姨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位金主。姨夫身体不好,她独自贩卖布料,经营餐馆,边攒钱,边买大黄鱼、小黄鱼(大小金条)。金姨觉得金首饰的含金量打了折扣,黄鱼含金量最纯,最靠谱,可以压箱底。
金姨一家住的是二手房,房子小,光线暗,姨夫想换房子。当时,邻居家的房子,造的造,买的买,只有金姨一家还像蚂蝗一样盯着那块地皮不动。金姨不答应,两人常为之怄气。金姨说,房子十多年就成旧房了,只有金子不腐不败,永远保值。
金姨家的房子等来了拆迁,小套变大套,还有现金补助。金姨高兴极了,她说,这个好运,有金子的一半功劳。金姨挑了一楼的拆迁安置房,后半间临街,廉价租给了一家打金店,房东和租户中间隔一道门,可自由进出。店里的金饰品,如戒指、镯子、项链、手链、耳环等,琳琅满目,金姨一开门,满眼金光闪闪,乐得她每天笑容满面,合不拢嘴。
金姨与打金店的老板娘总有说不完的话,金子的行情,金子的趣闻,金饰品的式样,等等。金姨一有空就主动帮老板娘管店,一见人就说这家打金店的金子品质如何好,饰品如何精美,好像那是她開的店。
金姨与朋友产生借贷,她喜欢将借款额按时价折算成金子的数量,到期借方就归还金子。想要现钱,借方可以到金店兑换。金姨说,这才是最公正的借贷方式。金姨向我妈借过几次钱,我妈的一条项链和一条手链都是这样来的。
金姨穿的都是我妈和我穿过的衣服、鞋子。她说,衣服会破,会过时,会贬值,金子不会,反而能保值,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动辄上千,还不如买金子哩。对于其他生活用品,金姨也是能省就省。
金姨从不旅游。不过,也有例外,她几次乘长途车游了同一家博物馆,馆里陈列着古代墓葬出土的金饰品。金姨看后异常兴奋,好像那些都是她的藏品一般。
金姨的儿子媳妇曾向她讨要黄鱼,金姨哪里肯答应。去年,金姨死后好多天才被邻居发现。据说,金姨生病,不能自理。儿媳闻讯匆匆上门,找遍屋里所有的地方,却不知那些金子藏在哪里。
附创作谈:
让亲人在作品中登场
浙江 / 蒋静波
素材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有一段时间,我苦于找不到素材,感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甚至连做梦也在想:到哪里去寻找素材?
前不久,我向一位前辈讲述我的一位亲人的故事(确切地说是其个性),他惊呼,这不是很好的素材吗?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兴奋得真想跳起来,好像饥饿时,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支队伍,我最熟悉的亲人们,正排着长队,向我走近。那是一座多么丰富的矿藏,而且,独属于我。
我决定,开始“亲人”系列微型小说的创作。
我的亲人们,有着平常的人生,过着平淡的日子。在他们的人生里,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精彩的故事。与之配套,我也想用平常的方法去表现。经验写作的好处是,脚下的土地扎实,走路踏实;坏处是,与土地贴得太紧,沉重,飞不起来。作品如人,如何让其既要着地,又要起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的每一位亲人,平常得就像一粒沙子,落在地上,就找不到踪迹。但如果拿着放大镜,即使再平常、再微小的沙子,其形状、颜色、大小,也有特别之处。小东西的特别,可谓小微妙。发现小微妙,不正是微型小说追求的目标吗?我想做的,就是抓住这种小微妙,去经营,去强化。
写熟人真事,最重要的是取舍。作品中的亲人,一位怕犯事,不说话,活成了哑巴;一位总拿“他们”作为挡箭牌,好像她是“他们”的代言人;一位爱金如命,却活活饿死,金子也不知去向。他们是我的亲人,但已不完全是我的亲人。之所以这么说,一是确有其原型,二是创作中对素材进行了加工提炼,作品脱离了他们的肉身。这好比一块布料,要制作一件衣服,得裁剪、缝合,还得加上纽扣、拉链、饰品等辅料。所以,由布加工而成的衣服,是布,又脱离了布。
墨西哥女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在其短篇小说集《大眼睛的女人》中,塑造了一群风情万种的姨妈。我的亲人们会被我赋予什么样的面貌?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他们同样生机勃勃,个性鲜明,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