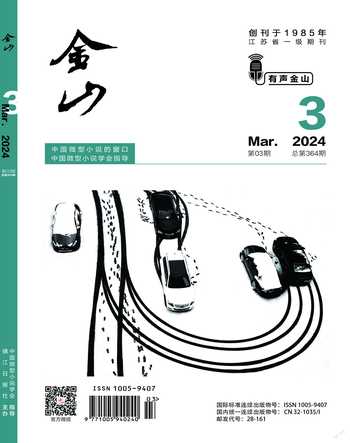1992年的“鳌头”
草色入涟

在我们那地方——冀东大平原,每到寒风刺骨的冬天,家家都会用生炉子热炕来取暖。生炉子就要搭炉子,搭炉子是粗活,在我们这儿,搭炉子这份活计天经地义、板上钉钉就该是老爷们做的事儿。哪家搭炉子,哪家炉子坏了,那肯定能听到娘们和爷们说:“哎,当家的,咱家炉子坏了,抽个空儿搭炉子吧。”而偏偏就有一个女人不信邪,她也抄起瓦刀搭炉子。
搭炉子要求严格,首先得好烧。就是当把炉子搭好的时候,人们就会抓来一把麦秸、几段棒子秸点着放进炉膛。一会儿,呼呼的噼啪带响的火苗就像孩子似的跳跃起来,就像在运动会上参加100米赛跑,顺着炉膛往炕洞里冲。
反之,什么是不好烧呢?就是你把点着的柴火塞进炉子,盖上炉盖,那辣辣的呛嗓子的浓烟还是会顺着缝隙往外蹿。那浓烈的味道,会呛得人吭吭吭地咳半天。那浓烟会熏得人脸上黑黑的,鼻子眼里也是黑的,就像黑包公。炉子要是搭成这样,免不了娘们儿的唠叨。
瓦匠我们那叫大工,锄泥给瓦匠打下手的叫小工,大工都是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爷们儿干,而小工是年老体弱的爷们和女人干。
“就她不到一米六的个儿,体重八十多斤,也就顶几块土坯的重量。”
“刮一阵风肯定都能刮跑她。”
“就她那手,一次只能让一块土坯战战兢兢地趴在手心,还搭炉子?”
“哼!”街头巷尾飞满了鄙夷。
女人不理这茬,抬起粗糙得像老树皮似的手对着土坯一抓,两块土坯就轻巧地,稳稳当当像燕子似的落在手心上。
转眼过了一年。
“哎,他婶子,上你家来串门儿,我特意看了看你家炉子,烧个水一会儿就开,做个饭,一会儿就熟,屁股一挨你家炕,身子哟立马暖和起来了呢。”
邻居花大妈回回来串门都夸几句。
“哎,大妹子。你家炉子咋这好烧呢?能不能让我取取经?”这是爱说爱拉呱儿的三姑的话。
……
每每听到这些,女人布满沧桑沟壑的脸总是会噌的一下浮上些红晕,随之她的心房被爱意渗透,如同浸水的海绵,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爱的气息。
“多出肉的土坯要消掉,少肉的土坯要按空隙的大小再塞上一小块。”“这是为啥呢?”
“是因为啊,炉子的炉帮要交错着搭,也就是第一层和第二层土坯的缝隙不能上下正对着。这样搭出来的炉帮才结实,不爱倒。”
“炉条一定要选条距适宜的,条距太宽,没有完全燃完的小块煤泥就会漏下去,那就白搭了煤泥。炉条条距太窄,用炉钩子钩炉子时,就不能把燃尽的煤泥钩干净。钩不干净炉子就不会旺,炉子上做个饭啥的就倾会儿不熟。”
“炉盖这也别稀里马虎的啊,四周一定要用泥抹匀再放炉盖……”
女人一边手上不停地忙活一边解说。不消半天,过道屋里挨着山墙大灶的边上,半米深的炉坑上方,就戳起了一个边长一尺半的四四方方的火炉。
女人成了搭炉子的老师。
快到小年的时候,女人那个一直在外地煤矿下井的爷们儿回来休探亲假,夜里一钻进被窝,女人对着爷们儿打开话匣子:“哎,炕熱乎不?”“热乎,也不看看是谁搭的炉子!”爷们儿拿着腔也拿着调,“咱家你是搭炉子的鳌头!”爷们儿嘴上说着手也没闲着,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作势去刮女人的鼻子。“别闹。痒,痒着呢。”女人扭头躲开了去,羞答答的样子像夏日里窗户前正要开的马青菜花。
“听娃们说,花大嫂、三姑她们家的炉子你也全包了?”爷们儿轻声询问。
“我向来热心肠,你又不是不知道。”女人娇嗔。
“傻丫头,当初就认准这点才娶的你,嘿嘿。”爷们儿又举起手在女人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全然不顾身边躺着的几个娃睡没睡着。
“嗯,全村搭炉子,你也是鳌头咧。奖励!奖励!”爷们儿边说边把嘴凑过去。“咯咯,咯咯……”女人边笑边用手捂住男人的嘴。
“啪”,灯灭了。
那年是1992年。那一年,远在百里地之外的国营煤矿面向附近村庄招协议工,凡是村子里的爷们儿们只要顶楞的,能出去的都报名去下了煤窑,也就从那时候起,文中的爷们儿——我的父亲,自然当了一名矿工,这个女人——我的母亲,就成了村子里搭炉子的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