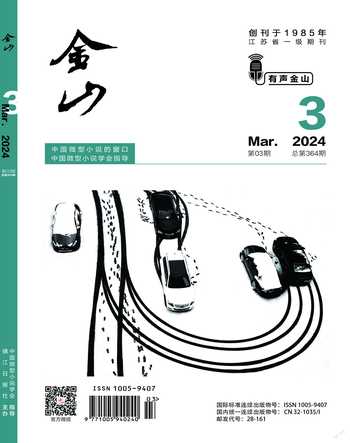挑 水
李国利
挑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事,细细算来,整整有二十多个年头挑水吃。挑水中有苦累,有艰难,有乐趣,也有尴尬。
小时候,城市自来水尚未普及,只有大机关单位和大型工厂用上了自来水,住平房的居民都是吃井水。
我们家住在咸阳市距火车站不远的一条街上,街上居住着上百户人家,全是普通百姓。整条街上仅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那时候没有人去跑步锻炼身体,而是早早地到井边排队打水。
井口之上,支着一个锈迹斑斑摇摇晃晃的铁架子,架着一只辘轳,摇着辘轳打水。那辘轳摇起来,“咯吱咯吱”很有节奏感地响个不停。那时候,男人们为了全家生计大多在外边辛苦打拼,打水挑水的基本都是女人或是孩子。我们家挑水的事情是我母亲做,我只能提个小半桶水跟在母亲身后。那时好心肠的人多,总有一些热心学雷锋的男人,轮换着摇辘轳,给各家打水。
话说咸阳,为什么叫咸阳,因为咸阳的水是咸的。那时的井水,不仅咸,还带点儿苦味。
我们在那条街上吃了几年的咸苦水。一天,有家夫妇吵架,男人家暴,女人挨了打,气愤至极。那时的女人活得很单纯,在家挨了打受了气,根本没有报警或是离婚的意识,只会选择一种自残的方式。女人哭哭啼啼跑出家门,冲向井边,一头扎了下去,街邻们纷纷涌来。有人将井绳绑在腰上,辘轳慢慢送他下去。人捞上来了,但没有救活,那时也没有120,好像也没有救护车。
唯一的一口井,不能再使用了,人们要到铁路北的居民区去挑水,每天打水排的队更长了。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我们家搬到了文汇路新建街,住进了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大杂院。院里没有井,要到外边不远处的一个压井打水,压井取水比用辘轳省劲,而且水质比开着口的井水干净。但每次去打水必须带上小半桶水,从出水口上方灌下去,边灌水边快速地抽压,形成抽力,水才能出来。
1964年,我们家被下放到咸阳地区的淳化县,住进了大山里的窑洞。
淳化的每一条山沟里都有一条小溪,溪流是泉水溢出而汇成的,大大小小的溪流最后汇成了河流。山沟里有多处泉眼,村民把泉眼凿大,就成了山泉。泉水清澈透底,可爱诱人,村民们世世代代就饮用这泉水。
山沟里的小溪流中,有很多螃蟹,只要随便搬开一块石头,下面就有好几只螃蟹。多数有鸡蛋大,最大的有拳头大小。有时会抓到母蟹,母蟹肚子下面的扇形尾盖(应该是生殖器)中,抱着一大堆密密麻麻半透明的小螃蟹,很可爱。除了有螃蟹,还有小虾,那是螃蟹的主要食物。
陕西人不知道吃螃蟹。那年代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时吃野菜,平日吃饭的下饭菜多为咸菜、酸菜,肉食就更难得吃上,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就是这样,也没人敢吃螃蟹。
不知道村里人有没有发现山沟里有螃蟹,我也是偶然发现的。一次,生产队的羊群在沟底溪流边上饮水,突然一只羊发疯似的连蹦带跑,拼命地甩头。我奔过去一看,羊鼻子上挂着一只螃蟹,原来是羊喝水时被螃蟹钳住了鼻子。我抱住羊头,费了好大劲才把螃蟹揪下来,羊鼻子被夹出了血。
当年我十二岁,哥哥姐姐在咸阳时就当兵去了新疆,弟弟還小,我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上山砍柴,下沟挑水,全是我的事。我不让母亲再下山沟里去挑水,都是我来挑,每次只挑两个半桶。我家的窑洞在村子最下边,距沟底比较近,有二百多米,但坡路很陡。
我喜欢挑水,因为每次下沟底挑水,可以抓螃蟹玩。有一次,我抓了几只螃蟹,放进水桶挑回家,连水带螃蟹倒进水缸。母亲做饭时,从水缸舀水添进锅里,把螃蟹也带进了锅中,螃蟹背部发黑,和铁锅颜色近似,加之窑洞里光线暗,根本没发现螃蟹。等水烧开,揭开锅盖,锅里有两只黄灿灿的东西,把母亲吓了一跳。
下沟底挑水抓螃蟹倒是好玩,但下雨天挑水就不好玩了,并且是非常艰难的事。那二百多米的山坡路,堪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那年秋天,连着下了六七天的雨,窑面的泥土大块大块往下塌落,听得人揪心。水缸里的水早就用完了,没办法做饭。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人都知道,饿死并不是个好死法。为了不被饿死,我只得戴上草帽,穿上胶鞋,挑起扁担下沟打水。
下去时,头顶着雨水,脚踩着泥水,侧身半马步,不需迈动脚步,只要把持住身体平衡,权当是在滑雪,就滑到了沟底。
到了沟底,我傻眼了,清澈的山泉没了,涓涓溪流没了,全被山洪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浑浊的泥水。没法子,泥水也是宝,为了过日子,泥水也得将就着取回家。自知力气不足,又不是晴天可以逞能,我只打了两个小半桶泥水。
我挑起担子,双手张开抓住两只水桶,一是减轻肩膀的压力,二是握住水桶不至于太摇晃。吸口气沉入丹田,我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
迈出的第一步,将脚插进泥里,再迈第二步。第二步有点儿难,因第一步脚陷在泥里,要使劲拔出,影响到第二步的脚向下滑,还好只滑了一点儿,第一只脚就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只上了半步。
就这样半步半步地向上移动,走出十来步时,由于操之过急,脚下没有踩实,又滑了下来,半天的努力白费了。
缓了缓气,再上。这次有了经验,不能急,慢着,稳着,一点儿一点儿地向上挪动脚步。当上至一半路时,又一股泥水顺着坡路冲下来,我被泥水带着又下滑,而且滑偏,向着沟边滑去,如果连人带水桶滚下深沟,就不是前功尽弃的小事了,而是非死即伤。
老天爷保佑!滑到路边时,一堆草挡住了我下滑的脚。踩着路边的草虽然没有泥水路那么滑,但几天的雨水浸泡,路边的土质松软,身体的重量加上水桶,会把路边压垮塌,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不可久站,必须加快步子。
除了泥水路的滑不可耐,还有一个麻烦,是被雨水打湿的衣裤,尤其是裤子,紧紧贴缚住双腿,严重限制了双腿功能的发挥,更是增大了挑水的难度。
好不容易挑回了两个半桶浑浊的水,母亲用明矾沉淀后,就可以做饭了,皆大欢喜。
1969年开春,我当了兵。部队驻进了酒泉卫星基地的戈壁深处,没有营房,全住地窝子。
戈壁滩上没有水,饮用水靠汽车到10号(基地司令部所在地)去拉水。我们部队驻在7号和9号,有两部拉水车每天分别为7号和9号两个驻地送水。汽车拉来水后停在营区空旷处,各连队纷纷前来挑水。然后一个班放一桶水,供全班人清早刷牙洗脸,晚上洗脚。连队炊事班用水多,炊事兵每天要多挑好几担水。
我那时给首长当警卫员,负责给首长住的地窝子挑水。首长用水也不多,很多时候每天挑一担水,首长用不完,警卫员帮着用。
在戈壁滩上挑水不费什么劲,全是平地,而且拉水车停放地离司政机关也很近。
戈壁滩上没有河流,战士们洗不成澡,几十公里外的额济纳旗北边靠中蒙边界有个居延海(湖泊),但不可能跑那么远去洗澡。夏天,战士们就在拉水车旁,打开阀门,冲一下算是洗澡了。冬天,加上春秋,半年多是不能洗澡的,可想而知地窝子里是什么样的味道。
后来,部队移防至酒泉。
酒泉是个历史名城,相传西汉时期,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军征伐匈奴,战功卓著,汉武帝对其褒奖,赐御酒一坛。霍去病说战功乃是全体将士的,吾岂能独自贪享,遂将御酒倒入泉水中,与几十万大军同饮之。酒泉之名因此而得。如今,那口酒泉所在之地已建成公园,泉边立碑记载此事。
部队驻在酒泉南边一个废弃的劳改农场,四周没有围墙,房屋虽然破旧,总比地窝子好。
酒泉不缺水,南边的祁连山为它提供了丰厚的水资源。劳改农场却没有水井,有条小河从农场旁边流过,农场的人可能是依这条河水为生吧。
我们部队进驻后,打了一口机井,原计划机井打好后建一座水塔,可供整个营区使用自来水。没想到机井打通后,清凉洁净的水自喷十多米高,水塔也不用建了。
井水自喷,战士们大喜过望,激动得欢呼雀跃。在缺水的戈壁滩那么久,见了这白花花清澈凉甜的水,能不激动吗?有战士直接脱掉衣服,站在井口冲凉。
部队后勤用钢管焊了一个多头分水管,扣在机井上,水从不同方向流出,方便接水。机井周围浇筑了水泥台,极大地方便了战士们洗衣洗被子。
有了自喷机井,但还少不了要挑水。好在机井处在营区中心,离司政机关也不远。由于心情好,大家都很乐意甚至抢着挑水,这么纯净清凉的水,谁人不爱?这比戈壁滩上汽车拉的水干净多了。我有时候会帮着炊事班挑水,哄得炊事班长高兴,打饭时会给我多盛两块肉,哈哈。
1975年,我退伍后来到伊犁,在巴彦岱乡党委工作。
那时的乡村,人们冬天吃雪水,夏天吃皇渠水,靠伊犁河近的吃河水。巴彦岱有几个村庄(现归属英也尔乡)长期饮用伊犁河水,有一年爆发甲肝,州地市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治。
有一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来疆考察,到了南疆,看到那里的人们饮用涝坝水,而且是人畜共用,很不卫生。李瑞环同志问:“打一口机井需要多少钱?”陪同人回答:“需要两万。”李瑞环同志当场说:“我捐两万,给农村打机井。”在李瑞环同志带领下,全疆各级干部纷纷解囊捐助。后来还是國家大力支助,为农村解决了吃水问题。如今,全部实现了自来水村村通,而且硬化道路也实现了村村通。
我在巴彦岱工作时,还没有自来水,是在政府跟前的皮里青河沟挑水吃。皮里青河并不大,但较深,是洪水常年冲刷形成的深沟,曾经两次发洪水将大桥冲断。
由于沟深,下去挑水是很艰难的。有人拿坎土曼贴着沟沿挖出长长的台阶,方便人们踩着台阶下去打水。可是冬天,有些妇女和小孩挑水时跌跌撞撞,免不了将水洒在台阶上,台阶上就结了厚厚的冰,别说挑着水,就是空手下去也很难。生活所迫,再艰难也得下去挑水呀。
我可能是当兵时受的政治教育多,或许是天生本性善良,骨子里就有学雷锋做好事的意识。我挑水时,看到老年人或是妇女小孩挑不上来,就放下自己的水桶帮他们挑上来。
那时我每到星期天就去岳父家,进了门就到处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儿干,揭开水缸盖子看看有没有水(大多时候是没多少水的),操起扁担就去挑水。要到村中百米外的水渠去挑,那水绝对不干净,因为牛羊也在渠里饮水,水里常会漂浮一些杂物甚至羊粪蛋。
岳父家的水缸还挺能装,要往返挑五次才能把缸装满水。
岳父有六个女儿六个女婿,我给老人挑水最多。我自嘲生来就是挑水的命,也或许是自己虚荣心强,想在岳父母心中赢得一个赞许吧。
1982年,我调到伊宁市委当秘书。
当时的市委连个办公楼也没有,在州党委对面的旧平房里办公,几个人挤一间办公室。院子中间的厕所是旧式圆圈形状,全是木板建造,由于年代久了,木板缝隙大,隔音极差,如厕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尴尬也没办法。
初到市委工作,没有住房,我就在胜利街后面租了一间民房。那里是好大一片乱糟糟自建房居民区,没有自来水,出门不远有条河不像河溪不像溪的水流,比溪大比河小,旁边有口泉,人们就饮用那泉水。为了挑水,我让一位木匠朋友做了一根漂亮的扁担,毕竟到了城市,巴彦岱用的那根扁担拿不出手了。到泉边挑水得下一个小坡,下雨也有些滑,但比起陕西淳化山沟好了千百倍。
住私人的出租屋挑了近一年水,后来,市委机关管理员给我安排了一套楼房,一室一厅,六十几平米。楼房是房管局的公租房,新建的,很简易,上下水没有接通,需要挑水吃,卫生间也无法使用。冬天没暖气,要架火炉,把窗户玻璃裁开一个洞,将铁皮烟筒伸出去。即便如此,能住上这楼房也是不易,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住楼房,蛮高兴的。
1990 年,我调到伊犁州税务局,先后换了三次楼房,都有自来水,再没有挑过水了。那根心爱的扁担一直保留了十几年,2009 年再次搬进新楼房,才恋恋不舍地将扁担送了人。
看来,自己也不完全是挑水的命。
挑水,那个年代的事,三四十年过去了,仍旧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