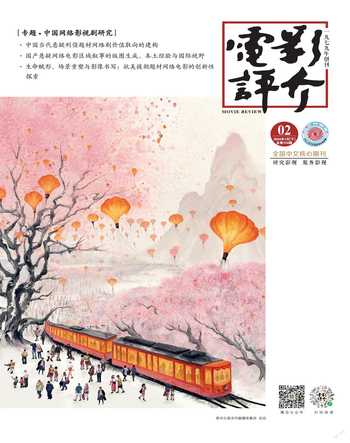“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新主流电影的嬗变、传播与文化共生
陈帅 柯祥德

电影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跨越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生的重要文本。随着我国对外人文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从国产影片销往海外到举办电影节展活动,大量优秀的国产电影传播至世界各地,使受众通过电影了解、接触到更加完整、全面的中国。与其他类型电影相比,新主流电影通过整合主流价值观、市场偏好、商业文化等因素,在与国际观众共情的同时,实现了文化共生的正面传播效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进一步发挥新主流电影的文化傳播功能,使国外受众更好理解中国,感悟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我国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我国学者马宁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1](1999)和《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2](2000)两篇文章中,提出了“新主流电影”的概念,认为面对好莱坞电影竞争,我国电影应立足主场优势,解放电影艺术的创造力,并将新主流电影作为主流电影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后备形式。学者王乃华在《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一文中对“新主流电影”的概念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他提出,新主流电影是一种电影形态,它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融合了商业电影的技巧,占据了电影格局中的主要地位。[3]这种电影形态的特点是将主旋律与娱乐片整合在一起,旨在创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电影。这一定义包括了小成本制作的电影,也包括了投资巨大的影片,但排除了仅关注形式探索的纯艺术片。新主流电影因此被视为旨在在商业市场中传递积极主流价值观的电影类型,它的出现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多样化和商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强调了新主流电影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使其在不同类型和风格的电影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16年由林超贤执导的电影《湄公河行动》,以11.84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①,成功引发大众对“新主流电影”的关注和热烈讨论。2016年11月,在“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上,我国学者陈旭光、赵卫防、皇甫宜川等人都对“新主流大片”的概念、特征发表了看法,拓宽了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空间和理论层次。其中,学者尹鸿在《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中进一步探讨了“新主流电影”的概念。他指出,新主流电影具备主旋律题材,强调积极正能量,贴近大众文化,以及故事性和戏剧冲突性的强烈表现。[4]这种类型的电影不仅承载着主流价值观,还在市场中具有吸引力,能够触及广大观众。新主流电影的概念突出了其在主流市场中的地位,同时着重于积极价值观的传递,使其在中国电影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理解新主流电影的特点和影响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新主流电影的“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好看的故事、大众的类型来表现主流观众所认同、所接受、所心向往之、所同仇敌忾的主旋律。”[5]
此后,电影《战狼2》(吴京,2017)收获56.78亿元票房①,《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收获36.28亿元票房②,代表着我国新主流电影逐渐从“概念理论”层面的认同上升到“市场”的广泛认同。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形式,具有引领民族精神的潜力,能够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的发展和文化传承贡献力量。与传统主流电影相比,新主流电影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视听风格等方面,均实现了全面超越。[6]我国新主流电影通过扎根现实生活,建构“宏观全景”的叙事框架,从多元视角来讲述宏大主题,塑造底层人物群像,用充满真情实感的镜头语言,开放包容的叙事姿态,讲述了大众面临的生活状况,书写了小人物的“大作为”,成功引发了广大受众的情感共鸣。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强烈的艺术包容性和文化影响力,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文化、艺术深度交流创造了重要平台。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是深化文化交流的重要素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新主流电影通过采用国外受众理解的叙事体系,登录其他国家院线、流媒体平台,参加国际电影节展活动,不仅有力提升了我国电影艺术的影响力,也助力国外受众读懂中国故事、理解我国文化。
(一)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途径
中国新主流电影通过在相关国家的主流平台上映,积极参加相关电影节展活动,充分唤醒了新主流电影蕴含的主流文化,也向海外受众生动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文化。[7]一是登录国际院线、流媒体平台,构建多类型传播体系。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等,2019)同步在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上映,并于第二天在海外40多个国家、100多家电影院线同步上映。从海外票房表现看,该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在欧洲的最高预售纪录、跻身澳大利亚的热映影片榜单前十名。电影《芳华》(冯小刚,2017)在北美上映后,观影人次达到20余万,占北美华人总数的5%。电影《流浪地球》(郭帆,2019)在美国流媒体平台奈飞上映,持续拓宽了影片的传播空间。电影《流浪地球2》(郭帆,2023)在数十个国家、地区上映,海外票房超过1亿元③,并且收获了较好的口碑。《战狼2》(吴京,2017)、《悬崖之上》(张艺谋,2021)《流浪地球》系列和《长津湖》系列(陈凯歌/徐克/林超贤,2021,2022)等新主流电影凭借主题共认、内容共情等优势,积极参与海外市场角逐,甚至将“春节档”带入海外市场。在完成院线上映后,新主流影片还在国际主流新媒体平台相继发行,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二是积极参加国际电影节展活动,持续扩大新主流电影的国际影响力。电影《湄公河行动》被作为第三届丝路电影节的开幕电影,并在缅甸“2019年中国电影节”、萨拉热窝的“中国电影周”等国际节展活动展映。电影《战狼2》先后在“2017中国-东盟电影节”“第一届塞班国际电影节”“新时代国际电影节”获奖。三是以中外合拍的方式,共同创作新主流电影作品。由中美联合制作的电影《月球陨落》(罗兰·艾默里奇,2022)、中俄合拍电影《永远的记忆》(谢云鹏,2022)等合拍电影,不仅有效兼顾了主流价值与商业艺术,也选择了易被国内外观众理解、接受的叙事模式,减少了“文化折扣”现象。
(二)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策略
综合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新主流电影在参与国际传播过程中,需要将其中蕴含的精神、理念及价值观进行符号化处理,随后通过消费、再生产等环节,使媒体和受众对电影符号进行解码、二次编码。[8]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极其容易产生解码偏差,出现“文化折扣”或者“文化误读”等现象[9],为促使新主流电影被国际受众认可,应找寻打动国际受众的传播策略。
其一,回应受众期待,传播正确价值观。尽管海内外受众在价值理念、审美方式与文化认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新主流电影通过回应观众的审美期待,讲述精彩的故事内容,打造精美的视听呈现文本,使主流价值观有效转化为容易被理解的故事文本。[10]由郭帆执导的电影《流浪地球》系列,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叙事核心,采用温情叙事,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合作意识融入全人类命运的畅想中,通过使用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诠释人类最真实的情感,实现了国际传播的理想效果。其二,新主流电影在参与国际传播过程中,通过书写平民英雄,凸显家国情怀,采用相对紧凑的叙事节奏,以较为克制、柔和、收敛的情感表达方式,塑造了更容易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叙事文本。
学者赵卫防在《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中指出,新主流大片有两个不变的根基。首先,主流电影在其本质中必然要体现主流价值观,因为这是其最根本的诉求。[11]主流价值观在电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引导和塑造观众的认知和情感。这意味着无论电影采用何种类型或风格,主流价值观应该贯穿始终,以确保电影与观众之间的有机共鸣和情感连接。这一核心原则有助于新主流电影在不同类型和题材中实现主流价值与美学表达的有机融合,从而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和期望。其次,必须依靠类型创作。新主流电影通过将弘扬主流价值观与其他各种类型电影相融合,汲取其他类型电影的美学技巧与叙事策略,使影片的叙事内容、视听风格都实现了创新和突破。比如,由吴京执导的电影《战狼2》通过对军事电影、动作电影、超级英雄电影进行类型融合,为观众呈现了动作电影的视觉奇观、军事电影的壮观惨烈和超级英雄电影的精神力量等内容。该片以56.8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首部进入全球票房前100名的“非好莱坞电影”,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40多条院线同步上映,海外市场整体票房达到760万美元。①我国新主流电影在积极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吸收、借鉴了商业电影的制作能力,以较高的艺术水准,收获了较好的市场成绩,凸显了我国文化的主体性,诠释了全球共享的文化观。
(三)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困境
我国新主流电影虽然在国际传播领域获得一定发展成效,但海外票房成绩、输出数量仍然明显不足,难以充分发挥电影的载体优势来传播我国文化,助力中外文化交流。[12]
首先,叙事模式相对固化,叙事情节过于单一。目前新主流电影大多采用“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叙事结构,其中设计的故事冲突、情节都大同小异,缺少足够的想象力。比如,《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万里归途》(饶晓志,2022)、《空天猎》(李晨,2017)等新主流电影都在讲述海外“营救”和“撤侨”的故事情节,存在明显的叙事固化现象。其次,文化亲和力相对不足,缺少共享价值观的输出。现阶段新主流电影尚未采用“全球性”叙事话语,其中讲述的情感、故事以及表达的问题相对局限,缺少跨文化思维的有效诠释,影响了叙事内容的全球共享。由于新主流电影是以类型融合的方式进行创作,其中以主流价值观为核心,只能尽可能地平衡主流价值与受众偏好,因此,影片的叙事文本、美学风格很难满足不同类型观众的观赏需求。最后,目前新主流电影的叙事逻辑、叙事能力相对薄弱,存在剧情零碎、受众存在文化隔离和叙事主题不够明确等问题,极易引发观众误解。虽然《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在国内获得较高票房,并进入2022年全球票房前十,但是在海外市场表现欠佳,仅收获票房57万美元,且主要面向海外华人。①受文化折扣、文化误读等因素影响,新主流电影对境外受众的吸引力仍然不足。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新主流电影的文化共生策略
新主流电影兼顾了主流价值观和商业电影技巧,对彰显文化自信、美学自信有重要意义。为更好推动人类文明互鉴共享,应以文化共生为基础,通过将“一带一路”主题合理拆解为海外受众容易理解、共鸣的故事细节,深度发掘“丝路”精神,提升面向海外“講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一)强化全球共情效应,彰显文化多样性
“共情”作为一种内在的、人类天性的情感表达,它表现为个体本能地模仿所观察到的对象的运动和表情,并因此产生与之相似的感觉,这种“共情”不仅适用于美学体验,还延伸到了精神领域。[13]这一理论强调了人类内在的共情能力,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情感和意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在美学体验中,也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共情是新主流电影成功突破文化差异、跨越文化壁垒的关键,通过探寻国内外受众公认的叙事策略,自然、生动地诠释主流价值观念,使观众在“共情”中,实现影片文化内核的价值共生。[14]为此,在提升我国新主流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进程中,应正视文化的差异性,尊重文化的多元性,顺应受众的文化习惯、审美偏好,找寻不同文化的情感共通点,通过对电影作品蕴含的文化、价值理念进行“软性”传播,更好引发海外受众的情感共鸣,使海外受众实现“顺应式”解读。
(二)践行共同体美学,关切审美多样性
新主流电影通过以“共同体美学”为基础,践行平等对话、开放包容的创作思维,突破了文化的封闭性、超越了创作视角的束缚,回归新主流电影特性和生活本身,聚焦真实人性、塑造真实人物,流露人类共通情感,启迪观众在深刻反思中,为情绪共振、文化共生奠定基础。[15]为助力我国新主流电影积极走向世界,实现文化共生,需要密切关注受众需求,积极面向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共同理想,在兼顾“主体”和“他者”的思维模式中,聚焦国内外电影在文化、审美等领域的共性,通过采用共同体叙事策略,对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文化的融合,创造一种能被广大受众接受、认同的影像文本。
(三)以“他我关照”为重点,迈向“转文化间性”
荷兰美学家约斯·德·穆尔提出了“文化间性”的概念,“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之间的可沟通性,“转文化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推动文明平等交流互鉴。[16]新主流电影作为主流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应以尊重他者、承认差异为前提,以文化对话为根本,以文化间性思维传播共享文化,通过采用“以小见大”的复调叙事策略,关切“互惠性理解”,将“丝路精神”融入视觉编码、叙事文本和场景构图之中,用自然、真实的艺术风格,刻画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从而在审美符号的转译下,反映现实、记录现实,以强烈的共情张力,彰显强烈的时代精神,增强我国主流文化国际传播的实效性,拓宽文化国际交流空间。
(四)重构记忆符号,增强主流文化的认同度
“记忆的共同体”概念强调了文化记忆在群体认同和自我认知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概念认为,当一个群体共同传承和共享特定的历史事件、价值观、故事和象征时,他们形成了一个记忆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特质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文化、认同和表达方式。[17]“一带一路”是文明互鉴、文化共享的倡议与理念,有助于创作者以艺术互动、文化共生的方式来思考如何利用文化艺术来凝聚多方共识,唤醒共同记忆,链接共同情感。为此,新主流电影应通过强烈的叙事话语功能,积极重构记忆符号,唤醒文化记忆、询唤文化认同,精选叙事文本,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以全球化的叙事策略,建构主流文化被广泛认同的语义环境,从而提升主流文化的国际认同。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8]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新主流电影积极走向国际市场,不仅突破了国外受众对我国电影、文化的传统认知,也有效扩大了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为持续提升新主流电影的传播效能,应以融通中外的全新叙事框架为基础,关注国际受众的审美期待,不断提升新主流电影的艺术品质,通过不断丰富新主流电影的文化内涵,努力增强我国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效能。
参考文献:
[1]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 J ].当代电影,1999(04):4-16.
[2]马宁.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 J ].当代电影,2000(01):3.
[3]王乃華.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 J ].当代电影,2007(06):138-139.
[4][5]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07):82-87.
[6]陆晓芳.时代语境·媒介场域——中国新主流电影文化实践的双维审视[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6):114-121.
[7]张悦,严励.当下我国新主流电影的话语表达与话语分析[ J ].新闻爱好者,2020(06):91-93.
[8][英]斯图亚特·霍尔.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黄卓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33.
[9]陆晓芳.“震惊”与“沉浸”: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 J ].文艺理论研究,2021(04):168-177.
[10]包磊.时空同构、身份重置与价值再造——“一带一路”语境下“新主流电影”“走出去”研究[ J ].电影评介,2022(Z1):130-135.
[11]张卫,陈旭光,赵卫防,梁振华,皇甫宜川,张俊隆.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 J ].当代电影,2017(01):4-18.
[12]吉爱明.新主流电影中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策略——以电影《我和我的……》系列为例[ 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2(03):178-181.
[13][美]亚瑟·乔拉米卡利.共情力[M].耿沫,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22.
[14]陈旭光,刘祎祎.“新主流”视域下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与工业美学探索——以《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为个案[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109-118.
[15]丁亚平,王婷.执著的风致:在电影的表达与存在之间——2022年中国电影发展总论[ J ].艺术传播研究,2023(01):5-22.
[16][荷兰]约斯·德·穆尔,麦永雄,方頠玮.阐释学视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 J ].外国美学,2012(00):312-336.
[17][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2.
[1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4.
【作者简介】 陈 帅,男,湖北荆州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柯祥德,男,福建安溪县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文化建设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福建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JAS20072)、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科研培育项目(编号:11192110014)成果。
①②数据来源:猫眼票房专业版APP。
③数据来源:中国电影网.中国电影“走出去”上年度交出亮眼成绩单[EB/OL].(2018-01-11)[2023-12-20].https://www.
chinafilm.com/xwzx/3423.jhtml?from=groupmessage.
①参见:豆瓣网.2017年全球票房冠军影片竟然是这部![EB/OL].(2018-01-03)[2023-12-20].https://www.douban.com/note/
651766453/?_i=4699944OXkmBgx.
①参见:知乎.总票房破299亿!2022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长津湖之水门桥》41亿位居榜首!十亿俱乐部影片7部 ![EB/OL].(2022-12-31)[2023-12-30].https://zhuanlan.zhihu.com/p/595753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