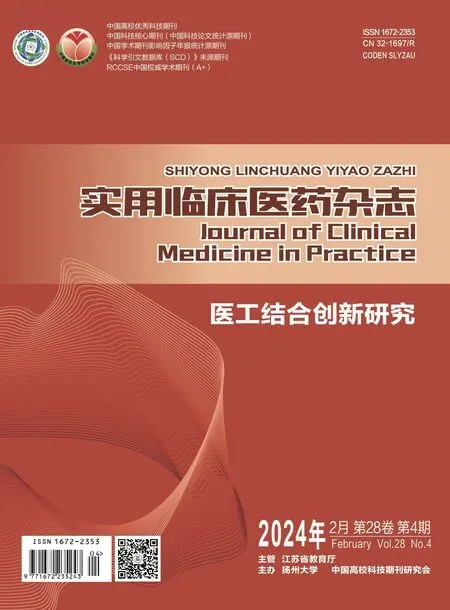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机制及阻断策略研究进展
金 鑫,彭 睿,高玲玲,周文杰
(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扬州大学附属苏北人民医院,江苏 扬州,225001)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母婴传播(MTCT)仍是中国HBV感染最主要的传播途径[1]。MTCT也是造成HBV感染慢性化的重要原因[2],阻断HBV MTCT是乙型肝炎(简称乙肝)防控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实施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联合乙型肝炎疫苗(HepB)的被动-主动免疫,中国HBV MTCT发生率已显著下降,但仍存在免疫阻断失败的现象[3],尤其好发于乙肝e抗原(HBeAg)阳性、HBV DNA载量高的孕妇。宫内感染是阻断失败的重要原因[4],孕期抗病毒治疗是指南推荐的阻断宫内感染的重要方式[5-6]。如何合理有效地阻断HBV MTCT已成为学者和临床关注的重点。本文就HBV MTCT的发生机制及阻断策略予以综述。
1 HBV MTCT相关发生机制
围产期转运已被认为是HBV传播的主要方式。MTCT可发生在3个时期:产前(经胎盘的宫内传播)、产时(分娩期间的传播)、产后(护理不当或通过母乳的传播),其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胎儿、母体、病毒、免疫、胎盘等,目前具体相关机制仍未完全阐明。
1.1 产前传播
产前传播即宫内感染,被认为是实施联合免疫后仍预防失败的最重要原因[3-4]。宫内感染可发生在妊娠的不同阶段,包括早期的配子感染、中后期的胎盘感染等。宫内感染的传播途径主要有胎盘途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途径、经生殖细胞感染途径。
1.1.1 胎盘途径:胎盘是重要的物理屏障,可以保护胎儿免受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有研究[7]表明HBV感染会导致胎盘发生炎症反应,使胎盘的储备和代偿能力下降,屏障功能变弱,更易发生宫内感染。经胎盘途径发生的宫内感染可分为细胞源性感染和血源性感染。
细胞源性胎盘感染指母体血液中HBV通过感染胎盘各层细胞,进入胎儿循环使胎儿发生感染。研究[8]发现从母体到胎儿,HBsAg、乙肝核心抗原(HBcAg)在胎盘不同细胞层中逐层转移,蜕膜细胞中表达最高,其次是滋养层细胞、绒毛膜间充质细胞、绒毛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与此结果类似,有其他研究[9]结果也提示宫内HBV感染途径可能为通过细胞转移机制的分层传播。此外,有研究[8,10]表明HBV宫内传播与胎盘感染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在感染绒毛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时更为显著,提示胎盘感染发生在离胎儿越近的地方,HBV宫内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血源性的胎盘感染,即胎盘渗漏,主要指胎盘微血管破裂引起胎盘屏障作用减弱或破坏,使母体血液中大量HBV进入胎血循环而导致胎儿感染,如羊水穿刺等侵入性操作[11]、先兆早产相关的子宫强烈收缩[8]等; 也可发生于妊娠早期胎盘不成熟或妊娠晚期胎盘老化引起的屏障作用减弱时[11]。
1.1.2 PBMCs途径:PBMCs可通过受体或吞噬作用感染HBV,受感染的PBMCs可能是HBV从母体转移到胎儿的载体。已有研究报道,可在感染者PBMCs中检测到共价闭合环状脱氧核糖核酸(cccDNA)[12-13]、松弛环状脱氧核糖核酸(rcDNA)[13],且研究[12-14]表明HBV宫内感染与PBMCs中HBV DNA显著相关; SHI X H等[13]还提出PBMCs中HBV cccDNA可能是宫内感染的直接危险因素。XU Y Y等[14]鉴定了119对母子在母胎PBMCs遗传谱上的差异,在存在PBMCs母婴转移的胎儿中,76.0%(57/75)的婴儿感染HBV,而在未检测到PBMCs母婴转移的胎儿中,25.0%(11/44)的婴儿感染HBV; 这种PBMCs途径使新生儿PBMCs HBV感染风险增高了9.5倍。
1.1.3 经生殖细胞感染途径:生殖细胞感染学说认为HBV可通过感染多种生殖细胞造成胎儿宫内感染。已有多项研究[15-19]报道在卵母细胞、卵巢颗粒细胞、精子中可检测到HBV DNA。有证据[15-16]表明,HBV可通过血睾屏障进入雄性生殖细胞并整合到感染者精子染色体中,尽管HBV感染会损害精子功能降低精子受精能力,但仍有发生父婴垂直传播的可能。而CAI Q X等[17]发现所有父亲携带HBV的父母中,其胎儿在子宫内HBV DNA均为阴性,且新生儿血液中HBV DNA均来源于母亲。YU M M等[18]对HBV感染孕妇及新生儿分别进行卵巢和胎盘的HBV标志物检测,发现若在卵巢卵泡或胎盘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中有HBsAg表达则HBV宫内感染风险较高; 而JIN L等[19]长期随访研究发现,卵母细胞和胚胎中的HBsAg可能不会垂直传播给后代。HBV到底能否通过生殖细胞引起宫内感染值得进一步探索,但目前大部分研究对通过女性生殖细胞发生母婴传播的现象持肯定态度,而父婴传播的证据相对较弱,但足以考虑该可能性[15]。
1.1.4 产前传播影响因素:目前,关于宫内感染的影响因素已有较多研究,多数证据表明HBeAg阳性、HBV DNA 高载量的孕妇,其胎儿更易发生宫内感染[9-10],且随着孕妇血清HBV DNA载量的增加,胎儿宫内感染的风险随之增加[20]。另外,HBV有显著的遗传多样性,HBV基因型不同则疾病进展、转归也不尽相同。亚洲最主要的基因型为HBV基因C[21-22],INUI A等[22]对HBV传播途径与基因型关系的研究提示,C型较其他基因型更容易发生MTCT。
1.2 产时传播
产时传播指胎儿在通过产道时吞咽了含有HBV的母血、羊水、阴道分泌物等,或在娩出时因长时间强烈宫缩导致胎盘屏障功能受损,使母血进入胎血循环而发生HBV的传播。产时传播被认为是HBV MTCT发生的最主要时期[23]。有研究[23-25]发现经剖宫产娩出的胎儿感染率低于经产道娩出的胎儿,尤其发生在HBeAg阳性、病毒载量高或孕期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产妇中; 同时也有研究[26-27]结果表明分娩方式与HBV MTCT的发生没有确切关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纳入研究的产妇本身状况、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等有关。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剖宫产在避免HBV MTCT方面比阴道分娩更有优势,且指南也不建议根据HBeAg状态或HBV DNA载量选择分娩方式,而因根据产科指征进行选择[5-6]。若HBV感染产妇未合并剖宫产指征行阴道分娩时,应注意产程并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1.3 产后传播
产后传播指新生儿通过接触HBV感染母亲的乳汁、体液、血液或通过其他密切接触而获得感染,其中是否可以母乳喂养是产妇最关心的问题。有研究者[28]在母乳中检测到了HBsAg和HBV DNA,但多数研究[5,29]表明,基于标准免疫预防后母乳喂养未增加婴儿HBV感染风险,即分娩后停药,HBsAg阳性母亲可母乳喂养[5]; 分娩后产妇仍需抗病毒治疗,已知核苷酸类似物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DF)在乳汁中含量很低[29],服用后可母乳喂养。新生儿普遍进行被动-主动免疫后,通过产后传播途径感染可能性较低。
2 HBV MTCT阻断策略
2.1 HBIG联合HepB免疫阻断
MTCT是中国HBV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近30年,国家在HBV防控工作中做出巨大努力。1992年,HepB被纳入免疫规划管理; 2002年,HepB被纳入国家扩大免疫规划; 2005年,新生儿可免费接种HepB; 随后国家又对15岁以下人群进行HepB查漏补种工作; 2015年,对HBsAg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实施HBIG联合HepB的被动-主动免疫阻断[30-31]。在各项措施的推动下,HBV MTCT的发生率大大降低。
有研究者[3,32]发现HBsAg阳性母亲的新生儿使用HBIG和HepB联合免疫策略较单独使用HepB可更有效地降低MTCT发生率,并且若母亲同时为HBeAg阳性时,效果更加显著; 也有研究[33-34]报道,对于HBsAg阳性HBeAg阴性母亲的新生儿,单独接种HepB与联合免疫的阻断方式在预防HBV MTCT的发生中效果等同。尽管如此,WHO和多数指南仍建议,HBV感染母亲所产新生儿均应在出生12 h内接种HBIG和HepB[5,35]。然而,新生儿普遍实行标准的联合免疫预防后,仍有HBsAg阳性母亲,尤其是HBeAg也为阳性的母亲,所生儿童成为HBV携带者[3]。宫内感染是免疫预防未能阻断MTCT的主要原因,而高HBV DNA水平和HBeAg阳性是宫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10]。此外,考虑到在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成本、运输等问题,HBIG的可及性仍较低,缺乏HBIG时更应综合考虑孕妇情况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
2.2 核苷类似物的抗病毒预防
有研究[36-37]报道,高病毒载量孕妇在妊娠中晚期口服抗病毒药物可降低外周血HBV DNA水平,结合标准免疫预防,能进一步提高HBV MTCT阻断率; 另外,HBeAg阳性孕妇中的90%HBV DNA水平高于2×105IU/mL,而HBeAg阴性孕妇的中位HBV DNA水平低于103IU/mL,其新生儿经标准预防后,几乎无感染,因此HBeAg阴性孕妇妊娠期无需服用抗病毒药物[6]。
目前,中国用于HBV MTCT阻断的抗病毒药物有拉米夫定(LAM)、替比夫定(LdT)、TDF,其中LdT和TDF为妊娠B类药物,LAM为妊娠C类药物,但LAM在临床上已被用于预防艾滋病毒MTCT较长时间,被证明是妊娠期间可安全使用的药物[3]。有学者[38]对LAM、LdT和TDF这3种药物的疗效进行比较,在一项网状Meta分析中纳入涉及12 740名孕妇的75项研究,结果显示TDF在预防HBV MTCT方面比其他2种药物更为有效; 加之有研究[39-40]证明TDF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更低的耐药性,因此各指南均建议TDF为HBV阳性母亲的首选治疗药物[1,6,41-43],但长期使用TDF治疗是否会导致孕妇肾功能损伤和儿童骨骼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44-45]。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是TDF的前体药物,抑制病毒复制能力强,在2018年被批准用于治疗慢性乙肝,并被推荐为一线药物。目前的多项研究[46-47]表明TAF在阻断HBV MTCT方面与TDF疗效相当,且能降低对肾脏和骨骼的不良影响,有望成为阻断HBV MTCT的新选择。但目前循证医学数据相对较少,仍需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来验证TAF用于MTCT阻断的可行性。
HBV感染孕妇在孕期进行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已得到公认,但各指南在治疗开始时间及HBV DNA阈值上仍未达成统一。临床工作中,仍应尊重患者意愿,并结合患者HBV DNA载量、ALT水平、家族史等,选择合适的时间及阈值开始抗病毒治疗。
3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中国在阻断HBV MTCT工作中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存在阻断失败的现象,每年依旧有万余名新生儿感染HBV。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MTCT阻断成功率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当前HBV MTCT发生机制和阻断策略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为解决该关键问题提供参考。但HBV MTCT的发生机制仍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如父婴传播是否切实存在、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存在本综述以外的重要传播机制等,都需研究者进一步探索;阻断方案也仍存在分歧,探索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需要更多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另外,本综述发现目前妊娠期抗病毒治疗的安全性数据大多来自妊娠中晚期,妊娠早期的数据相对较少,其安全性仍有待确认;抗病毒新药TAF上市时间较短,其能否成为阻断HBV MTCT的新选择及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安全性仍需要更多、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