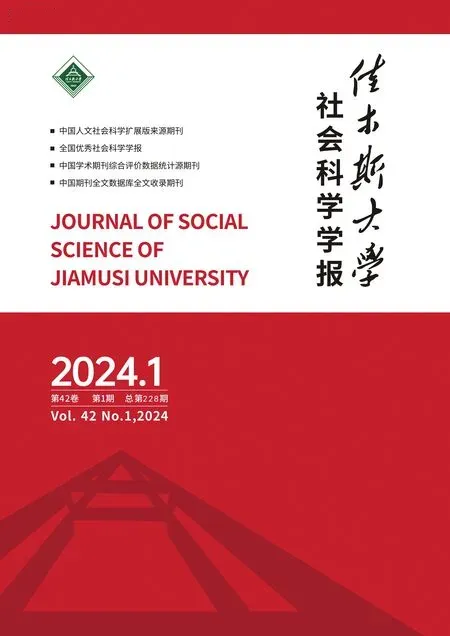艺术薪火跨界融合:汉剧声腔与美声唱法的结合研究*
贾 玲
(沈阳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汉剧是孕育了多种皮黄剧种的古老戏曲种类,它是中国戏曲剧种的杰出代表。诞生于荆楚文化之中的汉剧首创了皮黄合奏,其促成了皮黄腔系的形成[1]。传统汉剧声腔音色尖细,美感不足,随着陈伯华先生对其创新改良,吸收借鉴了美声唱法的诸多艺术元素,如胸腹式呼吸法、共鸣腔体发声技巧等,由此音色更为通透、华丽、圆润起来,与美声唱法的相融互嵌使汉剧的艺术价值与魅力得到大幅提升,其在新时代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一、汉剧的发展历程及风格特点
(一)汉剧的兴起与繁盛
汉剧也被称为楚调、楚曲、楚腔,它是湖北地区广为流传、影响至远的著名剧种。汉剧的发源地在陕西安康,川流不息的汉江将之带至湖北襄阳一带,由此形成了一青二黄三越调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流逝,越调、青戏逐步衰亡,二黄继续沿汉江而流转,至武汉地域形成了皮黄合流的汉剧[2]。汉剧的兴起与发展为皮黄声腔其他剧种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武汉是商旅聚集、经济繁荣的大都市,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各种娱乐场所鳞次栉比,汉剧因此而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发展条件,其与武汉当地方言的音韵创腔、九腔十八板等都建立起密切的关联关系[3]。明万历年间,学者袁小修曾至沙市观戏,后以文字记录了观演经历与感悟,在记载中他写道,“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歈,一为楚调”,由此不难看出汉调与楚调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顾彩在《容美纪游》中也写道,“初学吴腔,终带楚调”,这些文字记述皆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汉剧的历史发展沿革。
(二)汉剧声腔及行当的特点与风格
汉剧声腔即皮黄腔,它是皮黄声腔体系的开山鼻祖。皮黄腔系中其他剧种很多都是在汉剧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西皮腔也被称之为“下把”,它由秦腔及襄阳腔改造融合而成,陕西秦腔流入湖北襄阳之后,艺人对其进行了加工再造,使之更加契合当代艺术风格,从而很好地融入到地域剧种之中[4]。汉剧之西皮腔有着良好的可塑性,它节奏明快、情绪激昂,多用于表达人物兴奋、愉悦的情绪情感。二黄腔源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别名“上把”,早在乾隆年间二黄即已开始广为流传,正如檀萃所载,“西曲二黄纷乱咙”,二黄腔多见于抒情唱段中,其表现力丰富、旋律丰满,汉剧声腔除西皮、二黄之外,还有平板、杂腔小调两类声腔。平板轻巧、灵动,杂腔小调节奏清晰、曲调悠扬,汉剧声腔丰富多彩的旋律,刚柔并济的腔调使其独具艺术魅力与特色,形成了很高的艺术价值[5]。
汉剧行当主要有十大类,即末、净、生、旦、丑、外、小、贴、夫、杂,这些行当代表了不同的人物角色属性,其依据人物的年龄、性别、演唱特色等进行划分,所有行当中生旦演唱分量最重,旦在坤旦出现之前皆由男性扮演,其唱腔以小嗓为主。
二、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融合优势
(一)二者的内在契合关系
汉剧声腔具有浓郁的戏曲传统唱法特点,其审美独特、风格清奇,只是在口传身教的传承模式影响下,其科学性、系统性有所不足。传统汉剧四旦声腔音色既尖又紧,削弱了汉剧的美感,直到陈伯华先生创立陈派声腔之后,汉剧声腔才日益宽广、通透。陈伯华先生引领了汉剧声腔审美新方向,陈伯华之所以能创新汉腔风格与其学习借鉴西洋美声唱法不无关系,与美声唱法的融合实践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唱腔特色,在其影响下,汉剧声腔与美声唱法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二)二者的相似相通之处
汉剧声腔与美声唱法虽形成于不同的语言环境及文化土壤之中,但它们皆为音乐艺术的典型代表形式,它们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融相通的。首先,汉剧唱腔为表现音色的响亮性而主要运用小嗓来进行演唱,美声唱法与汉剧唱腔的糅合可使汉剧音色更为圆润、饱满,同时其传统风格与意蕴仍能得到很好的承继与保持[6]。其次,无论是美声演员还是汉剧演员,练嗓皆是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训练内容,只有坚持不懈地练嗓才能在舞台表演时展现更为完美的艺术效果。汉剧练嗓通常包括了喊嗓、吊嗓、发音咬字等步骤程序,喊嗓旨在使声音保持松弛状态,避免出现挤嗓等问题,喊嗓时需合理运用鼻腔共鸣、头腔共鸣等技法,美声喊嗓目的亦在于此,因此其与汉剧形成了共通性。吊嗓要求胸腹蓄气、吸气适当,其将唱腔、喊嗓、气息、发音咬字等统合在一起,美声唱法中的吊嗓也是对气息运用方法的锻炼。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在音色方面亦有异曲同工之处,陈伯华曾评论自己对小嗓的运用,在她看来,即便小嗓发声亦可宽亮圆润、柔和典雅。陈伯华是一位对西洋美声唱法有过全面深入研究实践的著名汉剧艺术家,前苏联声乐学者曾赞誉其为“东方古典花腔女高音”,她主张将西洋音乐中华丽、轻快的旋律运用于汉剧创作中,此外她还苦练多种发声方法,使自己的嗓音避开了先天缺陷,更为亮丽柔和。汉剧声腔与美声唱法的相融互嵌得益于陈伯华先生的勤勉实践,在陈伯华先生的不懈努力下,汉剧声腔挤嗓、尖细的瑕疵被巧妙规避,其不断推陈出新,在新时代展现出新的魅力与风格[7]。
三、汉剧《红色娘子军》唱段传统唱法与美声唱法融合实践研析
(一)汉剧《红色娘子军》唱段文本解析与探究
1.唱段所述故事背景
汉剧《红色娘子军》由武汉汉剧院在京剧同名样板戏的基础之上改编再创而来,它是武汉汉剧院享负盛名的保留剧目之一。唱段《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出自该剧目的第一幕,该唱段讲述了吴清华逃离土牢后被南霸天率人追踪毒打,晕倒后遭遇大雨,大雨将其浇醒的故事片段。吴清华在醒来后演唱了该唱段,其演唱表现了吴清华坚贞不屈的精神品质与对南霸天及苍天不公命运的愤恨与控诉[8]。
2.唱段歌词解析
《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是出自《红色娘子军》的一段著名唱段,该唱段的歌词细致深刻地描述了吴清华的内在思想与情绪情感,强烈地表达了她对反派南霸天的仇恨之情。吴清华在逃跑途中遭遇南霸天等人的追踪毒打,被打晕后在瓢泼大雨中醒来,死里逃生的她此时“昏沉沉只觉天旋地转”,她强忍疼痛,挣扎站立。在肢体表现上,其站立动作应是颤抖的、迟缓的,“咬牙关,挺胸站,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这句歌词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她坚强、倔强、永不屈服、绝不低头,哪怕在最危急的关头仍能向死而生,“关黑牢三天未见一粒米,遭毒打遍体伤痕血未干”,虽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虽跑一次打一次,吴清华仍旧未屈服,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她就会一次次地逃跑,这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反派势力的嘲讽。漆黑的深夜,瓢泼的大雨,雨水夹杂着血水流遍全身,吴清华浑身湿透,新伤旧伤重叠,千疮百孔,她的悲惨遭遇再次升华,这使她愤怒地斥问苍天为何如此不公,如此残忍,“黑压压看不清密密椰林哪是边”,“这世道,谁肯听我诉苦难,谁能替我报仇冤?”黑暗的深夜使她无法辨清方向,世道的不公加重了她的苦难,她愤怒,她控诉,“五指山,你为什么不把五指握成拳,打死南霸天?打死南霸天?”此处吴清华对南霸天等人的仇恨达到了顶峰,她百感交集,仇恨恶人之恶,质问苍天无情,同时强烈的求生欲支配着她不能妥协,不能倒下。对这一唱段的演唱,演员应有起伏较大的肢体动作,惊恐仇恨的眼神表情,强烈变化的情绪表现,由此才能传神地塑造人物,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与演绎出来。
(二)演唱融合实践分析
1.传统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在发声气息方面的相通相融
传统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有着不同的发声方式和音色表现,汉剧旦角演唱中多以小嗓发声,其音色尖细、紧绷,这样的发声方式会损害演员的声带组织,久而久之会缩短汉剧演员的演唱寿命。美声唱法讲究真假声的混合,其音色圆润、饱满、浑厚,且有益于保护演员的声带,而过度追求尖细、高亮音色的汉剧唱腔会使演唱者喉部、舌根出现明显的紧张感,有的甚至会在高音区破音,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究底在于对气息的掌控运用方式不科学。气乃声之本,运用美声唱法演唱汉剧,气息要契合声腔的变化,传统汉剧演唱强调气沉丹田,此与美声中腹式呼吸较为接近,随着声乐艺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得到更多艺术家的认可,汉剧演唱可借鉴该方法。首先,在演唱前要保持良好的吸气状态,打开喉咙,放平舌头,胸腹部自然扩张起伏,吸气量应在80%左右,吸气过满易导致气息堵喉部,呼气时要将气息送到咽腔,使气息一路畅通。比如对“咬牙关,挺胸站,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一句的演唱,该句首音处高音区,唱词速度快,即需做好演唱前的吸气工作,声带组织联合横膈膜共同发声,声音紧贴后咽壁。其次,在演唱中,要掌握蓄气、换气、偷气技巧,正确表现旋、转等字配的拖腔,气息要足量,气息通道要畅通,偷气换气要轻快吸气,胸腹协调配合,由此使气口自然且不突兀。
2.传统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在共鸣腔体运用方面的相通相融
演唱实践中共鸣腔体的运用直接影响着声响效果,汉剧演唱可借鉴美声唱法技巧来呈现高亢、通透的音色。比如演唱“血未干,黑压压”等词句时,这些乐句位于中低声区,要以美声唱法胸腹式呼吸来运用气息,打开畅通的气息通道,同时稳定喉咙,胸腔咽腔共鸣,以此来获得理想的声音。对于“报仇冤,雷电哪”等高声区乐句的演唱,要在前述演唱要求基础上加入头腔共鸣,放低舌根,如是发出的声音才能高亢同时不挤嗓。美声唱法中的胸腹式呼吸、共鸣腔体运用技巧等对汉剧演唱有丰富的借鉴价值与意义,藉此汉剧声腔得以优化,美感得到提升,汉剧可在新时期仍保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此外,汉剧声腔与美声唱法的融合不是一味地对传统唱腔求新求变,创新再造,而是要在融合的同时保留汉剧的传统意蕴与风格,此即需要美声唱法借鉴吸收汉剧唱腔的咬字吐字方式及方言运用特色。
3.传统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在咬字吐字方面的相通相融
汉剧演唱讲究依字行腔、字正腔圆,借鉴美声唱法进行演唱时,要同时注重汉剧的咬字吐字技巧方法。咬字联结着声音和语音,其与发音、口型等有直接关系,口腔运动要具有灵动性,发音要讲究位置的合理与准确。演唱者需按五音四呼发音规律来进行演唱发音,汉字发音对于每个字字头、字腹、字尾皆作出了要求,要咬字头、立字腹、收字尾。字头即五音所指的唇音、齿音、舌音、喉音、牙音,字腹指依韵母发音而划分的四呼,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字尾即收声归韵。在《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唱段中,“间”后有一长拖腔,拖腔演唱要始终保持正确的口型,清晰字的发音位置、着力点、收音部位,以防止咬字不清状况的出现。“间”字的演唱即要咬好字头“ji”明确字腹“a”,唱完后归韵至字尾n,对于“挺胸站”中胸字的演唱,要始终保持牙关打开,明确共鸣位置,快速咬好字头字腹,由此才能保证清晰明了地咬字吐字,且发声位置、气息与字的衔接不会出现断层。
4.传统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在方言运用方面的相通相融
汉剧有独具特色的语言运用方式,此对其传统风格意蕴的形成与展现有重要意义。在借鉴美声唱法来演唱传统汉剧的过程中,演唱者需熟悉汉剧使用的地方方言,在此基础上,运用美声唱法发音技巧、呼吸方式来演绎汉剧作品。比如对于前述唱段的演唱,即需听辨,模仿其武汉方言发声方式。武汉话属西南官话湖广片,其音调由平声、上声、去声组成,较为高亮,平声又涵盖了阴平声与阳平声两种类型,阴平声、阳平声、上声、去声分别对应普通话的第一、二、三、四声调。武汉话是典型的四声语言,在唱段中,依方言发音,昏沉沉之“沉”读作cen(上声),“只觉得”之“觉”读作jio(阳平声),“关黑牢”之“黑”读作“he”(阴平声),“分不出”之“出”读作qu(阳平声),“那是雨”之“是”读作si(去声)。武汉方言以平舌音来读翘舌音,美声唱法借鉴方言可保证汉剧的原汁原味与传统特色,使其独特的风采与魅力得以沿袭和展现。
四、结语
汉剧唱腔与美声唱法产生于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之下,它们有着诸多差异,同时又有很多相融相通、可互为借鉴之处。伴随着我国艺术的薪火相传,二者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为传统汉剧在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之力。汉剧唱腔运用美声唱法的呼吸方法和发声技巧可有效提升自己的音色美感,使声音更为圆润饱满,柔和典雅,汉剧的艺术魅力由此得以更好地彰显,这既是对传统戏剧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突破。
———汉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