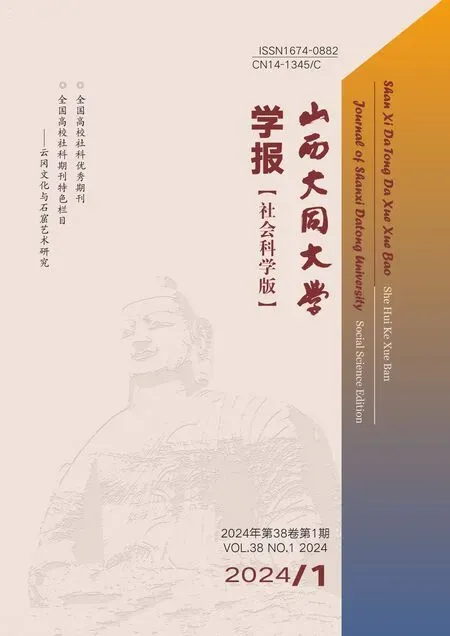流动、传承、变革:“跨大西洋”关系的文学重构
谭源星,王影君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起初,“跨大西洋”关注英国与美国之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重纽带,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1](P16)随着对大西洋两岸地域认知的扩大,研究者的兴趣也从最初聚焦在英美关系转变为欧美(美国)关系、非(非洲)美(美洲)关系上面。2001 年,“跨大西洋协会”(Transatlantic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旨在系统、综合、深入地研究大西洋两岸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结。国内学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关注仍然集中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畴内,主要围绕当下美欧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研究成果包括《“跨大西洋联盟”回得来吗》[2]《拜登任期,欧洲寻求重塑跨大西洋关系》[3]《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与前景》[4]等论文。有关大西洋两岸的历史、文学交流,只在比较文学中有零星涉及,但尚未有关于“跨大西洋文学”的系统论述。
作为一个“跨越”的概念,“跨大西洋”里的“跨”(Trans)应该放在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去讨论。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中,“跨”是必备的特性。它要求研究对象需要具备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条件;其中,跨民族是最根本的标准。[5](P7)可以说,比较文学为“跨大西洋”研究在文学领域找到了落脚点;“跨大西洋”也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语境下的可能性。如果说“跨大西洋”作为政治概念更关注当下问题,那么“跨大西洋”的文学身份则把视角的中心放在了历史问题上,将大西洋两岸的文学连接置于一个庞大、系统的地图中。
一、“跨大西洋”研究的文学意识
早在2001年,保罗·贾尔斯在专著《大西洋两岸的叛乱: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学的形成:1730-1860》[6](P70-99)追溯了英美文学从1730 年到1860 年之间的矛盾关系,探讨了美国文学传统是如何在与英国文化的谈判中形成的,肯定了英国文化对美国文学身份尤其是独立战争后的身份确立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贾尔斯的另一部著作《虚拟美洲:跨国小说与跨大西洋想象》[7](P22-87)再一次把美国文学放置在陌生的英国文化语境中,建立起英美文化的跨洋对话和谈判。相比第一部著作,这本书更为成熟的地方在于,贾尔斯试图从文学身份扩展到国家身份,论证美国国家身份的建立是通过排除对大西洋彼岸的想象而产生的。这部典型的跨大西洋文学研究著作以小说为研究体裁,以“国家身份”为中心话题,从传统参量(traditional parameters)以外阅读美国文学历史,在关注焦点、研究内容和对象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与前两部著作关注文学身份问题不同,贾尔斯的《大西洋共和:英国文学中的美国传统》试图打破限制性的民族主义,揭示英美文学相互包容又敌对的关系。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早已将英国文学从英语语言文学中分离出来,将纯粹的英国文学重新定义为后帝国主义框架内众多竞争话语之一。美国文学是被英国文学深刻吸引同时又心生厌恶与排斥的异种,它在英语世界制造混乱, 引发矛盾,并企图在传统的、安全的、已知的世界中制造一个更纯粹、危险和未知的世界。[8](P127)英国保守的批判思想很容易被美国方言同化,这一结果又进一步鼓舞美国作家努力重塑自己的身份。
基于贾尔斯对英美文学关系的认识,2007年苏珊·曼宁在其主编的《跨大西洋文学研究:一个读者》[9](P28-59)中提出了如何将跨大西洋模式在文学研究中发挥最大作用,围绕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议题,进行文学作品的解构与重构。这部作品是跨大西洋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部学术批评论文集,也是首次将跨大西洋研究放在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中进行探讨的编著。在反思跨大西洋文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2011 年,曼宁主编的另一部著作《跨大西洋文学研究,1660-1830》[10](P106-138)聚焦美洲殖民和国家政治分离后的时期;系统定义了“跨大西洋文学研究”的含义及其对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跨大西洋文学流派、生平写作、文学新闻、海洋文学、历史小说、浪漫主义、哥特小说等方向扩大了“跨大西洋文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同年,贾尔斯出版了《美国文学的全球重新定位》,[11]通过对比18 世纪与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文学,论证了美国文学只在内战后才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主义实体。贾尔斯认为,美国文学史是一部动态的、变化的、受不同语境影响的历史。曼宁与贾尔斯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贾尔斯把美国文学视为一种成长型文学,从接纳、吸收、怀疑到批判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一种自我满足、自我教育的模式,强调美国文学的动态发展。相反,曼宁在对待美国文学身份的问题上,先是设置了一个公平的“跨大西洋”模式,然后再将民族、殖民等问题平等地嵌入大西洋两岸的地域中,进行某个特定时期的静态比较,更关注历史的偶然性。
此外,伊芙·塔沃尔·本尼特在《跨大西洋故事与阅读历史,1720-1810:移民小说》中通过印刷文化构建了一个大西洋世界,融入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大西洋世界的不同看法,从弱势群体(比如女人、仆人、穷人、无权力者)的故事的编辑、出版、改写、重编等变化,探讨了为适应变化着的读者、时代与环境,大西洋两岸的出版商做出的巨大努力。[12]本尼特对书信体裁也有过系统研究,2005 年和2008 年分别出版了两部跨大西洋书信指南的著作,[13](P54-94;47-174;295-352)通过书信语言构建出跨大西洋两岸不同的文化观与价值观。和本尼特相似,鲍勃·尼克森也关注了跨大西洋出版历史以及19世纪以来的数字化趋势对英美文学关系的影响。[14](P163-174)
二、“跨大西洋”视角下的文学批评成果
不难发现,在历史观的引导下,21 世纪前二十年学界对“跨大西洋”文学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1.跨大西洋语境下文学的身份批评,尤其是美国文学的身份建立问题。2.跨大西洋语境下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女权运动、后殖民、生态等。3.跨大西洋语境下文学的审美与语言批评:文体类型、文学主题、(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可以说,“跨大西洋”这个概念像一个巨大的载体,为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语境,使得文学批评本身具备了比较性、互文性的特征。不过,这三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和讨论深度依旧存在不一样的特点。
在文学的身份批评方面,跨大西洋研究重新审视了美洲的原著民文化,还原了印第安文明被入侵、反抗、最终被融合的过程。例如,凯特·弗林特的《跨大西洋印第安人,1776—1930》[15](P26-85)和马克·里夫金的“跨大西洋印第安问题”[16](P337-355)都对传统的印第安文化在英国文学中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被利用做了解释。其实,印第安形象作为一种美洲本土象征,最初是为了帮助英国定义其自身身份。但随着美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印第安原著民反而变成了一种身份不确定的“特殊”族群。有着印第安血统的美国作家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身份,成为文学作品中印第安人是否接纳自己为‘美国公民’的热点写作。也就是说,美国文学身份的建立经历着印第安血统和欧洲移民血统的不断碰撞,并且始终被种族歧视和种族消融所影响。正是由于美国文学身份的特殊性,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印第安人”和“美国人”的形象才会一直被期待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中,跨大西洋语境重点关注的是殖(移)民、女权、生态这三个议题。和之前的身份问题不同,“殖(移)民”议题强调的是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的原著民到达美国后的身份尴尬问题。美洲殖民地的开拓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发展,促使美洲出现了一批非裔美国文学。文森特·卡雷塔就非裔美国文学中的著作权、国家定义、种族话语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解决这个作家群体的归类问题,首先需要设身处地想象一下第一代在美国的非洲黑人作家的地位问题,英语是否为母语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可以被定义为非裔美国人。[17](P11-24)也就是说,非洲血统在美国的身份确立必须首先完成原始语言的消融。其实,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早在到达美洲之前,黑人的身份就已经因为被迫离开居住地而变得尴尬起来。保罗·吉尔罗通过《黑色大西洋》描绘了运送黑人奴隶的船只是如何成为大西洋黑人文化的缩影。这种文化并非纯粹有关民族或种族。跨大西洋文学研究涉及复杂的移民和殖民问题,必然会导致新大陆居民对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产生怀疑,有了亟需重新定义族群身份的渴望。对身份的重塑不仅因为殖民问题,还因为美国文化与欧洲传统文化的矛盾,包括个人主义的发展等。《“种族”与“文化”之间:英美文学中“犹太人”的表现》[18](P41-42)分析了犹太人在英美文学作品里的地位差异。犹太人在英国文学中是“饥饿困顿”(hunger-bitten)、胡子拉碴(beard⁃ed)、甚至会带来黑死病的形象。伍尔夫、舒特、艾略特和庞德在各自的作品中痛斥犹太人的存在,试图从精神上驱逐犹太人,并将他们与肮脏的身体器官联系起来。而在美国文学中,约翰·贝里曼则认为,被人认作犹太人没什么不好的,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马克·吐温在1898 年有关犹太人写作中也对犹太人采取了更加友善的态度,并且不再把犹太人和疾病绝对联系起来,至少马克·吐温认为他们是具备公民责任感的。犹太人之所以在跨大西洋两岸的形象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19 世纪犹太人的解放与美国肤色矛盾有联系。欧洲人的反犹主义建立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目的是为消灭欧洲人未知的非我。而在美国,一方面基督教传统没有欧洲大陆坚固;另一方面,种族问题实际上被肤色问题转移了,加上犹太人能够参与到19 世纪美国的工业生产中,并利用西进运动和内战前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在军事、金融等领域扩大影响力,因此,美国社会总体来说对犹太人更加宽容。
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范畴内,跨大西洋语境也关注女权主义下的性别身份问题。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和女性文学人物的存在焦虑是女权运动在跨大西洋文学作品中的集中体现。路易莎·霍奇森把《小妇人》置于动态的跨大西洋交流中,通过小说中对社区(community)的虚构来反映女性作家是如何尝试构建更大的历史社区,[19](P1-14)探索女性作家与跨大西洋社区的关系,以及女性作家的性别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或限制了女性作家的文化输入。从19 世纪开始,美国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比如悲剧的穆拉塔(mulatto)——一个迷人却无法融入黑人与白人社会的混血女人,最终沦为了有色人种的牺牲品。她其实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悲剧的缪斯(muse)这一女性形象的延续和传承——同样充满异域特征的犹太女演员,却被定义为“堕落的女人”。她们都反映了女性身体在19世纪大西洋两岸被情色化、种族化、商品化的过程。由此可见,女性文学在美国的崛起从多方面展现了女性作家对英国甚至整个欧洲传统父权的挑战。女性作家名声的建立逐渐成为美国社会衡量进步的标准,类似犹太人在美国文学中形象的改善,这种趋势实际上宣扬了美国在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民族品位与能力上的优越感。
在生态问题方面,跨大西洋语境重点审视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海洋运输、殖民贸易带动了皮毛、木材生意,改进了农业等,引发了两岸文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再思考。关于环境保护的文学叙述,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都成为跨大西洋生态研究大量探讨的主题。在《跨大西洋文学生态:19 世纪大西洋英语世界的自然与文化》[20](P73-119)一书中,英国浪漫主义时代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冲突、维多利亚时代自然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演变、绿色浪漫主义对美国作家和美国读者的影响,成为跨大西洋区域生态流动和生态传递的热点问题。可以说,“跨大西洋”关系让生态批评首次在跨区域的广度得到关注与讨论,开启了生态批评与跨大西洋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补充,强化了“生态系统无国界”的意识。在漫长的19 到20 世纪,欧洲环境意识的有关文学实践在美国本土的接受和批评、英国与美国对自然世界的表现方式,成为跨大西洋文学背景下文学交流的关键方式之一。
抛开社会历史批评,跨大西洋语境在审美与语言批评范畴内的讨论,恰恰又兼顾了文学本身的意义,避免了文学完全变成心理学、社会学的工具。玛西亚·阿布勒将小说文体作为跨大西洋文化连接的元素,从小说的阅读、翻译、传播(贸易)三个方面,论述了19 世纪欧洲文学在巴西的影响,企图建立起巴西与欧洲的文学历史桥梁。[21](P15-38)阿布勒尤其强调用民族语言书写的文本的传播。他认为,民族语言文本放在跨大西洋语境下,就不再是对单一国家的讨论了,目标读者对小说的传播,对打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起决定作用。阿布勒在语言批评范畴内的尝试,让跨大西洋文学研究首次系统地跨越到了南美洲的领地,对于拉美文学在欧洲大陆的身份构建有开拓性的意义。除此之外,历史小说、哥特小说、自传小说等不同的小说类型,戏剧、表演、新闻等其他文学体裁在大西洋两岸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传播与演变。同时,跨大西洋语境重视“海洋”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欧洲大陆早期的大西洋殖民运动为美国移民后代积累海上生活、探险生活的经验提供了先例。跨大西洋海洋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海盗威胁、船舶搁浅、船员溺死等航海事件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为海洋旅行小说、科学发现散文、海上劳动颂诗的写作提供了新素材。
总的来看,跨大西洋语境一方面让文学作品找到了跨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依据;另一方面也让跨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在文学中得到了艺术表达与呈现。跨大西洋语境由大西洋连接起两岸大陆,更多地考虑外部因素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学特征的塑造作用。目前国际学界重点关注的是跨大西洋关系在19世纪是如何打破性别、种族、国家和文化的等级模式,通过可塑性主体与有关阶级、奴隶制、自然知识、民主、宗教等主题的互动,挖掘出美洲本土文化、宗教在英国和欧洲文学话语中的表现,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英美文学之间的传递(trans⁃fer)和延续(continuance)关系提供更庞大、更多重、更混合的想象空间。
三、“跨大西洋”范式下新的想象空间
现有的研究通常把“英美”(Anglo-American)关系等同于“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关系,事实上,英美关系是包含在更广义的跨大西洋关系中的。跨大西洋为欧洲、非洲、南北美洲文学搭建了沟通的桥梁。21世纪20年代以后的跨大西洋研究需要更兼容地去探讨洲与洲的关系,并将各种关系理论化,在流通(circulation)和交换(exchange)的新概念(有别于此前的传递与延续关系)下,将“跨大西洋”语境发展成一种方法论。
比如,在体裁的选择上,需要关注除小说之外的散文、诗歌等题材的跨洋交换。约珥·佩斯曾在浪漫主义“想象力”这一话题下探讨过非裔美国诗人菲尔斯·惠特莉和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诗歌的互文性,但局限在奴隶贸易下的人权想象。[22](P113-123)他将想象力解释为“意象—国家”(Imag-I-Nations),导致意识形态掩盖了诗歌的艺术性。梅雷迪思·麦吉尔和托拜尔斯·梅勒里也从经济贸易文化和废奴主义等移民色彩语境对诗歌进行过解读,[23](P37-80;55-78)但忽略了诗歌本身的语言艺术在历史传递中的变化,也未从诗歌语言本身传递的历史信息中进行阅读。对跨大西洋诗歌艺术的兴趣,是近年国际学界对英国文学遗产在美国的接受与批判的研究的一种延伸。弗吉利亚·杰克森试图找到英国古老诗歌流派(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应如何通过海洋航行,运用科学技术,流传到另一个大陆并成为活着的诗歌(living poetry)的方法。杰克森举例了英国传统民谣(ballad)、挽歌(el⁃egies)、颂歌(odes)等不同诗歌形式在19 至20 世纪美国的发展状况。[24](P157-164)这种把传统诗歌流派代表的文化与美国新意识相结合的尝试,有利于消除维多利亚诗学与美国诗学的分离,丰富了跨洋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在跨洋诗歌互文关系的探讨上,马克·桑迪(Mark Sandy)避免了过多的政治参与。他在“美国书写”一文中说到,尽管济慈从未去过美国,但在美国文学中的想象力却不曾减弱。[25](P300)作为具有高度感知力的诗人,尽管跨越时空,济慈和狄金森的诗歌经常在理论和情感上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是狄金森作为被贬低的女性诗人的身份,对济慈作为下层中产阶级诗人的身份被当时主流诗人团体排外的共情。不被当时主流诗界承认的济慈和狄金森,在怀疑声中清理出自己的空间,对自我(the self)和他者(the other)的关系站在生存哲学的角度进行再思考,从而产生了极具共鸣的身份焦虑。
在文学与文化的产出上,新的跨大西洋研究需要更关注过程中传递性(transitive)的、循环的、偶然性的经历。跨大西洋文学研究的初衷是以美国文学为中心,发掘欧洲大陆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现有的文献已充分展现出欧洲文学、英国文学对不同时期美国文学的塑造。然而,因为他们思索的起点在美国,是站在美国文学对欧洲文学“要”的角度而非欧洲文学对美国文学“给”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未形成“跨大西洋”的传递意识。比如,维多利亚文学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在英国本土就是一场浩大的革新。这一时代产生的生态问题、阶级矛盾、性别冲突、民族纷争等对美国本土文化的主动冲击是非常显著的。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短篇小说《公证人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与英国维多利亚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虽然律师角色的说话方式、叙述表达、思维模式是高度相似的,但在讲述司法制度腐败的根源和人物被异化的原因上却是完全不同的。[26]这种相似性源自作家相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而差异则是时代、地域、社会背景不同的产物。巴特比从始至终面对的就是针对其个体的“高墙”(the walls),在他被异化之前就已经被社会孤立了,作品中的人物从一心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取悦老板、奋力进取的辛勤劳动者转变为看不到工作意义、看不到未来前景的失望者。但是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劳动者们是被孤立的整体,没完没了的法律案件让所有劳动者都深陷法律系统的斗争中,以致耗尽所有的精力和财富。在两部作品里,人物被异化过程的差异需要从英美社会矛盾的差异去解释。狄更斯所处的工业革命时代更多聚焦的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即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而麦尔维尔呈现的是个人与整个社会环境的矛盾,这是因为美国当时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刚崛起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个人生活领域产生了重大冲击,对个人尤其是劳动工人的忽视改写了个人在社会当中的存在模式。这种传递性、偶然性的文学人物的经历,需要跨大西洋文学用全球性的变化着的视角去感知。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新的跨大西洋研究要尝试改善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边缘地位,避免在文学研究中出现某种“中心主义”。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虽然审视了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和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对帝国主义国内经济模式的塑造和生活品质的刻画,为去殖民文化和新政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显然某些章节的政治色彩仍然过于浓厚。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界定问题上,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文化现象,作为西方文化的欲望对象而出现,隶属于欧洲文化;而美国则是超越欧洲所有国家、最具影响力的超大国,具备文化主导的能力,这明显受到地域中心论的影响。[27](P70)在新的跨大西洋文学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需要隐退,在美国讨论欧洲,或在欧洲讨论美国,才能让跨大西洋文学研究保留多元文化的特色。
科琳·格伦尼·博格斯(Colleen Glenney Boggs)在对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则非常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地位的平衡。她定义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对大英帝国殖民范围内的非洲大地的两种想象。第一种想象是殖民文化下的移民、殖民和基督教黑奴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构建出来的;第二种想象则建立在现代散居黑人回忆中的群体意识中。不过,博格斯的视野不光停留在文学作品本身,更从作品延伸到与跨大西洋浪漫主义有关的性别政治、奴隶贸易、种族主义等其他问题上。她认为,跨大西洋提供了洲际种族构建的空间,为支持奴隶制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而跨大西洋背景下的殖民活动又为一部分黑人和白人作家建立超越种族差异的文化乌托邦提供了支持。同样,这也适用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印第安社会。美国本土文化其实是放在被种族化了的语境中去阅读的,这非常影响美国作家的写作风格。“跨大西洋浪漫主义”研究是一个交错复杂、需同时着眼全球(global)与地域(na⁃tional)文化的话题。同时,也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如何主导文学分析——应该强调作者和文本或者历史和地理,还是种族和性别?[28](P231)这些偏好的选择将直接塑造或重塑我们的研究对象。其实,关注跨大西洋文学的历史、政治问题时,可以运用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保留不同文学作品的民族性,又避免“文学”或“文本”始终处在边缘、参考位置。
四、结语
跨大西洋语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想象,促进了大西洋两岸文学作品特征的概念化,为现代文学批评中关注的种族、殖民、性别、生态问题呈现出新的研究范式。跨大西洋文学不仅关注跨洋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关注自然生态文明,重新看待人类与动物种群的脆弱性,将殖民运动给土著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联想到农业发展与城市化造成的生态问题对本土物种生存的威胁,为讨论19世纪土著民和本土动植物的环境意义创造了新的空间。由于跨大西洋叙事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它更新了对种族、性别的理解方式,模糊了外来人与土著人、土著生态之间的界限。回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上,“跨大西洋”文学要守住文学研究的边界,避免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不要让文学本身陷入身份危机中。[29](P11-17)现当代文学理论已经有将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方向转型的趋向:解构主义将文学向符号、修辞学上引导,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将文学向社会学上引导。文学作品中的读者与作者接连死亡,这些现象值得我们警惕。跨大西洋文学研究的意义之所以区别于跨大西洋研究,就在于它是从文学本身出发,最后必须回归到文学当中。任何脱离文学作品的讨论,或者仅把文学作品充当背景而不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都应该归为跨大西洋研究而非跨大西洋文学研究中。跨大西洋文学研究学者,必须权衡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让文化更好地为文学服务,不应该顾此失彼,或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