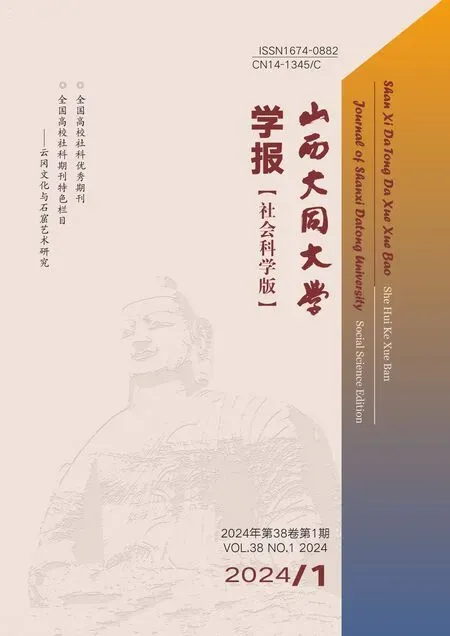中国青春电影中“萌”元素对大学生的美育影响
杨伟祺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由青年人群构成的观影群体已经成为中国观影市场的中坚力量,在青年群体之中,00 后大学生在观影群体结构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在青年人最为热衷的审美对象中,基于二次元文化的“萌”元素无疑是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特别是在国产青春电影中的“萌”元素运用已经受到广泛关注。“萌”元素凭借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强大的商业属性在国产青春电影中很快掀起了浪潮,它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介入过程和形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那么“萌”元素如何在中国主要观影群体的审美中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土壤中适应变化?它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融入给重要目标群体的大学生带来了怎样的美育影响?本文将通过梳理“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流变及表现特征,探讨青春电影中“萌”元素对大学生的美育影响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表现特征
正如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发展规律一样,“萌”元素这一外来二次元文化的亚类型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发展也经历着本土化的流变趋势,本土化就是努力发掘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同点,构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拉近外来文化与本国受众之间的关系,使本国受众更加乐于接受外来文化。[1]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先去“由外而内”地翻译它,而后才能够“自下而上”地收编它。[2]因此,“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渗入也经历着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流变过程。“萌”元素作为由青年网络用户所构成的亚文化群落的重要审美对象,在中国电影审美形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且随着中国观影主力群体年龄的不断下沉,青年网络用户群体已成为影响中国电影文化和审美趣味的新势力。[3]正如姚斯所说,“艺术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消费,而是显示赞同与拒绝的审美活动。”[4]因此,市场和观众的口味与期待反作用着电影内容和风格的变化。青春电影中的“萌”元素也在迎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中产生流变,并主要呈现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表现方式,主要存在三种基本特征。
(一)“萌”元素的硬植入 在日语词源中,“萌”大致有小而可爱的意思。[5]与传统审美体系不同,“萌”更多的是形容一种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标准,因此不同的人对于“萌”也有着不同的评判。[6]在电影世界中,“萌”元素可以通过不同的层面和手段表现,如ACG 形态的拼贴和剪辑、人物形象塑造的“萌”气质、以及在剧情推进和冲突营设中的“萌”处理,都是“萌”内涵或深刻或浅层的渗透表现。由表及里来看,如ACG 形态的拼贴剪辑和角色外形“萌”化等表面文章,都属于“萌”元素的硬植入。[5]这也是作为外来二次元文化融入本土文化产品的第一步骤。
在这一阶段,“萌”元素的体现在角色的外形之上,直观地将二次元文化中的“萌”形象嫁接在了青春电影中的三维人物上。比如黑亮浑圆的大眼睛和透露出的纯真眼神;清瘦身材的“卡哇伊”美少女形象;美丽温柔又纯洁的少女式美男子耽美现象等。[7]这种外形的硬植入方式是“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应用的初级手段,也是为了迎合庞大的二次元消费群体,抓住巨大的商业机遇,甚至将电影中的“萌”元素当作电影宣传吸睛的噱头而采取的原始快捷方式。[5]因此,在巨大商业利益的浮躁驱使和初期不成熟的运用方式下,“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初期形态是以硬植入的方式显现。在电影《小时代》中,杨幂、郭采洁等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场景中穿着类似日本动漫中的校服,在外形、表情、动作等表面形态上透露出小女生式的可爱和“萌”特征,且此类型的“萌”表现没有作用于剧情推进和冲突营设中,仅在人物外部表现中具有体现。虽然影片及相关场景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萌”植入带来了票房上的成功。[5]
在一些电影中,“萌”元素的表现以ACG(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电动游戏)形态拼贴剪接的形式呈现,这也是一种硬植入的呈现方式。电影《匆匆那年》中对经典日本动漫《灌篮高手》中若干场景的交叉剪辑以及对于后者主题曲的借用,是二次元及“萌”元素在片中的直观呈现。[5]同样用法还出现在电影预告片中各主要人物在滑冰场场景中的动漫肖像拼贴剪接。这些画面的使用对于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以及叙事结构都没有产生实质的作用。换句话说,假设去掉以上画面的拼贴也不会对影片整体的情节和叙事产生影响。所以这些画面的运用更多是为了唤起特定受众的情感记忆。[4]“萌”元素的拼贴场景在影片预告片中的运用,也印证了“萌”元素在当时电影市场中的吸睛引流作用。
此外,外形上的“萌”也会通过演员的选取得以实现。“萌”的特质与偶像派“小鲜肉”演员的外型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此类型演员柔和娇贵的面容给角色的外型带来天然的柔和感和“萌”质感,这种柔和感易激起人的保护欲,带来人心理上的安抚和暖意。[8]特别是男演员带来的这种柔和感,容易给人带来更加强烈的暖意和安稳感,如《重返20 岁》中鹿晗饰演的项前进和《左耳》中杨洋饰演的许弋,都是演员为角色带来的天然“萌”质感。这个时期青春电影中的男主角形象与中国传统意义上青年男性硬朗的审美形态产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这种运用方式已经开始将“萌”元素融入到角色的塑造设定之中,由硬植入的方式渐渐转变为内化融合的形式。
(二)“萌”元素的内化 虽然“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介入是基于迎合庞大的目标消费群体和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但在影片提质和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持续抓牢受众眼球,克服审美疲劳,更加迎合目标受众群体的审美,“萌”元素的运用也由简单的表面硬植入走向对人物塑造、剧情推进、矛盾营造等内化运用阶段。[5]
人物塑造方面,将“萌”元素巧妙隐藏在人物性格和行为模式设定中,而不仅是浮于形象外表,这是“萌”元素内化的重要表现。“萌”文化所对应的各种审美对象的类型,如“萝莉”“软妹子”“男闺蜜”等已频繁地出现并成为现时中国青春电影中的主要角色类型,并深度介入甚至改造青春电影的人物设定。[5]比如在2016 年上映的国产电影《中二病少女要拯救世界》中,片中女主就是一名被设定为“中二病”人设的人物。[9]这一设定被由内而外地表现,并决定着她做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这种设定下,“萌”元素被深度融合在人物的性格特征中,并影响其行为模式和后续剧情的发展。
剧情推进方面,“萌”元素的介入使新时期中国青春电影较传统意义上青春电影有了明显不同。“一个叙事均由一个状况开始,然后根据因果关系的模式引起一系列的变化”[10](P90)剧情通常总是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和矛盾冲突中推进的。然而“萌”元素作为二次元文化的一类亚分支,它的渗入给电影剧情推动的关键节点提供了新的处理方式。导演徐纪周曾在采访中谈到,自己本身是一名游戏宅男,受二次元文化的影响,他在作品创作之中就尝试将“打怪升级”的游戏叙事方式带入到作品的叙事中,用“打怪升级”式的剧情让冲突不断强化,使矛盾不断升级,以此推动剧情,直至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9]在《滚蛋吧肿瘤君》中,就拼贴了主人公进入一个由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和“CS 枪战”幻化出的世界,这种拼贴并不是硬植入的剪接,而是对于剧情推动具有提示意义的片段。影片在熊顿首次昏迷住院时接入了打斗僵尸的游戏式场景,众多袭来的僵尸代表病魔,这些僵尸被主人公一一消灭预示着病人在此次斗争中击败了病魔即将从昏迷中苏醒,最后从游戏场景中打向僵尸的一拳跳回并打到现实病房中的梁医生,也引出了接下来熊顿和梁医生之间会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萌”文化所代表的二次元文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风格介入并影响电影的剧情推进。
矛盾营造方面,“萌”元素在青春电影中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冲突的激烈性和严肃性,以“萌”的内涵软化了矛盾冲突的棱角,转而以一种阳光、柔和的方式处理矛盾关系,从而推动剧情发展。[5]纵观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无论是在20 世纪30 年代,以青年人为表现对象,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影片《马路天使》《神女》等;还是在17 年时期展现建设祖国的青年热血风貌的影片《我们村的年轻人》《战火中的青春》等;或是改革开放后展现时代与个人风貌的影片《快乐的单身汉》《顽主》等;甚至如新世纪以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等青春影片,都展现了在时代背景的大潮中,青年一代的记忆或伤痕。[11]由此可见,中国内地青春电影一直具有两个总体的特征,一是紧密联系社会时代背景,二是具有伤痕色彩和残酷性。然而在“萌”文化渗透下的新时期青春电影,却消解甚至颠覆了中国青春电影一直以来的残酷性。“萌”元素的渗入让电影整体的叙事套路和风格色彩显得阳光柔和。电影《闪光少女》是证明这一观点的最佳例证,《闪光少女》以二次元的美学风格、清新的气息颠覆了以往青春电影中“疼痛、怀旧、爱情”的幽暗伤感色调。[12]在影片的发展脉络中,共能够梳理出十五次矛盾营设,在这十五次矛盾营设中,仅有一次在二点五次元组合内部面临瓦解时成员间的冲突是略显激烈和严肃的,剩下近乎所有的矛盾营设都是以一种诙谐、柔和、洒脱的方式化解推进。在女主角陈惊表白王文师哥被拒绝并被当众讥讽后,虽然也在流泪伤心,但她还是面带微笑洒脱地留下了“等你回想起十七岁,肯定比我们后悔”的豪言壮语,而后和好朋友李由相视一笑,洒脱地弹掉脸上的泪水。这样阳光洒脱的矛盾营设一改多数青春电影中失恋场景的悲伤、坍塌、甚至堕落,以一种阳光的方式演绎矛盾,塑造年轻人的朝气和洒脱。影片这种矛盾营设也正是与影片“萌”表现和相应叙事线索的呼应,是“萌”文化中阳光积极的内涵在影片中的内化表现。
(三)“萌”元素的本土化 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介入和影响越来越深刻,同样其自身也在逐渐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和观众的欣赏趣味,克服在中国影视环境中的水土不服。因此,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将“萌”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使“萌”元素本土化,在中国青春电影中提升生命力和好评度。
其一,创作者将“萌”元素与本土文化元素相缝合,使“萌”元素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进行叙事发展和审美突围。[3]电影《闪光少女》中就讲述了几个热爱二次元文化的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传统民乐在与西洋乐的比拼之中由颓势扭转为胜局,并最终与西洋乐和谐共存,共同繁荣。角色千指大人、贝贝酱、塔塔酱等由内而外透露着“萌”气质和对二次元的身份认同,但她们更从心底深深热爱着民乐,民乐代表的民族文化和“萌”气质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在此处形成了一致。[2]影片的主题更是通过二次元的外壳进行了一场民族文化的弘扬,这是一种“萌”元素根植中国文化土壤,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的全新话语体系。[13]
其二,将“萌”元素作为一种载体,用它去表现表达优秀本土文化的内涵实质。“萌”元素中柔和的内涵可以作为一种美学表现去表达传统儒家思想中“大同”“和谐”的观念,把尖锐的矛盾变得平和。[8]在电影《闪光少女》中,代表“萌”气质的陈惊、李由一众在完胜西洋乐群体之后,他们作为胜者并没有展现出如西洋乐群体在平时咄咄逼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包容友好和尊重对手的态度选择与对方进行合作,最终达到和谐以待,共生共荣的局面。他们无论是从行为举止的“萌”,还是处理冲突矛盾时的态度,都传递出传统文化中和谐包容的精神内涵。
其三,随着中国二次元文化接受群体数量的增长,以及二次元元素在电影中更多的运用,“萌”元素作为二次元文化的分支,它在影视作品中的呈现也开始受到更多观众的包容,对它的欣赏不止是二次元控的专属,它在电影中的运用也渐渐不被大众视为异类。“萌”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分支,渐渐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特别是在青春电影中更是如此。“萌”对于受众来说更多存在于主观感受,而不仅是客观的客体样貌,它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已超越了二次元文化的受众传播范围。[14]电影《闪光少女》的情节很好地印证了“萌”元素以及它所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在本土化进程中的适应过程。通过传统民乐的缝合,陈惊由开始对二次元的毫无了解到最终也开始接受并喜欢二次元,李由从开始不敢暴露自己是一个二次元控的身份到最终大胆袒露自己对二次元的热爱;在与传统民乐的结合下,很多对二次元抵触的中老龄群体,也开始改变他们原有的态度。这些都暗示了二次元作为一种外来亚文化逐渐受到更多人的接受和包容,并逐渐适应成为大众文化之一。同时也说明了“萌”元素只有与中国文化土壤相适,适应本土化文化需要,与电影作品有机结合,才能够获得中国电影观众的认可。
“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本土化的进程很快,并表现出这三种典型的特征,从《小时代》等作品的硬植入到《闪光少女》等作品中“萌”元素的内化以及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也仅有4 年的时间差距。虽然带有“萌”元素及二次元文化的青春电影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它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在中国青春电影和主流文化中的适应速度也令人称奇。诚然,这与当代中国观影群体的结构是有密切关系的,根据《2022 年中国电影年度产业报告》,20—30 岁的男女性是目前电影市场中购票的主要群体。[15]同样《2021 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2021 年的电影观众结构中,00后年龄的群体占比19%,而2020年的比例是10%。[16]以上数据都表明了青年人在观影人群结构中的主导力量,以及观影群体的持续年轻化。大学生群体作为00 后年龄段群体的重要力量,观影活动对于他们有着不可忽视的美育作用。加之大学生作为“萌”元素所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和青春电影的重要目标群体,研究探讨青春电影中“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美育价值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萌”元素在近十年来中国青春电影中的应用展现出了很强的活力,由表及里的本土化演变趋势也让“萌”文化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土壤上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然而,“萌”文化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和更倾向于消费性的文化,它在青春电影中的应用也始终受到学界和观众褒贬不一的评价。因此,对于青春电影中“萌”文化对大学生的美育影响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应该辩证性地看待。根据研究,青春电影中“萌”元素带给当代大学生的美育影响既有值得肯定的积极价值,也有应令人警惕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二、青春电影中“萌”元素的积极影响
(一)满足了当代大学生的审美需要和心理诉求 正如“存在即合理”的哲学论断,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乎逻辑的一面。带有“萌”元素的青春电影能够在大学生群体中受到欢迎表明了它在这个群体中具有合理性。以“萌”文化为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在青年互联网用户群体中有着非常庞大的受众,特别集中于12-30 岁这个年龄段,它能够给受众带来一种遁世隐居的快感和柔和温暖的舒适感,借此来回避现实的社会压力。这种“萌”的感受给人带来了纯粹、简单的纯爱感受,具有一种童话般的美学气质,让观众在繁芜嘈杂的三维世界里寻找到一种纯真的审美体验。[5]这种“萌”文化给稚气未脱而又初尝压力的00后大学生带来了他们心灵深处所需要的安慰和纯真。因此,青春电影中的“萌”元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期待的美学需要和心理慰藉。
(二)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审美多元化发展“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呈现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青春”概念,在中国青春电影的发展历程中,青春的印迹是忧伤的、遗憾的,甚至是残酷的,是在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个人成长剪影。然而,在“萌”元素内化下的青春标签是阳光的、柔和的、没有大喜大悲的,它带来的是一种纯洁美好的畅想。“萌”元素输入的是一种能够治愈人心的、缝合大众在生活和情感等方面不悦心理的审美价值。[17]这给大学生带来的对青春的审美态度和回忆是美好而不留遗憾的。
“萌”文化在与中国青春电影的结合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思维的对话与碰撞,这种文化的碰撞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本土文化的繁荣有着积极意义,是利于大众审美多元化发展的。“萌”元素在青春电影中人物塑造上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电影中男女形象塑造的固化模式,弱化了性别二元对立的两性气质和关系。[5]比如在“萌”元素的影响下,男性的形象变得柔和娇贵而非阳刚硬朗,甚至有些“娘娘腔”,这里且不论这种性别塑造模式的褒贬与否,至少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与审美形态。
此外,“萌”文化所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在青年人群体中的消费性和娱乐化属性代表了青年草根们的娱乐愿望,是一种平民化、世俗化的特质体现。在审美的领域内,不仅应该有高雅型的艺术,也应该存在具有平民精神、商业价值和大众属性的世俗文化,这样的汇集才是一种能够产生多重意义和多元审美的公共空间。[18]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应该在这样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空间中去杂糅训练他们的审美能力。多元化审美的锻炼对于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创新活力,促进文化创新有着积极意义。[19]
三、青春电影中“萌”元素的消极影响
“萌”元素所带来的柔和感,能够让人获得短暂逃避现实的舒适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生沉溺于这种“萌”的柔和与幻像中,也会让他们形成逃避现实的认知惰性。“萌”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消费主义,是一种让人轻松愉快的娱乐文化,它不同于成长于本国土壤的民族文化,很难在不经本土化复杂改造的情况下与民族文化形成合力、和民族精神产生一致性。因此,以市场和娱乐性质为主的“萌”文化容易使受众特别是大学生受众缺少反思意识、不关心是否娱乐至死、在一味追求视觉和心理快感的刺激中缺少对于文化和现实的认识。特别是“萌”文化与青春类电影的结合,使观众在其中难以看到人性的冲突和现实的伤痛,容易使青春单纯地变成一件美好纯真的水晶制品,从而消解了年轻人的反思意识,弱化了他们应有的理性思辨,只停留在简单的快感中而失去了更高级的审美能力。[5]
更为具体来看,“萌”元素在人物塑造方面介入的最为明显突出,对于男性形象来说,“萌”的介入使中国传统认知中阳刚硬朗的男性形象转化为一种偏向于“少女式的美男子”,这是一种耽美文化现象的渗入,是在男性的形体之上,表现出一种女生般的美丽、温柔和纯洁。比如《小时代》中陈学冬饰演的周崇光、《重返20岁》中鹿晗饰演的项前进等,都是耽美文化渗透下的花美男形象。这种低幼化审美形象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流行,可以视作影视中男性形象气质变化甚至青春电影中整体审美倾向变化的一种重要诱因。[7]
以一种更为忧思的观点来看,“萌”元素带来的柔和与遁世,会压迫具有社会观照和现实反思的美学表现边缘化,对于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造成消弭倾向,对于美学风格形成中至关重要的“民族性”元素形成被吞噬的危险。[5]这种美学危机会对大学生的审美认知造成干扰,容易产生脱离民族优秀文化的审美态度。
“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运用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审美潮流,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年人的审美需要。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萌”文化带给他们阳光柔和的审美感受,激发了他们对于青春年华的美好印象,也丰富了他们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萌”文化原始的外来文化属性与娱乐化消费性属性,如果不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审美引导,就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文化审美供应。因此,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应用“萌”元素,可以视为一种在青春电影创作和青年群体文化审美供应方面的积极路径。
四、结语
“萌”元素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流变伴随着本土化的趋势显现出提质的过程,这既是创作者追求青春电影创新提质的努力,也是适应市场潮流和受众审美大势的需要。无论是目标受众的迷恋、市场的优厚回馈,还是存在的广泛批判与不同受众的鄙夷,“萌”文化作为二次元文化的类型之一,在中国青春电影中的介入和产生的影响的确应该辩证性地看待。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应该用辩证性的思维正确欣赏这种文化和审美对象。同时,我们实则也不必过度担忧“萌”文化对大学生美育甚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消极影响。正如陈旭光教授在《近代中国“现象电影”启示录》一文中所言,“不要把《小时代》里面的奢华的影像、物质化的欲望奇观看得过重,也不要把电影的文化功能看得过重,它实际上并不承载过多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负。”[20]青春电影中的“萌”元素也是这样,它不太容易以一己之力改变或颠覆大学生的审美价值,在多种美育方式和途径的合力影响下,青春电影中“萌”元素存在的消极美育影响会在美育教育的洪流中得以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