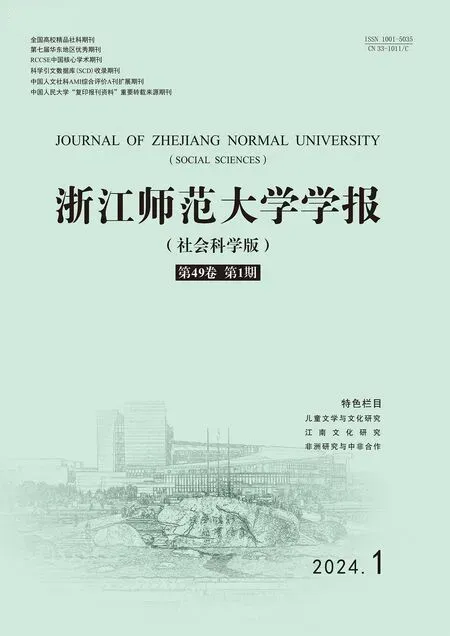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梁 杰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吴澄(1249—1333)是元代继承朱子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江西崇仁为中心,影响元朝南北方诸多地域,成为南儒中能与北方许衡双峰并峙的人物。而由他创立的草庐学派,也与许衡创立的鲁斋学派、刘因代表的静修学派,合称为元代三大朱子学派。吴澄及草庐学派众多的门生弟子,赫然成为元代江西学术史以及朱子后学的中坚力量。对于吴澄及草庐学派,明清学人如顾炎武、黄宗羲、全祖望等都曾撰有学述或评议。清末民初以来,在现代学术的研究视野下,对吴澄的研究有增无减,百年来涌现出大量成果。对这些成果,不时有学者进行回顾与总结,如查洪德《吴澄:一个正在被认识的重要文论家》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关于吴澄的文学研究论著,指出吴澄的文学价值亟待深究;[1]吴立群《吴澄哲学思想研究综述》从吴澄的学术立场、在理学中的地位、理学思想三个方面,分析研究者对吴澄思想的论述。[2]然二文仅考察吴澄个人,对草庐学派的整体研究尚有缺失。本文摭补海内外的学术成果,再次述评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的旧作与新论,分析百年来研究的走向及误区,以期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百年来的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民国时期,学人开始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吴澄,为吴澄在元代思想史中的地位做了奠基工作;二是1949年至1980年,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关于吴澄学术身份的研究占据了主要篇幅;三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大陆开始涌现有关草庐门人的个案研究;四是21世纪以来,草庐学派逐渐以群体的方式进入研究者视野,研究方法、视角推陈出新,为接下来的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民国时期学界对吴澄及草庐学派的关注
民国时期学界对吴澄及草庐学派的关注,被囊括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元代理学的相关分析里。这一时期,元代理学在各类哲学史的书写中地位不高——如吕思勉《理学纲要》(193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4),在最初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基本上“无元代理学的一席之地”[3]——但仍有部分哲学史著作对元代理学表示重视,如谢无量、徐敬修、钟泰等人的哲学通论著作就对元代理学派别的论述相对较多,而吴澄及草庐学派也被包含在内。总体来说,这类著作将草庐学派置于朱陆关系中来讨论,认为吴澄在“和会朱陆”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
具体来看,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将宋元哲学史与明清哲学史并列为近世哲学史,其中元代以“程朱学派”“朱陆调和派”“陆学派”三派为主要讨论点,吴澄隶属“朱陆调和派”。谢无量参考《宋元学案》收录的“草庐精语”,即“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4]来阐释“草庐和会朱陆二家之意”,肯定了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对吴澄所作的判断。[5]徐敬修《理学常识》列出“元代理学之派别”一节,同样认为吴澄是由朱入陆者。[6]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继续采用这种划分系统,将吴澄、郑玉单列一章,视作元代“和会朱陆”者。钟泰认为,吴澄以朱学为根基,融会陆学主静工夫,将朱、陆两派各自的流弊分析得十分清楚。[7]
这三部著作是民国时期吴澄研究的代表。可以看出,吴澄的学术倾向是学者致力阐发的重点,这种阐发源于他们在梳理中国哲学如何由朱入王(阳明)的过程中,试图以“朱陆和会”作为转变的原因,而吴澄则是将陆学引入朱学的关键人物。此时段研究成果数量虽少,且多为粗略的概括,对吴澄背后的草庐学派及门人也鲜有关注,但却奠定了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的基调,启发了后续研究重点讨论草庐学派思想里的朱陆关系。
二、1949年至1980年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
1949年至1980年,这一时期的哲学通论著作,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只论述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70—1980)则对元代思想只字未提,只有钱穆在撰写完《朱子新学案》后,为梳理元明后继朱子学说的缘故,对黄震、王应麟、吴澄三人各自作了学述整理。
钱穆的《吴草庐学述》是此期研究的代表作。钱穆通过细析吴澄的文章,指出吴澄之学渊源于程朱、邵雍,“毕生为学,依然是朱子精神”,又因经历亡国之痛,“退四书而进五经”。钱穆驳斥后世学者以吴澄为朱、陆调和者的观点,他通过吴澄《仙城本心楼记》《题四书》等文,自证吴澄只是砭“朱学末流之失”,而非“归于陆学”。钱穆的论述,在从《宋元学案》以来至民国时期有关吴澄的研究中显得别开生面,既敏锐地发现了吴澄思想的内核,又同情吴澄经历换代的遭遇。[8]惜其对吴文写作时间的考证有失误,如他将吴澄作于咸淳四年(1268)的《题四书》定在至大元年(1308),认为此文是吴澄为了回应元廷国子监众人的质疑而发,①但即使有误,却瑕不掩瑜,其中对“朱陆关系”的跳出态度仍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孙克宽则揪心于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出于强调“中华民族与他那深固不易的文化形态”目的,他特别关注元代蒙古人统治下的汉文化,将吴澄研究置于“夷夏之防”的背景中。他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中,将元初儒学分为“金源文化的注入”“江汉学派崛起”“江南文化的北来”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尤以吴澄为思想界大师。他热衷于讨论吴澄学术与时代的关联,认为吴澄首发《古文尚书》的伪造痕迹,“非北方之儒所能跻及”,故元代南人试图抬举吴澄“做儒学的泰斗,取许衡的地位代之”。[9]孙克宽指出,这种推崇汉文化的构想最终失败了,直到吴澄弟子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人,才借由文学成就在政坛话语权的争夺上占据了优势。孙克宽的研究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学者,首次将目光聚焦吴澄背后的群体,意识到吴澄及草庐学派代表着元代南人势力,对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是一种突破。但强烈的夷夏之心,使他特别重视文人在政治中的地位,认为吴澄“终其身不会大行其道,倒不如金许诸儒,闭门教授,不仕王侯”,对吴澄之学的影响评价不高。此外,袁冀的《元吴草庐评述》稽考了吴澄的行迹,“按年系入行事编年”,[10]成为第一部详考吴澄生平的著作。
美国学界也对元代南方文人给予了关注。劳延煊《元初南方知识分子——诗中所反映出的片面》分析了吴澄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感性诗》《题程侍御远斋记后》等诗文,指出以吴澄为代表的元初南方文人,在面对入主中原的元廷时,他们的反抗思想是如何由重变轻的。[11]劳延煊对吴澄文本的分析,至今仍值得借鉴。日本学界更重视吴澄与元代陆学的关系。石田和夫《吴草庐と郑师山——元代陆学のー展开》将吴澄定义为元代陆学发展的关键人物。石田和夫是日本陆九渊后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他揭示了吴澄研究与陆学的紧密关系。[12]
该阶段的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研究为主,较少受到民国时期“朱陆关系”热潮的影响,更倾向于立足现实背景,以汉族为中心,将吴澄视作元代南方文人的代表。此期虽未以草庐学派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具体论述中,对草庐学人如虞集、欧阳玄等也多少有所涉及。这种结合时代、历史的视角颇具新意,为之后的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起到了不同角度的示范作用。
三、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
19世纪80年代,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得到我国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吴澄首先以理学家的身份进入研究者视野,大量思想通论著作开始重点阐述吴澄及草庐学派。与此同时,草庐学人的个案研究也不断涌现,历史学、文学、文献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一)思想史通论著作中的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
通论著作中,唐宇元首开吴澄思想研究风尚。唐宇元重点关注元代思想史、哲学史。他在1982年先后发表《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吴澄的理学思想》两文,将吴澄视作元代“对朱学的偏离”和“朱陆和会”的代表。这两篇文章随后都收录到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13]唐宇元对吴澄的论述是民国时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朱陆关系”仍是分析的重点。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也对吴澄由“朱熹理学向心学的演变”轨迹作了重点分析。蒙培元认为,吴澄确立了以心为本体的思想,否定了朱熹心外求理的方法,对朱熹的格物说作出符合心学所需要的修改。[14]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同样也认可吴澄在“朱陆和会”中的作用。书中指出,元代理学有一个普遍现象,理学家为了避免程朱之学“流为训诂之学”,采用“求助于陆学”[15]的方式,许衡、吴澄、许谦都有此倾向。相比之下,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则跳出吴澄个人的思想,将目光聚焦草庐学派的整体思想倾向。他把元代理学分为鲁斋、静修、草庐、北山、徽州、陆学等六大派别,认为草庐学派是南方理学的重镇。徐远和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吴澄究竟是偏朱还是偏陆,他认为吴澄“以朱学为主,兼宗陆学”,[16]并对吴澄缘何重视“本心”之学进行了细致的阐释,指出吴澄之学为陆学的结论难以成立。徐远和还对草庐传人元明善、虞集进行考察,探讨了吴澄理学思想在元代中后期的传承与演变。
20世纪末,有更多的通论著作提及吴澄。如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将江西与徽州视作宋元之际朱陆合流的不同阶段,吴澄尤为江西陆学传衍的代表。[17]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指出吴澄“立足于学术综合和发展的观点”,“突破了狭隘的道统论”,对朱陆之学有所会通。[18]
通观这一阶段思想史通论著作可以发现,一方面,学者对吴澄的研究仍沿着《宋元学案》以及民国时期的路数,着重考察吴澄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无论是“对朱学的偏离”,还是“以朱学为主”,他们的判断都局限在哲学史书写的框架下,仍将吴澄看作朱学向心学演变的中间人;另一方面,草庐学派的研究仍然较少,且不成系统。因此,后续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仍有突破的空间。
(二)吴澄及草庐学人个案研究的涌现
这一阶段吴澄及草庐学人的个案研究开始涌现,其中,吴澄、虞集、危素特别受重视。
首先是吴澄的个案研究。与通论著作相似,吴澄的个案研究仍以其理学思想为主。方国灿《理学大师——吴澄》以朴素唯物主义的眼光,将吴澄生平与其“以夏变夷”的思想联系起来,认为吴澄的理学思想具备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19]章伟文《略析吴澄易学中的阴阳卦对思想》《略析吴澄的易学象数思想》两文,对吴澄的易学思想进行研究,指出吴澄以阴阳卦对来解说《周易》经分上下之义,超出了朱熹的易学思想。[20-21]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吴澄的思想成为讨论热点,詹海云《吴澄的〈易〉学》、杨自平《吴澄〈易〉学研究——释象与“象例”》、蔡方鹿《吴澄的〈尚书〉学述要》、姜广辉《评元代吴澄对〈礼记〉的改编》,四篇文章各自对吴澄的经学著作进行了阐述。要之,此阶段对吴澄个人思想的研究,偏重细析吴澄各部经注中的具体思想,使得吴澄研究更加具体化、细节化,这也是吴澄哲学思想研究的必经之路。
吴澄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关注。吴澄曾在元朝京师国子监任职,又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书院辗转讲学,因此,吴澄的教育思想很快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胡青《吴澄教育思想初探》吸收了唐宇元《吴澄的理学思想》的看法,将吴澄教育思想与朱陆合流联系起来,认为吴澄的教育思想是由宋代教育理论向明代发展过渡的重要环节。[22]随后,杨布生《吴澄草庐讲学与书院教育》、刘桂林《吴澄教育思想探新》均未脱离胡青研究的轨道。可以说,吴澄的教育思想研究是其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者也多从朱陆关系的角度论述吴澄如何通过教育来实践其哲学思想。
吴澄的文学研究异军突起。该热点源于元代文学研究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意识到元代文学不能只局限于元曲,诗文体裁都应该加以注意。[23]“而只要开展元代诗文研究、元代文学批评的研究”,[24]就必然会注意到来自理学的影响,因此,一直处于理学思想研究热浪中的吴澄就成了文学研究的对象。刘明今《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以吴澄为中心,阐述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特殊风尚。刘明今提出,与当时驳斥江西诗派的复古思潮不同,吴澄肯定了江西诗派的风格,并受到陆氏心学的影响,注重“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25]以诗歌表现真我。随后,王素美发表《传统诗教与非传统诗教之间——论吴澄诗歌理论的特点及其影响》《理学家的视角 儒者的情怀——论吴澄丧乱诗的特点》等多篇文章,集中对吴澄的诗歌理论进行了论述。这些论文后来被收录进王素美《吴澄的理学思想与文学》[26]一书中,成为与《许衡的理学思想与文学》《刘因的理学思想与文学》并列的三部曲之一。王素美的相关研究逐渐构建起完整的理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体系,开启了21世纪吴澄的文学研究。查洪德在1998年“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吴澄的理学与文学》一文,也将吴澄的理学与文学思想作为一个系统,认为吴澄是自觉运用其哲学思想来研究文学问题的。
此外,吴澄的生平考证也有进展。路剑《吴澄年谱》利用虞集《吴澄行状》、揭傒斯《吴澄神道碑》、危素《吴文正年谱》《圹记》《吴文正集》《元史》本传、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韩儒林《元朝史》、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冯君实《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书,并取时人别集,如程钜夫《雪楼集》、赵孟頫《松雪斋集》和有关方志等,对吴澄的生平事迹及著作作了简要梳理。[27]
其次是草庐学人如虞集、危素等人的个案研究。李才远《虞集哲学思想试探》将虞集的哲学思想追溯到吴澄,用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朴素辩证法来论述,认为虞集的思想是宗朱融陆的唯心主义,即“穷理正心之学”。[28]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对虞集理学影响下的文学观念进行分析。邓绍基的论点基于他对元代诗、词、文的重视,该文收入其《元代文学史》第二十章,虞集被列为“元代后期诗文作家(一)”,[29]范梈、揭傒斯等草庐学派文人也在该书中有相关论述。此外,周少川《虞集的史学思想》论述了虞集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史学观点;[30]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与文学主张》《虞集的诗文成就》考察了虞集的诗文主张;[31-32]胡青、桑志军《危素学术思想探析》、黄建荣《揭傒斯佚文两篇及其考证》等分别探讨了其他草庐学派成员的思想;[33-34]陈高华、孟繁清点校的苏天爵《滋溪文稿》对苏天爵的文章进行了梳理。[35]可以说,关于草庐学人的相关研究,起步较吴澄更晚,此阶段的研究仍是初步探讨。
(三)海外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仍在发展
这一阶段,海外有关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也在持续向前,且更加注重细节考证,这就为吴澄研究提高了准确性,拓展了深度。
日本学者福田殖《吴澄小论》针对唐宇元《吴澄的理学思想》和钱穆《吴草庐学述》二文里宗朱、宗陆的分歧,对吴澄思想进行了再分析。福田殖通过历叙吴澄的从学、从政生涯,辨析了清人李绂《陆子学谱》以吴澄为“祖述陆子之学”的观点,指出全祖望《宋元学案》成书与李绂思想的关联,认为“虞集所谓的‘朱、陆和会’的观点理解最深,而全祖望实证性的评价最为妥当”。[36]福田殖认可《宋元学案》的观点,认为吴澄的“朱陆和会”思想发衍于老师程绍开。而在三浦秀一的《学生吴澄、あるいは宋末における书院の兴隆について》中,此观点遭到了反驳。他列出左袒朱学的方回对程绍开的肯定,指出程绍开的学问本身并未偏向陆学,吴澄从程氏那里学到的也非“和会朱陆”。三浦秀一非常注重“江西书院及州学的学术环境”,他认为,与其说吴澄的思想是“朱陆和会”,倒不如说“只要为了实现圣贤之学,不管什么样的内容都值得肯定,朱陆等学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有效学问”,而这种包容的思想正是供吴澄学习的临汝书院及江西抚州州学的整体学术风向。[37]这两篇论文反映了日本学界的研究进展:对吴澄思想的分析由单纯的思想史进入与历史、社会等联系起来的阶段,这种分析的细致程度仍然值得当下学界借鉴。
韩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吴澄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孙美贞《吴澄心性论对韩国的影响》分析了吴澄对朝鲜性理学,尤其是处于丽末鲜初朱子学传播期的权近理学和发展期的退溪心学的影响,将吴澄及草庐学派作为中国理学自朱熹到阳明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而权近、退溪则继承了朱陆合流的倾向。[38]
综上,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仍以吴澄个案研究为主,仅有些许思想史著作注意到整个学派,对学派整体学术倾向的探讨仍是空白。对吴澄以外的其他草庐学人的个案分析开始出现,不过论述仍属于以吴澄“和会朱陆”思想的发散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的兴盛,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通常能更加关注元代诗文中草庐一派学人的作用。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周惠泉、杨佐义《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等文学史通论著作,多将元代文学史分为前、中、后三期,以吴澄为前期诗文作家、虞集为中期作家,对二人进行重点讨论。[39-42]与思想研究相类似,此阶段关于吴澄、虞集等人的文学研究也较多注重个案分析,真正讨论草庐学派整体文学倾向的研究要到21世纪才逐渐兴起。
四、21世纪以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新阶段
进入21世纪后,学界普遍意识到吴澄在元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关于吴澄及草庐学人的文学研究硕果累累;草庐学人的基础文献整理、思想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草庐学派这一群体开始受到青睐,一些论述学派整体学术、文学倾向的研究映入眼帘。
(一)吴澄及草庐学派的文学研究
吴澄及草庐学派的文学研究在上一阶段理学与文学思想结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正是在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里,草庐学派的整体为学倾向才真正受到关注。查洪德《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以吴澄和虞集为例,说明其学问“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和会朱陆’”,而是“融会各家,广纳百川,在融通中形成自我”,[43]他们代表元代中期江右整体的文学风尚,并由此形成元代代表性的诗风文风。查洪德在随后的文章中重点论述了吴澄、虞集的文章与理学的关系,将视野扩大到元代整个江西文风,提供了理学与文学研究的范本。[44]王素美《吴澄的理学思想与文学》一书,从吴澄的理学思想、理学对文学的影响、理学视域下的文学创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吴澄的大致思想与创作主张。[45]李宜蓬的吴澄散文理论研究对吴澄的文统论、文学创作论展开了具体描述。杨镰《元诗史》对吴澄身兼学者、诗人的双重身份进行分析。[46]黄金叶《吴澄“性情之真”及其元代诗学史意义》《吴澄的诗学性情观》《吴澄“性情”诗学研究》旨在分析吴澄如何利用性情论连接哲学与诗学,建立全新的理学诗学。[47-49]杨万里《吴澄文气论的理论创新》《理学思维下吴澄的文艺本体论与文道观》则关注吴澄建立的以“理”为本体的文艺复古理论。[50-51]孙文歌、吴光正《试论元代大儒吴澄诗歌中的出处情结》从南方士人的视角考论吴澄诗歌。[52]这类论述多以吴澄为中心,旁及以虞集为代表的江西文人,论述他们在元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尽管这些研究还未能打破江西的地域范围,但这种做法为该学派整体文学倾向的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
还有很多学者从元代文学研究专题的角度来讨论吴澄等草庐学人的文学倾向。例如史伟《元诗“宗唐得古”论》在讨论元诗如何“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时,将吴澄作为由宋入元士人的典型范例,认为他是“古诗似汉魏,可也,必欲似汉魏,则泥”,即反对僵化仿古的观点的代表。[53]丁功谊《元代诗论中的性情说》在分析元诗“性情说”时,吴澄因主张“诗道情性”而位列其中。[54]这类研究都注意到了吴澄在元代诗坛文坛中的地位,从不同角度填补了吴澄研究的空白。
真正从群体视角讨论草庐学派文学的,要数江南的博士论文《草庐学派文学研究》。该文对草庐学派的文学成就没有引起学界重视进行质疑,并基于此“对草庐学派的文学主张、代表作家对元代文学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梳理,为草庐学派的文学研究做力所能及的基础性工作”。[55]江南将草庐学派的整体文学倾向归纳为文道合一、诗法自然、酿蜜法般的诗法,以及衍宋脉、“宗唐复古”、取法先秦两汉的文风,指出草庐文风对元代盛世文风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对除吴澄以外的元明善、虞集、陈旅、贡师泰、苏天爵的诗文研究进行了分析。邱江宁《元代草庐文人与他们的文学时代》也将目光聚焦草庐学派。该文非常重视元朝“疆域辽阔、文化多元、思想驳杂”的现实,指出草庐学派有着和会朱陆的哲学思想、不立崖岸的人生选择以及和会包举以倡导清和雅正的创作风气,这些学派的整体倾向与元朝“大一统时代”的独特性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元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包括吴澄、虞集、揭傒斯、范梈、危素、周伯琦等为核心的草庐学派,“确立了他们自己在元代文化领域的中坚地位”。[56]可见,吴澄、虞集以外的草庐学人,是在2010年之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才受到重视的,而元朝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也开始引发关注,这对草庐学派研究来说意义非凡。
(二)吴澄及草庐学人的文献整理
文献整理是进行研究的基础,标志着相关研究正式启动。吴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献整理也在起步。世纪之交,吴澄诗文集的整理由各种文献汇编来承担。《全元文》第14、15册收录吴澄文章1 459篇,其以明成化二十年(1484)《草芦(庐)吴文正公文集》为底本,校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百卷本,“集外共辑得佚文三十八篇”。[57]《全元诗》第14册收录吴澄诗566首,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吴文正集》一百卷(卷九十一至九十八)编录吴澄诗,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年刻本《临川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卷四十五至四十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临川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顾嗣立《元诗选》初集《草庐集》校勘。集外诗编在其后”。[58]此外,《儒藏(精华编)》第246册收入李军校点的《吴文正集》。[59]该书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吴文正集》为底本,以明初刻本、明成化本、清乾隆刻本为校本,并参校《元文类》《宋元学案》《元诗选》等典籍的相关部分。底本所缺的《道学基统》和外集,自校本整体移录,置于最末。
以上工作对吴澄诗文集的整理很全,但对其真伪考证较少。仅以《全元文》为例。《全元文》中收录在吴澄名下的文章,很多都与《全元文》中虞集名下的文章重复,这是因为吴澄文集传世本里原有部分文章跟同时期其他文人是重合的,《全元文》没有筛选,又在辑佚过程中增加了更多重复的文章所致。②方旭东点校本《吴澄集》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很大修改,该版本是目前第一部吴澄诗文集单行本。
黄曙辉点校本《道德真经吴澄注》对吴澄在大德十一年(1307)订正的《老子章句》作了整理。[60]目前,囊括吴澄诗文集以及各种经注的全集尚未出现,有待学界整理。
草庐学人的文献整理也有一定进展。除却《全元文》《全元诗》中对草庐文人文献的整理外,尚有部分学人别集有现代整理版,例如王颋点校的《虞集全集》,邱居里、赵文友校点的《贡氏三家集》,李梦生标校的《揭傒斯全集》,等等,这些整理本均对草庐学人的著作进行了基本的梳理。
(三)吴澄及草庐学派的思想研究
首先是思想通论著作中的吴澄及草庐学派思想研究。进入21世纪,元代理学开始普遍依附在宋代理学中被学者论述,吴澄及草庐学派被论述得更加勤密。张岂之、朱汉民《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收录了朱汉民在《宋明理学通论》中对元代理学家吴澄的阐述,仍从天道、心性、朱陆和会三个方面来分析,体现了对朱陆关系的持续关注。[61]陈谷嘉《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指出,“元代思想文化研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并对涵盖“吴澄理学伦理思想”的元代理学家进行了梳理。[62]姜国柱《中国思想通史·宋元卷》没有论述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而是简要分析了吴澄的理气、人性思想。[63]而在陈来等所著的《中国儒学史·宋元卷》金元部分,方旭东则认为吴澄的思想“与其说是所谓兼陆或和会朱陆,不如说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全体大用’之学”,并基于此对吴澄的理气论、太极论、性情论等作了阐述,且在“元代陆学”一章中收录了对吴澄弟子危素的论述。[64]可以看出,21世纪思想通论著作虽集中分析了吴澄的个人思想,但对草庐学派的思想地位仍较少提及。这一阶段关于吴澄个人的论述,已经不再重点讨论“朱陆关系”,而是着重对吴澄的具体思想进行剖析。
一些关于元代思想的硕博论文也对吴澄及草庐学派有了更为细致的阐述。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提及了吴澄与草庐学派的四书学在元代诸学派中的地位,开始从学派的整体视角来考述,但重点仍是吴澄“于朱陆二氏之学互有发明”,即朱陆观在吴澄《四书》学中的表现。[65]周春健还对吴澄弟子袁明善的《四书日录》作了佚文辑录。朱军《元代理学与社会》沿用早期哲学史的做法,也将吴澄囊括进元代“朱陆和会”思潮中,认为吴澄“宗朱兼陆”,是“宋代程朱理学过渡到明代王学的关键人物”。[66]
其次是吴澄及草庐学人的专题思想研究。这一阶段,关于吴澄个人思想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方旭东、吴立群、许家星的研究。方旭东《吴澄评传》是国内首部研究吴澄的专著。书中对吴澄生平、理气论、太极说、性情论、心学观、格物说、主敬说等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附录了吴澄详细的生平编年,是对吴澄思想梳理最为完整的著作。与《中国儒学史·宋元卷》所持观点一致,方旭东认为学者以吴澄思想“兼主陆学”的误区在于过分看重程绍开对吴澄的师承影响。他指出,吴澄思想多是“私淑于经”,吴澄发挥的是程朱理学的心性理论,所推崇的“尊德性”也非陆氏心学的“尊德性”,而是继承《论语》《礼记》直到程朱的主敬涵养之说。方旭东试图彻底摆脱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主张全面论述,这对吴澄研究来说很有创见。[67]同样,吴立群《吴澄理学思想研究》一书,也指出“朱学、陆学或和会朱陆看待其(吴澄)学术思想,是无法理解其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的”。书中着眼于吴澄理学思想发生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儒家道统学说的演变为考察起点,阐述吴澄理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整体把握其思想脉络,全面揭示吴澄理学思想具有的内涵和特征,并试图借吴澄理学思想研究这一个案,管中窥豹,体认理学的核心话题以及这些核心话题的逻辑发展和内在联系,对吴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出说明。[68]而许家星的《朱子学的内在演变与朱陆合流——以饶鲁〈大学〉诠释对朱子学的突破为中心》《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等系列文章,则以“朱子学的内在演变”这一话题为核心,深入剖析吴澄的经典诠释学,说明由饶鲁到吴澄的双峰学脉如何修正朱子思想,并以此开启朱陆合流的思潮。[69-70]
研究吴澄专题思想的单篇及硕博论文集中出现。这些研究重点阐述吴澄的五经学和道家思想。总论五经学的有张欣《论元儒吴澄的五经之学——以〈四书〉独尊和南北抵触为背景》,《礼》学有刘千惠《吴澄〈三礼考注〉之真伪考辨》、朱娜娜《吴澄〈礼记纂言〉研究》、王启发《吴澄的礼学著述及相关问题》,《春秋》学有石梅《吴澄〈春秋纂言〉研究》、刘德明《吴澄〈春秋纂言〉中的“属辞比事”探析》,《易》学有章伟文《试论吴澄易学的理气论思想》、王新春《吴澄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张国洪《吴澄的象数义理之学》、翟奎凤《变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论》、杨效雷《吴澄的卦统、卦主、卦变说》、马慧《吴澄易学研究》,等等;道家思想相关研究有刘固盛《吴澄〈道德真经注〉试论》、刘怡君《吴澄〈道德真经注〉“援儒入〈老〉”的诠释向度》《吴澄〈道德真经注〉“心性论”探微——以理学诠解〈老子〉的义理向度》、毛佳佳《元代理学家吴澄对〈道德经〉的解读》等。这些研究对吴澄思想研究的深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1世纪以来,吴澄思想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一是开始有意识地不再拘束于朱陆关系的讨论,逐渐摆脱了哲学史式的书写,对吴澄个人独特性的论述提上日程;二是关于吴澄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与深入,具析吴澄五经学及其他专书思想的论文大量涌现,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凸显了吴澄的个人理学造诣。
与此同步的是,草庐学人的思想研究也逐渐增多。相比21世纪前,这一阶段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所加强和扩大。例如虞集,不仅有梳理其生平的,如罗鹭《虞集年谱》、刘东明《虞集之生平与交游》;研究其理学思想的,如姬沈育《宗朱融陆:虞集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还有探讨其文学思想的,如姬沈育《元代著名作家虞集的文学思想》、何东、申慧萍《论虞集送别诗的艺术特色》、邓锡斌《论虞集诗歌宗唐复古之风》、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邹艳、陈媛《论虞集的江南情结及其反映的群体心理共性》等,研究群体不断壮大,研究角度也在不断扩展。尽管如此,草庐学派整体的“历史地位与其研究现状不成正比”,[71]接下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来补充。
最后是有关草庐学派整体思想倾向的研究。该研究是以考察“元明朱子后学”的主题方式出现的。周茶仙《偏离与转向:元代江西草庐学派及其学术特点》指出,草庐学派的吴澄、元明善、虞集等人,他们一方面以朱子为宗,致力于探寻朱学本旨;另一方面则利用陆学发展了朱熹思想,陆学也因地域性的文化认同被草庐学人拯救并发扬光大。[72]周茶仙的论文被收进其与胡荣明合著的《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一书。书中,草庐学派与存斋晦静息庵学派、双峰学派并列,共同构成探讨江西朱子学兼陆学关系的主体。[73]同样,朱冶《元明朱子学的递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研究》一书,也从朱子后学的角度对草庐学派进行分析。此书明确划分了元代南方朱子学流派,并以吴澄、虞集作为江西草庐学派的代表,对他们的为学宗旨、与同时期北山学派和徽州学派的交往冲突作了阐释。[74]可见,关于草庐学派整体思想倾向的研究,既有继续从朱陆关系进行讨论的,也有具析草庐学派为学气质的,但整体上仍集中于吴澄、虞集二人,对于学派其他“二三流思想家”[75]缺乏更深入的探索。
(四)以草庐学派地域群体为视野的研究
21世纪以来,草庐学派以地域群体的面貌出现在元代江西文人群中被研究,其中又以周鑫、李超、邱江宁、罗海燕的研究格外突出。周鑫《乡国之士与天下之士:宋末元初江西抚州儒士研究》通过稽考宋末元初抚州儒士在“宋元易代和元初科举停废两大历史场景的言行事迹”,试图摆脱韩明士抉发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论点影响,即“习惯以家族为中心探讨其地方活动,以朱子学为中心建构儒学的地域流传”的研究方法,讨论儒士地方活动与儒学地域流传的多元面相。在周鑫的笔下,吴澄、刘岳申、刘辰翁等一大批草庐学派文人,都从具体事迹来说明他们易代时的动向与思想转变。[76]李超《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一书,同样聚焦元代江西文坛,并将其分为前期(以刘辰翁为中心的庐陵奇崛文风)、中期(以吴澄和何中为代表的抚州儒者文风)以及后期(以虞集为代表的馆阁文臣的盛世文风)。李超吸收了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对吴澄的评定,认为“元代中期江西的圣贤气象实际是从他(即吴澄)开始添加的”,吴澄作为江西文派的盟主,引导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人共倡雍容和平的盛世文风。[77]同样,罗海燕《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文坛格局》也认可吴澄是江西文派的代表,并将元代诗文流派分为中州、北方、江西、金华、新安、高丽六派。[78]邱江宁《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从元代文坛南北多族融合的角度出发,讨论吴澄领导的草庐学派,以南人北进的步伐共同倡导清和雅正的文坛风气,主导着元代文坛走向。[79]而江西文派以草庐学派为主,他们以理为诗之本,提倡平淡自然,主张辞由己出,在元代文坛具有重要地位。
通观21世纪以来的研究,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讨论出现了更为可喜的变化。一方面,思想类论著对吴澄及草庐学派不再是一掠而过,大量的专题论文、著作就吴澄及草庐学人的为学倾向进行了具体论述,并且这种论述也在渐渐改变着21世纪前那种集中于朱陆关系的讨论导向;另一方面,关于理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草庐学派正式以一个群体的样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断壮大的研究群体,从不同角度重现了吴澄及草庐学派在元代思想界及文坛的地位。
五、总结与反思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史,整体呈现为“纠察‘朱陆’成分—关注学术背景—讨论学派整体学术、文学倾向”三个阶段的变奏。民国时期几部思想史著作对吴澄思想中朱陆成分的分析,奠定了吴澄研究的基调,时至今日,讨论吴澄“和会朱陆”思想的研究仍层出不穷,如刘佩芝《元代信州理学“和会朱陆”特点》认为吴澄是元代江西理学和会朱陆第一人;[80]冯会明、孙玉桃《吴澄会通朱陆的原因探析》从师承和地域文化的角度讨论吴澄和会思想之形成。[81]1949年至1980年,在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吴澄作为元代南方文人的学术身份被屡屡提及。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学界涌现的关于吴澄及草庐学人思想的研究,更多延续了《宋元学案》和民国时期朱陆关系的热潮,不过吴澄的文学家、教育家身份也仍旧为人注意,相关文学思想的阐发在元代文学地位提高的趋势下得到论证。21世纪以来,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吴澄及草庐学派的整体学术及文学思想得到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可以说,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取得许多高质量成果的同时,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仍有可改进之处。
其一,过度聚焦吴澄及草庐学人思想中的朱陆成分。虽然这种聚焦确实符合吴澄以朱熹后学自任,却又兼领江西地域陆学思想成分的实际,但却忽略了吴澄及草庐学人思想的其他方面。吴澄对先学的态度是兼包并蓄的,只要能对朱子末学偏重琐碎的误区有所修定,又不失对道体一以贯之态度的学说,都为吴澄所借鉴。因此,无论陆氏心学还是张载之气、邵雍之数、王安石新学,都有可参考之处。而现有研究则重视吴澄吸收陆学成分的探讨,忽略了吴澄以朱子后学的立场矫正末学之弊的出发点,过度围绕朱陆关系来阐发吴澄思想的陆学成分。这种为学倾向有其学术史来源——自吴澄在元代朱学官学化的背景中提出兼容陆学,便有学人指摘吴澄之学为陆学,以至于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出现评判矛盾:既认为吴澄之学“终近于朱”,却又提出“草庐多右陆”。围绕吴澄之学究竟是朱学还是陆学的讨论由此生成,无论哲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教育学研究,“和会朱陆”这个标签都紧随其间。其实,只有摆脱过分看重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方能重现吴澄思想的全面性与特殊性,草庐学人的研究亦然。
其二,缺乏从横向角度整体统合、还原吴澄及草庐学人所处的文化生态研究理念。不少学者从自身学识出发,孤立地探讨吴澄及草庐学人的理学、文学思想。这种模式虽在纵向上彰显了吴澄等人于学术史及诗文传统脉络里的价值地位,却未能真正观照横向的文化因素。实际上,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演变,都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及环境,它们在时间横向的层面共同构成文化生态,忽略文化生态来讨论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出现,往往很难洞察其本质。因而在定位吴澄及草庐学派的思想时,不可一味将其置于学术史演变中仅考虑其如何继承朱熹之学,而是更应关注其如何与现实互动生成新的文学观念与哲学思想。譬如吴澄的祭祀观念就与元代的统治密切相关。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允许藏传佛教进入儒学“太庙荐佛事”,直接催生了吴澄将太庙同堂异室转变为都宫别殿的建议。若忽略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特殊性,就难以了解吴澄理学思想的形成原因。吴澄曾数称元朝有“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82]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从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的视角来观照其时文人群体的流动性及整体创作面貌与格局”,[83]是吴澄及草庐学派乃至整个元代文学研究亟待探索的路径。
其三,草庐学派整体的学术、文学思想研究依旧薄弱。尽管21世纪以来呈现了由吴澄个人扩展到整个草庐学派的研究趋势,但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吴澄、虞集二人,研究角度或将草庐学派视为聚集江西的朱子后学以考察学术的流变问题,或以理学、文学结合的方式阐释草庐学人的文学主张,对于学派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范围界定、学派性质以及整体文化主张的探赜,尚属空白。这种情况同样是因为学者多依据《宋元学案》所列的《草庐学案表》来观照学派组成状况,忽略草庐学派的全貌呈现所致。实际上,草庐学派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文学组织,它囊括了大量因元朝政治时局统合在一起的多元人群,如草庐门人元明善既为服膺于吴澄之学的上进门生,同时又是北方汉人董士选政治势力的重要成员,他是以学术和政治两层身份与草庐学派结缘的。因此,只有打破思维局限,具析并绾合草庐学人的政治、文化背景,关注成员的文化诉求,整合草庐学派复杂的人员构成,才能真正探明学派的特殊性与存在意义,为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寻求新的学术孳长点。
注释:
①实际上,吴澄曾在《题四书》落笔称其作于咸淳四年(1268):“咸淳四年戊辰春二月二十七日戊申,吴澄题四书后。”可证此文写作的具体时间。而此时尚未入元,因此吴澄的看法只是他在宋末进行书斋学习时积累的学习经验。吴澄:《吴澄集》,方旭东、光洁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2019页。
②相关论文如李舜臣:《〈全元文〉误收吴澄集外文一篇》,《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查屏球:《周弼〈唐诗三体家法序〉辑考》,《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