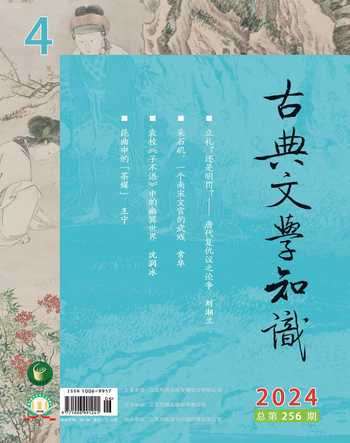“如人间唱台戏初散光景”
沈润冰
冥界,是人类在观念世界里构建的死后前往的平行生活空间。出土于马王堆的西汉帛画绘制了天上世界、人间世界以及幽冥世界,重庆大足石篆山石窟中则有北宋时期地藏十王的雕塑石像,明十三陵在其神道两旁立有众多的石人石兽……纷繁各式的艺术创作反映出人们对亡者栖身之所的文化崇拜。与此类似,从《左传》中郑伯一声决绝的“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到西汉相和歌辞中的“蒿里谁家地”再到《搜神记·胡母班》里受“泰山府君召”的晦冥之游,可以说,冥界早已被纳入本土的文化传统之中,并被纵展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母题。文人们或酣畅抒写或率意吟咏,在去神秘化的艺术加工中一点点地堆砌他们对于冥界的想象与认知。历经了魏晋和唐宋的文化积累,明清时期反映冥界题材的故事创作更为成熟,袁枚《子不语》便是其中的显著代表。纵观其书,冥界故事繁多,“冥间”“幽冥”“冥狱”“阴司”“阴府”“地狱”等词汇大量充斥于字里行间,那么袁枚笔下的冥界又呈现出何种面目呢?
复杂多面的冥神地吏
经由袁子才之笔的刻绘,读者可以看到《子不语》里的一批批冥界官吏:从拉引凡人、持帖传唤的青衣皂隶到手执典簿、笔兑生死的阴官冥神,从狰獰诃詈、收受私贿的差役牛鬼到乌纱绣服、依情依理的阎罗冥王。一方面,他们公正严明而通人情。《子不语》中的冥神地吏有大公无私、惩治罪人的一面,如《钟孝廉》中钟孝廉前世心生贪念、谋害友人,今生为人正直仗义,但冥神仍旧秉公惩处。《山东林秀才》中林长康将有功名,但阴司也因其曾有私通孀妇之小过而“记其恶而宽其罪,罚迟二科”。不过,这些冥官在行其公正以外还有破例开恩的一面,略带人情,如《江轶林》中,冥官感念江氏夫妻二人之善且情缘未尽,因此加以通融,令其重归阳世。有时也表现出通透明达,如《七盗索命》记叙盗贼被捕后贿赂县官以求免死,但没想到县官假公济私杀人取财。听闻盗贼陈词,阴官仍言:“盗亦有道”,并支持盗贼复仇索命。
另一方面,他们也贪赃枉法,徇私势利。《地藏王接客》中,狂傲不第的裘南湖到达冥界后,偶遇纸店一老翁,老翁对其指点:“阴司最势利,故吾挂之,以为光荣。纸钱正是阴间所需,汝当多备,贿地藏王侍卫之人,才肯通报。”此后抵佛殿时,听闻刑部郎中朱履忠到,地藏王则亲自出迎,裘南湖极其愤懑,痛批叱骂:“果然阴间势利!”而阎罗管辖之下的鬼差、役使则更为狡诈,好索要私财,有时甚至会以冥府召见的借口在阳间敲诈、作祟。如《蒋厨》中的蒋家家厨李贵突然中邪倒地,而鬼隶趁机要挟,从中索取三牲、纸钱。
此外,他们地位低微,远逊神佛。《狮子大王》中尹廷洽误为冥界差役所拘,幸得土地神相助,路遇西天狮子大王而解祸。水落石出之后,冥官对土地神说:“尔此举极好,但只须赴本司详查,不合向狮子大王路诉,以致我辈均受失察处分。”这里的狮子大王是西天诸佛之一,佛教语典多用狮子作为意象,以表现佛法之威力。《金刚作闹》的故事里,人们为去世的司寇不断诵读《金刚经》,金刚神便大闹地府,冥间众官难与抗衡,最终只得释放罪人。书中也借判官之口言明此意,即“既曰冥司,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职,如人间府县俗吏,风尘奔走甚劳苦,贤者不屑为”。《子不语》绘制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冥神地吏百态图,看似单面刻板,实则灵动立体,而书中所表现的多面形象实质上是复杂人性的一种迁移与映照。
取材现世的阴司建制
审判司法是阴司职能之关键,在《子不语》的冥界故事中多次出现,其中有如此记载:“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门如王者居,门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记甚忙。判毕,则黑气一团,覆于簿上,有椎腰蹙额自称劳苦者。”又如:“被勾神误摄入冥,既讯明,释魂欲返,则殓时用柏香簪,魂不能再入。”可以看出冥界的司法程序与现世司法诉讼极其相似,同样为:上诉状告、司法受理、持帖捕人、审讯取证、判决奖惩。
在冥官的选举方面,鬼差、阴官、阎罗多由阳间人所补,且允许兼职当差,如《鬼多变苍蝇》中的“邻妇”、《判官答问》中的谢鹏飞、《阎王升殿先吞铁丸》中的闵玉苍。他们昼如常人,而夜间或为鬼差拘捕亡魂,或赴阴司勾当公事。当然,更多情况下,即将离职的冥官会前往阳间寻找全职的继任者,如《杨四佐领》中的阎罗王对杨四佐领言:“第七殿阎罗王缺,无人补,南岳神已将汝奏上帝,不日随班引见,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而从中也可以看出补位冥官的选拔标准—“德”与“才”,如故事中阎罗举荐蒋士铨是由于他的“才子之名”,举荐杨四佐领则因其“性直而和”,举荐唐配沧成为城隍也是念其“居官清正”。不过,有的故事中冥官可由在世者充当,但在有的故事中则必须死去才能继任。
另外,阴司对鬼魂的收留也自成条例。枉死者冥府不收,只得随处飘荡。死于官署者,则为官衙神所拘,除非官衙的墙屋倾颓,否则也不能进入冥府。死前精通儒学、佛学的人,亡故后也会被遣派到不同的去处。此外尚有一些特别的规矩,如“阴间中秋官不办事”“吏逐名点唱”等。不难看出,冥界阴司的设置实际上就是人世官僚的真实写照。
猎奇怪异的冥俗风尚
冥界的风俗怪僻惊异,有“大锅烹物”的风俗:“老妪数人,拥大锅烹物。启之,皆小儿头足,曰:‘此皆人间坠落僧也,功行未满,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阳世不得长成即夭亡耳。”“殿旁小屋有老妪拥镬炊火,问:‘何所煮?曰:‘煮恶人。开锅盖视之,果皆人头。”又有阳间人不可用鬼食的禁忌,即“鬼肉不可食,食则常留此间矣”,甚至还记载了诸多以身试法、招致身殁的个例,如《鬼市》中的汪太守仆人李五偶入鬼市,误食阴间的面饭蒸食,结果“俯而呕之,蠕蠕然在地跳跃。谛视之,乃虾蟆也,蚯蚓蟠结甚多,心甚恶之,然亦无他患,又数岁乃卒”。再如“锡锞一锭阴间准三分用”“死后银钱不带入阴间”“白雄鸡招魂”“洗紫河车”等冥俗同样给人一种神秘幽奇之感。
实际上,书中的冥俗与现实的风俗密切相关,如《洗紫河车》中鬼妇在河边清洗小儿胞衣,并以洗净为贵,即“洗十次者,儿生清秀而贵;洗两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秽浊之人”。而六朝时期《产经》便记载了古人清洗、埋葬胞衣的方法:“凡欲藏胞衣,必先以清水好洗子胞,令清洁……取子贡钱五枚,置瓮底中罗烈,令文上向。乃已取所裹胞盛纳瓮中以盖覆之,周密泥封……按随月图以阳人使理之,掘深三尺二寸……能顺从此法者,令儿长生,鲜洁美好,方高心善,圣智富贵也。”《清俗纪闻》里也有清人对胎衣“洁净”“掘三四尺深”的描述,只不过已经不用取古钱同埋了。又如清人笔记中也有用白雄鸡丧葬的记载,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有载:“(某人)乃预以钱三百买白雄鸡一,即令鬻鸡者抱鸡于某时向某处葬地走过,鸡仍付之。至时,问:‘有凤来否?凤当白色,当谨视之无忽。少顷,鬻者抱鸡来。人咸曰:‘不见凤,唯有白雄鸡来。乃喜曰:‘鸡即凤之类,天下谁见有真凤耶。吉时至,当速葬。葬者亦心喜,以为特奇也,而不知堕其术中矣。”可见这些冥俗源于真实民间,只不过袁枚为其赋予了一层奇诡怪诞的皮囊,幽冥色彩的凸显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餍足了读者的猎奇之心。
惩恶劝善的文化寄托
游走袁枚笔下的幽冥世界,故事的背后常常有所寄托,潜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子不语》对冥界官僚和阴司审判的书写,内里其实寄托着对于吏治清廉、官员守正的道德期待。例如《土地受饿》就描绘了一个宁愿受冻挨饿也不贪图非分之财的土地神,作为一方福祉之神甚至还“衣裳褴缕,面有菜色”,两袖清风的追求显现其神格操守之高迈。不过,在弘扬清廉守正之余,冥界也有公道晦暗处,作者也在故事中对阴司的苞苴盛行予以批判。《蒋厨》故事中就有一讽语:“谁谓阴间官清于阳间官乎!”《文信王》中冥界宫门镌刻的门联更是昭然写道:“阴间律例全无,那有法重情轻之案件;天上算盘最大,只等水落石出的时辰。”
明清八股文对读书人的荼毒,充分暴露出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点在《子不语》的冥界故事里也有所体现。《子不语》虽不像《聊斋志异》那般冷峭地进行抨斥,但也对此有所讥诮。《地藏王接客》一文借地藏王吐露出对八股诗文的不屑:“汝焚牒伍公庙,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无耻之甚也!”《时文鬼》亦是如此,将评点时文的吕留良在地府中用“铁锁锒铛”缚住,甚至罪状大书“时文鬼”三字,字里行间充满了戏谑与否定。甚至在一些故事中,冥界能直接掌控考生的科考禄命,《史宫詹改命》《梦中事只灵一半》中便记载了多起冥官改变科举禄命之事。换言之,世人苦心孤诣寒窗苦读数年,金榜题名抑或名落孙山都是交掌于幽冥神力,由鬼神所决定,而非真才实学。从侧面来看,其实也是借幽冥鬼神向世人醉心的科举考试投以微嗤。
《子不语》还常借冥界故事来渗透一些佛教理念。佛教认为万物皆有轮回,《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言:“众生没在生死海,轮回五趣无出期。”在轮回观念下,人的生命终点渐趋模糊化,其轨迹由直线化成循环之圆。轮回观使得限制于此时此岸的生命观得到扩展,大大延长了生的限度。《江轶林》记载主人公江轶林与亡妻彭氏前缘未了,十七年后他遇到彭氏的后身,依旧与之续缘。“业”一词源于佛典,指人因思想、语言、行为所累积的结果,行善业有善报,为恶事得恶报,“业”不断累积,导向最终之果。《子不语》中的冥界故事同样强调因果报应,为非作歹的人终究难逃恶报。《裹足作俑之報》中记载李后主欣赏女子缠足之美,使这一畸形风尚盛行,贻害后世,最终受到无足女鬼的报复,被迫服牵机药而死,而且还得在冥间织屦一百万以偿冤孽。这和佛教中的“前世报”“现世报”“后世报”相互对应,“业”并未因此世肉身陨逝而消解,轮回的存在也使得来日报应成为可能。
察其背后,《子不语》中的冥界文化实质是理念导引和价值劝惩,它以官场文化为基础,体现为对冥官司法公正的阐扬和对阴司舞弊行为的抨击,其文化内核旨在借冥界故事重构合理有序的官场,寄托了对清中期官场现实的深刻思索。同时,巫术信仰、儒道观念、佛教观念等交融并存的文化体系让《子不语》中的冥界故事并不完全如《幽明录》《冥报记》一样讲演佛法、敬告世人礼佛,它更多借用佛教观念来搭建一套简单易懂的伦理评判体系,用善性观念导引世人,用不法膺惩告诫大众。它是利用冥界题材对现实人间—不论是官场大夫,抑或民夫民妇—进行更为通俗生动的现身说法,用因果报应倡导人的道德责任。
生死乃人生大事,冥界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观念给予了古代人民一个超验性的文化依赖,幽冥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彼时人们的生命焦灼。南朝的《冥祥记》有一段对冥界地狱的描写:“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而《子不语》中的冥界并没有这般恐怖,袁枚设置了模拟阳世的叙事空间,渲染冥界的人情世态,并通过入冥者的体验来表现故事中的冥界与阳世一般:“所见城郭宫室,悉如阳世。其人民藐小,映日无影,蹈空而行。”“我死后到阴间,所见人民来往,与阳世一般。”“裘往买帖,见街上喧嚷扰扰,如人间唱台戏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头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时相识者。”“如人间唱台戏初散光景”正是对《子不语》中冥界最好的概括,冥界正是现实人间的投射,所谓“冥世”不过“现世”。实际上,袁枚是用“鬼性”来显现“人性”,用“鬼之制度”模拟“人之制度”,用“幽冥文化”的外表包裹内在的“人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