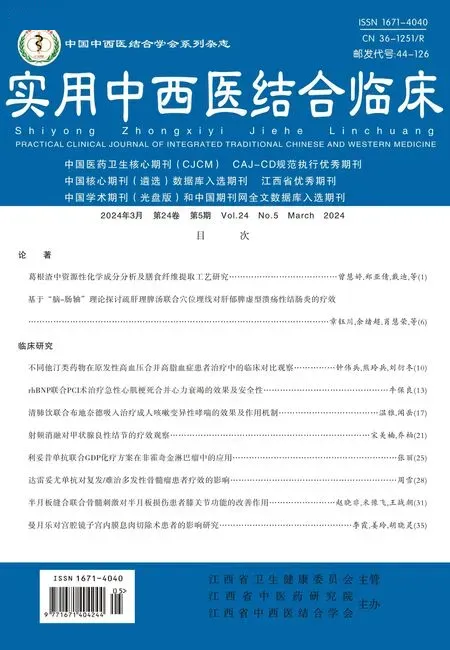基于“脑-肠轴”理论探讨疏肝理脾汤联合穴位埋线对肝郁脾虚型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
章钰川 余绪超 肖慧荣吴娜 涂艳琴
(1 江西中医药大学2021 级硕士研究生 南昌 330004;2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昌 330006)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常见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容易复发、难愈、并发症多,如治疗不充分易导致持续的肠道损伤,增加手术、癌变风险。目前对于UC 治疗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急性发作、缓解症状,注重黏膜愈合[1]。其中5-氨基水杨酸作为一线治疗药物,通常难以达到满意疗效,停药后易反复,且伴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2]。而中医药在治疗UC 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具有灵活多变、整体调节、安全性好等优点。本研究针对肝郁脾虚型UC,选用疏肝理脾汤配合穴位埋线进行治疗,临床效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 年1 月至2023 年1 月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80 例UC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 例。观察组男18 例,女22 例;年龄24~61 岁,平均年龄(38.12±9.79) 岁;病程2~83 个月,平均病程(36.60±19.56)个月。对照组男21 例,女19 例;年龄22~64 岁,平均年龄(39.25±9.70)岁;病程4~84 个月,平均病程(37.18±19.70)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设计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相关理论要求[3],在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下实施。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8 年·北京)》[4]、美国胃肠病学会(ACG)拟定的UC 临床指南[5]。中医诊断标准参照《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1]辨证为肝郁脾虚型。主症:(1)常因情志不畅而出现大便次数增多;(2)情绪抑郁或焦虑不安;(3)呈稀烂或黏液便;(4)腹痛即泻,泻后痛减。次症:(1)排便不爽;(2)食量减少;(3)腹部胀痛或肠鸣亢进。舌脉:(1)舌质淡红、苔薄白;(2)脉弦或弦细。当符合主症2 项,次症1 项或2 项,参考舌脉,即可诊断。
1.3 入组标准 纳入标准:(1)西医临床诊断为慢性复发性、活动期UC,严重程度属轻中度;(2)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证;(3)年龄18~70 岁,生活可自理、无沟通障碍;(4)未参与其他临床研究,患者及家属同意治疗且能积极配合;(5)停用相关UC 治疗药物2 周;(6)3 次粪便病原学检查均阴性。排除标准:(1)合并肠道梗阻、肠道局部狭窄、肠穿孔、结直肠癌等肠道疾病者;(2)合并严重心脑血管、肝、肾、内分泌系统疾病者;(3)过敏体质或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4)妊娠期、备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瘢痕体质患者,艾滋病、梅毒等性病患者。
1.4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美沙拉嗪肠溶片(国药准字H20030501)1 g/次,4 次/d,口服。观察组予疏肝理脾汤口服以及穴位埋线治疗。(1)疏肝理脾汤组方:柴胡10 g、炒白术12 g、白芍15 g、防风10 g、炒陈皮10 g、黄芪15 g、茯苓15 g、炒枳壳10 g、炙甘草6 g、木香6 g、黄连5 g、三七粉3 g。方药配制成颗粒剂,饭后温水调服,2 次/d。(2)穴位埋线:选用肝俞、脾俞、章门、上巨虚、天枢、足三里等穴位进行穴位埋线治疗。操作方法:常规消毒后,在上述穴位的双侧1~2 cm 注射局部麻醉皮丘,然后使用无菌2 号皮针从局部麻醉皮丘的一侧刺入0-1 号羊肠线(双线),在穿透穴位下方后,从对侧局部麻醉皮丘中刺出。接着修剪两端羊肠线头,在局部皮肤松弛后,揉捏局部,使线完全埋入皮下组织内,最后用创可贴进行覆盖[6]。保持埋线创面清洁、干燥,同时覆盖无菌棉球以及固定胶布,1 次/周。两组均持续治疗8 周。
1.5 观察指标
1.5.1 中医证候评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对两组UC 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进行评分。主症包括腹泻、黏液血便、腹痛、情绪抑郁或焦虑不安。根据患者严重程度分别记0、3、6、9 分;次症包括里急后重、排便不爽、饮食减少、腹胀、肠鸣,根据不同严重程度分别记为0、2、4、6 分。中医证候评分为主症评分与次症评分之和,两者相加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的症状越严重。
1.5.2 改良Mayo 评分 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8 周后进行改良Mayo 评分。其中内镜检查由具有丰富内镜经验和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IBD)诊疗经验的高水平医师操作结肠镜并评估。
1.5.3 脑肠肽指标 分别于清晨同一时间抽取治疗前及治疗8 周后两组患者空腹静脉血,并置于-80℃环境下储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血清5-羟色胺(5-HT)、血管活性肠肽(VIP)、P 物质(SP)水平。
1.5.4 不良反应 记录两组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6 疗效评定标准 (1)临床疗效评定:运用尼莫地平法计算两组治疗前后的疗效指数,疗效指数=(治疗前中医证候评分-治疗后中医证候评分)/治疗前中医证候评分×100%;对于患者症状、体征基本消失,疗效指数≥95%评定为临床缓解;70%≤疗效指数<95%,则评定为显效;30%≤疗效指数<70%,则评定为有效;症状、体征无明显减轻,疗效指数<30%,则评定为无效;总有效率=(临床缓解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7]。(2)内镜下肠黏膜愈合率:参考改良Mayo 评分内镜亚评分,绝对分0 分或1 分归属为黏膜愈合。黏膜愈合率=黏膜愈合例数/总例数×100%。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用%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2.2 两组肠黏膜愈合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肠黏膜愈合率为57.50%(23/4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0.00%(12/4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46,P=0.013)。
2.3 两组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在主症评分、次症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主症评分与次症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表2 两组中医证候评分比较(分,)

表2 两组中医证候评分比较(分,)
次症评分治疗前治疗后对照组观察组组别n主症评分治疗前治疗后40 40 tP 24.60±4.08 25.28±3.90-0.756 0.452 17.77±4.21 11.77±4.58 6.103 0.000 12.90±3.92 13.95±3.15-1.320 0.191 9.05±2.90 6.25±2.57 4.571 0.000
2.4 两组改良Mayo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改良Mayo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改良Mayo 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3。
表3 两组改良Mayo 评分比较(分,)

表3 两组改良Mayo 评分比较(分,)
组别n治疗前治疗后对照组观察组40 40 tP 7.82±1.45 7.78±1.37 0.159 0.874 4.55±1.72 2.52±1.32 5.898 0.000
2.5 两组脑肠肽指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5-HT、SP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VIP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4。
表4 两组血清5-HT、VIP、SP 水平比较()

表4 两组血清5-HT、VIP、SP 水平比较()
注:与本组术前比较,*P<0.05。
组别n5-HT(μg/L)治疗前治疗后SP(ng/L)治疗前治疗后对照组观察组VIP(ng/L)治疗前治疗后40 40 tP 96.20±6.57 95.45±7.13 0.490 0.626 71.22±4.57*59.59±4.46*11.507 0.000 0.48±0.11 0.45±0.07 1.179 0.242 0.66±0.15*0.77±0.17*-3.086 0.003 45.05±8.81 46.17±8.91-0.565 0.573 40.57±7.55*34.42±7.67*3.613 0.001
2.6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在治疗过程中,两组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3 讨论
近年来研究表明,大脑-肠道的相互作用成为促进UC 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9]。脑-肠轴(BGA)是一种复杂的、双向的脑-肠互动系统,包括神经内分泌通路、自主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的多重互连[10]。UC发病与BGA 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BGA 可能是解释心理困扰与UC 的关键因素[11],这与中医情志致病有异曲同工之妙。心理因素与肠道炎性反应可能通过BGA 起到双向调控作用。心理应激通过影响BGA 活动,使得患者肠道通透性增加、菌群改变,并激活肠道免疫反应从而使UC 病情恶化;反之,应激引起菌群组成改变,通过神经内分泌和菌群代谢信号潜在地调节行为和认知功能[12~13]。5-HT、VIP、SP是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相关的生物分子,在UC 生理和病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5-HT 水平与UC 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当患者5-HT 水平升高,会导致UC 病情加重[14~15]。VIP 具有降低肠道炎症反应的功能,它能够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调控免疫细胞活性,并对肠道通透性有调节作用。因此,VIP 在维持肠道黏膜的正常生理状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发现,在UC 患者中VIP 含量明显下降,可能与疾病的发展和病情的恶化相关[16];SP 是一种神经调节肽,在炎症和神经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胃肠道系统。当组织受到损伤或感染时,神经系统可以释放SP,SP 的作用包括扩张血管,增加局部血流量,增强血管通透性,导致白细胞的迁移和炎症介质的释放,从而促进炎症过程。已有研究证实,SP 水平与UC 疾病活动呈正相关[17],在UC 患者中,SP 的过度释放可能导致肠道黏膜的炎症和损伤,加剧疾病的进展。
UC 在中医学中属于“痢疾、泄泻”等范畴,是以脾虚为本的本虚标实之证,众医家一直认为情绪失衡是UC 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其持续性和复发性的主要因素之一[18]。中医情志致病与西医精神心理因素致病相通。情志由脑所主宰,脏腑所承,导致肠腑功能受损发为UC,其中以肝脾为情志致病的关键。肝主疏泄,调达气机、舒畅情志,若肝失疏泄,则致气机郁滞,致大肠传导失司、脾胃升清降浊失常,使得肠腑壅滞,水谷下迫,或津停湿聚,下注大肠,久之酝酿成毒,血败肉腐而下痢脓血。因此,情志改变引起脏腑失和,进而导致肠腑受损是UC 中医情志致病的机制,且肝脾不和为UC 情志致病的关键。而肝郁脾虚亦是UC 的重要发病机制,实责之于肝气郁结、湿热壅滞,虚责之脾虚湿困,以下痢脓血为标,以木郁土壅为本,贯穿于UC 整个病理过程之中,故临证当以疏肝理脾为要,注重情志调畅。疏肝理脾汤是由江西省名中医拟定的经验方,全方由柴胡、炒白术、白芍、防风、炒陈皮、黄芪、茯苓、炒枳壳、木香、黄连、三七粉、炙甘草组成,有疏肝理气、健脾化湿、缓急止痛之效。
穴位埋线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疗法,通过将医用无菌可吸收线埋入人体特定的穴位,形成持久而温和的刺激,从而延长和增强针灸治疗的效果,具有理气血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激发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改善肠道功能。本研究以肝郁脾虚型UC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疏肝理脾汤联合穴位埋线进行治疗,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中医证候评分、改良Mayo 评分、血清5-HT、SP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均更低,VIP 水平比对照组高,且临床疗效、黏膜愈合率均高于对照组,提示疏肝理脾汤联合穴位埋线治疗肝郁脾虚型UC 具有良好的疗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BGA 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医情志致病理论基础,从肝脾同治入手,选择疏肝理脾汤联合穴位埋线治疗肝郁脾虚型UC,疗效良好,可以调节患者脑肠肽水平,改善患者症状,减轻患者黏膜病变程度,提高生活质量,为UC 治疗提供更加有效、安全、实用的方法,也为临床多元化的治疗方案选择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