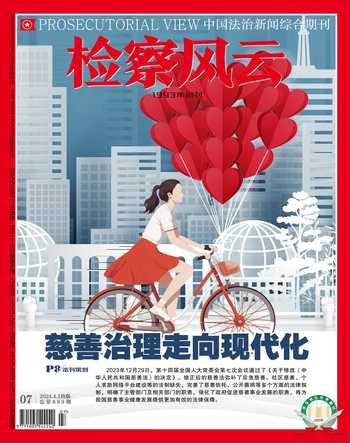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慈善法》规制
孙伯龙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将于2024年9月5日起施行,其中规范对个人求助行为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条款,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结合近年来“轻松筹”“水滴筹”等个人求助平台迅猛发展并产生的一些问题,本次《慈善法》的修改是对慈善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基于恻隐之心帮助特定受益人的行为的法律认可。由于个人求助与慈善公益活动有本质区别,个人求助部分并未出现在慈善捐赠、慈善募捐等章节,而是放置于附则中。那么,这一条款具体如何细化落实,如何让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真正得到规范与健康的发展呢?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兴起
在本次修法的背后,是我国个人求助平台近十年的发展。自2014年9月,轻松筹上线以后,爱心筹、水滴筹、悟空筹、無忧筹、360大病救助等个人求助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与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相比,个人求助依靠社交媒体快速传播,更容易触及群众,有额小量大的特点,为个体筹措大病救治资金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道。因此,其在缓解患者家庭困难、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成效。
毋庸置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已成为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在过去几年间,遭遇重病却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人,已经习惯了到个人求助平台上寻求捐赠。2022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平台研究报告(2022)》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9月至2021年底,累计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通过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个人求助信息,超过20亿人次通过各个求助平台捐赠资金,筹款规模超过800亿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31日,水滴筹累计向286万多名患者家庭、筹款共计约584亿元,轻松筹已累计帮助253万个家庭、筹款超过255亿元。
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来看,个人求助网络平台规模大、范围广、不收费,是一种具有公益属性的捐助活动。但是从法律层面而言,个人求助是一种互帮互助,属私益慈善,个人求助平台的运营主体在性质上不属于慈善组织,而属于“营利法人”,在个人求助平台上不论是募集方还是捐赠方,在捐赠时都明确受益方是某个特定的个体,因而这类活动尚不属于“慈善募捐”。许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为个人大病救助发起募捐,这类公开募捐活动涉及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个人……为规制网络募捐活动,《慈善法》出台时就制定了“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条款,但是个人求助平台与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就造成对个人求助平台的规制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近些年来,在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等网络筹款平台的助推下,个人求助比传统慈善活动更加活跃、涉及人群和资金更加庞大,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更加突出。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乱象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全面普及,我国网民数量已达10.79亿人,个人大病求助也逐渐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网络)社会。据调查,个人求助大概36%的救助资金来自求助人的亲朋好友,有64%的资金来自筹款链接,即陌生人的捐赠。从互助共济、保障民生的角度来看,个人求助网络平台已不止于对个体的帮助,其已经成为我国多层次社保制度中的重要补充。以往,由于我国并未将个人求助网络平台行为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中,造成了行政监管和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随之而来的是个人求助平台中的骗捐、收费、中介推广等情况层出不穷,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首先,是骗捐屡禁不止。2018年唐某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氧化碳中毒为由,在某求助平台发起筹款,后经警方侦查,唐某所披露的病历、身份等多项信息系伪造,求助的文案内容系抄袭平台某真实案例,预留的手机号则是网络虚拟号码。再如,莫某为患重病的儿子在某互助平台上发起个人求助筹款,却隐瞒家庭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后被举报,筹款平台将其诉至法院要求返还筹集款。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莫某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构成违约,法院判决莫某全额返还筹款15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这也是我国首例网络个人求助纠纷案。此外,各种伪造病历、隐瞒家庭财产的骗捐事件层出不穷,从而引发了个人求助平台的“信任危机”,也侵蚀着个人获得网络救助的信任基础。

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已成为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图文无关)
其次,是平台收费“吃相难看”。运营一个公益众筹平台,不仅需要人力成本,还包括开发费用、维护费用、服务器费用等,因此需要较高的资金成本。网络众筹平台本身不是公益性组织,具有一定的商业属性,主要的运行模式是:求助平台雇佣线下推广人员帮助患者发起求助,再将患者的各种社会关系转化为平台用户,在取得用户流量后平台通过销售“互助产品”或者保险产品进行变现。尽管筹集的资金不收取手续费,但一些平台会在用户捐款时,默认引导用户点击一种“绿医服务”或者是“平台支持费”“平台服务费”,由此在捐款数额外产生扣款,并且收费的标准在不同区域并不相同。客观而言,网络求助平台免费运营多年,设定合理的服务费标准能够帮助平台良性持久发展,但是对捐助人或者求助人隐藏收费、诱导收费、捆绑收费只会引起公众反感。
最后,是平台顾问恶意推广毫无底限。个人求助平台在实际运行中需要大量推广人员将筹款人与捐助方匹配起来,因此一些第三方组织或个人以帮助筹款人推广筹款链接为由,除了与部分医院“合作”外,还会主动联系发起筹款的患者及家属帮助推广筹款链接,向筹款人收取高额的“推广费、佣金”,甚至按照实际募集到的资金抽成。例如,陈某为患白血病儿子在某一平台筹款1万元,却被筹款中介李某索要8000元推广费,虽然最终查明是筹款顾问的个人违规行为,但无疑揭开了“公益”背后的“生意”,最终损害的是个人求助平台的信誉。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法律规制路径建議
第一,立法明确平台定位,凸显公益属性。
正如我国首例网络个人求助纠纷案的判决书中指出的,“目前仅有部门规章规定个人求助行为不属于慈善募捐、慈善公开募捐信息,对于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中网络平台与赠予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无明确规定”。2023年修改后的《慈善法》对个人求助行为与网络平台专门作出规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法律明确了网络求助平台的定位。笔者注意到,原来修正草案中表述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正式公布的法律文本中被改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并且在市场准入门槛上要求“需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通常来说,“指定”是一种行政许可,这就意味着未经指定的平台,一律不得提供个人求助发布的服务。未来民政部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时,很可能对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进行更加严格的资质认定,平台的公益属性将大幅增强,有助于形成更具特色的“医疗互助制度”。这也符合2020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第二,细化规制主体监管职责。
修改后的《慈善法》在附则中对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纳入法律规制,实际也是明确这类活动是一种具有“私益与公益重叠复合的慈善”。从规制主体来看,是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因此有权对此类平台管理的部门包括民政、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通常个人求助网络平台的运营主体如果不是慈善组织,还应当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监管。因此,在政府对个人求助平台规制中,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由民政、医保、网信、工信、市监等多部门对平台上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过程展开合理细化和协调。
第三,明确平台查验义务的范围和规则。
修改后的《慈善法》规定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应当对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查验。个人求助平台在对求助人发布信息查验时,应当包括病患者身份信息、基本病情、家庭财产、收入来源等信息,但是这一范围仍然比较模糊,在实际操作中平台也只能对求助人主动提供的材料予以审核,很难通过政府部门对求助信息进行共享和比对。因此,平台这一义务的前提是求助信息发布者要履行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同时,对平台的信息查验周期、查验方式(线上或者线下)、查验真伪的标准、结果反馈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予以明确。
第四,健全网络平台自律规则,引导形成自我规制。
早在2018年10月,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水滴筹、轻松筹和爱心筹等便已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和《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1.0版)。2020年8月,在民政部的引导下,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360大病筹联合签署了上述自律倡议书和自律公约的2.0版,内容包括加强信息审核、信息公示、资金监管,平台约束员工和合作伙伴等。个人求助平台企业应当以修改后的《慈善法》的实施为契机,在主管部门支持下健全平台行业自律规则,严格落实行业自律规则,形成以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为依据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定期公布行业内存在不规范行为的“黑名单”。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