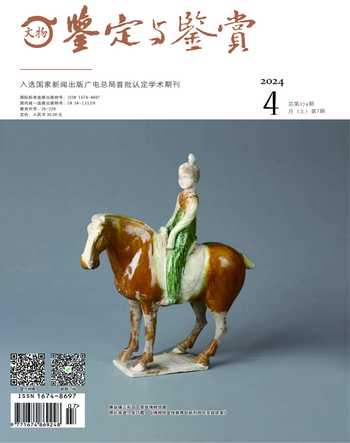浅析清至民国金铜佛像
秦丰


摘 要: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见证了佛教在政治影响下的变迁。汉藏文化不断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极具时代特点的佛像样式。至晚清民国时期,佛造像已无任何框架束缚,仅单纯作为以求舒心的膜拜对象,尽管工艺难以比拟,但承载的精神内涵同样丰满。
关键词:佛教造像;汉藏融合;风格演变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7.002
清政府对于佛教的崇奉显然分析学习了元、明两朝对于宗教事务的管理经驗。清朝作为满族建立的新王朝,如何稳定群众与巩固边疆地区的拥护显得尤为迫切,从而形成了以萨满教、儒教、道教、佛教、喇嘛教等多教兼容并包的宗教文化体系,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足足经历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文化交融点,佛教毋庸置疑成了最为主流的信仰对象,藏式佛像为宫廷中陈列最多的样式。
1 清中早期汉藏交融在宫廷造像中的表现
1.1 艺术的交融碰撞
清中早期,以宫廷造像来说,雍正佛像传世并不多见,能说明考证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围绕康熙、乾隆两朝。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清康熙二十一年铜镀金药师佛像为例(图1),其吸纳了永宣造像铸造规整的艺术风格,并结合当时的工艺审美,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清康熙时期的经典之作。
该造像缩短了上身比例,四肢纤细,更为俊秀,肉髻高隆,上顶髻珠,结构转折处圆中带方,穿着坦右肩式袈裟并反搭衣角,强调服装质感,相对更加厚重,衣裙满刻花卉,一直蔓延到底座边沿,这种密集的装饰方式在汉传造像中较少见,多流行于西藏地区,但刻画的纹饰为汉地常用的花卉纹样,此外还在衣角处装饰中国传统纹样—回纹,通过纹饰的巧妙融合,造像在匠人的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活力。身下所承半月形双层束腰莲花座呈梯形,结构宽大、稳重,所饰莲瓣肥硕饱满并装饰卷草纹,并刻有三处铭文,其中在莲花座面上和正面座壁边沿的两处分别刻汉藏两种文字的佛名,而第三处为铸造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所铸铭文书写方式不再如永宣时期一味地迎合西藏地区从左往右的读写习惯,渐渐有了相互尊重彼此文化习俗的风向,以汉藏两地各自的读写习惯刻写。该造像作为现知最早的一尊清代纪年佛像,为之后宫廷造像的铸造树立了标准典范。
1.2 造像所承载的精神内涵
故宫博物院馆藏清康熙二十五年铜鎏金四臂观音菩萨像是康熙帝为其圣祖母寿诞专门铸造的,四臂观音在雪域向来有守护神的称号,将这位长者比作四臂观音的化身,足以表达康熙帝对这位至亲的尊重与爱护。该造像的开脸完全参考康熙帝圣祖母的样貌,同时秉持了当时造像眉眼下视的惯用手法,整体神态柔和,给人慈祥庄严的感觉。而发髻效仿北方游牧民族高高束起,两根发辫整齐地搭在肩膀两侧,头上佩戴五花冠,镂空处理,层层叠叠,非常复杂。身材肌肉饱满健硕,贴合满蒙所崇尚的力量感。
该观音造像外搭披帛,绕过手臂落在腿上,再顺势垂搭而下,衣纹处理行云流水,写实感极强。为进一步增加尊贵的气息,装饰有耳铛、项圈、璎珞、臂钏、手钏和脚钏,其中耳珰、璎珞所用的花纹引用西藏地区的样式,呈圆形,几层花瓣相叠错落组合而成,并镶嵌珍珠、珊瑚、青金石等宝石,分布均匀,色彩搭配和谐。眉宇间的白毫选用盛产于松花江的东珠,当时仅王朝可以佩戴使用,在无形中又强调了无上的政权地位。造像下呈双层束腰仰覆莲花座,莲瓣满饰一周,底边边沿满刻铭文,内容为“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为圣祖母庆寿特地铸造,祈佑赖菩萨感应,保佑祖母圣寿无疆。”遗憾的是次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孝庄太皇太后便离开了人世,享年75岁。不禁让人与这尊造像74厘米左右的高度联系在一起,当时康熙时期留存已知的造像基本在20厘米左右,而这样特殊的大型尺寸,是否在铸造时也有相关联的考量呢?
这尊清康熙二十五年铜鎏金四臂观音菩萨像的可贵,不仅仅是通过细节的装饰来表达康熙本身对于藏传佛教的喜爱及继承祖辈维系与边疆地区和谐管制的政治因素,更多的是他作为小辈借以倾诉对祖母的美好祝愿,以造像作为媒介,为我们揭开了这段过往史实的朦胧面纱。
1.3 宫廷造像模式化的形成
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认识与崇奉要远远超过康雍两朝。史无前例地将个人形象入画唐卡中,这类唐卡的诞生一方面向大众展示了帝王对于藏地喇嘛及佛理的高度认可;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与边疆地区的密切关联。这一阶段宫廷造像的铸造在数量上达到了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造像度量经》被成功翻译,进一步造就了模式化的形成,六品佛楼绝对是模式化影响下最为鲜明的代表。
与康熙时期造像相比,开脸为瓜子脸,躯体表现上挺拔感弱化,隐约有消瘦之态,肩膀圆,且溜肩下沉,体型的变化极有可能与长期的汉地文化熏陶有一定关联,在装饰上也明显简化,仅用连珠纹勾勒,底座采用单层覆莲,且莲座高度降低,莲瓣仅装饰正面半周,形状细长饱满,微微卷翘,仅用线条体现莲瓣的层次,上边边沿用大小不一的三圈连珠纹环绕一周,形状与早期的圆润饱满有细微区别,略有方棱之感。清乾隆时期,六品佛楼造像的另一大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铜烧古的技法,通过色彩对比营造层次感,除此以外,此项装饰技法还被大量运用到仿古佛中。
1.4 宫廷仿古佛造像
此尊清乾隆坐像转法轮印释迦牟尼佛便是采用了铜烧古的技法,是将多重风格融于一身的仿古造像(图2),该佛造像身材比例匀称,层次分明,肉髻高隆,衣纹线条精致,从见肉泥金的修饰方式,到台座正面底部的纪年款识,无一不在表达其铸造的具体时间。而仿古借鉴部分非常新颖,造像身着坦右肩式袈裟起源于斯瓦特地区,特点是衣褶非常多,甚至可以用密集来形容,所有衣褶都从左肩出发,呈“U”字形向另一侧回收,符合衣纹正常走向的情况下又增添了戏剧化的夸张感。另一处仿古借鉴部分是方形台座,流行于克什米尔地区,台座上垫厚坐垫,装饰大颗连珠纹,下方镂空,左右两侧装饰狮子一对。这种多文化元素的搭配组合对佛教文化的了解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与清康熙时期的借鉴不同,这种新的尝试在保留各自特点的前提下又有所改良,是清宫中独具创意的艺术形式。
1.5 无量寿佛与帝王的信仰
无量寿佛题材是乾隆时期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且藏式风格数量庞大。据传,乾隆七十大寿之际还特地向六世班禅定制了五十六尊无量寿佛并供奉于养心殿的紫檀宝塔中,同时清宫内务府铸造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一题材只是在细节和工艺上略有区别,除此之外无论是铸造样式还是尺寸都几乎如同一模所出。除了藏式风格外,汉传造像亦有铸造,如清乾隆金无量寿佛像(图3),既延续了明代造像的艺术风格,又在每一处细节中无不展现清宫精湛的铸造工艺。该佛像以真金打造,背光及两侧装饰采用了掐丝点翠工艺,头光镶嵌以镜子,身下是由玉石组合而成的仰覆莲,金光璀璨,无比奢华。清乾隆时期无量寿佛的题材无论是金铜造像或是瓷器、字画、绣品等都有一定存世作品,对于帝王来说,多为求身体康健、延年益寿,显然已不存在任何政治缘由,只是一位帝王最本能的初衷愿望。
2 清中晚期至民国佛造像的发展
清乾隆之后国家受到了强烈冲击,佛教和佛像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抑制,这一阶段似乎出现了造像发展过程中漫长的空白期,标准器的缺失为我们继续研究学习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1 宫廷造像对清中晚期造像的影响
笔者对此尊六臂大黑天(图4)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如何判断他铸造的具体时期笔者也非常困惑,其主要的两大原因其实是矛盾的:其一,这尊造像并没有具体落款,但其所呈气韵与清乾隆时期非常相似。飘带舞动的姿态都如同火焰般向上扬起,用插销固定主体与莲座,莲座在造像中的比例到莲瓣只装饰正面半周以及背后留白的处理手法都与之不谋而合,但在细节处理上又有细微差距,具体为开脸、四肢、躯体的塑造更加纤瘦,莲瓣刻画转折生硬,流畅度削弱,鎏金层薄,隐约透出底下铜胎,而清乾隆宫廷造像鎏金至少需叠加5~7层,色泽呈中黄,偏冷色调,再将底座翻转,可见先前使用垛口法固定封底的垛刀痕,封底已佚,内部的结构与铜质一览无余,铜质冶炼不够细腻,打磨粗糙,再加上当时民间对于藏传佛教的接受度不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造像的出处、铸造时间抑或是怎样的一位供奉者会供奉这样一尊密教造像?着实让人好奇,同时也有探索寻觅中的迷茫,希望在未来的学习中能不断更新理论,解开尚未挖掘的真相。
2.2 民国造像的风格演变
晚清民国时期,佛造像已无框架束缚,题材喜闻乐见,仅单纯作为以求舒心的膜拜对象。弥勒佛是其中备受追崇的佛陀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见证中国佛教演变历程的佛陀。早期弥勒以佛装或菩萨装的形象示人,来传达其不同的修行阶段,五代时期弥勒也显现出了民族化的形象—大肚弥勒,这种僧人形象是寺庙中供奉最常见的弥勒化身,相传这种形象的出现与浙江奉化一位名叫“契此”的和尚息息相关。此像便演绎了“契此”用他的布袋收服收了6只小妖的传说(图5)。其中4只小妖已收服于布袋中,另外两只趴在弥勒圆乎乎的肚皮上,而和尚依然随心自在,露出豁达的笑容,开阔的心胸,不为外物所干扰,便是它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涵。开脸部分眉眼格外細长,鼻翼宽大,并为他修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裟衣半搭于肩,衣纹处理与身体结构稍有偏失,原本漆金已有剥落,早期时为保证牢固,工艺更为繁复,显然缩减了制作成本,造像内堂打磨粗糙,还残留有翻砂的痕迹,绿锈也浮于表面,都为我们判断年代增加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3 商业化的民国仿古佛
民国时期以上海古玩市场为首的交易场所兴起,仿古佛是常见的品种之一,但这些仿古大多与早期时的慕古有所不同,更多是一种营销手段。受时代背景影响,洋人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中国文物充满探索心理,我国商人因此嗅到了商机,唐代以前的造像实物流通量低,人们接触得少,便成了古玩商最好的仿制对象。
此尊民国铜杨枝观音像(图6)难得之处是其背光刻有铭文,铭文中所记载的熙平二年(517)为北魏时期,而北魏时偏好大面积的舟形背光且人物塑造端庄,没有大幅度的姿态变化,身材比例也相对矮短,显然与铭文标注年份并不符合。撇开铭文单看造像本身更接近唐代,背光小巧呈桃形,身体自然呈“S”形站姿,两侧飘带随风舞动,身下为仰覆莲,并由四足高台座承托而起。但背光随意简化的纹饰、莲瓣平面化的表现手法再到从上往下往外廓的四足台座,与唐代时直上直下的腿部处理有一定的差别。造像与台座组装的媒介是用一颗铆钉固定,早期我们常见的是焊铸一体而成,或通过插销组合,造像原本的鎏金已斑驳不清,露出铜胎和鲜艳的绿锈,在不同的光线下能看到铜胎处有细微折射的结晶体,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造像保留了很好的学习标本。
当初铸造仿古佛的目的可能是作为仿古工艺品,也可能是单纯的作假,以谋求利润,但无论最终的铸造因由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人们对于佛造像的认识是相对匮乏的,因此将不同时期的标签拼凑到同一尊造像上,但通过一代代人的学习研究,实物的大量被发现,对于造像文化的解读也在逐渐明朗起来。
3 结语
清至民国时期见证了中国佛教题材造像的兴衰,康熙时期出现了清代第一尊纪年款宫廷造像,多元化的艺术风格为清宫造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藏传佛教的崇奉也多了一丝世俗化的念想,在汉地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们似乎就诞生于这块土地,这种真实的感受就是汉藏文化不断融合、影响的表现。模式化的出现迎来了佛教最鼎盛的阶段,在帝王的全力推崇下,密教造像的铸造让我们更直观地意识到佛教体系的庞大与包容并进。仿古是古往今来从不间断的铸造式样,目的各不相同,但对铸造者与佛教文化的掌握有着极高的要求,尽管清宫主推藏传佛教,但整体风格皆承袭于明代,其中不乏精美之作。民间所推崇的艺术风格与清宫不同,题材喜闻乐见,铸造水平各不相同,按区域划分更是风格迥异。
佛教的源远流长与人们的信仰息息相关,是心灵寄托,更是从内而外支撑我们坚定意志,帮助我们努力找寻抵达目标的明灯。文化的传承是有序的,那些被遗落在角落里的时代印记也在不断指引我们寻找历史的真相。
参考文献
[1]黄春和.汉传佛像时代与风格[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2]黄春和.元明清北京宫廷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及特征[J].法音,2001(1):31-36.
[3]黄春和.千古帝王一如来:一幅特殊的清宫御制乾隆佛装像唐卡赏研[J].文物天地,2019(6):96-103.
[4]罗文华.藏传佛教造像[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5]罗文华.从民间散佚宫廷造像谈乾隆六品佛楼[J].艺术市场,2007(5):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