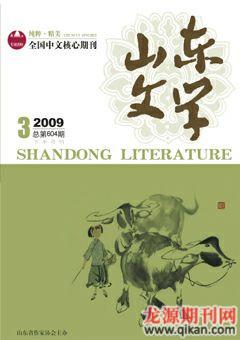种麻人家
冯 伟
二十多年前,汶河平原家家户户都种着大麻。扒下皮儿卖掉,立能见着现钱不说,光那麻秆吧,用处多着呢:烙饼、摊煎饼时,用它拨拉拨拉鏊子下面的麦秸,就不再冒烟呛人;下面条或水饺时,锅底下续上一把,不用担心它们会糗了;熏得漆黑的那把锡壶,装满二两六十度的老白干,点着一把麻秸温了,火硬着呢,热得快;那些扒得在行的长秆儿,还能用来夹障子做篱笆。但就是从种到收,像政府机关改革审批制度以前那样,手续太多,真是“麻烦”。
且从收割说起吧。棒子苗才长过麦茬高,三五个汉子便挂上镰刀又拿起了钐刀。麻地头上,比那边“冒火”的麦茬地里可凉快多了,但仍然穿不住上衣和长裤。于是,大年下演杨子荣打虎上山时当道具的那块白笼布,如今又斜披在肩上,只是手里的马鞭换成了钐刀。这钐刀不是字典里写的那把钐镰,而是宝剑形状,一面开刃,专用来钐麻叶——大人手里的一把利器,却是小孩眼中的一件宝物。农闲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背着大人,将那把装在刀鞘里已经锈迹斑斑的钐刀,挂在腰间当宝剑玩耍。割麻还是要用镰刀的。割麻和钐麻叶合起来叫“杀麻”。那些杀麻的汉子,割的割,钐的钐,无论是主家还是帮工,全都汗流浃背,正在跟头顶上的烈日叫着劲呢!地头的树阴里,这些不惜力气的庄稼汉子,每人能吃一筷子高的一摞白面饼,能一气喝下一瓦罐凉好的绿豆水。种麻人家把终年难见的好饭食,全都运到了这场“攻坚战”的前沿阵地。歇息的时候,老李顺手抽过两根细麻秆儿,三两下就编成一个好看的笼子,捉了一只叫声好听的蝈蝈儿,装在里面,引得那些来凑热闹的孩子们争抢起来。
割好钐净的大麻,全都捆成个儿,运到了“淀池”边。这是长方形的池子,大小不一,多数一人多深,专门沤麻用的。沤好起池后的大麻,沥干污水,就等着晾晒了。
盛夏的清晨,太阳出得早,种麻人家已经肩扛车推地往外运麻了。场院里,大路边,到处是摊开的大麻。半晌,午后,一根根翻麻杆子“哧——哗——”地动起来了,一片片大麻像一扇扇平铺的门板被相继翻过,搅乱了灼热的阳光。夕阳西下时,风光了一天的大麻,干了,白了,又被送回了家门。挑剔些的人家还不满足,在大门底下或饭屋里,用几块土坯砌成一个长方形的池子,放进大麻,用硫磺熏。次日晾干后,果然更白,等着卖好价钱。
最难忘的还是扒麻的夜晚。晚饭过后,大街小巷,家家门口都点上了防风的提灯,一拉溜儿坐满了扒麻的妇女。灯影里,到处都是或唱着儿歌或追逐打闹的儿童。劳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多数正在喝茶聊天,或者已经躺在院子里的破草席上打起了鼾声。也有一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儿,专爱扎女人堆儿,边帮着扒麻,边练习嘴皮子功夫。因此,单调重复的扒麻动作并不寂寞。有个叫“彩坏儿”的小光棍儿,就爱讲才子佳人相会于墙头马上的故事。不过,在他的版本里,才子全叫“白学生”,佳人都是“俊小姐”。而且佳人皆如祝英台一样聪敏,才子都似梁山伯那般愚钝。比如:有个“白学生”上学或者赶考的路上渴了,向井台上正在打水的“俊小姐”讨水喝。女的便先出道题来考考他。女的左右伸直胳膊,两腿一叉,问是什么字,男的说是个“大”。女的又将扁担平放在头上,男的说是个“天”。女的又让男的也伸直胳膊叉好腿,让他再猜,男的还说是个“大”。女的就说不对,是个“太”。听故事的人就“扑哧”一声,哄笑起来。有的前仰后合,放下麻秆直拍大腿;有的则用麻秆敲了一下“彩坏儿”的头,骂道:“你这个坏蛋!”小孩子也跟着瞎起哄,连那些蛾子和甲虫,也在一串串的光点里上下翻飞着。嬉闹声冲破了黑暗的夜空。
有月亮的夜晚最好。月影里,那些忙碌的妇女,哪里是在扒麻,分明是善舞的嫦娥,坐在人间的蒲团上,舒展着那薄如蝉羽的长袖。不为平添的那份诗意,只为省却的几角油钱。在“咔吧咔吧”的扒麻声里,那武松打虎的故事,鹊桥相会的传说,还有收音机里刘兰芳正在播讲的评书,便同近处孩子们的欢笑,以及远处荷塘里此伏彼起的蛙声一起,渐渐融化在如银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