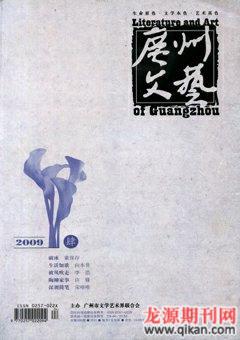陶柳家事
许 锋
许锋1971年6月生于甘肃兰州,自小游历于内蒙古大兴安岭、吉林白城等地;曾在兰州从事多年新闻工作,后在广东某大型国企任职。现居广州。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萝岗区作家协会主席。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广东青年作家创作培训班。已出版长篇小说《新闻记者》和散文集《心灵北疆》等5部作品。获全国报纸副刊银奖、第六届广州文艺奖等。在《飞天》、《四川文学》、《短篇小说》、《小小说选刊》、《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大公报》等发表作品。散文、杂文、随笔、小小说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多种选集。现任职于广东南海东软信息技术学院。
算下来,那一年筠子的外婆离世时,活了足足90岁,她应该觉得知足了,大家也觉得人活到这份上够本了,丧事就有了“喜”的成分,该哭的还哭,却没那么悲烈,哭过,闹过,饭一吃酒一喝,完事了,像是一个工程的收尾。
老太太留下了一座院子,那是筠子外公留给老太太的。筠子外公在的时候是金城一路诸侯,还是个书香门第的大财主,成分比较复杂,但按现在的话儿说那是经历丰富,农民,读书人,有钱人,集众多亮点于一身。“陶半街”财富茂盛,钱倾半条街,人就送了他这么个外号。老爷子的父亲老太爷是有名的秀才,据说早期金城的城门要见了陶家太爷才开呢。
陶家有势有钱,老爷子又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就时常去捧一个名伶的场。那女子确实生得闭月羞花,七岁即登台一炮走红,人送艺名七伶子。老爷子捧得专注,只要有七伶子的戏,他是一出不落,唱前唱后送花又披红,高潮迭起时拿着银元往台上“砸”,绫罗绸缎的戏服、镏金镶银的戏冠,送了一套又一套,可以说是烧钱,也可以说是痴情,话有几说,都是人说。
这样的光景大约过了十年。
戏子在风月场里厮混,自小就热闹惯了,完全适应了在男人堆里八面玲珑的生活,不愿意把自己绑定在老爷子一人身上,搁到现在,老爷子那样的儒商要是看上哪个二三流的演员,“哗啦啦”的钞票一甩,床是随便就上啦,这年头上床越来越没有分寸与品位,但老爷子是个有情意的男人,他捧七伶子不是为了一夜快活,他想娶她,明媒正娶。但是老爷子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之后,一气之下又娶了第三房。第三房是大户人家出身,识文断字人又漂亮,还巾帼不让须眉,不曾裹脚,一双三十八码的天足,很有些个性。此人就是筠子的外婆。
老爷子精力充沛,身体非常好,但先前的两个老婆都无福消受老爷子的风光,各留下一个儿子后没几年就驾鹤仙游去了。筠子的外婆自然顺理成章地接班、掌门,要不怎么说她眼力不错呢。她陪着老爷子走过风风雨雨,老爷子也对她呵护有加,俩人几乎一口气生了六女一儿。再想生时老爷子没那能耐了,又过了几年,老爷子赶赴黄泉。
去世前,老爷子立下遗嘱,现有的一院房子,一半归老太太,一半归三儿六女。这很公道。所谓树倒猢狲散,老爷子的大房和二房各留下的儿子在老爷子还在世时,无疑是有些地位的,老爷子走后,两个爷们眼见大势已去,就都默默无闻了。但谁也没想走。那里原来是一个完整的院子,后来爷们各自娶妻生子了,就在老太太的主持下象征性地把一院房子分成了几家几户,没砌墙也没重新开门;分户后,各家根据自己的地盘大小又起了简易房当作厨房或者厕所,其中大房的儿子分到了一间临街的房子,他把窗户弄成推拉窗,里面摆了些烟酒副食什么的,街坊到别处去买和到他那里买,价格是一样的,但路近,也就捧了场。大房的儿子下岗了,门面补贴了他拮据的生活。这样,在院子里落了户的就有四家:筠子外婆,筠子外婆的儿子,大房和二房的儿子。四足鼎立,表面上看去相安无事,其实都冷眼旁观暗地里较着劲,心照不宣尽心尽力地守着大本营。
筠子外婆的几个女子虽然早已嫁作他人妇,但也时常在一起嘀咕:不管怎么说,这院子以后有我们一份,如今几个爷们霸着将来是个事儿!女人不干事时黏黏糊糊,干起事来心狠手辣。有一回趁着重新丈量登记房子的空儿,大家把房本子从老太太手里拿出来,办完事,就留在了筠子母亲手里,老太太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也没再要。
老太太那房子也是经过修整的,其实大家惦记的不只是那房子。前些年老太太有时嫌城里闷得慌,就收拾东西回老家呆几天,有人就偷偷在她的房子里翻腾过,结果是什么都没翻出来。有一次,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毁坏了金城许多弱不禁风的房子,陶家的房子也出现了险情,尤其是老太太的那几间,都摧枯拉朽般地倒了。几个爷们喜出望外,都撅着屁股挖宝贝,那架势非要掘地三尺不可。老太太听说消息后赶回来,战战兢兢地站在废墟上一言不发。几个姐妹们赶到时来了气,说,房子都成这样了,你们还有心思挖宝贝?妈还没死呢!大房和二房的儿子说,别说得比唱得好听,房子不倒我们还没机会挖呢,老爷子走时肯定留下了宝贝,肯定埋在这院子里,天灾人祸,房子倒了,我们把宝贝挖出来大家都有份。
老太太叹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都觉得我藏了宝贝,都以为藏在地里,其实我告诉你们,老爷子走前把家产都折腾光了,就剩下了这一座院子,你们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如果有宝贝,我这把年纪,不知道享受?要是我真有宝贝你们还不把我当佛似的供着?没有什么宝贝,你们别丢人了,让街坊们笑话——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老太太像一截柴火棍似的倒了下去,地上的浮土烟似的飘起来,人们乱作一团,赶忙叫救护车,几分钟之后救护车“救命”、“救命”地开走了。
老太太命大没死,花了大家的几万块钱,大家心疼,但谁也不敢吱声。后来,老太太那倒了的房子也重新盖了。
又过了些年,紧接着的几场秋雨,让老太太得了感冒,身体每况愈下,大家就商量着要派人照顾老太太,请保姆觉得不划算,再说姐妹里,有提前病退的,闲闲呆着,就商量每月每家出100元由伺候老太太的子女掌管,伺候老太太的这个人就不用出这100元,大家都同意。筠子的母亲赋闲,就先上岗了。两个人的饭是做,多几个人的饭也是做,添几双筷子的事,于是筠子小舅一家也跟着吃,而到了周末,其他人也都风风火火地赶过来看望老太太,一来一大家子,筠子的母亲杀鸡宰鱼还要好烟好酒地招待,大家海吃海喝其乐融融,这么运行了几个月,筠子母亲亏空得厉害,正好有个机会,筠子的母亲找上工作上班去了,知难而退。大家再次商议,也凑巧筠子小舅又下岗了,他一家既和老太太住在一起,又有充足的时间,这任务就非他莫属,他也同意,于是大家还是按原来说的一家100元,筠子小舅不用出。
男人干体力活没问题,但照顾老人到底操不上心;筠子舅妈还在上班,早出晚归的,老太太就受罪了。老太太吃的饭要软和一点,小儿子炒菜按着自己的胃口,硬,还辣,老太太受不了。按着老太太的胃口做,米饭得按稀饭熬,菜得按烩菜的标准炒,小儿子的媳妇和儿子不爱吃。尤其是早饭,小儿子爱睡懒觉,老太太早早就醒来了,没吃的,就啃干粮,牛奶倒是有,但没人热,有时老太太就干熬着。小儿子睡醒后忙不迭地跑到街上,端一碗牛肉面给老太太吃,牛肉面里有蓬灰,是为了增强面的强度和韧性,老太太就十分吃不惯,久而久之,吃出了毛病,身体更加差,住了几次院,花了不少钱,她的子女虽然多,但经济情况有好有差,好的自然不在话下,差的就有些吃力,怨气就都憋着。
此时,筠子小舅的儿子结婚后生下儿子,找筠子的母亲要房本子落户,筠子的母亲在大家的“倡议”下,硬是没给。这脸就快撕破了。
小儿子找老太太要说法,老太太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家成了这个样子,外人都比亲戚好。老太太内心里偏小儿子,虽然说过以后房子大家平分的话,但那是在安慰大家,可既然这样说了,要把房本子从女儿手里要回来给小儿子还真难。筠子小舅找其他姐姐要说法,大家都异口同声,你把妈照顾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
火烧沟路窄,有坑,白天不知夜的黑,夜里连灯都没有,整个一条长街,从这头走到那头,耳朵得一直竖着,得出几身汗,一不小心还摔个跟头,若是赶上风沙天,那里就像一条阴森的古道,到处布满陷阱到处都是吞噬人的口子,女人系着的围巾隐约飘舞起来像个魂似的——老太太的魂儿终于被收走了。
活了90岁的老太太的喜丧办完,小儿子自作主张地搬进了三间上房,其他人正想闹事,好消息传来,政府要拆迁了,报纸上都发了告示,大家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盼来了这一天。大家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分配房产,其他人还没说话,筠子小舅站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妈这些年一直在我身边,是我把她养老送终的,这些房子理所当然是我的。其他人一听就来气,妈是在你身边,但你照顾得怎么样?再说就算你照顾了,我们每月也都给钱我们都尽了孝心了,怎么房子成了你一个人的?筠子小舅说,妈临终前说了房子给我。那你拿出遗嘱我们看看,再说妈要是立了那样的遗嘱,我们不认,太偏心了。
大家不欢而散。虽然大家都没见到遗嘱,但心里也在嘀咕,老太太真要是悄悄立了那样的遗嘱,还真麻烦,大家都是念过几年书的,自然不会动武动粗,那就打官司。几个姐妹们抱成团儿专门咨询了律师,律师觉得这事够复杂的,话说得也明白:老太太继承遗产时只继承了一半,另一半分给子女们,子女们分了家,又在院子里盖了房子,这财产就发生了变化,要是老太太临终前只把自己的一半给了她的小儿子那还好说,但要是她把全部的房产都给了小儿子,这个问题就不好处理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事到了法院法院也为难,还是你们自己协商解决的好。
等于没说呀。
大家也都在盘算自己能分多少,那么一座院子,政府要给的话估计是五套房子,按市场价值算总计得有八十多万,平分的话每人八万多,要是只拿出一半来分就四万多,而筠子小舅独占四十多万。太不像话了。但大家心里有底,因为房本子在姐妹们手里,政府见不到房本子怎么敢冒然拆房子?而筠子小舅要想拿到房本子,比登天还难,女人有时是有先见之明的,把最关键的东西捏到手心里,旁人没辙。
很快,政府拆迁的准确范围在报纸上公布了,大家趴在上面看了半天,失望得就像心跳了楼——陶家那院子偏偏就与此次拆迁擦肩而过。
大家的气儿一下子就泄了,泄了个扎扎实实,但姐弟之间从此结了怨,形同陌路,视为仇人。也倒是便宜了筠子小舅,没有房本子,但是白住着房子,自己单位分的房子又出租出去收着租金,有些齐人之福的味道,还真是惬意。几个姐妹有时也冲动地想,找些人冲进去把房子拆了,看他得意不得意,但从没落到实处,这事就这么搁浅了。
老百姓的日子里的许多事,都这么搁置着,憋着,攒着,挤着。
筠子姓柳。
柳家也曾是金城的大户人家,家业庞大。从解放门以南一直到滨河路都属于柳家的地盘。筠子的爷爷很能干,搁到现在也是个儒商(要不筠子的父亲和筠子的母亲如何门当户对)。解放后他以私营企业家的身份风光过一阵子,比如出国考察,到过日本、朝鲜等国家,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作为私方代表,执掌了金城最大的木器厂。那叫什么?黑白两道通吃!但世事难料,有一天风向一转,他被人拍着脑袋定性为资本家,全部产业充公,到了这时,一般人也都回天乏力了,政治要是开起玩笑,那可老大了。后来反右,老爷子又被打成右派。老爷子是个商人,不会和政府硬碰硬,也就老实认罪低头做人,享受到就地劳动改造的待遇,当年可是好多右派分子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关于夹边沟传说就多了,小说也有好几本,那是地狱,有去无回,甚至尸骨无存。老爷子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后来公房改造时,国家工作人员拿着户籍册按人口核定:柳家总共三口人,给两间房,其余的房子充公,就见一块5厘米宽7厘米长的白色牌子“梆、梆、梆”地被钉到了门框上,牌上书着“国产”二字。
刚改造完那会儿,公家“拿”走的十来间房子还给柳家房租(就是点利息,每月十多元钱),到后来利息不了了之,到了这时,柳家也就是一户地道的老百姓了。倒是天底下老百姓最多。
但是接着“文化大革命”又排山倒海地来了,有人翻先人倒祖宗,老爷子被扣上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被又红又专的革命派拉了去天天斗,要其交代特务行径——那不跟让黄花闺女交代和多少男人上过床一个道理?你就是给一个思路那细节也编造不出来。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让老爷子苦不堪言。
老爷子就有了死心。
有一天傍晚,老爷子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独自在院里坐了许久,然后进屋对老婆子说:“你去给我买点肉,我晚上想吃炸酱面。”老婆子应了一声,拿了一块钱就出门了。
不远处,他的儿子正和几个同龄的“狗崽子”聊天儿,老婆子走上前说:“赶快回去,你爸回来了,你去陪陪他。”
那时买肉要去撞运的,老太太得去寻。
儿子回到家,见上房里没人,出来见厨房的门紧闭着,就走过去推门,推不开,扒到窗口望去——老爷子正提着刀抹向脖子,他惊恐地大喊:“爸——”叫声未落,老爷子脖腔里一股血岩浆似的喷了出来……“爸——啊——”
年少的柳父的惨叫引来了不少邻里,有两个和老爷子一起接受思想改造的“坏分子”闻讯赶来,把门砸开,但老爷子已经断了气,他们把尸体拖了出来,血已经浸透了身下一大片地。老婆子正进院,她的手里提着一挂新鲜的肉,那肉,也仿佛滴着几滴血。老婆子呆滞地望着院地上的老爷子,半晌又半晌,却一声也没哭。她把那一挂肉搭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上,然后使劲把厨房的门板卸了下来,大家用门板和其他一些东西在院子里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灵棚,老婆子把家里最好的一套被褥半铺半盖在老爷子身上,然后把已经吓傻了的儿子叫到跟前,披麻、戴孝、下跪、磕头……是的,老婆子自始至终一声都没哭。
老爷子死后,就剩下筠子的奶奶和筠子的父亲相依为命,也自那以后,柳家一蹶不振。
历史的悲怆风吹云散。
现在进入小院之前要穿越一条狭长的巷道,阳光砸在参差不齐的砖头垒的矮墙上,如人的小肠里探进去的明晃晃的镜子,肆无忌惮地摇曳在随意搭建的小炭房和乱堆放着的黄河石上,狭隘、扭曲的小肠尽头是一扇门,木门残缺得像老头的嘴,豁着牙漏着风。
门里面那条狗却老早就叫得昂扬了。
进得院子,窄窄巴巴的,四处都是房子,再四面就是高大的院墙,往上再看去,城里耀武扬威的楼房割断了小院狭隘的天空,那是一种让人压抑的格局,因为院子里随便哪个角落的人的细微的动作,“楼上”都会一览无余,他们住在楼上,好像炮楼或者碉堡里的鬼子,时刻都拿着望远镜,一点点,细致入微地窥视。在鬼子眼里,眼底的这个破院子就是个茅屋,随时都有可能被端掉,他们也恨,这院子煞了大家的风景,但也因此而产生满足与自豪感,是的,一些市民的优越感往往是建立在贫民或农民的困苦之上。
柳父和柳母住上房。儿子娶了媳妇后,俩人挪到厢房,上房给了儿子一家。整个院子里有上水,一根水管子从院中央的地下突兀地冒出来,像是丹顶鹤细致的脖子。一到冬天,脖子就梗阻了,不浇半壶开水上去,那脖子就死活不通畅。院子里也没有厕所,男人小便时找个背人处,尿到切了口的油漆桶里,女人小便时要先尿到痰盂里,再倒到油漆桶里。所以大夏天的一进院儿就有股怪味儿。大便就要拐出门,到旁边的胡子观里去解决,那里香火鼎盛,有个旱厕,退休后的柳父无聊,有事没事就往观里跑,潜心向道,他没资格入道,却和几个小道士关系不错,称兄道弟的,别的没学会,敲敲磬打打鼓,满身的香气被不知情的香客们称为“柳道”。“柳道”兼职的好处是大家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拉屎而不用伪装成善男信女,大家风风火火地去爽爽快快地回,连偌大的香炉都可以不屑一顾,有了这一显赫的业绩,“柳道”那一身的香气就显得有些亲切了。
不管是命运多么悲惨的人,一生中多少也会有那么一星半点的暖阳,否则老天爷也太混蛋。“柳道”也有,十几年前筠子的奶奶还活着时,工厂分给了“柳道”一套房子。钥匙拿到手里,“柳道”骑着自行车带着柳母兴高采烈地去看,那是一套新房子,在厂区对面,五楼,二房二厅,那个亮堂——俩人回到家,兴冲冲地商议如何布置时,老太太不依了,她寡居了大半辈子,怕儿子住进新房后忘了娘,死活不让他要那房子,说:“前脚你们搬家,后脚我就上吊,你们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话够绝的。老太太不想儿子离开她,那就一起去住楼房,但她又舍不得这个小院,“柳道”实在不能看着母亲上吊,自己两口子又不能分居,没办法又把房子退了。当然,这个事情的前提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在省城有这么一片祖业还是格外有优越感的。但一晃十几年过去,当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时,柳家院子残存的那点优越感消失得比女人的青春还快,原来没房子的亲朋好友羡慕得眼红的那些人现如今都住上了楼房,有的还不只一套,那些人原常来的,来了满嘴啧啧声,如今偶尔来一两个,一说话就是:“您怎么还住这里?这还能住吗?”
当年退房子一事让“柳道”没少落抱怨,柳母抱怨了十几年,后来生了筠子、柳丁,柳母把抱怨传给了孩子,孩子们继续抱怨。儿子娶了媳妇,媳妇也开始抱怨,大家所有的抱怨都集中在“柳道”身上,他抱怨谁呢?
祖业有时也是害人的。
等拆迁是没希望的,这里靠着胡子观,拆这里的房子下一步就得打地基、盖高楼,地基和人的经脉一样,手和脚有没有关系?一打地基胡子观就有反应,就破坏了古迹,谁敢担这个罪名。
那就盖吧,“柳道”报了申请:人口多,居住条件紧张,现有房屋经年未修,漏风漏雨。一个礼拜后批文下来了,可在原地盖二层楼,楼高在6米内,批文上盖着一枚鲜红的印章。
接下来就是筹钱,筹措了一大圈,出入不是很大,柳家亲戚多,就他家属于弱势群体,别人家可都是电力、铁路、民航的,都是垄断行业,房子一个比一个大。“柳道”乐了,一挥手:“孩子们,做好准备,明天开工。”
但下午些时,狗叫了,来人了,那人,岁数和“柳道”相仿,他脸上的笑抽搐着:“听说你要盖房子?也不和我说一声。”
“柳道”掩饰不住喜悦,笑道:“老弟,盖好了请你喝酒。”
他皮笑肉不笑:“至少要和我说一声啊。”
“柳道”笑道:“到时咱老哥们喝个痛快。”
笑收紧,人家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冲“柳道”闪了闪:“先别盖,把事儿弄清楚了再说。”
“柳道”愣了:“什么事儿?”
“柳道”着实目瞪口呆。20年前,街道派出所从农村调上来一位姓张的民兵,民兵没房子住,带着老婆孩子住在办公室里,挺可怜的。居委会的大妈带着他们来到小院,筠子的奶奶看那个大女儿披头散发趿拉着鞋子,小女儿和小儿子蓬头垢面的,就尊重居委会的意见,把隔壁那间柴房借给了他们,那时不兴租房子。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年,儿女们都长大了,民兵又央求奶奶同意他们在柴房门口再搭个棚子,奶奶也同意了,后来民兵上调到了其他单位,还是什么执法部门,刚开始还是没房,就继续住着,逢年过节象征性地送点土特产、挂历什么的,再后来他在新单位分了房,搬了家,但柴房却一直没交还,一把老锁还在门上挂着。柳家有房,用不着那房,也就没催过,而那房子经常有民兵老家来的人住,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日月如梭,光阴荏苒,没想到老民兵通过关系把那间柴房和门前棚子的产权办到了自己手里。
自然,老张不是不让盖,而是要坐收渔利,要一层。
“柳道”想抽他俩耳光,当初要不是可怜他,他有现在的鸟样?“柳道”说:“什么事情都要差不多。”
老张的手混账地摆了摆:“你也别想不开,我立个户政府拆迁就会给我一套,我要是不立这个户你们也多拿不上一套,归根结底我是想沾政府的光没想着沾你们的光。”
“柳道”说:“话是没错,你沾政府的光跟我没关系,但我现在要盖房子你占我的地儿我怎么盖?”
老张的手又混账地摆了摆:“老哥别盖了,政府拆迁后你不就有房子了?费那个劲干啥,你前脚盖政府后脚拆,还是给你那么大,你吃亏呐。”
“柳道”的火陡然上来,瞪大了眼珠子:“我在你身上就吃了大亏了,我还怕吃政府的亏!”
老张一点都不生气,撇撇嘴不谈了,临走:“我警告你,你敢盖,我就敢拆。”
“柳道”踮着脚喊:“不要命你就来拆!”
院子里,风一阵比一阵紧,“柳道”铁青着脸,青铜色的鼻头倔强地挺立着。楼上断断续续飘下的纸片,像迷失方向的蝴蝶悠悠而落。
“柳道”一跺脚:“不管他,盖,大不了我跟他拼了老命。”
筠子也一拍巴掌:“我们这些人都想妥善地解决问题,他们硬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硬来,他敢把盖好的房子扒了?”
“柳道”坐镇指挥,该扔的扔该卖的卖。
“柳道”到马路上找了个工头,带到院子里,说:“包工包料,砖混结构,年前完工。”工头说:“没问题。”就要了个价,“柳道”打了7折,工头说:“不赚钱,8折,否则你再找别人干。”“柳道”说:“行,但一定保证质量,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工头捣蒜似地点头,“你放心,没几下子怎么在城里混?”
五六个民工猴子似的蹿上房开始揭瓦了,一时间狼烟四起,对面楼上的窗户“啪啪”地关上,对这户贫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麻烦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情绪。
“柳道”站在院门口,表情复杂得像灌了铅。
等老张再次悠闲地前来打听动向时,柳家的房子已经盖到一层半高了,老张跺跺脚回到家,越想越气愤,越想越恼火,血猛地向脑门上涌,脑袋里的毛细血管承受不住突然涌来的压力,爆了。
是一个悲剧。“柳道”听到老张死了的消息,先是“咯咯”乐了两声,接着长长地叹了口气。
“柳道”知道夜长梦多,就加快了建设速度,但北方的冬天来得迅疾,突然就下了大雪,工头和“柳道”商量:“要不开春再盖?”“柳道”摇头,“不行,你们放手干,有什么困难只管张口。”工头在工地上架起了炉子,架起了大锅,顿时就有些热火朝天,动静一大,环保局的来了,说冒烟了,影响空气质量,罚款2000元。
“柳道”急了:“满城的小煤炉你不抓你抓我干吗?你瞅瞅那些烟囱理直气壮地冒黑烟你怎么不管?”
环保局不屑一顾:“你不服是吧,你去告啊。”
这边还没消停,消防局的也来了,一进院喊:“怎么回事,点这么大的炉子,把楼烧了怎么办?”
“柳道”说:“这和楼差十来米呢,绝对没事。”
来人喊:“有事不就晚了?你说没事,对面楼上已经吓坏了,把人吓死了你负责啊?”
“柳道”赶紧打发柳丁出去买了两条烟,一人一条,来人喊:“这是行贿啊,你严重干扰我们执行公务!”
“柳道”找工头商量,把火灭了吧,我给你们多加工钱,工头看看天,说:“冰天雪地的,我干,工人们不干啊。”“柳道”只好给工人们一人一身棉大衣,两双棉手套,还郑重宣布,工程完工时,每人再奖励500元。工人们的积极性这才调动起来。
经过大家的努力,二层小楼总算是封顶了,工头拿了钱刚走,法院突然来人了,说柳家这块地有产权纠纷,被人告了,得先冻结,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封条贴上了。
“柳道”急了问:“谁告我?这是我先人留给我的房产,共产党砸的门牌,你们不是共产党是土匪?”
法官说:“你跟我急没用,我是个办事的,有话到法庭上说。”
“柳道”气血攻心,休克过去。
到这时大家明白,张家不是好惹的。
“柳道”醒来后,伸手就把封条撕了个稀巴烂,嘴里还骂道:“共产党就给我留下了这么点祖业,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
大家尽可能地让脸上呈现出喜悦的样子,这二层小楼,总共有8间房,“柳道”和柳母住一楼,柳丁和媳妇住二楼,筠子两口子属于非常住人口,二楼把头的给她们。
“柳道”专门到胡子观找人看了日子,说明天早上10点是黄道吉日,可以搬家,柳丁提议中午大家到饭馆庆祝一下暖暖身子,明天干活才有劲儿,大家都支持,一家人在重庆火锅城海吃海喝直闹到下午5点多钟,“柳道”酒喝得步子都打摆子了。
打了两辆出租车回来,“柳道“刚推开院门,就觉得不对劲,房顶怎么看不见了,“柳道”卷着舌头:“没错呀,我住了几十年,不会错呀。”筠子搀扶着“柳道”,“柳道”一把甩开她,箭步冲过走廊,搡开木门,傻了,房子落了顶,偏瘫似的挤在一起。是工程质量出了问题。
“柳道”身子一软,筠子手快,扶住了。
柳家人一时没了住处。
筠子母亲没法子,厚着脸皮去找筠子小舅商议,想回去过渡一下,筠子小舅哈哈一笑,铁青的大手一伸:把房本子拿来!
责任编辑潘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