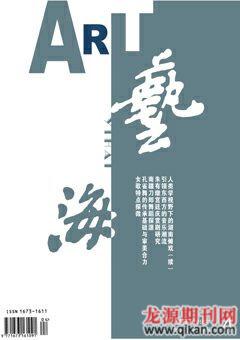孔雀舞的传承基础与审美合力
谢莲花
一、引言
传承是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标志。孔雀舞作为傣族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与毛相、刀美兰、杨丽萍为代表的三代艺术家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探索是分不开的。由于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因而理念、技巧上他们各自代表了自身所处那个时代民间文化的特质,他们在自身的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品格。如果说,毛相的孔雀舞还只是停留在原始的图腾娱神也娱人的层面,那么刀美兰的孔雀舞则是在提炼中演化为舞台化的一门艺术,而杨丽萍的孔雀舞却业已上升为一种在创新中的回归。作为一种接通历史的文化之链,他们在继承、发展和创新孔雀舞的同时,又是以什么为传承基础而构成和显示孔雀舞审美合力的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探究的课题。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人本的体现,艺术的精神反映的是人的精神。舞蹈艺术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进程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范畴。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族群生活记录、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艺术正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有生命意义、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又是最具表现空间的一门艺术。在云南美丽的傣乡,孔雀舞是傣族先民图腾意义的渡桥,也是神人叙语的纽带,在孔雀舞飘逸动态结构的背后,蕴含着傣家丰富的生命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孔雀舞由早期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表现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它映衬着艺术的起源与人类社会模仿大自然紧密相关的心路里程,更标志着以傣族先民为代表的人类社会对精神的欲求超越了本能的需求,使人的“最高精神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我们从孔雀舞的肢体造型、衣着道具以及舞台调度的结构中,能看到傣族群体性格中哲学思想的深厚积淀,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以及傣家内心情感的深刻内涵。这类舞蹈中,道具是整体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孔雀舞的道具在其发展中并不是后来附加的成分,而是和原始舞蹈同时产生的,它似乎源于“干戚羽旄”、“百兽率舞”的原始传说,即插着羽毛带着假面的原始图腾舞蹈的历史踪迹。当原始舞蹈从先民运用工具的劳动生活中萌芽时,形体动作就和工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类舞蹈艺术早期的审美形式。如原始的孔雀舞,舞者身背象征翅膀的沉重道具来舞蹈,通过模仿孔雀的各种形态,既是对他们图腾的崇拜,同时也达到自娱的效果。从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各种各样的舞蹈道具和与之相适应的舞蹈动作均源于同一生活,都表现同样的内容,并为同样的思想感情服务,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民间舞蹈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其民族性内涵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它是民间艺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民族艺术形式成熟的标志。傣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这充分证明艺术人类学的一条定义:在少数民族的心目中,他们的生活就是艺术本身。
二、 孔雀舞的来源及其开拓
孔雀舞在傣族地区有着悠久的传承基础。早在明代《南诏野史》中就有关于孔雀舞:“婚取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的记载,可见孔雀舞的历史之源远流长。在云南景洪市嘎酒乡嘎酒佛寺有带道具的孔雀舞木雕,在勐连县中城佛寺有戴道具的孔雀舞壁画,它们都是清代留下的反映傣文化的历史见证。在缅寺的壁画和雕刻中,都有表现栩栩如生人面鸟身的孔雀形象,这正与傣乡现有的头戴尖塔和假面具、身着孔雀服的孔雀舞十分相似。
孔雀舞是傣族人民最为喜闻乐见的舞蹈,分别流传于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在早期是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是依附在宗教活动中的文化事象,它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标志着艺术起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和崇拜。傣族全民信奉小乘佛教,追求超世脱俗、人生佛陀和空灵的境界,这与孔雀静态的温顺娴雅和动态的优美灵动正好不谋而合,于是人们便以孔雀翎献佛,跳孔雀舞求吉祥,因此孔雀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傣族舞蹈文化与审美的表征之一。孔雀舞构建了一个芸芸众生普通灵魂能够进入的精神空间而成为图腾崇拜的舞蹈,也构建了傣族民众族群识别的标志和强化生命记忆和生境的镜像:热烈的鼓乐声中、由民间艺人带领下万众参与、群情振奋,这一切都激发起千万民众将他们身上所潜在的激情和能量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以狂欢求得群体认同的目的。正是这种文化的功能,更刺激了人们投入到民间舞蹈的活动中去,并继续激励人们去模拟与再创造。正是民间舞蹈文化的超凡魅力,才使民间舞蹈得以传承。正如珍妮·科思所说:“所谓舞蹈风格,指的是有一部带有作者阶层、宗教或学派特质的舞蹈作品表现出来的特性。”(珍妮·科恩:《对舞蹈风格与舞蹈作品的反思》 载《舞蹈艺术》总18期125页)
傣族丰富多彩的传统舞蹈语汇对孔雀舞的形成构成了强有力的艺术语言支撑。如果从舞蹈语汇的表现层面去分析,傣乡纯朴的民风特征是其最大的影响。舞台上、凤尾竹下、草坪中、竹楼旁都是他们随意起舞的场所。这些文化基因都为孔雀舞艺术风格的形成发生着作用,表现出孔雀舞的传承正是源于傣家传统的动作母体语言中生发出来的,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构成了孔雀舞的生命之根。
大凡一种文化的传承,民间艺人既是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承者,更是给民间文化注入生命力的创造者,他们使文化传承永远具有聚散分合和吐故纳新的生命和活力。先后拜过三位“撒拉”(舞帅)的著名德宏民间艺人毛相,由他开创的徒手孔雀舞为傣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奠定了文化的传承基础,使孔雀舞的表演从追求形似达到了追求神似的境界,这和毛相的刻苦勤奋与内心的聪慧是分不开的。据说,为了揣摩孔雀富有灵性的神态,每天他都会到孔雀栖息之地,观察孔雀的生活习性和动态,并坚持在水滴下苦练不眨眼的功夫,从而为他的表演增添了熠熠的光彩。正是这种厚积薄发的积累,使他具备了超常的功力和精湛的表现技巧,也推动了孔雀舞的发展与传播,更使他成为了傣乡金孔雀的化身和审美的对象,成为人们追俸的“撒拉弄勐卯”(瑞丽大师傅)。用现代审美的眼光来考查,毛相表演的孔雀舞尚不能称为纯艺术,但它却是一种源于生活、源于自然、更是源于内心信仰的纯真表达,是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文化之果,因而其表演更能为广大民众所喜爱、更具有民间传承的认同感。我们说,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内在的传承机制,民间舞蹈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内在机制保证了民间舞蹈能在主体的操纵中自然的代代相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具有能够选择传承主体的辨别力。
民间舞的独特风格和鲜明特色是源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采摘。 孔雀舞正是傣家人表达热爱生活、向往祥和生活这一心境的物化写照。或许可以说,是民间舞承载了人们的精神释放和自我炫耀,更是民间艺人中的代表继承和发展并成全了民间舞的传承。如此民间艺人既是民间舞的“消费者”,也是民间舞的“生产者”,更是民间艺术的审美者。民间艺人在民间舞蹈的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民间舞蹈传承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毛相正是一位在傣家泥土中成长起来的乡土艺术家,由于受到能歌善舞的乡亲们的熏陶,使他从小就热爱本民族的舞蹈,更由于他特有的勤奋和悟性,历史的必然使他最终成为雄性孔雀舞的集大成者和表演的典范。
三、孔雀舞在近代的传承与发展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样,舞蹈艺术的创新是在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服务于创新,从而才显现其价值的,才不会与社会脱节。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继承与创新之间,更需要用新的思维,揉进新的基因,开拓出新的色调和意境。刀美兰正是在这种时代的需求下、顺应时代的潮流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孔雀舞传人,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而成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心中的孔雀公主。如果说德宏雄性孔雀表演的是阳刚之气,而以刀美兰为代表的西双版纳雌性孔雀舞却形成其阴柔之美,从而形成了毛相、刀美兰二者各具特色、各有不同审美艺术指向的孔雀舞表现风格。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宗教意识的淡化,孔雀舞作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物象,它也必须顺应时代的改变而发展并突破传统孔雀舞中男性和女性均为表演者的现实,专由女性来装扮孔雀,以突出肢体语言的柔软、自由与舒展,更凸显出孔雀妩媚的灵性。这种完全出于审美目的而生成的舞蹈,使孔雀舞成为舞姿丰富而且优美的超越于民间层面的艺术制品,从而逐渐把祭祀性的文化范式提炼升华为“具有宗教主题的世俗舞蹈”作品,并在现代语境中进行传承与传播,由此完成了由民间向舞台艺术升华的过渡。
刀美兰的代表作《金色的孔雀》,在继承傣族人民喜爱的传统孔雀舞蹈语汇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民族舞蹈的语汇,赋予了孔雀舞一种全新的表现意义:典雅、传情,具有更高的审美格调和文化内涵,具有艺术表现的开拓意义。这也带来了一种启示:即舞蹈家需要将个人的生活体验、民族精神及其个人生活的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最终熔铸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生命精神。《金色的孔雀》既有版纳孔雀舞的柔美,又有德宏孔雀舞的技巧,使作品成为表现傣族人民精神世界的艺术典范,在当时众多的舞蹈作品中独树一帜。具体来看,这首先是刀美兰对传统正宗规范的傣族舞的承袭;其次是她学习、吸收、掌握不同地区和流派的傣族风格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表演风格,以达到以情感物的境界;再次,在孔雀舞原有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刀美兰实现了民间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整合。经过加工、改进、提高的孔雀舞,不仅继承了民间孔雀舞的基本动作,而且创造和发展了许多惟妙惟肖的舞姿。尤其是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丰富的面部表情,把孔雀的特征和傣家人民美好的心灵刻划了出来,使舞蹈的语汇打破了早期孔雀舞中许多程式化的表演而更努力于为作品的精神内涵服务。正如刀美兰所说:“我的灵性,我的艺术魅力,其实来源于故乡那片神奇的土地”,这证实了艺术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艺术要关注民间、更要关怀民众。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都必须以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积淀,以鲜明的地域文化为依托。通过刀美兰创造性发展后的孔雀舞,其丰富的舞蹈语汇表明:民间孔雀舞的每一个特点在她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巧妙的拓展,使原生的舞蹈语汇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让观众感受到心灵的触动。舞蹈评论家许淑英是这样评价刀美兰艺术的:“她是用心在舞蹈,将她的感情溶化在每一个动作之中,以此来跟观众进行深层次的交流”, (征鹏著《她用自己的心跳舞》载《舞蹈女神——刀美兰》207页)的确,当我们欣赏刀美兰的表演时,就会如魔似地跟她犹如巡游在傣乡的竹林深处,同纯朴的傣族乡民共处,分享着她抒发出来对傣乡的一往情深……
四、孔雀舞在当代的创新和回归
一种风格的涌现并非单一因素所成,往往是集数个条件于一体后的嬗变结果。而文化精神的历史传承因素是最大的支柱。就一种艺术风格的确立来看,是很难不与历史文化的繁衍发生关系的,更无须说同宗同源的文化传承影响了。如果说,毛相的孔雀舞还只是停留在原始的图腾娱神也娱人的层面,而刀美兰的孔雀舞则是在提炼中得以发展起来的一门舞台艺术,那么杨丽萍的孔雀舞则业已上升为一种在创新中的回归。从审美人类学的立场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会是绝对静止的,文化的变迁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必然,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孔雀舞而言,只有在保留其精神本质和文化内涵的前提下,继承和创新的实践才能在一种双向流变的理性自觉中得以回归。杨丽萍的《雀之灵》等作品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孕育而生的产物。正因为杨丽萍的艺术创造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雀之灵》等作品才从艺术的生命价值中寻找到了人性之根,使其达到性灵的升华和艺术的涅槃,使她的众多的作品成为当代民族舞蹈的典范之作,进而赋予民族舞蹈审美的合力。
一个舞蹈家的成长是她长期体验生活、刻苦磨练的结果,从而逐渐趋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傣族传统的精神气质早已被分解为高原特有的集体精神气质。杨丽萍《雀之灵》的灵感正是源于傣家文化的生活之链,源于她对古老图腾文化的当代诠释。她说:之所以有创新孔雀舞的欲望,是一种信仰的驱使。孔雀作为傣族的图腾,人们尊重它,崇尚它,他们跳舞是为了和天地沟通,和神灵对话。杨丽萍能够站到前辈的肩上,把傣族传统的舞蹈语汇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和升华,使其形成独有的、个性化的真正发自内心的表演,这是她源于生活、依托传统来表现的结果。正如其所说:“民间舞蹈千百年流传下来,有厚重的历史沉淀痕迹。所以现在要有人将它上面的灰尘掸去,让它重新焕发光彩。我们的方式就是把那些民间的即将消逝的舞蹈整合出来,让观众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一个活的博物馆”。 (杨丽萍:《云南映象是活的民族博物馆》中国舞蹈网http://www.woodao.com/Article/Class1/Class34/200504/1774.html)
舞蹈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肢体只是观念在舞台上的替身,而观念则是肢体在文化中的化身。杨丽萍正是把这种质朴、细腻、自然的肢体语汇溶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把“形、声、情”和谐地运用到舞蹈中,进一步彰显出舞蹈的美学张力,使民族艺术获得了更高的存在价值。
海德格尔说:心灵越是自由,越能得到美的享受。正是这种自由的心灵之花铸练出杨丽萍出众的才华。很难相信,在这个纤弱女子的躯体中,竟然包裹着高原土著精神的狂飙,因而她的作品与传统的孔雀舞又有很大的区别,即不以展现性格、不以展现具体的人物刻画或典型形象作为目的,而是努力在肢体的灵动中塑造一种文化的形态,宣泄的是炽热如火的激情和天马行空的民族性灵,引领的是一场静悄悄的审美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杨丽萍的表演与其说是一种风格的呈现,莫如说是一种心象的反映,传达出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斑斓色彩。这我们可以从她众多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心灵的物象之源。
基于克莱夫·贝尔提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 (〈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马钟元译《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9月版第20页)的观点,可以认为,“意味”和“形式”是分别开来的两个概念。即“意味”是一种审美体验和审美情感,是内在的体会,杨丽萍根据自身的体验和情感逐渐创新,这是一种感知的表达;而“形式”则是一种外在的、纯形式的审美框架,这是一种认知的传达。在她的《雀之灵》中,就整体的“语言”结构而言,舞蹈的灵动、意境的悠远、场景的深邃体现出巨大的审美想象空间。她把自身对生命的体悟和感受融合自身的审美和创新而变化成一种艺术语言的创造力,以此唤醒审美心理的感受能力,成功地把动态的优美和静态的闲雅相统一、把美的表现与美的感受相统一、把感官的愉悦和理性的欢畅相统一,充分展示了作品的审美合力。以这种语汇作为语言材质解构重组,但却没有失去本有的文化气蕴和原生文化形态的内在关联及艺术魅力,既不失其特色神韵,又适应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既有民族特性的剖析,又有观念的超升。杨丽萍赋予孔雀舞新的寓意,赋予表演新的内涵的实践,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谛——真正的艺术是对艺术的超越,真正的表演是内心狂涌着的情感的宣泄。
一个从西双版纳雨林走来的新一代孔雀精灵,杨丽萍用舞蹈表现着高原民族的文化、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和毛相、刀美兰一样,杨丽萍的孔雀舞也是依托于民间,吸吮着大地的营养和水分,但是又游离于民间的传统,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象、梦想改头换面地宣泄和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着自己的梦想。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时代要求孔雀舞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杨丽萍的《雀之灵》则正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而发展了孔雀舞,使得孔雀舞在新的时代成为大众潜意识中理想的审美对象。传统是根,文化是魂。杨丽萍的成功告诉我们:只要没有脱离民族的特征、没有脱离民间的文化,就能够形成一种超越不同民族之上共同的人性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可沟通性,并按照新的创作思维把它发展和完善,就是一种可能获得成功的创新。无疑,杨丽萍的创新是成功的,她真正把心灵、文化、情感构成了一条熠熠生辉的金线,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对艺术的理解用舞蹈尽情地宣泄了出来,把舞蹈的诗意境界和内心的浪漫情怀融为了一体。
艺术风格的体现有着两面性:既代表着自己,又代表着自己所属的那个集体。前者反映个体的人本精神,后者体现着集体的趋同性,二者互为条件又相互依存。作为新时期孔雀舞的代表,杨丽萍既代表个体,又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群体。她正是在一种不断发展和创新中体现出民族舞的风格和特色的,如她的《雀之灵》,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其内在的本质,使她创作的心路历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其创新精神的回归和自我本色的彰显,是历史所需又是历史必然。如果说毛相的孔雀舞是傣家审美视觉的再现,那么刀美兰的孔雀舞就是傣家审美的升华,而杨丽萍的孔雀舞则是傣家民族深层心理在舞蹈文化中泛起的涟漪。如此,杨丽萍作为傣族的文化精灵,构成了云南各民族文化精神的身体解码和族群记忆。因此她理所当然成为继毛相、刀美兰之后的傣乡新一代孔雀精灵。
传承是一种动态的概念,被传承的文化是不会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流变而停息的,它犹如一面时代的镜子,常常以动态的形式观照文化与时代的变迁。孔雀舞能发展到今天,与孔雀舞发展阶段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分不开的,对孔雀舞的开拓与创新既是基于艺术家对民间舞蹈审美意识的升华,又是民间舞蹈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毛相、刀美兰、杨丽萍他们三人走过的艺术之路说明:民间文化的传承既要依托传统又不能拘于传统,既要尊重传统又要超越传统,这样才能将历史之链的两端系在一起,艺术的创造才能顺应自己所处时代发展的步伐,一种既往传统才能寻找到自己新的生命支点,因而,艺术的生命之花也才会开出更加艳丽的花朵。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把客观物象与心中的主观感受统一起来进行创造,并把客观世界的现实图象转化为主观世界的心灵图象,最终以恰当的肢体语言将这一心灵图象物化为能够表现自我情感、充溢着精神魅力的肢体构成。毛相、刀美兰、杨丽萍正是依托民间,构成了孔雀舞传承的三部曲,即:毛相源于自然的拙朴韵律向刀美兰娴静端庄的舞台神韵的过渡,再到杨丽萍的空灵淡泊和浪漫情怀融为一体的超念升华,他们的艺术创造与舞台实践,使傣族的传统文化真正具有了时代审美合力普遍的社会意义和跨越时空的文化价值。
(作者单位: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晓芳
——以中缅边境地区孔雀舞发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