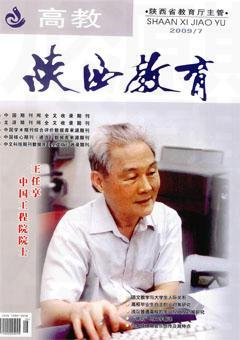再论《娇红记》
孙 琳
[摘要]《娇红记》是继汤显祖的《牡丹亭》之后的又一部宣扬至情的传奇创作,只是孟称舜看到了在思想解放的年代,人欲逐渐超出了道德可以管束的范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社会上充满淫亵的味道,所以努力把“情”建构在遵从道德的基础上。晚明是个复杂的社会,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不疑,士商的互动让知识分子对于一直信仰的道路产生疑问。孟称舜自然脱离不了这样的社会,他也开始反思了。
[关键词]《娇红记》孟称舜情理“新四民论”
《娇红记》是孟称舜的代表作,叙写申纯与王娇娘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它产生在心学思潮汹涌澎湃此起彼伏的晚明,是晚明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共同作用的产物。王学思潮在泰州学派的鼓荡下,肯定人的情感,追求个性自由,张扬世俗享乐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文化思潮。一时间,“主张个人的真实情感,抒写实感的文艺思潮”席卷整个文坛。为了将人欲横流的情纳入传统意识的正轨,有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的将肯定情欲与遵从道德结合起来,情欲是以道德的完善与张扬为皈依的。孟称舜的《娇红记》就是情与理逐渐走向融合的代表作品之一。
明嘉靖万历以来,随着商业经济萌芽的迅速增长,中国的思想界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程朱理学重“理”轻“心”,使得“致良知”的王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让久在“牢笼”中的“本心”得到了放松,在真性情的世界里自由的徜徉。随着王学的发展,其中对于“内在自然主义和追求自然的精神,渐渐超出了王阳明设定的极限,也超越了主流意识和政治秩序允许的范围,也把世俗民众本身当成圣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王娇娘与申纯二人都是在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上,追求自由的本心。王娇娘在一开始就发出这样的感叹,【前腔】“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若乃红颜失配,抱恨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才。“娇娘乃有思想之女子,实是孟称舜所欣赏之女子形象。敢于面对内心的情感,而且所祈求的姻缘是“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跃。”这是杜丽娘的深思,不只要一个相爱的人,而且还应该是心心相惜,情投意合的同心子,自然是又进了一步。当社会上“情”打倒“理”居于上风时,理性的约束被彻底抛弃,社会伦理规范超前的破败,世风日益走向情欲的凸显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孟称舜,他的使命感使得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社会的风气,没有直接的介入,说出情欲的泛滥应该被遏制。而是用一种独特的眼光,去关注所发生的各种人事沧桑,可以称之为“冷眼旁观”。他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角度,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坚守自己作为社会注视者的文道,提醒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这是作为人文学者应有的眼光与立场。他看到被历史建构起来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渐渐失坠,原来表面遵从的伦理同一性在生活世界分裂的情况下被渐次打破。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看到各种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种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不能诊断和疗治这种变化万端的社会,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求得各种正确的知识,冒悲剧性的危险,不逃避,不诡随,把自己认为正确的,而且是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影响到社会上去,在与社会的干涉中来考验自己,考验自己所求知识的性能。这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显现。在社会礼乐崩溃,色欲横流的情况下,他走出了“至情”的圈子,将有情人的情用“节”或称之为“贞”来烘托。四十八出《双逝》是《娇红记》不同于以往爱情传奇的地方,也是其作者盂称舜的深意之所在。它完成了晚明情理二元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对于社会“合理秩序”的重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用戏剧来引导下层民众对于“理”的重新跟随,将情框在道德的范围之内,从泛滥引向正途。
十六世纪以后商业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是“士”的转向的另一重要背景。由于王学左派观点受到大范围的认同,明儒生对于“治生”“人欲”“私”都有了新的理解,因此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明清小说戏剧的流行,与城市商人阶层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这种商人阶层所嗜好的民间文学愈来愈发达,慢慢受到士人的重视,士人也开始民间戏剧方面的创作。这就是非文人大传统文化对少数上层文人的大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民间文化对正统文化,通俗文化对学者文化,世俗文化对科层文化)。士人们提出“新四民论”,即士商农工,使得商人一跃而成为与士同属“大”阶层的地位。士与商只是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的界限模糊之后,“弃儒就贾”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另一方面是商人通过财富也可跑到儒生的阵营。在这样的背景下《娇红记》虽然是一部爱情悲剧,内容里表现出的社会商业背景也不容小觑。商业社会中银钱的流通,使得一部分讲求实际的儒生已经不可能平静的满足通过道德提示扭转道德与金钱的不平衡,而是被迫追求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平衡金钱和道德,于是用贵金属的花费量来测定道德功善的可能性,为儒家道德经济给银钱一个正当的地位开辟了道路。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当时,金钱与财富似乎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科举入朝为官似乎都已经不重要了,这些都可以用钱来实现。这些观点与晚明士人复杂的心态有关。由于传统价值的崩溃,士人思想自由,行为放纵,但是政治的黑暗,功名的束缚与物欲的压迫同时又是相当严重,因此,对于晚明士人的义利复杂心态,我们更多的应该是理解,而不应该指责和蔑视。
参考文献:
[1]王季思.《中国十大悲剧集》齐鲁书社出版,济南1991.
[2]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9.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
[4]万俊人.《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东方出版社,北京2002.
[5]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4.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3.
[7]葛兆光.《古代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
[8]卜正民(韩国).《纵乐的困惑》三联书店出版社,北京2004.
[9]吴承学,李光摩.《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2002.
[10]左东岭.《王学与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