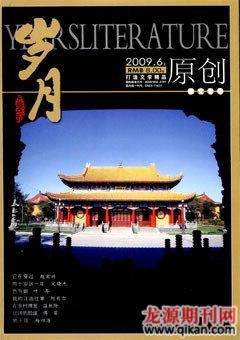心灵的历程
王灵均
第一次读到赵宏兴的散文《它在穿过——记一次旅行》,颇感诧异。与这位作家接触虽然不多,还是可以感觉到现实生活中的赵宏兴是位爽朗、豁达的人,待人接物总是那么热情诚恳、彬彬有礼;以前读过他的散文集《岸边与案边》,书中多数作品是叙述性的散文,而《它在穿过——记一次旅行》则为之一变。
赵宏兴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在《它在穿过——记一次旅行》中,他没有在具体的火车行程上面展开,而是重点放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多采用寓意、象征、变形、自白等手法,基调沉重、文字多义性指向明显,作品中的“我”也是一个象征化、符号化的意象,可以视为现代人的心灵化身。作品中的火车旅行可以看作人的生命历程,着力描绘的夜景可以看作挤压现代人生活空间的社会环境。所有的这些意象描写,都指向了一个主题: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义。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指出,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知识代替了神话和幻想,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迷信中解放出来,要求从实际上支配自然。它借助于科学知识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可以精确计算的要素。与此同时,形式逻辑的发展又为人们提供了计算事物的逻辑格式和进行推理思维的可能性;数学也成了启蒙的准则,把一切都还原为数。于是,启蒙精神就以事物的同一性消灭了多种多样的个性,导致了思维的程式化。数学和逻辑通过科学技术成了人类肢解自然、统治自然的有力工具。但是,启蒙精神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另一方面它也成了奴役人的枷锁。“文明的发展是在绞刑酷吏的记号下发生的”,“恐怖是和文明分不开的”,科学技术作为启蒙精神的“物化”,既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也是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有力手段。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总是以失去自己的人格自由为代价而获得文明进步。人类智慧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终都变成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对于现代社会人类的异化生活做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阐释。赵宏兴的散文则是对于这一理念的艺术阐释。
作品只是点名在秋天的旅行,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也没有说明旅行的目的,这种缺乏具象的描写,增强了散文的象征意义,它和充满着罪恶,谎言,欺诈,恶心的黑夜、火车一起构成一幅荒诞、冗长的画面。
在文章里,作者很少写白天,即使提到白天、阳光,也没有轻松的笔调。“清晨的田野上,飘浮着淡淡的雾气,有着舞台上刚要揭开还没有揭开序幕的样子。田埂上,到处是被焚烧过的痕迹,黑色的灰烬,一块块地,伤疤似的留在地面上”,“太阳的光线是垂直的,深渊的四壁长满了奇怪的树木,岩石上的石缝里嵌着古老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应该是黑色的,即使阳光透彻,也是这样的,眼睛看不透的时间,掩盖着真实”,可以说,黑夜构成了这篇散文的第一意象,漫漫长夜,充满了怪诞、诡异,又是那么沉闷乏味,它是如此的顽固,“窗外闪过一片灯光。灯光下是空荡的,不见一个人影,堆积的光亮被黑暗挤压成坚硬的一团”,“黑暗连着黑暗,黑暗套着黑暗,丧失了记忆的旅程,在宇宙中膨胀,距离变形成一桶方便面,快捷但没有营养,飘着一股廉价的味道”,这些晦涩的句子背后我们仿佛听到现代文明重压下的整个人类疲惫的喘息声和无奈的叹息声。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说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把天地看成万物的旅店,把时间当作历史长河的旅客,可以为赵宏兴的散文做一生动注脚。赵宏兴的这篇散文着力描写的火车旅程实际上是人生旅程更是心灵旅程的形象化比喻。
“乘务员过来让我写旅客意见,年轻的服务员,有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刚刚过去的黑夜就消失在她黑色的眸子里。我问,这火车的吱扭声是怎么回事?她说,这不是火车问题,是这段路的路基不好。
这就奇怪了,我怀疑我的灵魂是否奔赴在一段危险的旅程上;或者说,这一段旅程还没有维修好,我的灵魂就开始了一场奔赴。
这个‘路字,是对我的唤醒吗?
我抬起身来,想看看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字,这时,我才看到了完整的句子:‘中国铁路”。
本段描写堪称生花妙笔,正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危机的形象写照,被后工业文明异化统治的人类社会就像行驶在不牢固的路基上的火车。如同尼采说的“上帝死了”的命题,丧失了心灵家园的人类将如何前进。在这种形势下,“我”,这一人物、这一意象,可以说是浓缩了人类心灵的意象。
“我提着硕大的旅行包
——它的腹内鼓胀着,它是母性的,当我把那些小日用品一件一件地往里面装时,它就受孕了,它孕育了我整个游荡的梦。
但随后它的重量会慢慢地减轻,它变得空空的时候,便诞下了我的灵魂——那是旅程的尽头。
逃走——
我在沿着空间的边缘逃走,我的双手用力推开这钢铁的门扉,慌乱的脚步必须轻轻起来,不要惊动守卫的士兵。这轰隆的声音,是门扉打开的声音。
我的身体被禁锢得太久了,肌肉里剩下的最后一点力量,用来寻找自由、幸福、未来……”
这是现代人类的自我救赎和反抗,这是对于异化社会的控诉和抗争。虽然作品中也出现了警察、乘务员、乘客、民工、美女等人物形象,但是都难以具象化,都是“我”的感受到的富有象征性的意象。这是生命的路程,心灵的旅程。
寻找精神家园的旅程不仅是漫长的,更是孤独的,痛苦的。
“火车在土地上面奔驰,隆隆的声音之后,土地又归于一片沉寂。
没有人关注这列火车,因为我的存在,这列火车载着的是我一个人。
它在奔驰,它没有双腿被束缚时的局促。”
前面说过,作品中出现的警察、乘务员、乘客、民工、美女等人物形象,都难以具象化,与散文中的“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心灵交流,如此种种突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缺乏心灵的沟通,现实中本来拥挤嘈杂的火车几乎就“我”一个乘客。与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中那两位感情淡漠到如同陌生人一样的夫妇的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山洞,这短暂的黑暗,一个连着一个。
这些洞窟不能久留,必须快速地穿过。
时光在黑暗中凝固,在阳光中融化。
瞬间的黑暗,瞬间的光明。
火车带着撕裂般的疼痛,一路奔驰,突破。”
人类千百年来的文明就是如同这火车一样夹杂着光明和黑暗,带着累累伤痕悲壮地前行,谁也无法知道前面的黑夜意味着什么结局。
真正的心灵探索更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火车将载着我横穿几个白天和夜晚。——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时间将像养肥了的猪,被屠杀并发出绝望的嚎叫。——那里没有多少人到达,但却是真实的,而我所到达过的地方都是虚拟的。”
现实生活是纷繁芜杂、真假并陈,只有精神生活是深刻的、真实的,可是被现代文明遮蔽了灵魂的现代人类又有几人可以进行这种心灵的探询呢?可以说,“我”这一意象不仅浓缩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更是那种反抗异化社会的知识精英的代表。
阿多诺提出在现代异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应当在“先锋派艺术”的审美乌托邦中实现审美救赎,这最终将流于虚幻和脱离实际。赵宏兴的心路历程虽然缺乏一个完满的结尾,但是最后还是变得有些光明之处。刚说到:
“这是秋天了,冷空气在北方聚集。
一场火焰会在指尖到达,掐灭的黑暗会重新到来,布满身后空隙。”
可是随着民工的下车,车厢也空敞了,作者的笔调也轻松起来了。
“这是一渠洪水,在两岸间的河谷里流动。
它的奔流像无数大提琴、小提琴、爵士鼓、长号在演奏,奔放,自由,激烈。
我是随波逐流的一条小鱼,在洪大的水流中翻腾,跳跃,游动。
时间的沙滩是白色的,是每次洪流从高处携带下来的心灵的积淀。
它越往前走,地势越平坦,但内里的力量仍没有减弱。
它推涌着我,这个游荡的灵魂。
火车奔跑的脚步踏在这秋后的盛典里。
边缘被它一次次抛在身后,
它要奔跑,它停止不下来,在激烈的铿锵声里。
火车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这是最后的晚餐。
也是重新开始。”
应当说民工下车这段内容相对于前面的旅程的描写现实色彩要浓厚一些。是的,人总归要回到现实之中,但是这种回到现实是经历了痛苦、孤独的心路历程之后的基础上的回归,较之艰难的心灵跋涉之前更加深沉、自信,这一深沉、自信似乎看起来有些突然,可确实是经历了灵魂煎熬和拷问之后的当下直觉和真实呈现,尽管还没有到达终点,但是“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这是最后的晚餐”,“也是重新开始”。
人类的生命历程还要走下去,不过步伐更稳健、果毅了,虽然前方不知道还有什么艰险,终归还要迈步走过去。我相信读完《它在穿过——记一次旅行》后的人,会有类似的信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