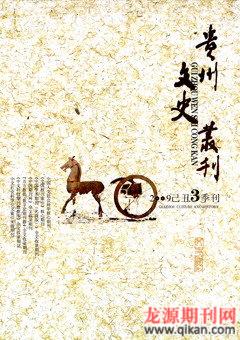“出郭九行”与“诗史”精神
马将伟
内容提要:出郭九行“是对清初文学家魏禧及其兄魏际瑞九首叙事诗的总称。这组诗以沉痛的笔调描述了顺治末年百姓在官兵掳掠、盗贼横行之下的惨痛生活,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践履;在艺术手法上,也吸收了牡甫叙事诗的艺术精华,井予以活用,体现出杜诗在清初诗坛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出郭九行诗史精神魏禧魏际瑞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3-53-58
“出郭九行”是指清初著名文入团体“易堂九子”中坚魏禧及其兄魏际瑞所创作的九首诗歌。其中包括魏禧六首:《出郭行》、《人郭行》、《从军行》、《卖薪行》、《孤女行》、《孤兄行》;魏际瑞三首:《猛虎行》、《将军行》、《恩官行》。以“出郭九行”命名这九首诗歌,自于魏际瑞。在其《跋出郭九行》中,把魏禧的六首诗称为“前六行”,己作三首为“后三行”,合称其为“出郭九行”。
一
在《跋出郭九行》中,魏际瑞将上述九首叙事诗与杜少陵的诸“吏”诸“别”相较,开宗明义,指出“出郭九行”之来由,其云:
老杜《石壕吏》、《新婚》、《垂老》、《无家》诸别,每读辄怅惘累目,以谓人生到此,当者惨毒,固已安知若命;旁观岌岌哀惧,翻若不能终日。叔子作前六行,予作后三行,非规杜作。古人谓:惟以告哀,如有疴痛,不觉其呼于口也。昔杨升庵每病老杜“诗史”之称,乃摘其寡妇痛哭诸语,谓非诗人温厚平和、怨而不怒之旨。然刺褊心,斥遄死,着无良,指鬼蜮,《墓门》、《圻父》、《何草》、《羔羊》所直指斥者,盖不一而足矣。《书》云:诗言志。有为而作,固非有所择而为之也。
显然,“出郭九行”之命意直接来自于杜甫的“三吏”、“三别”。解读其中意旨,大凡道出了魏氏兄弟这九首诗歌之所由作也,盖心中有所“疴痛”,不由自主地发抒而为诗歌;而且这些诗歌皆属“有为而作”,合乎所谓“诗史”之旨。对于明代杨慎对杜诗“诗史”之称的诟病,魏氏颇不以为然,并举例予以驳斥。虽然文中明确说明“出郭九行”“非规杜作”,但显然是受到了少陵“三吏”、“三别”的直接影响,甚至可以从这些诗歌中看到“规摹”杜诗的影子。然而这种“规摹”绝不是简单的摹仿,即所谓的“优孟衣冠”,而是对于“诗史”精神的重新肯定与弘扬,并以自己的创作来实践这种诗歌观念。强调诗歌须“有为而作”,并倡导弘扬“诗史”精神是以魏氏兄弟为代表的“易堂九子”共同的诗歌理念和追求,这也是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明末清初之诗风密切相关。
少陵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时期,社会动荡不堪,尤其是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少陵的一生几乎就是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环境里游走,由此他真实地触摸到了百姓的心声,再加上自己生活的穷困潦倒,使得他对于民瘼之痛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诚如前人所言,“甫于行役所经,伤心惨目,上悯国难,下痛民穷,加以所遇不偶,怀抱抑郁,程形赋音”,他以诗人的敏感和深刻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几于一字一泪”。杜甫“诗史”之称始于唐代孟柴,其《本事诗》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人故多因此说而赞誉之。总其精髓,盖有以下两端:其一为实录精神,即《新唐书,杜甫传赞》所言其“善陈时事”,《塵史》云:“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胡宗愈说少陵诗“读之可以知其世”清人施闰章云:“杜子美转徙乱离之间,凡天下人物事变无一不见于诗”。以实录笔法写诗,以诗存史,杜陵为古代诗歌创作别开天地,明人胡震亨云:“以时事人诗,自杜少陵始。”施闰章亦云:“古未有以诗为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这为后世诗人倡导诗歌创作须“有为而作”,勇敢地直面现实起到了典范作用,也使得诗人具有了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其二,辞寓褒贬,具有“春秋笔法”之微义,辞约而旨丰,于叙写时事之时,诗人自己之爱憎情感同时见于辞语之中。杨维桢云:“世称老杜为诗史,以其所著备见时事。予谓老杜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徐增有诗称少陵“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在冷静的叙事中,诗人的讽喻之义自然溢于笔端。
“出郭九行”中,魏禧的《出郭行》、《人郭行》、《从军行》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卖薪行》、《孤女行》、《孤儿行》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魏际瑞的“三行”亦作于此后不久。考清初顺治末年之历史,虽然距甲申之变已有十几年的时间,满清之统一大业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然处在历史夹缝之中的百姓仍然饱受战争之苦:满清政府对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展开最后的围剿,同时各地汉人的起义仍然频繁,清政府则予以残酷镇压。清军纪律松弛,所过之处满地狼藉,如在滇地,清军虽奉有“勿得擅取民一草一木”之命,但实际上是“戎车所至,狐兔不存”。洪承畴密奏顺治十六年(1659)滇之情形时云:“如衣粮财务头蓄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盖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病残,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哭地,莫可控诉”,甚至有的地方“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里杳无人烟”。此为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因战事所迫,军队粮饷紧缺,国库不盈,清政府不得不加紧催集钱粮。顺治十八年(1661),各地欠饷甚多,又因滇闽用兵,治顺治帝之丧,钱粮不充,当年入不敷出达五百七十万两以上,而且支付在即。窘迫万状,于是决定加派练饷,八月初八日户部奏准:查明季加征练饷例,按每亩一分征收,直隶、山东、江西等十三省共田地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余顷,该征银五百七十七万余两,在加上各地官吏之敲诈盘剥,把百姓逼人了“守法常得死,何不豫为贼”(魏禧《入郭行》)的绝境。当时滇黔兵寇之祸害最为惨烈,然亦波及江南各省,魏氏家乡江西赣南也不得其免。魏氏兄弟同堂挚友曾灿描述其乡之祸乱云:“滇黔发难初,流祸及闽粤。吾乡亦传烽,盗贼恣驰突。川谷起黄埃,郊原多白骨。田园日就荒,庐舍渐芜没。”江右之惨状据此可知。
此时民生之惨状相较于安史之乱时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是易堂九子之一的李腾蛟就说:“今日之乱,甚于安史”。魏氏兄弟亲眼目睹了兵荒马乱中下层人民的惨痛生活,郁积于心中,自然而然地和杜少陵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诚如魏际瑞所言:“老杜《石壕吏》、《新婚》、《垂老》、《无家》诸别,每读辄怅惘累目,以谓人生到此,当者惨毒,固已安知若命;旁观岌岌哀惧,翻若不能终日。”此一语有无限辛酸泪,与少陵共淌,于是有多少“疴痛”积于心,何以告其哀,便“不觉其呼于口也。”
二
“出郭九行”以冷静而沉痛的笔触记录下了当时普通百姓的惨痛生活。魏禧《出郭行》真实地描一绘了顺治末年“逼良为盗”,百姓处于生死两难的现实境遇之中,行行悲哭,句句血泪。《出郭行》开篇即写“盗贼”之盛及其无恶不作:“郭门日萧条,盗贼纷纷起。十家村务中,乃有五家是。大者肆屠杀,小者驱牛豕。纵火烧谷屋,系人要货贿,”盗贼如此猖獗,以致使村人“薄夜携妻儿,往伏荒榛杞。侵晨望四山,乃复
归墟里。哭声满中野,不敢直言指。”读至此,陡然令人对这些如此丧尽天良之所为而感到深恶痛绝。然而,在听下面“盗贼”在官衙前的陈述之词,这种痛恨之感一刹那又荡然无存了,反生无限同情。何则有如此之大之反差?盖“盗贼”乃被逼所为:
终年苦力作,不得养妻子。食缺衣不完,谁能饥寒死。地方日索钱,豪民恣驱使。大户瞰缙绅,小户饱士子。一人身富贵,婚友争搏噬。舆皂仗官威,吸唼尽脑髓。一或逆人意,夤缘人犴狴。见官我所愁,见我官所喜。无钱死饥寒,有钱死系累。要之均一死,不如作贼是。(《出郭行》)
此血泪之辞,道尽“盗贼”之所由来,令人痛彻心肺。他们遭受着“地方”、“豪民”、“舆皂”等多重欺压,致使面前只有死路一条,遂于无奈之中铤而走险,由良民一变而为“贼”。更为可笑的是,有“仗剑客”为“贼”说情,言“四境大苦贼,贼亦可哀矜”,并质问审问盗贼的长官“汝号民父母,何以特无情”时,长官居然也笑着道出自己那本难念的经:
汝但晓贼意,独不晓官情。初我得官时,早夜苦经营。胥吏前致辞:到任礼先行。恒愁令节至,辄复闻生辰,民奸财不易,敲扑何由停。无钱败我官,子贷谁为应。甚或丧性命,岂得爱他人。愚民感作贼。剿杀有官兵。(《出郭行》)
由此来看,长官之“无情”亦实是无奈之举,世事逻辑至于此,实已荒唐至极,不复能言矣。最后魏禧发出感慨:“贪吏诚当为,盗贼良可矜。两皆不得已,慎勿为良民。”其心痛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慎勿为良民”一语一针见血,戳穿了“逼良为盗”的残酷现实。
魏禧《从军行》与魏际瑞《将军行》控诉官兵以剿贼为名,而对百姓无情的掳掠。由于盗贼纷起,顺治末年官兵屡屡以缉逃剿贼为藉口而对百姓进行大肆侵扰,成为当时一大祸害。据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兵部督捕右侍郎陈协等题称:“应捕以缉逃为奇祸,以拿贼为利媒。地方中拿一逃入,必令咬报富家,以为窝主诈吓,遂欲,竟行释放,然后又诈一家。有不顺其心者,指示逃入硬为窝主,及至有司审明,而良家之家产一荡然矣。”“应捕”即缉捕盗贼的吏役。其又“明知逃入而相交好,窥小民之愚懦者,不曰曾买本人之产,则曰欠本人之债,串通同辈三五成群,攘臂而入,捉妇女,夺资粮,致令百姓吞声而不敢问,盖皆惧逃入之波累,故甘心而忍之。”其毒害之深可见一斑。而魏氏兄弟的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对当时惨烈现实的最好注解。
《从军行》中,将军点兵到山县拿贼,然“山贼闻兵来,窜走无遗踪。”将军捕贼本应是为民除害,百姓高兴才对,但再看百姓的反映,则知道事情并不简单,“百姓闻兵来,行往两怔忪。”何以“闻兵”而“怔忪”?原来百姓早已知晓将军盖非真正为拿贼而来,其意在于掠夺而已:
后旒未出郊,前旗已先临。骑上挟鏃矢,步卒横长縱。呵云此近贼,焉得不相通。遂使絷子女,搜牢何从容,斬木取犁铁,橐米碎瓦甕。背负生彘肩,鸡鸭笼中鸣。
在百姓面前,官兵竟如此之威风,不去追捕逃贼,反诬陷民众与贼相通,这就是他们对百姓“搜牢何从容”的藉口,而百姓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被一扫而空,甚至是犁铧之铁,也不放过。
《将军行》则讲述了将军与贼人沆瀣一气,致使一壮丁鬻亲身母的故事,正是应捕“明知逃入而相交好”的鲜活实例。当有人叱责这个年轻人卖母的“大恶逆”行径时,年轻人不得已尽道其中之隐情:
贼谓将军曰:此间多顽民。某某合诛僇,某特赢金银。某有美妻子,某与某姻亲。将军闻贼言:尔是好男子。假尔千守把,尔但作吾事。踝骨绞弓弦,倒悬勒拇指。一刀分所甘,求死不得死。左邻卖妻子,右邻掘坟地。甚或无亲丁,权鬻甥与婿。可怜我孤穷,独有此老母。
贼人不但未受到惩治,反而成为了“好男子”,得到了“千把守”的职位,因为他能够向将军提供掠夺乡民的最直接的线索。由此而观,将军与贼人实并无区别,俱以危害百姓为其要务而已。于是乡邻俱遭其祸,出现了卖儿鬻女、甚至是卖母的人间惨剧,把百姓逼到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地。何人为之,非为贼人,实为将军。
魏禧《孤女行》、《孤儿行》,则刻画了这一年代中儿童的凄惨遭遇,一个是在“龙蛇画梁头,雕刻及柱足”的“官街”中独自哭泣的孤女,不禁让人想到少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一个则是被“公税数加派,私费十倍之”的沉重的赋税弄的家破人亡的孤儿。《卖薪行》讲述一个以卖柴为生的“下有三岁儿,上有垂白亲”的男子被强行驱入狱门,后又被驱人军门的悲惨经历,刻画出一个“路逢暍死人,身僵口微蠕,竟作路傍鬼,仰卧当青天”的人间地狱图景。魏际瑞《猛虎行》叙述了一个猎户为民除害,射猎了一只危害乡里的老虎,然而却由此惹得里正前来敲诈的悖谬生活的逻辑的事件。《恩官行》讲述的则是发生在宁都的一出闹剧:一个“自分是耕夫,宁敢充衣巾”的在宁都作“长年”(长工)的农民莫名其妙被“捉”为“俊秀”,“农已升为士”,并以此来逼交“区区只百金”的官银。令人感觉到可笑与不可思议的同时,不觉声泪俱下。
“出郭九行”以生动的写实的笔触再现了顺治末年百姓的不幸,他们深受着战乱、官府、军队、贼盗等的残酷蹂躏与任意践踏,处在“求死不得死”(《将军行》)的生存悖论之中。同时表现了魏氏兄弟深切于民瘼,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民生之极度同情,以及对于这些罪恶制造者的嘲讽和痛恨。九首诗皆以诗存史,直面惨痛生活,是杜甫“诗史”精神的践履。
三
“出郭九行”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法,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再现出清初顺治末年的社会一生活图景。在艺术手法上,“出郭九行”继承了杜甫以“三吏”、“三别”等诗为代表的叙事艺术,以沉静的笔触把读者带人那个混乱不堪、民生惨烈的历史情境之中。这组诗不是仅仅把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冷冰冰的临摹对象而作简单的客观描绘,而是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将自己的爱憎情感、思想倾向等寓于冷静的叙述中,从而在叙述之中抒情,把“言志”“缘情”之诗与“纪事”之史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话式叙述与独白式叙述。
“出郭九行”所采用的最重要的叙述方式是对话体叙述方式。往往通过当事人自己的叙述凸显事情的经过及原委。《出郭行》、《人郭行》、《孤女行》、《孤儿行》、《猛虎行》、《将军行》、《恩官行》都采用的是对话式叙述。玆以《出郭行》为例说明。《出郭行》中主要有两个对话场景,一个是被拿“盗贼”与审讯官的对话,一个是“仗剑客”与审讯官的对话。前者是“盗贼”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而为官所拿,官问“盗子”答:
嗟汝盗贼心,何叹灭天理。盗子闻斯言,欷獻复长跪:君心肯和平,为君说始终。……
以“盗子”之口亲自说出其之所以为盗的原委,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无钱死饥寒,有钱死系累。要之均一死,不如作贼是。”后者以“仗剑客”为问,审讯官为答:
有客仗剑来,谓汝太不贤。四境大苦贼,贼亦可哀矜。汝号民父母,何以特无情。堂上双抚手,大笑老书生。汝但晓贼意,独不晓官情。……
长官于是说出一番所谓的“官情”来,其“无情”亦不得已而为之,世事竟然可笑至于此,“两皆不得已,慎
勿为良民”,然而在可笑的背后,却隐涵着令人欲哭无泪的哀情,诗人之意深矣,其心痛亦剧矣。
《卖薪行》则采用了独白式叙述,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一位“下有三岁儿,上有垂白亲”的卖薪人被抓为兵丁的不幸遭遇。独白式的叙述方式增强了事件的逼真性,读者如亲闻其哀述,其声如泣,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从而强化了叙述的情感性。
场景的描写与细节的刻画。
“出郭九行”非常注意在场景之中叙事,有特别讲究特定场景之中细节的刻画。如《出郭行》中,长官要审讯“盗子”的时候,有生动的场景描写,其云:“侵晨鸡载鸣,鼓声何田田。舆皂喧公府,长官坐高厅。”“鸡载鸣”之时,府堂之外鼓声震耳,多么肃杀;府堂之内皂隶喧哗,多么阴森;高厅之上长官横坐,多么威严!就在这个时刻,“有客仗剑来”,大声叱责长官:“谓汝太不贤。四境大苦贼,贼亦可哀矜。汝号民父母,何以特无情。”在这样的场景之中,“仗剑客”居然敢于做出如此之举,其光明磊落、勇敢直爽的形象跃然于纸上矣。《卖薪行》中,通过“我”的视角,描绘出了被抓为兵丁者的不幸:“陆行荷重担,水行牵大船。水深风不顺,力尽船不前。解缆暂登舟,拔刀斫我肩。或遇浮沙潭,并命没黄泉。更驱次班下,努力各争先。”活是一副人间地狱图。《从军行》中剿贼之兵掠夺乡里时,是这样的场景:“斯木取犁铁,橐米碎瓦甕。背负生彘肩;鸡鸭笼中鸣。”在这幅图景中,军兵残绝人性、丧尽天良之性毕露无遗。
再看细节刻画。《出郭行》中,当“仗剑客”痛斥长官“太不贤”时,对长官有非常生动的细节的刻画,“堂上双抚手,大笑老书生”,用“抚手”与“大笑”两个动作的细节把长官飞扬跋扈、老于世故的情状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仗剑客”的正义力量也在长官的拍手笑声中被消解了,令人感到绝望窒息。《从军行》中当将军下令要点兵剿贼时,“山贼”与“百姓”的不同反映:“山贼闻兵来,窜走无遗踪。百姓闻兵来,行往两怔忪。”此处诗人用“怔忪”这样一个细节描写,不仅把过往百姓此时惊恐不安的心理状态非常逼真地描绘出来,也给读者留下了疑惑:兵来剿贼,对于百姓来讲本是好事,应该庆幸才是,而此处百姓却为何具有如此惊恐之状?真是咄咄怪事!通过这个细节的描写,引起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与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反衬出兵对民之残毒之甚。《人郭行》中当“予”看到“扬扬数骑来,下马俨佳客。一再拜主君,环作酬杯酌”而感到错愕不解时,曲道处的一位老人“附耳向予言”,道明“主君”祸害乡里的事实,此处“附耳”一个细节有非常丰富的意蕴,老人又怕“主君”听见而惹来杀生之祸;但又愤怒郁积心中,不吐不快,其情状通过这一细节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场景与细节的描写和刻画增强了事件的生活质感,使事件中人物的性格、情状更加凸显,叙述的张力也由此表现出来。
比兴手法的运用。
“出郭九行”使用了传统的比兴手法。如《孤儿行》中,开篇没有直接展开对事件的叙述,而是描写田中之野鸦捡食余粒的情景:“野鸦朝暮噪,集我田中飞。行行啄余粒,田空鸦苦饥。”然后才进入对孤儿“独夜归山邱”的叙述。显然是以野鸦之“苦饥”暗寓孤儿之情状,是典型的“兴”的手法,彭士望于此两句诗后评曰:“起兴好。”“比”之使用如《人郭行》中老人向“予”讲述“主君”施方略其人时说:“此人性咆哮,吞噬比鲸鳄。”又如<猛虎行》中,本述猛虎之毒,而实际以虎毒影射官吏之毒,写虎毒:“大儿死樵採,兄弟死田亩。半夜发庐壁,床内攫老母”,而猎户因猎虎除害反而引火烧身,“明日里正来,官府使问汝,虎皮有几张,虎肉几多许。爪牙胫与骨,各依钧票取。自后为正供,汝当充猎户。设或无此物,岁以白金赎。老妻鬻无多,幼子典不足。赎程未及半,此身已孤独。”由此,只得“誓折弓矢,宁甘受虎毒”,是“苛政猛于虎”的实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篇辞约而旨丰,意隐而毕现,语尽而思远。善用比兴也是“诗史”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要区别之一,清人施闰章在谈及少陵“诗史”与“史”的不同时说:“史重褒讥,其言真而核;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而且诗可以使“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因而“其用有大于史者。””“””‘出郭九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也印证了这一点。
叙事语言的通俗化与口语化。
在语言上,少陵叙事诗通俗易懂、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元稹称其“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房希白也称赞道:“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出郭九行”继承了杜甫诗的这一语言风格。通俗化是指不求语言之华美新奇,也不作刻意的雕琢,直接引“当时语”、“寻常话”等民间语言人诗,如“下有三岁儿,上有垂白亲”(《卖薪行》),“前者阿父死,阿兄逃深谷”(《孤女行》),“邻里相劳问,呜咽不能辞”(《孤儿行》),“见官我所愁,见我官所喜”(《出郭行》),“壮丁标老妪,日日行千里”(《将军行))等等。有时,当地之俗语亦被采人诗中,如“恩官听告诉:我是南丰人。宁都作长年,雇值日一分”((恩官行》)中的“长年”一词即为南丰方言,诗后魏际瑞自注云:“南丰人谓雇工为长年。”由于“出郭九行”主要以对话或独白为叙述方式,因此诗中具有大量对话的内容,而这些对话叙述皆随口而出,如亲耳聆听当事人之述说,因此使其整体上呈现出口语化的特点。不同的对话者,因其地位、身份不同而其语言亦自不相同。如《猛虎行》中县官的两段对话,“此乡甲被虎,县官大生嗔:四邻不救护,纵虎而食人”;“汝在虎窝中,虎去汝还住。汝既不射虎,当是虎亲故。前日虎陂下,雷击田中夫。我罚彼乡人,一家千青蚨。”读其言,县官之荒唐可笑、蛮横无理、狰狞之面目跃然纸上。又如孤儿、孤女等惨民之述,如泣如述,如幽咽泉流,闻其言,其惨状如在目前。
当然,叙事语言的通俗化与口语化并不等于说不对辞语进行精心锤炼。《卖薪行》写官府对卖薪者的奴役,使用了三个“驱”字,“驱我入狱门”、“驱我人军门”、“更驱次班下”,魏礼评论道:“三驱字妙,直如猪羊之人屠肆。”(魏礼于诗中夹评)三个“驱”字就把官吏之残毒、百姓之惨苦状写出来了。又如《孤女行》中写孤女的外貌,也只是寥寥几笔,“发短不及眉,身长才二尺”、“五木交十指,骨见不遗肉”,其剪影已鲜活欲出。
“出郭九行”在艺术手法上明显地受到杜甫叙事诗的影响,但又能活用其法,叙写当代惨痛之事,抒发一己疴痛之情,此魏际瑞所言“非规杜作”也。
责任编辑俞菲